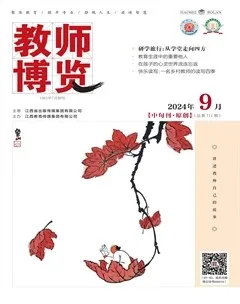一个数学教师的人生方程式
1982年深秋的一天,我去章崇堂老师家串门,看到他家堂屋临时搭起的床铺上,一位农民模样的中年男子拥被而坐,在演算着什么。我很好奇,问章老师此人是谁。章老师兴奋地说:“他是我高中同学张复常,苏塘赵公大队的会计,山芋棚村人。学校聘请他当代课教师,下学期教高中数学。他现在在我家临时搭伙、落脚。”章老师又以他一贯的风趣、幽默道:“他同我在‘无中’‘捣了三年腿’。除了自己老婆外,他同我在一张床上睡觉的时间最长了。”
我一听,乐了,又惊了。章老师1966年从无为中学高中毕业,现已16年了。16年一直在家务农,高中学的知识还没忘?虽然现在在复习、准备,但他能行吗?这位新来的张老师,难道是天才?
那时的中国农村教育,不愁生源,也没有升学的压力,最突出的矛盾是师资不足。当时我们开城中学初、高中总共15个班级,学校教育教学一片红火,严桥、襄安、无城等地学生也纷纷来“开中”上学。令学校领导头疼的是,数理化教师严重不足。为保障教学,学校领导往往通过个人关系,去城里聘请教师,利用星期天来校上课。但那时交通、通信不便,实在麻烦。被聘老师只上一天,效果也不好。虽有大专毕业生陆续地分配到学校当老师,但学科并非总能配套。
一转眼,新学年开始了。张复常老师长女张会上初中,安排在我班上就读。一天早晨,我被一阵歌声吸引住了。循声而去,原来是张老师在教张会唱歌。我一看,不禁感叹,真是“颜回之乐”。张老师新分配的教工宿舍,是学校废弃多年的猪棚:土坯、草顶,矮小、低洼,阴暗、潮湿。这样的屋子里竟然传出快乐的歌声,住在里面的人脸上竟然挂着幸福的笑容——张老师真是一位贤人。
我对张老师产生了兴趣,喜欢同他聊天。同他聊天,增长见闻,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譬如由他家村名“山芋棚”说到山芋,张老师说山芋是粗纤维,帮助排便;说某个大队吃粗粮,大便一次一大盆,简直像牛粪;说过去的中国山芋筋多肉少,抗战时从日本人那里缴获了品种改良技术。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张老师谈起他读高中时,家境贫寒,辍学一年,在家拾粪。他风趣地说,他知道大粪的味道。回忆在“无中”读书时的生活,有件事让他十分得意。那就是他参加数学竞赛,得了一等奖,学校奖励他一支水笔。
张老师有时不免自得:“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有时又臧否人物,直言不讳,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尽管他所说的都是真话、实话,但“可信者不可爱”。我明白了,凭他的水平,凭“无中”“老三届”的含金量,张老师高中毕业回乡后,欲当“民师”而不得的原因了。但当我提及此事,出乎意料的是,张老师并未怪罪任何人。
那时的中学,教师身份往往分为三类: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代课教师地位最低,工资最少,工作最累。可在我眼中,张老师从未因饭碗问题而巴结、奉承他人,也从未因工资低而抱怨、发牢骚。张老师白天在学校上课,课余还要回乡务农。一次,张老师白天上了一天课,晚上回家摇了一夜水车,我也从未听到张老师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
我敬佩张老师,他积极的人生态度让我很受教育。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到底怎样呢?我还是很困惑。
我读过一些自学成才的故事,我读初中、高中时也有许多“民师”或“民师”转正的优秀教师,譬如物理童天龙老师,化学章崇堂、卢贤能老师。我记得范先白校长曾几次以程荷生老师为例子教育我,一个教师的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敬业、肯钻研的态度。有道是“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事”。理论上,我承认张老师能胜任教学工作,能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可相较于其他人从未丢下过书本,张老师一丢就是16年。我无法说服自己,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向数学组伍先能、钟平、周光剑等年轻教师打听,他们一致评价:“张老师解题能力强。”我还向老教师程荷生、童朝胜老师打听,得到同样的回答。这些回答远远不能满足我,解题能力固然是数学老师的重要素养,但组织教学能力、驾驭教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也很重要。我还要继续观察、了解。
张老师每次走进教室时,衣服虽旧,但必定干净、整洁,脸庞黑瘦,但必定精神饱满。张老师上课不带备课笔记本,似乎习惯把教案写在纸上。下课时,经常听到张老师与同事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争辩着。这些都表明张老师良好的工作状态。
我的弟弟在张老师班上。一天放学后,我看他在认真抄着什么,我拿起一看,原来他在抄张老师的备课笔记。看到张老师的备课笔记本,我的困惑立刻消除了——张老师是花了真功夫的。我问弟弟,班上同学对张老师的教学是什么态度。弟弟回答道,同学们十分喜爱数学课,张老师的备课笔记本同学们传着抄。
校园里渐渐开始流传张老师的教育故事。寒冬的一个深夜,睡梦中的张老师夫妇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以为学生来下面条吃。张老师急忙穿上军大衣起来,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浑身冰凉的张老师才重新上床。早起的师母打开门一看,堂屋里的桌椅全都移在一边,水泥地面上写满了粉笔字。还有一次上午放学,张老师远远地向爱人大喊:“快!快!快买一个饭缸!我把一个学生的饭缸子从三楼教室摔下去了,学生中午没饭吃。”爱人买回饭缸,张老师立马盛满饭菜,又火急火燎地送往教室,并请该同学来家里用餐,进行安抚。为什么砸饭缸?原来没等张老师宣布下课,该同学就提前从课桌里拿出饭缸,准备冲向食堂。
张老师的教育故事,别人无法复制,也无须复制。张老师对学生的“严”和“爱”,则是每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典范。我很想当一回张老师的学生,听他讲课,可我实在找不到机会走进他的课堂,因为我教语文。
我在“开中”读书时,有幸遇到两位优秀的数学老师——程荷生老师、蒋克钊老师。两位老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极强,课堂语言干净、简洁、高效。我想拿张老师同他俩对比一下。
我只有趁张老师上课时,在教室外走廊或后窗来回走动听课。不出所料,张老师满口原汁原味的土语,散发出泥土的气息和田野的芬芳。课堂上,张老师姿态从容,神情专注。但让我奇怪的是,张老师总是站在讲台的内侧,莫非他有意腾出黑板,好让学生看清板书内容?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张老师年轻时就患有胃病。因此胃疼时,张老师就用讲台的一角抵住胃部,缓解疼痛。
张老师家庭负担重,上有老母亲,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女,爱人无工作,他微薄的工资无法承担一家人生活。张老师的爱人很能干,很能吃苦。她起早贪黑,发馍馍、下面条,补贴家用。面对困难,张老师更是表现出坚韧的精神和极强的生存能力。张老师家里有两件中国教师家庭所罕有的用具:板车和洋镐。无开公路拓宽时,路上几乎所有的树疙瘩都被张老师刨回家了。看到张老师刨树疙瘩,我对他形象的认识变得模糊又清晰,是农民形象叠加,还是教师形象剥离?他分明又是我的“人师”。张老师儿女心重,为两个女儿在铜陵办户口的事,怕影响工作,他总是星期天早早骑自行车出发,从开城到铜陵,晚上便赶回来。只有一次归途中,天降暴雨,他在蜀山镇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早早赶回。
1995年,张老师荣获“无为县十佳教师”光荣称号。张老师花了三十元钱照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张贴在学校宣传栏里。张老师很上镜,照片上的张老师慈眉善目,清癯的面庞上是和善的笑容。
这一年,张老师的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西安交大,我们都替张老师高兴。张老师几次亲口对我说,送孩子上学时,他从家里带了一个水瓶,装满开水,担心火车上没热水喝,怕胃受不了。回家后,张老师不顾疲劳,立即走上讲台。其实,这时的张老师已是胃癌晚期。最后的课堂上,张老师常常疼痛难忍,大汗淋漓,衣衫浸透。
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张老师不幸去世,享年54岁。
想起张老师的一生,我感慨万千。作为一名优秀教师,他是“典型性”的,又是“非典型性”的;他是“苦难型”的,也是“智慧型”的。张老师有着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口碑,有着高尚的师德和出色的师能。但他无大学学历,无论文论著,无学生竞赛成绩,也无法定量分析出他今日所谓的高考升学率、达标率。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每逢落难,总有贵人相助:辍学拾粪时,巧遇体育从达力老师鼓励他重回校园,完成学业;回乡务农,不惑之年,幸有老同学章崇堂老师力荐,范先白校长爱才、惜才,面试负责人潘恒俊老师慧眼识才,让他走上了讲台,后来又转正,成为教师队伍中的优秀分子,充分实现自我价值。不幸的是,子女纷纷成才,尤其是儿子留学海外、事业有成,他却不能看见。
人生是一道复杂的试题,我辈岂能破解?感念张老师生前对我的友善、友好、友爱,我读懂了他的生命方程式:无悔的生命=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职业道德+吃苦耐劳的品德。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中学)
(插图:珈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