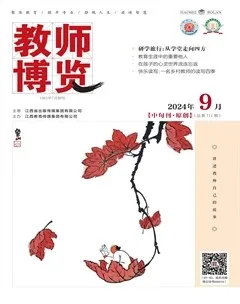教育生涯中的重要他人
有人说,教师的成长与发展充满了变数与机遇,却离不开“三个关键”,即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关键书籍。回望从教生涯,我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个个亲切的名字,一件件温馨的往事。他们犹如教育旅途上的灯塔,在不同时期为我指引方向、照亮前路,让我鼓起勇气再度出发,走在通往美好的教育路上……
一
前不久,我整理书柜,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封面上赫然印着“四川省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几个字,勾起了我尘封的记忆。
2005年是我踏上讲台的第十三个年头,严重的职业倦怠裹挟着我,让我教书毫无激情,育人缺乏干劲,成了“三等”教师——每天等下班,每个月等工资,每年等退休。一天,教导主任告诉我,镇中心校安排我暑假去成都参加为期一周的培训。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诧异,也有些高兴:诧异的是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到我这个普通教师的头上;高兴的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正好可以游玩成都的风景名胜。想到这些,我对这次培训充满了期待。
转眼间,暑假到了。7月22日,我坐了5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成都,站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看着林立的高楼,大都市的繁华气象扑面而来。第二天早上8点,我满怀兴奋与期待,早早步入会场。坐在宽敞明亮的会场,服务人员立即送上一杯茉莉花茶,花茶氤氲着芬芳,让人心旷神怡。如此培训真好。我不禁如是想。
这次培训活动的主持人是四川省继续教育专家组组长杨东老师,他在开场白中介绍了培训的背景与意义,提出了建议与期望。当时,他指着会场上的横幅“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项目/四川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级培训班”,有些沉重地说:“什么时候我们的教师培训能够把‘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项目’这样的字眼去掉就好了。这些赠款,一百多年前原本就属于我们。”其言外之意,大概指的是我们还不够富强,才需要别人的赠款,不要忘记了那一段历史,教育要肩负起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的大任。
为期一周的培训,我聆听专家讲座、观摩名师课例、参加小组交流、参观考察名校。每天培训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学习生活紧张忙碌,我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次培训,我观摩了口语交际、识字与写字、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综合性学习等五种语文课型,课后参加相关的专题讲座;聆听了专家深入浅出地解读新课程理念,用名师课例解析新课程教学策略;第一次听到于永正、靳家彦、窦桂梅等名师的名字;参观了成都市名校泡桐树小学……这一切对我这个乡村教师而言,无疑是一场精神盛宴。
培训过程中,我认真记录,生怕漏掉了重要信息,于是密密麻麻地写了50多页,近2万字。笔记中不乏金句,譬如“教育只有科学的原则,没有科学的方法”“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回到简单”“当你不能改变现实时,就改变自我”“有名的老师善用巧劲,给学生提供更多机会”“老师要坚持自己的个性”“不同的文体与语体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为学生的成长负责,做一个敢于变化、敢于承受暂时的失败的老师”“儿童天性决定活动应当成为小学教育的主要形式”“教学是艺术,需要感觉”“把自己变成一本精彩的书,让别人去读”“语文水平不是教出来的,是‘用’出来的”“语文不仅仅是语言文学,其内核是思想的表达、情感的交流”“学生的错误是美丽的错误”“教师职业态度三重三轻,即重过程,轻结果;重唯心,轻唯物;重自评,轻他评”……上述思想观点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我认识的藩篱,撞击我思想的大门,引发了我的深度共鸣与思考,即便是18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这次培训让我看见了外面教育的美好,见识了专家的风采、名师的课例,特别是听了杨东老师自身的成长经历,很励志。他说:“教师要像养蜂人一样,哪里鲜花开放,就朝哪里走。鲜花代表美好与梦想,教师要做追梦人,勇于追逐美好与梦想。”从此,我开始审视自己的教育生活:还有二三十年的工作时间,难道我就这样消磨下去,直到退休吗?我有教育梦想吗?我的教育梦想是什么?这次培训活动中出场的专家名师,谁不是博览群书,一身书卷气息?这些问题在我的大脑萦绕,让我开始怀疑过去的教育人生。
回到学校,我不由自主地跑到邮局,花了三百多元订阅了《语文报》《教育文摘周报》《教育时报》《小学青年教师》等报刊。“改变与成长:从阅读开始”,这是我当时心里冒出来的想法。记得培训总结会上,杨东老师提出:“教师要做叙事研究,把教育教学事件记录下来。”于是,我开始记流水账,把教育教学中发生的故事写出来。读多了,写久了,心里萌生出投稿的念头。很快,我的第一篇“豆腐块”文章发表在《语文报》上。从此,教育写作,一发不可收。
后来,我与杨东老师成了QQ好友,我们时不时交流一些想法和思考。有一次,我收到2014年4期《教学与管理(小学版)》样刊,恰好同期刊登了杨老师的《课堂观察的类型与方法》一文,他提出的同伴互助型、切片定量型、专家诊断型、结果评价型四种课堂观察,观点鲜明,操作性强,对一线教师观课极具指导意义,成为我观课评教的秘密武器。2016年12月,杨老师把四川省陶行知教育研究会活动搬到了宜宾,邀我去听讲座。讲座现场,杨老师的观点直击当下教育的痛点,引发与会老师的共鸣,让我对当时的语文教育有了更加清醒而理性的认识。2017年3月,杨老师发来国学经典活动邀请函,我心动不已。春寒料峭的3月,我坐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学术厅,观摩了大学教授教小古文,学习了优秀校长、教师开展国学教育的经验。我特别有幸观摩了“经典素读”倡导者陈琴老师执教的《诗经·王风》,其教法朴素,符合诗歌特点,让人在情韵生动的吟诵中,走进诗歌意境,触摸作者情感,美哉。与杨老师交流,阅读他的文章,参加他组织的活动,对我的教育、教学、教研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对教育生活永远保持观察和思考,并且时时追问朝哪里去。我庆幸自己在职业倦怠期,赶上了2005年7月成都的那一次培训,遇见了杨老师,让我跳出了“三等教师”的泥潭,从庸常的教育生活中开始蜕变、成长。
二
教师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教育实践与同人进行专业交往,这种专业交往是自发的、主动积极的。除了同伴、专家、名师外,教育期刊的编辑无疑也是教师专业交往的重要他人,而投稿是一种很好的专业交往方式。事实上,同伴之间水平大多相差无几,专家名师往往可望而不可即,教育期刊编辑却是“来者不拒”。只要教师愿意投稿,没有哪个编辑会拒绝新颖独到的教育观点与富有成效的教育实践。
2009年秋,办公室的同事带回来几本《教育科学论坛》。期刊封面设计素雅,文章学术味浓,我颇有一见钟情之感。捧着一本喜欢的期刊,总是会冒出一种天真的想法:要是自己的教育实践与思考,能够刊登在这本杂志上,该有多好。我尝试着写了一篇《把思考的权利和空间还给学生》投了过去,没想到这篇“千字文”刊发在2010年2期的《教育科学论坛》“课改研究”栏目上,这激发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和勇气。同年,我在该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和一则“读者心声”。
那一年,当地狠抓教学质量,学校大小会议常常传递一种观点:教师写文章是不务正业,抓学生考试成绩才是正事。我有些心烦意乱,开始怀疑教育写作的价值,不知是否还要坚持写下去。心静不下来,书看不进去,写作慵懒了,上班也无精打采,我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拽着我,让我滑向看不见的深渊。
煎熬中,时间慢腾腾地来到了2011年3月。某天,《教育科学论坛》编辑何静老师向我发来了邀请函,希望我参加杂志在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南鹰小学举办的一线读者、作者笔会。接到消息,我有点受宠若惊,一个草根教师何德何能得到一本省级期刊的青睐?同时我内心夹杂着不安:一是学校会不会准假?二是我一个普通教师参加学术活动,会不会出丑?这次笔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读者、作者,参会的都是喜爱教育写作的老师,还有杂志社编辑的讲座和点评,何不出去散散心?我拿着邀请函到学校请假,没想到领导同意我去。
坐了8小时大巴车,到了广元时,已是华灯初上。我在宾馆住下,期待着第二天的活动。我不记得那次听过的讲座内容是什么,但是我清楚记得自己站在台上,诚惶诚恐地分享了《农村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绊脚石”》后,一位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缺乏新意,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知灼见。
参会期间,我与编辑们共进午餐,大家谈教育、谈教师专业成长、谈教育写作……何静老师对我说:“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张老师能够静下心来思考研究教育、写文章,难能可贵,要好好地坚持写下去。”谁说教师写作是不务正业?为什么现实中还有不少教师在写作呢?我之所以能够参加这样高端的学术活动,见识专家名师的风采,得到他们的指点,不正是教育写作带给我的回报吗?何老师的话又点燃了我心中写作的热情。
从广元回来,我更加坚定地走教育写作之路,不管今后有多少风吹雨打,永不放弃用笔思考教育。后来,何静老师到成都市武侯区教科院当教研员,兼《武侯教育研究》执行主编,负责策划、审稿、编辑工作。她邀请我做杂志特约编辑,负责“班主任工作”“名师论坛”两个栏目的编辑工作。我深感荣幸,因为这是向同道学习的一种方式。同时,我也觉得这个担子重,必须认认真真,尽最大的努力做好。针对“班主任工作”栏目,我策划编辑了“班级凝聚力”“班级文化建设”“个性化班规”“家校沟通”“如何做好副班主任”等专题。在“名师论坛”栏目,我拜读过李镇西、何立新、罗晓晖等名家的文章,他们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我与其说是在编辑他们的文章,倒不如说是在学习他们的教育思想、治学态度、研究精神,我赚大了。
武侯区是成都市的教育“高地”,聚集了一大批优质教育名校,加之何静老师之前在《教育科学论坛》做编辑,拥有一批高水平的作者朋友。因此《武侯教育研究》虽然是一本内部刊物,但稿源充足,质量上乘,最难得的是还发稿酬。每期刊物出来,何老师总会给我寄10-20本,我如获至宝,认真研读。我在《武侯教育研究》上先后读过华东师范大学张华、华南师范大学王红、南京师范大学石军、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沈曙虹、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包兵兵等名家的文章,学习了高校教授、教科院研究员以及全国各地名师的文章,极大地开阔了教育视野。汲取了名家的教育思想的营养后,我看教育的眼光发生了变化,喜欢追问现象背后的原因。同时,我会把刊物赠送给学校以及周边区县喜欢阅读的教师,鼓励他们撰写读刊感受,记录教育思考。特约编辑的经历训练了我开发专题的能力,夯实了我的文字功底,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我“偷”学了教育大家的思想。
2017年10月13日,何静老师邀请我到成都市武侯区教科院为幼儿园骨干教师分享教育写作经验。这次活动,我有幸聆听了《教育科学论坛》资深编辑陈兴中老师的讲座《教育研究刊物编辑的价值诉求》,让我真切感受到一位资深编辑的深邃思想、独到见解,明白了思想才是写作的生命与核心。在活动过程中,我也分享了教育写作经历。陈老师激动地说:“如果早点晓得你,我早就向你约稿了。” 2018年8期《教育科学论坛》刊发了文章《从课改走来:我的“三观”之“变”与“惑”》,就是陈老师向我约的稿。2022年3月,陈老师又向我约稿,参加“‘双减’背景下拔苗助长的教育乱象观察、审思与突围”话题讨论。这对我这样的普通教师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与鼓励。
参加武侯区教科院活动后,我收到《教育科学论坛》副主编余秀丽老师的邀请函,她希望我能在杂志社主办的读者、作者、编者交流会上分享教育写作经验。我很诧异,后来才知道,是何老师觉得我的教育写作分享很实在,特别适合一线教师,便向余老师推荐了我。2018年1月8日,我在四川大学附属小学学术厅分享了教育写作经历与思考,受到编辑和参会老师的好评。
因为一本杂志,认识一位编辑,产生了“蝴蝶效应”,让我这样的普通教师有机会参加高端学习活动,过了一把编辑瘾,还阅读了不少名家的文章,与同道分享教育写作思考,获得了一次次历练与成长。像何老师一样鼓励与厚爱我的编辑,不正是教育人生路上的一座座灯塔吗?
三
2013年9月开始,我再也没有当过班主任,对于班级管理的思考,少有涉及。我的教育写作视角更多地指向了语文教育、教师成长、校园文化、校本教研等内容。
2016年,我加入了“宜宾老班”QQ群,群主是“点灯者徐痴人”——宜宾市教科所德育教研员徐卫老师。之前,我读过他一些文章,觉得他很有思想。难得的是,他居然“下水”——到学校上示范课。徐老师常在群里发布教育思考的文章,鼓励大家分享教育智慧。群里也有宜宾市各区县的教研员和名优教师。我胆子大,不怕出丑,也不怕批评,经常把文章链接发在群里,没曾想得到了徐老师的鼓励。一来二去,我们有些熟了。
2017年2月15日,应徐老师的邀请,我在“宜宾老班”群,分享了《用写作打开教育生活的另一扇窗》,引起热烈反响。有的老师写了听讲座后的感受:《过一种有思考的教育生活》《教育写作:教师的一种自我成全》。令我深感意外的是,徐老师也写了一篇《教育写作关键要能“感”善“悟”》,我读之颇受鼓舞。
2018年3月,宜宾市小学班主任风采展评活动在高县实验小学举行。得徐老师的错爱,我忝列评委,观摩学习,获益良多。这次活动让我见识了宜宾市小学班主任的精英,开始思考班主任对于学生成长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于是我的写作触角伸向了班主任成长与班级管理。每当在德育研究上产生什么困惑与疑问时,我喜欢与徐老师交流,且多有收获。徐老师出差到屏山县,总会联系我。我们一边喝茶,一边促膝长谈,话题涉及学校教育、教师成长、德育活动……相聊甚欢。不得不说,接触徐老师后,我开始站在更加广阔的视角看教育、研究德育,关注学生行为背后藏着的“秘密”。我在德育和班级管理方面的思考逐渐深入,相继在《中国德育》《中小学德育》《福建教育》发表了十余篇文章。2019年9期《江苏教育》刊登了我的《班级教师群体共育的实践与思考》一文,引起成都市龙泉驿区教科院德育教研员李进老师的关注。他邀请我为该区中小学班主任做《德育成果的提炼与撰写》讲座,受到好评。我在德育方面取得的点滴成绩与徐老师的引领分不开。
2022年4月,学校邀请徐老师做《班主任心艺术》讲座。那段时间,班上几个特殊学生特别闹腾,我陷入迷茫和困惑,找不到出路。徐老师在讲座中提到“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问题儿童”“学生任何一种行为都有合理缘由”“教师要有慈悲心肠”“教师要把学生放进他所处的环境中”。这些观点一次次敲打着我的心扉,让我开始带着悲悯情怀审视特殊学生:长成现在的样子,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已经不幸了,不是更应该得到老师的关爱吗?想到这些,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看到那几个调皮学生时不再是厌烦,而是多了一分爱怜与同情。我尝试着去理解、认同他们,并抓住契机,促使他们自我蜕变。没想到,真见到了效果。
我把听讲座的思考,结合与特殊学生交往的故事,写成《教师要有一颗慈悲心》,发表在2022年1期《教师博览》。收到样刊,我把文章拍下来,发给徐老师,分享喜悦,感恩他的引领。他告知我,他把文章分享到了朋友圈,希望更多的老师向我学习,学以致用,用以促思,思有所成。为了保护学生,我请徐老师把文末单位抹去。他夸赞:“心中时时刻刻装有学生,这是真正的慈悲为怀。”随后,我给徐老师寄了一本样刊,感谢他像一束光照亮一线教师的思想原野。
在与徐老师的交往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教育还有远比教给学生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真正的师者应该关注学生的个体生命,尤其是对待特殊学生要多一点慈悲心。
往事并不如烟,我从教育人生中打捞出点点滴滴美好,心里充盈着感动、感激、感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教育观念,影响着我的教育行为,塑造着我的教育思想,改写了我的教育人生。他们无疑是我教育生涯中的重要他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未来的教育生活中,我将努力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既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成为有缘之人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作者单位:四川省屏山县学苑街小学)
(插图:谭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