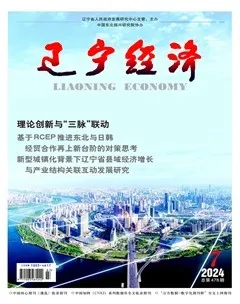理论创新与“三脉”联动
〔内容提要〕2024年5月11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中央党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座谈会在杭州召开。以下为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先生的发言实录。
〔关键词〕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理论宣传
一、理论研究与宣传应是什么关系?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讨论理论创新与理论宣传问题,首先要搞清二者关系。
我自1979年春天加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专注于经济理论研究已有45年。在这几十年的实践中,我深切体会到理论研究与宣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两支队伍,一个使命,相互成就,共同发展”来描述。
今天,中央媒体如《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也参与了会议。我打算以我与几家报纸的关系作为案例,说明这两支队伍如何相互支持。
首先,讲《人民日报》。我的第一篇学术研究文章是在1980年5月9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的。1979年我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后接受的第一项调研任务,就是参加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的“东北调查”。当年10月,我被派到黑龙江省,调查了70天,在调查中发现了国有经济在工业部门“几乎一统天下”的现象。回来后我经过研究相关资料发现,不仅局限于东北地区,整个国家工业部门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这一现实引发了我的深思。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应该“长期并存,比翼齐飞”。说是“长期”,但至于多长,我当时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应该长期并存,而且这两个翅膀应该是“比翼齐飞”。虽然我当时并未使用“民营经济”这个概念,而是称之为“非国有经济”,但这篇题为《长期并存,比翼齐飞》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曾予以广播。
经过45年的发展,如今我们国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特别是浙江在发展非国有经济方面,更是一马当先。中国有两个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一个是广东,一个是浙江,我经过比较研究后认为,浙江的改革更带有“本土性”,广东带有中国港澳的和海外的外延影响。据我掌握的情况,不包括个体户,2023年中国的民营企业有5200多万家,占全部企业的93.2%,从数量来看,这个比重是比较可观的。然而,从资产来看,还是国有资产数量可观,国有总资产达800多万亿元,民营资产比它少得多。有意思的是,2023年11月,中央的媒体搞了一个叫做“唯改革者进”的报道,里面重提“比翼齐飞”,回想起来多亏当年《人民日报》理论部支持。
第二个案例,是《经济日报》。1984年9月,我参加了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举行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感谢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浙江人民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讨论改革理论的平台,这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2024年恰好是莫干山会议40周年。40年前的莫干山会议,代表如何产生的呢?遵循“五不讲”原则:不讲学历、不讲职务、不讲职称、不讲名气、不讲关系,只讲一条“以文选人”,即通过提交的学术文章为国家改革献计献策。这种“五不讲”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我当时提交的文章题为《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提出了“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上借鉴香港的商品经济模式,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承蒙《经济日报》理论部的厚爱,这篇文章从124篇参会文章中脱颖而出,与其他17篇一起发表在《经济日报》专版上,对中青年学者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第三个案例,是《光明日报》。1986年,我曾向教育部申请了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课题,研究《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经过多年的研究,我出版了第一本相关专著《人本体制论》(后来又出版了《人本型结构论》)。2008年《人本体制论》出版后,《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孙明泉同志次年进行了长篇访谈,并用书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将其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理论巡礼成果之一。
以上这三个案例,只是理论界研究的沧海一粟。我对理论宣传对理论研究的意义有三点感悟:第一,对国家来说,它能反映理论界的研究、探索与突破,宣传是一种反映;第二,从世界来说,它能展示中华学人对文明的思考和见解,宣传是一种展示;第三,对个人来说,它能记录其研究成果,宣传是一种历史“留痕”。
二、理论创新,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
今天重点研究理论创新,我认为势在必行,而且任重道远。为什么?我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从体制创新角度,二是从技术创新角度。
以体制创新为例,我提出一个看法供大家讨论,即中国经济体制的“基因问题”。具体来说,传统理论的基因认为市场不是个好东西。经典作家的原话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商品生产必须被消除。基本观点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水火不容。要实现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商品经济;要搞商品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传统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是“基本原理”吗?我认为不是,但它也不仅仅是“某个具体的个别论断”,似乎比基本原理小,但比某个具体论断大,属于重要的甚至是基调性的论断。这个“设想”中是否含有“一点空想”的成分?这种观点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认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骨子里是反市场的。因此,他们主张搞计划经济体制。
从理论创新角度来说,经过45年的改革,体制的“基因再造”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中国的基因还需要继续再造,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任重而道远。
第一,从历史维度研究。从历史上看,中国长期缺乏商品经济意识而存在高度集权的思想。对过去传统体制的弊端我们虽有反思,但是我认为仍未反思到位。
第二,从理论维度研究。2018年1月,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一个多月后,某著名大学有人发表文章,他断章取义地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话,宣扬“消灭私有制”而阉割了马克思原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重要前提。马克思讲的是消灭什么私有制?他说得很清楚,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不是消灭人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此外,关于“资本到底姓什么”的问题,我在1992年出版的《资产重组》一书中提出了“资本中性论”,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完全解决。
第三,从国际维度研究。我国政府在2021年9月提出申请加入CPTTP,因为从总体上看,CPTTP的经贸标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才申请加入。然而,2023年未能成功加入。深挖原因,涉及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隐性壁垒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劳工权益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也倒逼我们继续进行基因再造。
第四,从现实维度研究。当前的现实目标尚未完全实现,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我和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书稿,有40多万字。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必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这七大要素。
总之,经济体制必须用市场化的思路进行改革。我认为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理论创新。
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最近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我注意到《浙江日报》发表的“之江智库”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新质生产力的特征、生成机制与布局协同,这是智库研究的成果。关于新质生产力,仍有许多需要探讨的地方。例如,新质的“质”到底是“质量的质”,还是“性质的质”?在实践中,如何将新质生产力与各地的特质生产力以及优质生产力结合起来?如果进一步挖掘,我们如何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这些方面都还有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
总之,无论是在体制理论创新还是科技创新领域,都有一些未解之谜,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和创新。
三、“三脉”联动
我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后就跟《浙江日报》有交往,近些年来联系更加紧密。根据我的观察,总结出以下“三脉”。
(一)紧扣国家战略性的“命脉”
例如,《问答中国》(之江会客厅访谈录)刚刚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有几组标题,第一组是思想引领,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组是改革创新,如《中国:如何推动动力变革》;第三组是新发展格局,如《怎样更好高质量发展?》;第四组是共同富裕。中央让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先行示范区,那么共同富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曾在《浙江日报》接受采访,题为《从发展大局看共同富裕》,认为应是“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而不是无差别的共同富裕)。第五组是政府治理等。这些选题实际上涵盖了我国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战略性、命脉性问题,抓住了关键。

(二)汇集人脉
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但不是一个社科大省。实事求是地说,浙江的社科界专家远不如北京和上海多。然而,这些年来,他们能够“北上,南下,东进,西拓”,主动邀请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参与。例如,首都经济学界的张卓元先生;哲学界的胡福明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浙江日报》抢救出来的,这篇文章成为他的“生命绝唱”,非常珍贵;还有史学界的王巍先生,他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通过“之江会客厅”的汇集本《问答中国》以及《学习有理》,再加上《思想人生》,共汇集了50多位专家,其中大多数是外地的,汇集人脉不错,这为浙江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开辟了新的天地。我个人在外地调研时,理论部潘如龙主任也曾多次到京外的东北、山东、浙江莫干山、广东深圳、海南找我,功夫下得很深。
(三)“心脉”
我今天想与大家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理论宣传如何才能打动人心?如何才能更深刻?深刻到哪里?我认为要挖掘内心世界深层的东西。所谓深层的东西,不是浅层的,更不是表层的。那么,深层的东西是什么?今天我举胡福明先生在《思想人生》中谈到他当年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例。他说,当年写这篇文章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的原话是“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打算”。这挖到了他的内心深层。那么,他这种思想从哪里来?在《思想人生》中,胡福明谈到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时,提到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团中央书记来北京大学作报告,这位书记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善于判断是非”,特别强调“不要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可能就是这句话点拨了胡福明,“不要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振聋发聩。据我所知,“诺诺”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诺”即yes,“谔”是“谔然”(俗话说“发愣”),这真正挖掘了学者(“士”)内心深层的东西。我在2024年3月18日《浙江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9年前《人本型结构论》书中的一句话,“创新创意之源:人的心灵放飞”。要真正创新,一定要心灵放飞。同样,国家要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需要缔造一个让万众“心灵放飞”的良好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