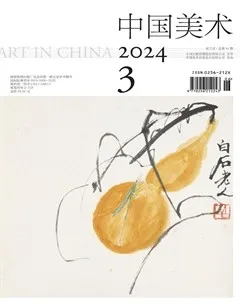背靠背的双重表达:达·芬奇《愉快和痛苦》的寓意探究
摘要:达·芬奇一生完成的油画和壁画作品屈指可数,因而学者们多从其手稿入手对其展开研究。他作为一个多面的全才,手稿中隐藏了许多奇思妙想,许多学者皆试图通过手稿中的线索来还原历史中真实的达·芬奇。本文以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寓意画《愉快和痛苦》为研究对象。肯尼斯·克拉克曾画中形象评价为“有双头的‘怪物’”,贡布里希亦说:“莱奥纳多发明的那个双胞怪魔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显然,在这些艺术史学者的眼中,仅从人物形象来看,达·芬奇画的是一个超自然的“怪物”。本文则尝试用图像学方法分析手稿的图文,追溯图像原典——雅努斯和文本,即《会饮篇》《斐多》和《伊索寓言》中的双头形象,并结合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进一步探讨《愉快和痛苦》的创作意图,找到研究该图像的新视角。
关键词:达·芬奇 《愉快和痛苦》 寓意画 手稿
一、图像志:《愉快和痛苦》的人物身份及寓意

达·芬奇的手稿恰如其人,充满着奇思妙想,吸引着中外学者不断地研究、发掘。通过这些传世草图,人们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达·芬奇。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基督dcf55ea2adf9168d8a0db9e81f5cb1dd62477d0a2fe4339278c5023b7fe25ce0教堂学院的一幅手稿曾引发学者们的广泛讨论。这幅寓意画即《愉快和痛苦》。卡罗·卫芥在《达·芬奇传》里曾谈道它:“画面呈现出一个双头四臂的狰狞怪兽,一个头年轻,另一个头衰老。”[1]肯尼斯·克拉克亦言简意赅地将画面形象评价为“有双头的‘怪物’”。[2]贡布里希说:“莱奥纳多发明的那个双胞怪魔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显然,在这些学者的眼中,仅从人物形象来看,达·芬奇这幅手稿中画的是一个难以被人理解的超自然的“怪物”。那么,画中形象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幅手稿和达·芬奇的其他手稿类似,由图像和文字两部分构成,即贡布里希所说的“图画文字”。贡布里希认为,达·芬奇“喜欢错综纷乱,也由于他对相互作用的问题有一种科学的兴趣,所以他构造了一些图画文字”[3]。

既然我们无法通过图像来辨别画中“双生人”的身份,那么不妨根据手稿中的文字来寻找线索。手稿中的文字由达·芬奇一贯使用的镜像书写法写就。如果我们把手稿中的文字进行镜面翻转,便可以看到人像头部上方写道:“愉快和痛苦像是一对双胞胎,因为他们从不单独出现,似乎总背靠背地在一起,因为他们彼此相对。”[4]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背靠背姿态的“双生人”代表着愉快和痛苦这两种相生相伴的情绪。16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吉安·保罗·洛马佐在《绘画、雕塑与建筑艺术论》中对愉快和痛苦进行过描述:“支撑它俩身体的右脚踩在一捆干草上,左脚踏在一块金匾上,以表明它俩的区别:右脚代表世俗愉快的情感,又低、又弱、又软;左脚代表不快的情感,它踏在金匾上,既壮实又坚定,经过痛苦的磨炼,它变得像箭头一样坚硬了。”[5]画面中,“双生人”的两只脚分别踩着两块区域。左边年轻者的脚下是一个不规则形状,下方写着意大利语的“泥”(Fa n go)。右边年老者的脚下踩着一个矩形,下方写着意大利语的“金”(Oro)。结合洛马佐的著述,我们可以推测出左边那个有着卷曲头发,戴有发带或花冠,鼻子精致直挺,嘴角上扬,下巴圆润,面庞清秀的年轻人可能指的是愉快这种情绪。他背靠着的那个头发乱糟糟,眉骨突出,有着鹰钩鼻,嘴角下撇,下巴突出,有点“地包天”,表情愁苦的老年人指的是痛苦这种情绪。笔者通过对比手稿中的文字,发现洛马佐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年轻人,也就是代表愉快情绪的人脚下踩的是泥,而非干草。图像的下方还有两行字,写着“如果你选择了愉快,要知道在他的背后有一个人会带给你痛苦和忏悔”[6]。其大体意思是愉快和痛苦总是如影随形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达·芬奇把他们画成了背靠背的“双生人”。图像中有四只手臂,每只手里都拿着不同的物品,其中靠近画面前景的两只手臂相互交错,画面背景中的另外两只手向上举着,好像在向人们展示手中的植物。那么,他们手里究竟拿的是什么呢?
其实,达·芬奇在图像的左侧写下了一段文字,对图像内容进行了阐释:
愉快联结着痛苦,像孪生兄弟一样,这是因为两者不相分离,彼此相反,背靠着背。它们存在于同一躯体上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基础,劳苦是愉快的源泉,痛苦来源于空虚……的愉快。因此,就像右手握着一根无用和脆弱的芦苇一样,由它造成的损伤是有毒的。在托斯卡纳,芦苇被用来支撑床铺,以示虚妄的梦境在这里出现,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里被消耗,许多有用的时间在这里被浪费。在清晨,头脑清醒,静静地躺着,积蓄着新的劳力,以便重新开始工作。这里同样产生许多虚泛的欢乐,头脑里出现许多虚无缥缈的事物,身体也享受着那些常常造成生命衰竭的欢愉。[7]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得知代表愉快的人手中拿的长条物是芦苇。达·芬奇对愉快的评价是“无用和脆弱”“由它造成的损伤是有毒的”“在托斯卡纳,芦苇被用来支撑床铺,以示虚妄的梦境在这里出现”。由此可见,象征着愉快的“芦苇”和“泥”有着一些共同特征,即软弱、无支撑力,会让人陷入虚妄的欢愉。那么,在达·芬奇看来,人又应当立于什么之上呢?在笔记中,达·芬奇写道:“人应该睡在坚实的木板上。”[8]可见,达·芬奇认为木板和金板一样,更能给人带来踏实感。
在笔记中,达·芬奇并没有对另外三只手中的物品进行解释。之后,洛马佐阐释道:“痛苦的右手拿着一大把铁蒺藜,表示不快给心灵造成的尖刻而毒辣的损伤。”[9]蒺藜原为一种植物,果实有刺,后来被用来形容一种四角分叉的武器。将其置于地上时,其中一角会自然向上,可以用来阻碍敌军的人马通过。达·芬奇在笔记中也提到过这种军事武器。[10]这种武器象征着愉快中所暗藏的痛苦,将会把人刺伤。洛马佐接着写道:
痛苦的左手拿着一串带有玫瑰刺的枝条。正因为没有刺,玫瑰就不能生长,所以痛苦把刺攥在手中,让玫瑰凋谢。一串带刺的玫瑰没别的意思,只表明易碎的愉快很快就会失去,眼前的自信将导致麻烦和苦恼。愉快的左手握着一大把硬币,伸到痛苦的眼前。有些硬币在往下掉,表示痛苦正躺在愉快给它准备的世俗虚荣之上。[11]
至此,我们基本上弄明白了“双生人”的身份——达·芬奇绘制的是一幅代表愉快与痛苦的寓意画。在他看来,愉快和痛苦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虚幻浮华的欢愉给人带来的可能不仅有甜蜜,还有伤害和刺痛。
将愉快和痛苦两种情绪表现为“双生人”是达·芬奇自己的奇思妙想吗?其实,“拟人和寓意的那些形式,后来在欧洲的艺术中有了长久的生命。古典的神明获得了新的、表示自然现象或抽象概念的寓意功能。另一方面,抽象概念获得了拟人化的形式”[12]。韦伯斯特教授曾将拟人视为希腊思维中的一种模式。[13]诗人用拟人化的修辞表现抽象的概念,画家则根据诗的语言,将抽象概念视觉化,创作出带有寓意的图像。那么,达·芬奇绘制的这个形象是否存在原典?
在柏拉图的《斐多》中,曾记录了苏格拉底被处死前在狱中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所谓愉快,真是件怪东西!愉快总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联在一起。看上来,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对冤家,谁也不会同时和这两个一起相逢的。可是谁要是追求这一个而追到了,就势必碰到那一个。愉快和痛苦好像是同一个脑袋下面连生的两个身体。我想啊,假如伊索想到了这一对,准会编出一篇寓言来,说天神设法调解双方的争执却没有办法,就把两个脑袋拴在一起,所以这个来了,那个跟脚也到。[14]
苏格拉底说愉快和痛苦是“同一个脑袋下面连生的两个身体”,也就说明二者是如影随形的关系。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的记录能够证明达·芬奇看过《斐多》,但在达·芬奇所处的那个时代,意大利佛罗伦萨有一位对文艺复兴思想及艺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菲哥利恩,并在佛罗伦萨接受教育,学习人文学科、哲学和医学。1462年,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卡雷吉交付给他一栋房子,并把一些希腊文手稿交由他处理。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就是在此时建立的。1469年之前,费奇诺就已经完成了包括《会饮篇》在内的柏拉图著作的译注工作。作为柏拉图学园的灵魂人物,费奇诺会在教堂等地发表关于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公开演讲。他在世的时候,新柏拉图主义学说的影响力已经从佛罗伦萨传播至欧洲各国。[15]科西莫卒于1464年。同年,达·芬奇来到了佛罗伦萨。1469年,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德·美第奇继任,统治佛罗伦萨并继续资助柏拉图学院以及一些艺术家,其中便包括达·芬奇的老师韦罗基奥。因此,达·芬奇也间接受到过洛伦佐的资助。[16]1482年,达·芬奇受洛伦佐的委派前往米兰,向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大公呈上了一把里拉琴。
在前往米兰之前,达·芬奇极有可能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影响,接触过柏拉图的相关文章和观点。1495年前后,达·芬奇在手稿中(按:第559张纸正面,即旧版第210张纸正面的“a”部分)列了一张书单,提到了40本书的书名,其中包括一些古代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多半是新柏拉图主义学者兰迪诺[17]翻译的俗语译本,包括《伊索寓言》和西塞罗的《论选题》等,[18] 其中《伊索寓言》中的《渔夫们》这则故事写道:

渔夫们起网,觉得渔网很沉,高兴得手舞足蹈,以为捕获一定很丰富。他们把网拉到岸上后,发现网里鱼并不多,尽是些石块和沙子,非常懊恼。令他们不快的主要还不在于收获不多,而是结果与期望相反。这时,他们中的一位长者说道:“朋友们,别伤心了,欢乐和悲伤显然是两姐妹。我们怎样高兴过,就应该承受怎样的悲伤。”同样,我们应该看到人生多变幻,不要总是为顺利而欣喜,应该想到晴天过后会有暴风雨。[19]
另一个译本中也写道:“朋友们,别难过,快乐总与痛苦在一起,她们如同一对姐妹。”[20]可见,《伊索寓言》中也提及了愉快与痛苦的相伴相生。因此,《斐多》和《伊索寓言》中关于愉快和痛苦的描述很有可能就是达·芬奇《愉快和痛苦》的文本来源。

二、图像史中的双头形象与达·芬奇的画中形象
“双生人”最早表现为罗马神话中雅努斯的形象。作为罗马人的门神,雅努斯的两张脸象征着很多二元概念,例如年老的脸象征着过去,年轻的脸象征着未来。从14世纪开始,艺术家在表现“四大美德”之一的明智时,便不再满足于使用中世纪传统的拟人方式,而是开始借鉴雅努斯的双面形象来表现其特点。
将雅努斯的形象和达·芬奇《愉快和痛苦》中的图像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雅努斯为一头两面孔或双头形象,而达·芬奇笔下的“双生人”却有两个上半身,包括两个头、两个肩膀、四只手。我们通过梳理雅努斯的图像,发现绝大部分的雅努斯像都是着衣的,而达·芬奇所绘人像却是赤裸的。可见,达·芬奇笔下的“双生人”形象跟雅努斯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那么,其画中的“双生人”形象到底从何而来?
其实,早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便曾经出现过对“双生人”的描写。在《会饮篇》中,当苏格拉底和阿伽通及宾客在对爱神进行赞颂时,阿里斯多潘就描述了“双生人”的形象。他认为,爱神值得赞颂,因为爱神医治好了人的病。原因是从前的人本来有三个性别,即男人、女人、“双生人”。从前,人的形体是圆形的,腰和背部都很圆,每个人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头,头上长着两副面孔,一副朝前,一副朝后,耳朵有四个,各器官的数目皆依比例翻倍。当时的人很强壮,试图与神一较高下。众神担心人的能力危及神,却又因为需要人的崇拜和祭祀而不能灭绝人,故而把人劈成两半,一方面削弱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使侍奉神的人数量加倍。自此以来,被劈开的人一辈子都在寻找另一半身体,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种对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爱。[21]其实,达·芬奇也不仅画过这一种“双生人”形象,其在另一幅作品中同样画了一位年轻人和一位长者。这幅手稿中的人物与《愉快和痛苦》中的“双生人”有着类似的眉眼、鼻子和下巴,并且年轻者的头上都戴有发带(或是花冠)。年长者从袖口伸出的右臂若隐若现地搭在年轻者的肩上。然而,达·芬奇好像并未画完这幅画。恰恰是因为未完成,画面缺失了人像的下半部分,因而两个独立的人像仿佛变成了面对面的“双生人”,恰似《会饮篇》中提到的被宙斯劈开的“双生人”。

在达·芬奇的手稿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一直乐此不疲地表现美与丑、年轻与年老,画中通常都是用一个“地包天”、鹰钩鼻的老者和一个卷发的年轻人作对比。例如,在1478年的《温莎手稿》中,达·芬奇反复练习描绘头像。马丁·克莱顿认为这份手稿分别表现了青年男子、青年女子和老年男子三种形象,而这三种形象都是达·芬奇笔下标准面容的变体。他通过研究面部结构如何影响人们的年龄、性别和对美感的感知,对嘴巴和下巴的形状进行了细微调整。[22]通过比对,我们能够看出青年男子和女子的面部特征极为相似——鼻梁的线条从前额笔直地延伸至鼻尖,鼻头秀气,嘴唇和下巴饱满,睫毛纤长上翘。这些或许就是达·芬奇认为美与青春应该具备的特征。
迈克尔·夸克尔斯坦认为,达·芬奇在表现年轻者与年长者的形象时,适当借鉴了古代钱币上的头像。例如年长者的形象可能来源于罗马皇帝加尔巴,年轻者的原型可能是安提诺乌斯。[23]当然,达·芬奇也跟其他艺术家一样,擅于记录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人像,也就是将身边人作为模特。那么,这幅《愉快和痛苦》是否也有现实原型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达·芬奇在米兰结识的一个年轻人——萨莱(Salai)。根据达·芬奇手抄本中的记录,其画室在1490年7月22日雇用了一个名叫乔瓦尼·贾科莫·迪·彼得罗·卡普罗蒂的年轻人作为学徒和模特,其另一个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字便是萨莱。萨莱其实是个绰号,意为“小恶魔”或“小鬼”,首次出现在达·芬奇写于1494年1月的一张账单上。在萨莱来到画室当学徒的第一年,达·芬奇就在一份清单上列举了因其举止不当而给他造成的各项损失。这份账单的末尾还列有其为萨莱支付的服装费用。在另一份写于1497年4月4日的萨莱开销清单中,可以发现达·芬奇曾送给萨莱一件时髦的斗篷作为礼物。向来节俭的达·芬奇愿意为其购买华丽的衣饰,可见他对萨莱是照顾有加的。根据瓦萨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萨莱和达·芬奇反复表现的少年形象十分相似。换言之,萨莱的面容有一种达·芬奇常常描绘的理想男性之美。不过,萨莱的样貌又与克拉克所说的“达·芬奇早期作品中具有韦罗基奥风格的男孩”有着细微的差异。他的下巴更圆润,头发更短、更卷曲,前额到鼻梁之间是一条平滑的线。根据萨莱肖像的特征可知,前文提及的两幅“双生人”形象作品中,代表愉快的人物原型应该就是萨莱。

在《温莎手稿》中,画面中央画有一个与《愉快和痛苦》手稿中年长者相貌相近的老人,同样是鹰钩鼻,嘴唇紧闭,有着近似无牙的“地包天”下颌。贡布里希认为此画的中心人物是达·芬奇自己,而周围那些从面部表情和手势便可看出不怀好意的人物代表着误解和嘲笑达·芬奇的人。[24]笔者认为,这最多是一种漫画式的自画像。一方面,达·芬奇早在韦罗基奥工作室时期便开始描绘类似的老者形象,当时其自身仍是一个青年人。另一方面,从达·芬奇晚年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出,虽然皮肤纹路和发质显露出了他的年纪,但是整体来说,仍算得上是一位保养得当、精致的老者。即便如此,艺术史学家仍未放弃将达·芬奇笔下的老者形象解释成其自画像。夸克尔斯坦提出,新柏拉图主义认为灵魂既塑造身体,又指引艺术家之手,因而创作者倾向于在作品中描绘自己,即“自我模仿”。[25]那个“地包天”的老者或许并非达·芬奇的真实写照,而是一种化身和自我投射。
三、《愉快和痛苦》的创作意图
达·芬奇创作《愉快和痛苦》这幅作品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选择从达·芬奇的另一幅寓意画《米兰政治状态的寓言》入手,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马丁·坎普认为这幅作品可能是达·芬奇为赞美卢多维科的盛装游行和化妆舞台的布景所进行的装饰设计。亚历山德罗·诺瓦认为,这两幅手稿都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尺幅相近,可能属于一个系列的草图。因此,二者很可能出于同样的创作目的。也就是说,这幅《愉快和痛苦》也可能是为赞美卢多维科的庆典演出或化妆舞台的布景所进行的装饰设计。[26]肯尼斯·克拉克曾提到,达·芬奇为了满足卢多维科的喜好和赞颂米兰宫廷,花费了大量精力创作类似的寓言故事,希望通过这些创作来彰显卢多维科家族的伟大。

除此之外,在《米兰政治状态的寓言》中,达·芬奇在表现拟人的“明智”与“正义”时,主要沿袭了这两个拟人形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例如“正义”手中的剑、象征“明智”的镜子、双头形象以及蛇等。然而在《愉快和痛苦》中,“双生人”的形象特征则隐含着达·芬奇的个人喜好与情感倾向。肯尼斯·克拉克在《成为达·芬奇:列奥纳多的艺术传记》中写道:“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中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寓言题材草图貌似具有某种我们已无从得知的政治含义,对达·芬奇来说其吸引力可能在于充当了他荒诞幻想的释放口。这些噩梦中的形象被列奥纳多用急促、跳跃的笔触画成,这种技法他只在创作真正感兴趣的对象时才会使用。”[27]换言之,《愉快和痛苦》这幅寓意画或许是达·芬奇的奇异幻想或个人喜好的表达,就好比肯尼斯·克拉克提出的画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侧面对比像是达·芬奇的一种喜好。[28]亚瑟·波普汉认为达·芬奇早年便有这种喜好,甚至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达·芬奇在一次又一次描绘年轻而美貌、年长而丑陋的面孔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29]年轻人与老年人是达·芬奇笔下不断出现的形象,贯穿着他的创作生涯。达·芬奇不断重复描绘的“双生人”很有可能是他想表达的“另一个自我”。达·芬奇看到萨莱的脸,便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萨莱的母亲名叫卡泰丽娜,和达·芬奇的母亲同名,这或许又加深了二者间的心理关联。[30]“另一个自我”由此成为达·芬奇的影子,也成为其创造力的源泉。
四、余论
关于《愉快和痛苦》这幅作品的创作目的,艺术史学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笔者只能试图从多个角度出发,尽可能地还原达·芬奇的创作意图。这幅画作无论是作为米兰宫廷庆典演出人员造型的草图,还是作为达·芬奇自己的“影子”,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独特的、带有寓意的“双生人”形象生动地彰显了达·芬奇异乎寻常的创造力。

注释
[1]卡罗·卫芥.达·芬奇传[M].李靖静,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43.
[2]肯尼斯·克拉克.成为达·芬奇:列奥纳多的艺术传记[M].李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91.
[3]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M].杨思梁,范景中,编选.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185.
[4]Leonardo,Thereza Wells,Irma A. Richter,Martin Kemp.Notebook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44.
[5]同注[3],186页。
[6]同注[4]。
[7]同注[4],244—245页。
[8]同注[4],233页。
[9]同注[5]。
[10]Leonardo Da Vinci,Edward McCurdy.The Notebooks of Leonardo Da Vinci[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2012:352.
[11]同注[5]。
[12]比亚洛斯托基,杨思梁,宋青青.图像志[J].新美术,1990(1):74.
[13]同注[3],253页。
[14]柏拉图.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M].杨绛,译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6-7.
[15]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M].姚鹏,陶建平,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42-53.
[16]沃尔特·艾萨克森.列奥纳多·达·芬奇传[M].汪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9.
[17]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1424—1504),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意大利语言学家、诗人。他主要评注古典作家的著作,并将他们的著作与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学说联系起来。
[18]卡罗·卫芥.达·芬奇传[M].李靖静,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52.
[19]伊索.伊索寓言 古希腊文、汉文对照[M].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9.
[20]伊索,伊索寓言[M].徐晓然,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37.
[21]柏拉图.会饮篇[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4.
[22]Martin Clayton.Leonardo Da Vinci :The Divine and the Grotesque[M].London:Royal Collection,2002:16.
[23]Michael W.Kwakkelstein.in Leonnardo da Vinci:The Language of Faces[M]. Bussum:THOTH Publishers,2018:35-36.
[24]Ernst H.Gombrich.The Heritage of Apelles: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1976:71-72.
[25]Martin Clayton.Leonardo Da Vinci: The Divine and The Grotesque[M].London:Royal Collection Enterprises Ltd,2002:54;E. Gombrich.in The Heritage of Apelles[M]. Oxford:Phaidon,1976:69-70.
[26]Alessandro Nova.Coming About:A Festschrift for John Shearman[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2001:381-386.
[27]同注[2]。
[28]Kenneth Clark,Carlo Pedretti.The Drawings of Leonardo da Vinci in the Collection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at Windsor Castle[M].London:Phaidon,1968-1969.
[29]同注[23],36页。
[30]Charles Nicholl.Leonardo Da Vinci:Flights of the Mind[M].New York:Viking Penguin,2004: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