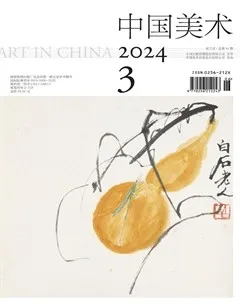关于当代中国美术批评的批评
摘要: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美术批评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美术批评存在着“失语”“失准”以及话语权丧失的问题。本文从美术批评本体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当代中国美术批评应该通过明确现实态度解决“失语”危机,在美术史视野中规范当代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借助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实现话语权的重塑。如此,美术批评“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担当和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关键词:美术批评 中国美术批评 话语权 艺术现实
200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艾金斯教授在著述中深刻剖析了美国美术批评的诡异现状。[1]当代美术批评的发展态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蓬勃,“它吸引了大量的写手,并得到高质量的彩色印刷和全球性的发行”[2]。不过,美术批评的声音和效力却“极为微弱,而且成了朝生暮死的文化批评背景上的喧闹”[3]。它变得没有什么生命力,成为一种“没有读者的写作”,陷入了普遍的衰落状态。
吊诡的是,蓬勃与衰落如今正并存于中国美术批评领域。中国理论家总结出了三种怪异的现象,即“西方术语的‘滥用’与中国批评的失语”“商业批评的鼓吹与价值标准的模糊”“网络批评的大肆兴起与专业批评的权威丧失”。这三种怪异现象的实质是中国美术批评面临着“失语”“失准”以及丧失权威的困境。如何据此找到突破困境、恢复话语权的方法成为当前更为紧要的任务。
一、“立时代之潮头”:以现实态度解决“失语”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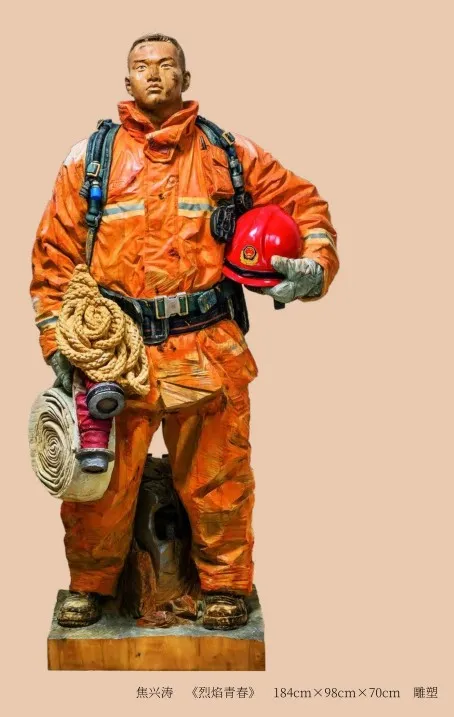
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批评深受西方影响。不过,通过借助西方理论体系,前者在获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愈加强烈的“免疫排斥”——西方理论的“不适用”现象开始凸显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经过几十年的理论交流与学习,国内学者对西方艺术理论及相关术语已经产生较强的依赖性。当这种“免疫排斥”发生之时,一时局促的理论家便会突然陷入“失语”危机之中。因此,有学者认为美术批评的“失语”、失信在于西方专业术语的滥用:“就批评话语而论,是以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阐释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用外来词语来描述中国的美术现状,是西方学术语的滥用,亦即‘中国文化的失语’、中国文化的缺位。”[4]这种观点并非孤例。同样有学者认为“中国艺术理论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术语均来源于西方,这些术语在进入中国后,往往又会在汉语文化的背景下、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从而总是处于一种难以被确切翻译与表述的‘流动性’状态”[5]。
可以说,这种对“滥用”的批评与反思为“失语症”找到了某种合理性。然而,究竟何为“滥用”?如今我国的科技、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也在关注着西方的实践进度和理论成果。通过不断加强中西方的学术交流和理论沟通,对我国实现科技成果创新、强化国家文化建设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为什么这些领域很少出现美术批评所面临的“滥用”危机?这其实牵涉到我们对西方术语之“滥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滥用”一词并非指西方术语被过多引用,而是指被无效引用。其无效性表现在脱离了中国当下的艺术潮流,丧失了批评功能,使美术批评既泛滥成灾,又被孤立于鲜活的创作之外。换言之,部分国内学者在了解西方艺术理论的过程中过分沉溺于哲学层面的理论思辨,固执于在批评实践中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从而出现生搬硬套、格式化批评等现象,最终造成了隔靴搔痒的结果,毫无批评效应。
在这种环境下,若要消除“失语”危机,必须培养批评家敏锐的审美能力与敢于批评、擅于批评的激情,使其增强对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关注,为大众而批评,为时代而批评。比如,殷双喜认为“没有批评的研究,就无法在浩瀚的史料中发现问题和艺术史演进的脉络。艺术史的研究没有扎实的批评和理论基础,只能是美术现象的剪辑和堆集”[6]。还有的学者认为美术批评“不仅包含了对同期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个人判断,还提供了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精神氛围,一种与当时的趣味密切相关的视觉上下文”[7]。这就要求批评家要以人民审美趣味为立足点,以作品的社会接受效应为着眼点,关注当下艺术创作的风格观念和价值解读。

为此,批评家既要深入了解相关艺术家及其创作活动,又要在时代语境中大胆地进行批评话语的构建。也就是说,一方面,美术批评必须深深扎根于特定的时代语境,以直白、天真的态度讲述作品。另一方面,批评家应该放开手脚,脱离开西方理论的束缚,在直面作品的过程中大胆的进行批评话语的建构。从历史角度来看,西方美术批评的经典范式无一不是建立在时代语境下的理论创新和话语构建。无论是18世纪以社会接受为中心的“公共言说”式批评,19世纪以作品价值解读为中心的“艺术家”式批评,还是20世纪以形式语言为中心的“形式批评”,均是由批评家针对创作现状提出某种审美主张,又经学术共同体不断巩固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结果。因此,只有扎根当下的艺术世界,大胆地进行话语构建,才能突破“失语”的困境,发挥美术批评“立时代之潮头”的社会担当。
二、“通古今之变化”:规范当代美术批评的价值标准
综上所述,当下的中国美术批评应该大胆建构,而这意味着需要确立一种价值标准。事实上,当前美术批评还存在另外一种极端现象,那就是“太敢说”。在部分学者看来,“我们本民族绘画传统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观念已不再提及,艺术研究的严肃性与纯粹性正在深受考验,代之而来的却是更多的无道德、无原则的空谈的理论家编造的伪理论话语,在空疏的‘理论’构建中,学术的庄严荡然无存”[8]。他们以功利的心态吹捧艺术家的作品,以鼓吹式的表扬抹杀了美术批评最重要的价值评判功能,丧失了批评家的独立性。
针对这一现象,学界将商业利益视为罪魁祸首。在大家看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却也降低了批评的纯度和准确度。为了获得丰厚的经济报酬,许多批评家热衷于参加各种展览的研讨会,利用“艺术表扬”,将批评变成一种服务型行业,帮助艺术家提高艺术品的知名度,提升艺术市场指数。在这种商业环境下,“艺术家做展览或者出版画册,批评家就拿文章去贺喜。红包批评、有偿批评大行其道……学术文章已深深打上了商品属性”[9]。正如杜大恺所言:“尤其‘孔方兄’的不期而至,更导致艺术批评的矮化,使艺术批评已完全没有尊严可言。”[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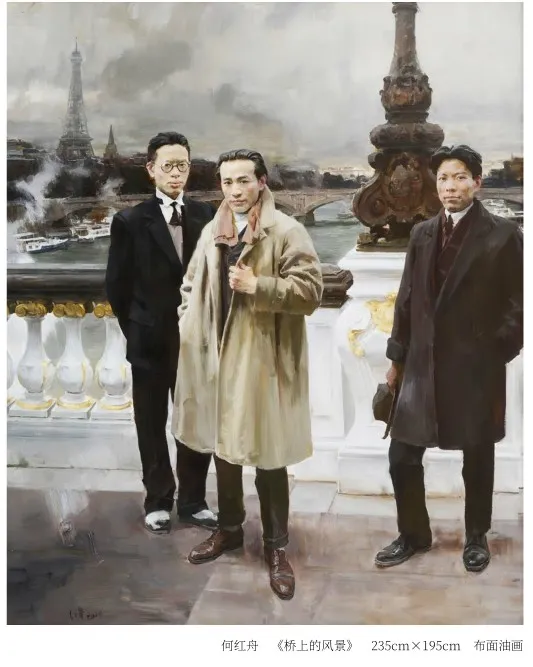
然而,商业真的应该承受这种严厉的指责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如今,我们似乎习惯于将学术与商业划清界限,以此来保证前者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似乎一旦沾染商业的“潜规则”,学术就无法保持“纯洁”。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担忧其实更像是一种“文人迷思”,并没有找到根本问题。事实上,古往今来的众多优秀艺术创作和史论文献都离不开商业因素的影响。对此,李铸晋和柯律格都进行过相关研究。李铸晋借助宏观的社会学视野,点明了画家与赞助人之间的交易行为,[11]重点分析了王世贞、恽寿平及周亮工等精通绘画评论并有著作传世的批评家。柯律格则在《雅债》中提到,李东阳曾因撰写一篇墓志铭而“收到丰厚的笔润”[12],他同时也认为文徵明的社会生活充满着“艺术交易的本质……与文人艺术家作为自发而不受拘束之创作者的理想化形象相悖”。正如李雪曼所提出的“‘人情’网络”一样,任何时代的美术创作和艺术批评都无可避免地夹杂着人情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的相关案例其实有很多都成功地彪炳青史。这不仅是对“商业原罪”的驳斥,而且指向了美术批评的价值标准问题。
商业文化的弥漫只是造成艺术批评空泛的导火索,价值标准的丧失才是造成此类困境的根本原因。“进入学术的前沿地带,批评界的老同事、老朋友也很难形成共识,价值判断往往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容易发生冲突,让外界产生一盘散沙的印象。”只有将批评的标准明确下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批评家们各行其是、南辕北辙的尴尬处境,才能在商业环境中坚守学术原则,发挥批评作用。
那么,艺术批评的价值标准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价值标准的重塑?对此,我们可以从艺术批评的本质问题切入探讨。艺术批评“旨在为艺术作品和艺术实践提供一种具有历史感的价值判断,这种历史感来源于对艺术史总体框架与发展脉络的把握”[13]。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成为艺术创作的“裁判员”,利用对艺术史的把握进行艺术品评和价值判断。这既是艺术批评的本质,又是它的重要使命。这种本质和使命要求批评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从艺术史的意义上考量其艺术价值”[14],毕竟“最大的谬误是区分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如果事实不被用于判断,则毫无价值,判断不基于事实则全然错误”[15]。纵观中国古代画论,无论是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对顾恺之“悟对通神”的落实,张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路标意义,还是龚贤“唯恐是画,是谓能画”的文人画批评,都是在美术史视野下对当前创作进行的价值判断。概言之,只有从美术史视野出发来建立批评标准、考量艺术价值,才能实现美术批评“通古今之变化”的历史作用。
三、“发思想之先声”:重塑美术批评的话语权
当前,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信息渠道的拓宽,激发了艺术批评界的创作热情。不过,前者的草根性也对学术批评的权威性起到严重的消解作用。有的学者对这种影响颇多顾虑,认为网络平台的门槛降低将导致美术批评“无处不在”,批评主体业余化,批评文章流俗化,最终使美术批评走向荒芜。[16]
然而,在笔者看来,新媒体的草根性与美术批评的权威性并不相悖。前者指的是新媒体信息交流的措辞特点,后者则是一种公信力。从某种角度来看,平易、通俗的交流方式恰恰是获得公信力的基础。就美术批评而言,其当下性、鲜活性等特点不仅要求美术批评直面作品,而且还决定了其必须与社会受众的接受效应形成互动,在赢得认可的同时获得话语权。换句话说,美术批评不同于理论研究,既不应该充满佶屈聱牙、空洞玄幻的措辞,也不应该在完成后便束之高阁,成为一种没有任何社会效应的存在。相反,它应该以“日常哲学”的姿态接近大众,成为大众审美接受的代言人和引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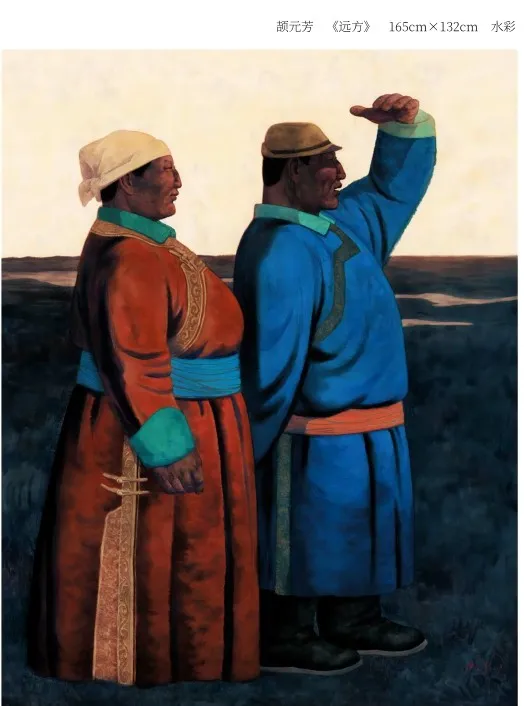
为了重塑美术批评的话语权,我们不仅要明确美术批评的现实态度和价值标准,还要建立一种受众面更广的批评途径,而新媒体的兴起便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伴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无论是拥有庞大粉丝基数的美术网站、专业的艺术App还是微信公众号,批评文章时时更新,点击量节节攀高,这为批评家感受社会效应提供了全新的机会,也为社会效应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场域。在新的场域中,美术批评可以面对并争取前所未有的大量观众,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参与其生活,由此获得大众的认可,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确保话语权时时“在场”。
新媒体平台美术批评的业余化和流俗化问题又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此类问题的出现在于批评主体的泛化,毕竟其意味着不同层次的艺术爱好者皆可在网络媒体中发表言论。由于这些批评主体缺乏立足现实的使命意识,不能在美术史视野中自觉规范批评的价值标准,往往输出的都是泛泛之谈。为了避免这种泛泛之谈对专业批评产生消解,批评家应该在新媒体平台上自觉营造一种积极的批评原则,身体力行地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这里的“理”即美术史之理,“物”即当下创作之物。如此,才能既避免美术批评的流俗化,又使得话语权在受众面更广的传播平台得到重塑,从而实现“发思想之先声”的时代目标。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美术批评之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从各个角度指出了美术批评的困境之所在。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美术批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滥用”西方专业术语而导致陷入“失语”困境,同时因追逐商业利益而使“艺术表扬”成为服务型行业,又因网络平台的草根化导致了话语权的丧失。笔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西方术语、商业利益以及网络平台并非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还是美术批评的价值标准并未严格确立下来,批评主体脱离了当下的创作现实。我们应该以现实态度解决这种“失语”困境,在美术史视野下规范当代批评的价值标准,继而借助新媒体来重塑美术批评的话语权,这样才能使中国美术批评“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注释
[1]詹姆斯·艾金斯,陈蕾.一种对当代艺术批评的批评[J].东方艺术,2009(11):106-115.
[2]同注[1]。
[3]同注[1]。
[4]薛永年.美术批评失语失信[N].美术报,2012-04-14.
[5]庞弘.艺术理论的当代使命与发展方向——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理论高层论坛”会议综述[J].艺术百家,2013(1):120.
[6]殷双喜,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文选[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7.
[7]杨小彦.篡图:杨小彦艺术批评文集[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404.
[8]尹沧海.艺术的纯度与批评的深度[N].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2019-08-28.
[9]周明聪.国内美术界现怪象:红包批评泛滥[N].江西日报,2014-12-05.
[10]杜大恺.艺术批评的失语[N].光明日报,2011-12-02.
[11]李铸晋.中国画家与赞助人[M].石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12]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M].刘宇珍,邱士华,胡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5.
[13]郑梓煜.艺术批评何以进入历史[J].美术研究,2018(4):99.
[14]李磊.商业环境中对当代艺术批评的思考[J].西北美术,2016(2):16.
[15]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M].邵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7.
[16]刘涵.当代艺术批评现状的反思[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