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认知:语言人类学中的未知

“一部电梯落入大气层上空,经过一个升入外太空的热气球,两者超越一个世纪的时间相望,共同构筑了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理解具身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和语言的温床……”这是笔者的好朋友、多伦多都会大学的符号学教授雅明·佩尔基(Jamin Pelkey)关于认知语言学的文章的开篇。这句话提及了爱因斯坦的电梯思想实验,佩尔基引用了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说的话:“我想知道的是,当电梯落入虚空的时候,电梯中的乘客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化用了美国歌手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 Williams)轻快的流行歌《快乐》中第一段的歌词:“我想要说的听起来也许很疯狂。阳光,她在这里,你可以休息一下。我是一个可以去太空的热气球。”
这个开篇不要太酷了!更酷的是佩尔基近十年来的研究,他尝试对语言演化和语言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方面做出综述,并极大推动了对具身认知的探索。他把他的研究主要归结在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内,然而他的作品在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符号学和认知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认知科学、哲学、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仍然在“心智-身体”二元的框架内探索个体认知、个体语言习得和整体语言演化。也就是说,这些智识过程基本上都交给了“心智”。然而佩尔基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具身知识的思考和研究,想要打破二元论的垄断。
那么为什么佩尔基认为他的研究应该归结在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内呢?我们来看看认知语言学对语言本身和语言演化的理解。首先,认知语言学家们不认为语言就只是说出口的带象征性的展演过程(对应语言学中的“言辞”和“口头交流”概念)。语言这些可观察的、基于使用的方面对了解其本质和语言作为现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但语言同样参与了不直接以交流为导向的活动,例如思考、计划、推理、想象、梦想、疑虑和思考等活动。认知语言学家们同样不会把语言和语言结构(如词语、短语、句法、文法等等)混为一谈。对他们来说,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是由语言意义TgjdJ84CLdF/lDvJItdQjQ==驱动和调节的。而语言意义主要的且更普遍的是经验性的,或者说是具身性(embodiment)的。
佩尔基本身有很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和神学修为。出于对庄子的兴趣,他曾经在中国做过十年少数民族语言学田野调查,同时学习汉语文学。他在研究中分析过大量中国古代文学和修辞学作品,当然他涉猎更多的是现代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作品。然而他的理论框架非常艰深,大部分读者会看得云里雾里。所以我们可以用相对简单的例子浅尝他的思路,来看看他是怎样分析上面提到的歌词和电梯思想实验故事的。
在《快乐》这首歌词中,太阳(歌词中以阳光转喻)位于叙述者和观众的上方,而在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中,电梯正在坠入虚空。对这两种情形的描述如果要对听众产生意义,涉及空间位置的“上-下”关系,而它们共同构筑的垂直性这一概念的共享经验基础也是必要的。至于歌词中的“她”(无论是谁),她刚刚从某个地方到达了一个想象的目的地或目标。假定有一个源位置和一个中间移动路径。更重要的是,她来到这里,带出了“近”和“远”的位移区别。至于爱因斯坦的电梯,里面有一群乘客,而电梯本身却掉进了虚空,这不仅带出了“源位置-路径-目标”的相对关系,而且带出了“里-外”的关系及它们共同构筑的容积空间的想象。这些经验/空间关系在认知语言学中被称为“图像图式”。
与图像图式相反,模仿图式是身体记忆的模式,更明显地面向动作、活动和事件,例如吃、爬、跳、坐、站立、接吻和跌倒。虽然认知语言学中的所有图式都是交互导向的,但模仿图式应被视为动态的、具体的和前语言的表征,涉及身体意象。就个体发育而言,模仿图式可以说比图像图式更基础,因为站立、坐、攀爬和跳跃等活动对于形成更抽象的身体记忆(如垂直性)是必要的。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以上图式构筑的概念以动觉、感官体验为基础,这些概念具有有意义的结构并相互关联,包括知觉级别和身体记忆图式,这些结合起来为认知模型提供信息。而具身认知模型被影射到我们共同努力理解世界的更抽象的思维、交流和模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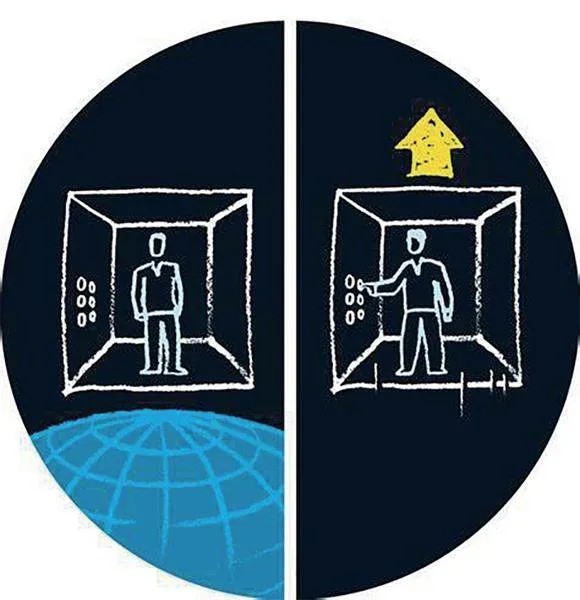
最后我们可以引用佩尔基分析过的一些具体的例子来看看他怎样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对语言人类学关注的群体语言演化以及个体语言意识形态做一些分析:在许多语言中,基于身体的关联与认知比英语更有效、更系统。例如,在西阿帕奇(美国原住民部族)语中,对汽车的认识是在三个层次上构建的,包括“身体”(所有通用部件)、“面部”(包括引擎盖和挡风玻璃)和“内部结构”(包括挡风玻璃后的一切);引擎盖是汽车的“鼻子”,挡风玻璃是汽车的“前额”,前灯是“眼睛”,前轮是“手臂/手”,后轮是“腿/脚”,电线是“静脉”,电池作为“肝脏”,油箱作为“胃”,等等。类似的具象化的类比投射在萨波特克语和采尔塔尔语等中美洲语言中甚至更加系统化,其中基于形状和基于矢量的身体部位被用来理解物体之间的所有“部分-整体”关系。在萨波特克语中,“头”影射所有上部覆盖物,例如盒子的盖子、房子的屋顶和锅盖,而“嘴”影射所有物体的开口,例如盒子、锅口或家门。相比之下,在采尔塔尔语中,“嘴”影射除了这些开口的边缘和边界之外的所有开口,同时也延伸到没有任何开口的边缘和边界;其他身体部分名称被影射到广泛的面向矢量的现象上,例如“鼻子”,它被影射到所有的突出物上,从种子芽和叶尖到乳房乳头和刀尖。这种由身体的直接经验构筑的语言使用中的隐喻,能更清楚地带我们看到上面所说的图式和其标记的关系。
时间和空间看起来都很抽象,但我们在空间中移动的第一手经验自然会让它们更容易被认知。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通过移动主动创造了空间。被广泛讨论的“时空连续体”(space-time continuum)就是上述两种图式构筑的概念隐喻的例子:也就是说,时间就是空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时间的进展就是空间的运动。与大多数语言一样,英语中的时间概念必然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过去和未来同样抽象,因为我们都无法直接体验。相反,我们依靠空间关系来帮助我们理解两者。但这些方面在不同的语言中以不同的方式映射到空间关系上。即使使用相同语言的人只是在思考,而不是在交流时间,也可以通过依赖不同的概念隐喻来对它们进行不同的理解。虽然很多种语言(包括英语)认为未来位于自我前面,过去位于后面,但至少在历史上,有使用其他语言(例如中文彝语或傈僳语)的人认为过去位于自我前面,未来则在背后。

 Pvcse5MZ79g1b6VZHlUh5trg/XZMouUexNiGSEtMqRA=
Pvcse5MZ79g1b6VZHlUh5trg/XZMouUexNiGSEtMqRA=具身认知目前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范畴,远远没到可以形成系统学科的程度。但佩尔基认为认知语言学的探索足以有力挑战“心智-身体”二元论这一统御了西方认知、哲学和语言学研究几个世纪的范畴。我们不妨乘上快乐的热气球,跟随佩尔基,像爱因斯坦曾经遨游太空那样遨游我们每个人身体内混沌的认知海洋。
(责编:刘婕)
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
一种认知理论,认为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其多数认知特征是由生物体全身的各方面塑造而成。大部分认知理论和认知相关的哲学理论着重讨论通过语言和文字传递的认知过程。但具身认知理论注重涵盖具身体验(包括运动和知觉,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心理过程和对生物体结构与认知过程的互文的探索。这个领域的学者们指出,身体运动在个体发展或总体演化过程中都是先于神经系统构架的,所以现象学经验在具身认知的研究中理应被置于优先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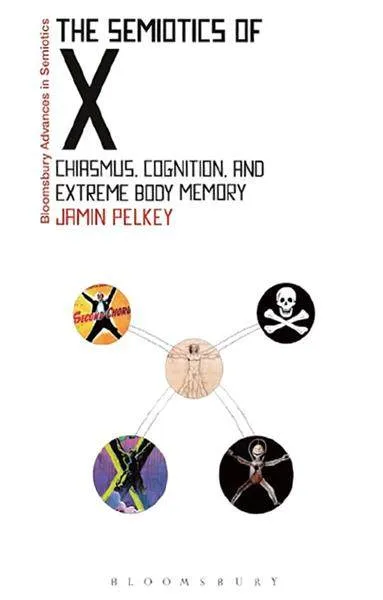
雅明·佩尔基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他的书《关于X的符号学》。书中有大量关于身体对称性如何影响了认知过程的讨论。另外他关于老子的符号学讨论以及关于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Dylon Thomas)诗歌对称性结构的分析都让他的思想备受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