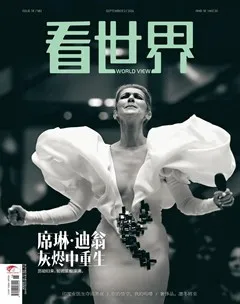奥斯曼的奴隶制比起欧美更“人道”?

许多来自非洲的黑奴被阉割后成为太监;高加索地区的白人成为富人的妾或皇宫的侍女、嫔妃。
在近现代黑奴贩运的历史研究中,欧洲帝国主义的行径固然是焦点,但关注这一主题的人也必定会注意到,西亚北非的黑奴贩运也与欧美的大西洋贩运同时发生着。例如,19世纪末,东非就有无数黑奴被阿拉伯裔奴隶贩子所掠,被送至桑给巴尔岛的种植园,还有更远的伊朗、阿拉伯半岛等地区。这一东非路线与跨撒哈拉路线、红海路线等,一起构成了黑奴被输送到西亚北非地区的主要管道。
进入21世纪的当代社会脉络里,黑人在西亚北非社会的处境也仍是受关注的议题。例如,在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上,许多斋戒月期间的热播电视剧总有贬损或嘲笑黑人的桥段;在北非国家,黑奴后裔或新移民仍长期属于底层劳动力;在西亚的卡塔尔主办世界杯期间,黑人移工受剥削的苦境受到批评与广泛报道;在土耳其,去年受关注的新闻是卡拉毕克大学的一名加蓬女留学生遭性侵杀害,后来网络出现大量污名黑人留学生的仇恨言论,警方拘捕了发表言论的网民,性侵嫌犯也被捕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许多因素使得探讨西亚北非地区的种族歧视及奴隶制议题并不容易。首先,这一地区本身也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其次,欧美针对当地奴隶制传统的呈现(从早期的油画、当代的好莱坞电影到今日媒体的报道),往往给西亚北非地区加上野蛮落后或异国猎奇的滤镜,这转移了对欧洲自身行径的批判,也忽略欧洲与西亚北非的种族歧视或许有重叠、混合及交互影响之处。
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涵盖西亚、北非及巴尔干地区达300年之久,因此黑奴后裔很多是奥斯曼时期的后代。虽说奴隶制是建立于掠夺、贬抑与控制上,但帝国时期的奴隶也有许多可以进入政府高层的例子。研究者既不应像有些辩护者只主张奥斯曼的奴隶制比起欧美更“人道”,从而贬低奴隶所受的苦难,也不能把奥斯曼的奴隶制想象成新大陆种植园中的残酷景象。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当时的奴隶制?
理解任何社会的关键在于,了解该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新大陆殖民地的种植园与矿山是被拓殖者利益驱动的榨取型项目,奴隶劳动力服务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被残酷对待。但奥斯曼帝国是由政治军事集团构建起来的体系,治下的各种族裔群体类似于被控制的资产,许多来自非洲的黑奴被阉割后成为苏丹后宫的太监;高加索地区的白人成为富人的妾或皇宫的侍女、嫔妃;巴尔干的儿童则被强制带离家庭接受帝国的训练。在这种体系中,奴隶旨在完成指定的职能,可以凭着功绩升到高位,但同时被确保不造成威胁。依据《古兰经》及《圣训》中关于释放奴隶的规定,奴隶在一定年限或支付足够金额后可以成为自由民。
以上的描述,或许可以比较清楚地帮读者理解奥斯曼奴隶的处境(至少在帝国核心区域):通常奴隶是在军事征伐或贫穷困苦的情况下沦为奴隶,受到族裔与肤色的限制,而且可能遭遇阉割、性剥削、带离原生家庭、强制劳动等伤害,但同时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
而当代西亚北非国家雇主束缚移工自由的方式,既有服务企业的利润动机,从安排外来劳动力从事特定职能的方式,亦可看见奴隶制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