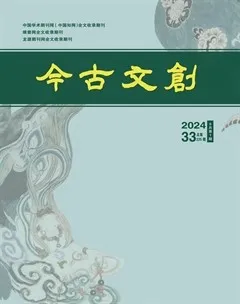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摘要】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持。本文以乔治·斯坦纳提出的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为框架,对《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挖掘和分析,旨在丰富阐释运作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四步骤;译者主体性;《许三观卖血记》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10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30
在传统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地位和主体性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人们普遍认为译者应忠实于原文,将原文作者摆在首位。译者仅被当作转换语言的桥梁,其主体性无人重视,因此译者的身份也一直被视为是“戴着镣铐的舞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思潮,译者才开始逐渐从翻译活动的边缘地位走向中心。自此以后,译者的主体性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引领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随着译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从各种理论视角对译者主体性展开深入研究。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构建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是一个极具研究意义的角度,本文将在此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研究《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以期为阐释学的实践运用和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一、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
阐释学(Hermeneutics)也称为诠释学、解释学。阐释学理论关注的是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研究发现了阐释学和翻译之间的相通之处,并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详细阐述了阐释学与翻译的特征与联系,其核心观点是“理解即翻译”,并提出了重要的“翻译四步骤”[1],他把翻译过程分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
信任是翻译的第一步,是进行一切翻译活动的基础。翻译始于译者对译本的信任和选择,而信任和选择又源于译者对原文本的评价和认识,译者需要相信原文有意义,并对文本进行深度分析[2]。这种信任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信念感,就是译者不仅要对原文的可译性持有充分的信任,还要认为所选择的文本是值得翻译并且值得让读者观看的。
侵入作为第二个步骤,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主要指的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由于译入语和译出语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两种语言,译者在理解过程中势必会与源语言文化产生冲突和碰撞,正如斯坦纳认为翻译的过程是一种接近和挪用原文意义的行为,因此翻译活动中的理解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侵入模式[3]。面对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以及语言背后各自代表的社会习俗、文化习惯和历史背景等,尽管译者尽量突破以上诸多语言文化的局限,但在深入理解原文时依旧会受自身经验和文化认知的影响,从而导致在翻译时以译入语的角度对原文产生“进攻”行为。因此,斯坦纳将这一步称为“侵入”,是对原文的“侵占和发掘”[1]。
翻译的第三步是吸收。吸收是在侵入的基础上进行的,译者需充分吸收原文的意义和形式,并且为在此前侵入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赋予新的内涵和活力,将它们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给目标语读者。根据不同译者的知识水平和采取的各种翻译策略,吸收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
补偿是翻译的最后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斯坦纳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侵入和吸收过程难免会造成原文含义的缺失,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无法避免地会造成原文与译文的不平衡,而翻译又要尽可能表达出原文的全部含义,补偿这一步骤可以弥补缺失的部分[4]。补偿作为翻译过程的收尾工作,译者可以发挥自身的主体性,通过采用添加注释、增译等手段,来弥补翻译过程中意义或内容的流失,以达到使译文保持平衡和为读者带来完整的高质量译文这一目标。
二、译者主体性
文学作品与科技文本、商务文本的最大不同就是情感的掺杂与体现,因此,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中能够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发挥。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尤其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根据自身对原文的理解和双语掌握程度,将作品转换为目标语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具有译者独特的翻译风格及语言风格,从而彰显译者的主体性。但是主体性并不能随意发挥,也会受到一定因素的限制,如原文的写作风格、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译者需要在尊重原文写作风格及思想情感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翻译经验及多种翻译策略,在翻译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
三、《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分析
(一)信任
在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中,信任是翻译的首要前提。译者不仅要对原文抱有充分的信任,也要有对自身文化和语言能力有信心。《许三观卖血记》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许三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背景下努力生存的故事。作者以一种温情、朴实的笔锋,描绘出那个年代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艰难生存状态和对抗苦难的不屈精神。虽然作品展示了种种人生的苦难,却也让读者体会到平凡人面对不幸与挫折时的顽强精神和对家人的无私奉献。该作品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占有一席之地,也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读者青睐。译者安德鲁·琼斯出于对此作品的欣赏,体会到书中想要传达的深刻含义以及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反思,从而认为这本书是值得翻译的,对原文产生了信任。因此,选择把这部小说翻译成英语。
(二)侵入
在译者完成信任的建立之后,翻译过程便进行到了第二步“侵入”。在这一环节,译者还充当着读者的身份,要有自身对原著的理解和把握。译者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各种文学才能,包括情感、审美、想象力等,才能将源语文本生动地传递给读者[6]。在此步骤中,译者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加入自身对原文的解读和分析,两种语言和思想发生冲突,这正是一种目标语对源语言的侵入。
例1:“你爹来对我说,说他到年纪了,他要到城里去和那个什么花结婚,我说你两个哥哥都还没有结婚,大的没有把女人娶回家,先让小的去娶,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
译文: “Your dad said he was old enough.He told
me he wanted to go into town and marry some ‘flower’ or other.I said, ‘Your two older brothers haven’t gotten married yet.’If the eldest hasn’t even gotten married yet,how could I let the youngest go ahead and take a wife before him?Around here,that’s not how you play by the rules.”
这句话是许三观年迈的爷爷所说,译者将这一长句进行断句处理,分成三个独立的句子,使句子逻辑更加清晰有条理,也更加通顺易读。“到年纪了”在中文里是一种比较口语化的说法,译者选择使用归化的策略,将其译为“old enough”这一表语成分,含义贴切。再看“把女人娶回家”和“没有这规矩”这两个短语,在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中,没有与“嫁”“娶”完全相对应的词语,无论男女,皆用“marry”来表示;而“规矩”在原文这一段中指的是礼法、成规。因此,译者同样采取了归化策略,将这两个短语直接译为“take a wife”和“that’s not how you play by the rules”,把它们以常见的英语表达方式呈现出来,以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语言模式。
例2:油条西施,也就是许玉兰,有一次和一个名叫何小勇的年轻男子一起走过了两条街,两个人有说有笑,后来在一座木桥上,两个人站了很长时间,从夕阳西下一直站到黑夜来临。
译文: One day Xu Yulan,the Fried Dough Queen,
walked a few blocks with a young man called He Xiaoyong.They talked and laughed,and later they stood by the railing of a wooden bridge until the sun started to set and night had nearly fallen.
原文写到许玉兰被人称为“油条西施”,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人们常用其来形容女子的温婉美丽,并且由于油条也是中国独有美食,因此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词汇来翻译这一短语,译者便选择发挥创造性,将“油条西施”译为“Fried Dough Queen”。然而“Queen”在英语里主要指的是“女王”“王后”等地位崇高的女子,与原文想表达出女子之美貌的目的并不贴合,这样的“侵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译者自身理解和语言文化导致的,使读者无法确切获取原文的真正意义。
(三)吸收
这一步的核心实则是把原文的意义与风格吸收到译文中。译者不仅要把从原文中提取的信息,选取相对应的词汇,以译入语的形式表达出来,还要做到让译入语读者能接受。
例3:许三观在里屋咬牙切齿,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又笨又蠢,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这个女人只要往门槛上一坐,什么丑事都会被喊出去。
译文:Xu Sanguan stood inside the door gnashing his teeth in frustration.This woman,he was thinking to himself,is a stupid fool.You’re not supposed to air your dirty laundry,and here she is sitting on the doorstep crying for the whole world to hear,and there’s no telling what kind of idiocy she’ll come up with next.
“咬牙切齿”这一成语在中文里用来形容竭力抑制某种情绪,原文中作者用其来描述许三观正竭力忍耐他的妻子许玉兰的大声哭喊。译者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段,将这一成语按其代表的意思译成“gnashing his teeth in frustration”,并增以“frustration”来表明懊恼的情绪,准确表达了应有的含义,同时避免了给本土读者阅读时造成障碍。除此以外,原文中提到的“家丑不可外扬”,也属于中国文化里常用的成语,指家庭内部不体面的事情不应向外人宣扬,译者发挥能动性,以归化的方式将其译为“air your dirty laundry”,属于英语里对应“家丑不可外扬”的特定表达,因为在译者的本土社会文化中,把脏衣服晾在外面视为一件不体面的行为,这一译法可谓巧妙,完美“吸收”了原文的信息,又符合译入语读者平时的语言习惯。
例4:“当然是以前,”许三观说,“你想想,我做了九年的乌龟,我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我再替他把你儿子住医院的钱出了,我就是做乌龟王了。”
译文: “Of course,it was before,”Xu Sanguan said.
“Think it over.I’ve been cuckolded for nine years now.And I’ve taken care of his son for nine years despite all that.If I were to pay the hospital bill for your son in addition to everything else,then I’d really be the king of cuckolds.”
原文里,作者用“乌龟”一词来暗指许三观的妻子有外遇。译者显然理解了“乌龟”想要指代的意义,但是在英语中难以找到意思能够准确对应的意象,因此,译者依旧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选用了“cuckold”,意为使(丈夫)戴绿帽子,词义精准明了且符合原文的语言风格,并与原文达成意义上的对等。
(四)补偿
“补偿”作为翻译过程的最后一步,有着两层含义:一是从语言的角度,使原文语言、风格、句法、习语等不可译因素,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二是通过翻译增强原文文本的力量和影响[7]。也就是说,“补偿”实则担负着查漏补缺的重任。
例5:他会看上林芬芳,那个辫子垂到了腰上的姑娘,笑起来牙齿又白又整齐,还有酒窝,她一双大眼睛要是能让他看上一辈子,许三观心想自己就会舒服一辈子。
译文:Then he would choose Lin Fenfang,the girl
with the braids that dangled down to her waist,the girl whose smile revealed a row of straight,white teeth and a pair of dimples,because he figured that he would never tire of looking at her,even for a lifetime.
在例5中,也可看到译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中文是动态性语言,而英语是静态性语言。译者将“笑起来”这一动作译为静态的名词“smile”,并采用增译的方法,增加了动词“reveal”来彰显林芬芳笑起来牙齿的白和整齐这一特点,使原文的句法以这种形式得到补偿。此外,译者运用正义反译的翻译技巧,把“舒服”译为“never tire of”,把原文里的肯定说法变成译文中的否定说法以达到忠实于原文的目的,同时增加连词“because”,补偿译文语句的逻辑性和连贯性,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
例6: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译文: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karma.You get what you deserve.
译者在翻译这句话时对其进行了意译处理,并且用了佛教里意为因果报应的单词“karma”,同时加了“You get what you deserve”,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活该”,以此来详细地解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一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习语,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征,又体现了译者为达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信息平衡,所做的努力和发挥能动性来进行“补偿”的积极措施。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建立在原作者、译者、读者等多方联系的基础上的活动,是一个寻求各层面动态平衡的过程。显然,译者在此过程里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本研究便以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为理论指导,从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方面展开,对《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进行了具体分析,寻找译者主体性的痕迹。研究发现,译者首先建立对原著的信任,接着以自身文化认知和理解能力去提取原文信息,在翻译时发挥主体性,以西方文化“侵入”汉语,然后运用归化、异化等多种翻译策略,吸收原文风格和意义,并在最后采用增译等方法对原文流失的信息和内容进行补偿。
在翻译过程中,尽管受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译者积极地对原文进行深入理解,运用多种翻译手段去克服困难并发挥译者主体性,为目标语读者译出了一部优秀的著作。同时,本文从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展开研究,也是希冀能够拓展阐释学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增强对译者主体性这一课题的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Steiner G.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Third edition.New York:Open Road Media,2013.
[2]王泽康.阐释理论指导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袁昌英译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dge为例[J].海外英语,2023,(20):39-41.
[3]宋晓容.阐释学视域下杨必《名利场》汉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J].今古文创,2024,(02):107-109.
[4]刘中阳,彭潍坊.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观分析《青木川》英文译本[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19):173-177.
[5]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21-26.
[6]徐国祥.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以李继宏译《追风筝的人》为例[J].今古文创,2023,(40):108-110.
[7]刘志军.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1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