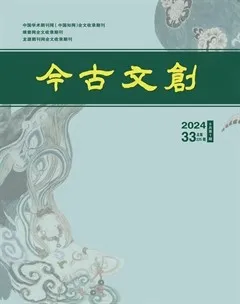明代江南舟船犯罪研究
【摘要】明代江南水路交通发达,舟船犯罪频发。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舟船犯罪,主要分为谋财害命、诈骗盗窃、拐带人口三种类型。舟船空间狭小封闭,行船过程中管控难度大,水上交通来去无痕,这些特点导致舟船犯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难以及时侦破。针对舟船犯罪问题,明人总结出了慎雇舟船、结伴而行、言行谨慎、照看货物、防范船户等经验,并倾向于对船户这一职业进行负面评价。
【关键词】明代;江南;犯罪;船户;水路交通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75-06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23
明代江南地区(本文“江南”指南直隶、浙江一带)整体上呈现出河流纵横、水网密布的水文特征。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时期的江南水路交通相对发达,商业贸易较为繁荣。由于桥梁建造技术的限制,人力船只仍然是主要的渡河方式。舟船这一水上交通工具,既为人员流动、商品贸易提供了便利,也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特殊场所。本文研究的“舟船犯罪”,指的是罪犯利用舟船交通工具实施的犯罪。
学界在明代水路交通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漕运、航道、造船业等方面。现有的明代船户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于船户生计问题和政府对船户的管理,近年学界也关注到船户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但就水路交通中的犯罪问题而言,学界多着眼于有一定规模的水上盗贼或船户本身的犯罪,对非船户身份的罪犯利用舟船实施犯罪的情况研究较少,对江南地区的舟船犯罪鲜有针对性研究。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相关文献中的案例,对明代江南舟船犯罪的各种类型进行研究。其中不仅包含船户犯罪,也包含非船户的犯罪。同时,本文也将尝试探究江南地区舟船犯罪的特点及原因,以期有助于这方面的深入探讨。
一、犯罪类型
舟船犯罪指罪犯利用舟船交通工具实施的犯罪,包括以舟船为犯罪空间或以舟船为逃窜工具的犯罪活动。明代判牍及笔记小说记载了不少江南地区的舟船犯罪案例。根据具体罪名,可以将这些案例分为谋财害命、诈骗盗窃、拐带人口三类。
(一)谋财害命
谋杀、抢劫是舟船犯罪中常见的犯罪类型。罪犯以获取财物为目的,或抢劫自己船上的乘客,或抢劫其他船只。罪犯劫财后,为了防止受害人上岸报官,常将其推入水中淹死,或在船上将其杀害后抛尸河湖。
崇祯年间刊行的《新镌官板律例临民宝镜》列出了“稍公害命”“水手谋命”两个典型判例。“稍公害命”案中,艄公“驾扁舟而载货,贪财害客,用谋劫以肥家”[14]177,夜晚将乘客主仆二人灌醉后丢入江中淹死,将其货物占为己有。案发后,凶手被处斩。“水手谋命”案中,艄公、水手与牙侩合谋,将乘客引入其船,然后以讨赏钱为借口窥探乘客囊中钱财,半夜将船驶至僻静无人处,杀死乘客主仆,将其尸体丢入水中,最后“装至芜湖,牙侩知而分赃”[14]177。案发后,凶手均被处斩,并枭首示众。书中收录这两个判例,供地方官员判案时参考,反映出当时船户抢劫、谋杀乘客已经成为一类社会问题。
明代江南地区常以舟船运输货物,船户杀人越货的案例,在这一时期的法律文献中并不少见。李清《折狱新语》记载,宁波府船户汤见将船只给孙庆等人驾驶,导致“庆等恣行劫杀”[15]703,判决时孙庆已死,汤见被判处杖刑。毛一鹭《云间谳略》记载,松江府船户王成、沈德二人合伙抢劫乘客陆佩,“手持刀斧,打伤破面”[16]539,被巡逻士兵发现并抓捕,二人最终被处斩。案件发生在白天,且在士兵巡逻范围内,因此受害者能够得到救援。
然而,一些船户的犯罪手段更加高明,乘客往往无法像陆佩那样保住性命。凶手“稍船僻处,豫备人知肆恶;更阑操刀,杀主仆于非命;行凶夜半,丢尸灭踪迹于江湖”[14]177,选择夜晚在僻静处行凶,避免被人察觉,行凶后快速抛尸离开,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当船上有凶手和受害者之外的第三方时,有的船户会下船行凶,防止作案过程被第三方直接目击。例如船户丘二、鲍二见乘客毕时选携带大量白银乘船,便假意为他提供酒菜,将其灌醉。因船上还有其他乘客,丘、鲍二人选择半夜靠岸,送毕时选下船,然后尾随上岸,在僻静处将毕时选勒死,夺其财物。同船证人只看到“时选挈囊先行,而二等比肩尾后”[15]683-689,认为毕时选已经喝醉,船户需要上岸送客,所以并未怀疑。
拦截其他船只进行抢劫、勒索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例如宁波府沿海地区一伙强盗,将船埋伏在韭山列岛附近,一见渔船便“张弓叩刃,呼风尾后”[15]699,跟踪并拦截渔民蔡来源、蔡国京等十人的渔船,杀害蔡来源等九人,并扣押蔡国京为奴。另一案中,余姚县沈其禄、沈小舟等四人自恃熟悉当地环境,在水势险急的姚江下坝拦截过往船只,“遂假下坝为奇货,而肆行横索;大舟或以一二钱计,小舟或以二三分计”[15]618,行经此地者不敢多作停留,只能听凭其勒索钱财。
(二)诈骗盗窃
比起谋杀、抢劫等恶性犯罪,舟船中更常见的犯罪类型是诈骗和盗窃财物。骗子和窃贼往往伪装成普通乘客上船作案,作案后就近上岸逃窜。
用铁、锡制成的假银掉包真银,是明代社会常见的骗术。“审得高某……熔铁煽铁做造假银,博与棍徒使用。此不市之物,千万物市之也;不独祸一人,千万人祸之也。合行毁炉绝火……依律杖警,断绝将来。”[14]266为避免被受害者发现,一些骗子利用舟船不稳定的空间进行诈骗。《杜骗新书》中《换银骗》一类,以《成锭假银换真银》《道士船中换转金》两个事例,分别揭露了以锡冒充银、以铜冒充金的骗术。骗子都在船中实施诈骗,受害者发现被骗时,骗子已经不知去向。《成锭假银换真银》中,骗子汪兰伪装成普通乘客上船,盯上从铅山乘船去南京买布的客商孙滔,于是诈称自己是孙滔同乡,去芜湖买货。获取信任后,汪兰借口换银,施展掉包计将假银换给对方,然后“须臾起岸分别”[17]16。孙滔毫不怀疑,直到抵达南京,打开行李检查,才发现被骗。《道士船中换转金》中,南京老棍假扮道士乘船,“故提及辨珠玉宝贝之法,诸人闲谈一番。又说到辨金上去,道他更辨得真”[17]17,引诱贲监生将足色金交给他鉴定,借机掉包成铜。此时天色渐暗,又在船中,假道士掉包后,贲监生并未仔细检查,便将假金收起。假道士次日离船上岸,而贲监生一路上不曾察觉,回家后才发现被骗。
船舱空间相对狭小,乘客所携财物易被窃贼窥探。例如鄞县人王昌义在舟山乘船,被窃贼方一偷走银二两、银簪一支。方一原为绍兴卫军舍,有偷窃前科,此时假扮成士人,“口称相公,而高巾盛服,巍巍然踞坐于中舱内”[15]669,随身携带一管箫,以体面的形象骗取同船乘客的信任。于是王昌义放松警惕,中途上岸买饭,将慎袋留在舱内。方一趁机割袋窃银,然后“掷巾解服,踉跄惊走”[15]669,改变装束后迅速离开。方一的作案手法已经为官府所知,且其在言谈间透露真姓,因此捕吏得以将其逮捕归案。若窃贼借助舟船流窜到更远处作案,侦破难度则将大大增加。
船舱是人员流动性较强的公共空间,舱内人员萍水相逢,来去无常,彼此底细一概无从知晓。乘客难防范,罪犯易得手、易逃窜,导致此类案件多发,且报官后难以侦破。
(三)拐带人口
舟船行于水上,过处无痕,来去踪迹不明,因此常常成为拐带妇女的工具。例如松江府无赖顾昌、顾文兄弟买一小舟,半夜破门强抢妇女到舟中强奸,并准备用舟将其挟往藏匿之所。[16]544-545苏州府赌徒国延纪因负债累累,欲将母亲邓氏卖给广东富商蔡天寿做妾,便“诈称母为妻,欲嫁以偿债”[17]102;又怕母亲得知后向舅舅求助,于是与蔡天寿秘密商定“叫人送到船来,人与银两相交付”[17]102,对母亲“诈称母舅家接母”[17]102,骗其上船。一旦开船,邓氏就无法逃脱。幸运的是,她在船离岸前发现真相,借口回母家取衣服首饰,得以脱身。
江南地区的拐子为避人耳目,也会用舟船藏匿拐来的儿童。例如浙江一伙拐子,专门拐骗十岁左右的儿童,或卖为娼妓,或将其致残后强迫乞讨。拐子为了敛财享乐,用冻饿、殴打等手段强迫儿童完成每日行乞指标。“驱此双瞽者、拐脚者,叫乞于道,每日责其丐钱米。多者与之饱食,少者痛酷捶打,令乞者方肯哀丐。晚复聚宿舟中。棍得其钱米,置美衣美食,在舟中歌唱为乐。暇或登岸,又四出拐带,极为民害,而人不知。”[17]132这一团伙以船为家,在各河道流窜作案。每到一地,拐子一面令船上的残疾儿童四处乞讨,一面寻机拐骗更多儿童,并用船只迅速将其带到另一地区。江南地区河道纵横交错,情况复杂,即便岸上有人目击,也难以明确指认船只去向,导致无处追踪。一旦有儿童试图求救,拐子便“撑入湖心痛打,以儆他丐”[17]133。最终,临河而居的向乡官从河岸一侧的后门听见船中惨叫,派人将拐子逮捕。
上述案例中,谋杀、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活动中,罪犯依托舟船实施犯罪、逃避追捕;而拐带人口类犯罪活动中,舟船则充当犯罪工具。尽管罪名不同,社会危害程度不同,但这些犯罪活动都以舟船为中心,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并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舟船犯罪的特殊性。
二、舟船犯罪的特殊性
舟船犯罪主要位于水上,具有与陆地等其他空间不同的表现,这与舟船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一)空间狭小封闭
明代江南商业贸易的繁荣和水路的便利,使当地商人便于采用水运方式运输货物。经商者携带货物和钱财上船,与潜在罪犯共处同一狭小空间。若同行伙伴、仆从较少甚至独行,易成为罪犯的目标,轻则被骗被盗,重则因财丧命。且中途停靠时可能增加搭船乘客,因此陌生乘客相对而坐是常态。在这样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中长途乘客缺乏隐私,容易被船户和其他乘客窥视财物。例如前述丘二、鲍二谋杀毕时选一案,受害者也正是登船时“朱提盈笥”[15]688,行李中携带不少白银,被凶手看见,故而招来杀身之祸。
船户替乘客搬抬行李上船时,也能通过掂量行李分量来猜测物品种类。《杜骗新书》第十二类“在船骗”专门揭露舟船犯罪过程,《带镜船中引谋害》一篇中,富家子熊镐第一次做买卖,在湖州购买笔墨、镜子各十两,搭船返乡。两个舵公抬行李时“见财主威仪,家人齐整,奈何行李只两小箱。及抬入船中,觉箱中镇重,想必尽是银也”[17]72,误将镜子当成白银,遂起谋财害命之心。上岸前夕,舵公将熊镐灌醉,又极力劝其仆人饮酒,欲将主仆二人杀死于梦中。仆人满起感到危险,故意开箱显示里面没有白银,又各送舵公一面镜子,才与主人平安下船。同书《买铜物被艄谋死》一篇中,船户掂量乘客装满铜器的行李,“疑是金银,乃起不良心”[17]69,半夜移船僻处,将乘客主仆二人砍杀,抛尸江中。
(二)管控存在困难
行驶中的舟船,在管控方面存在一定困难。根据前文案例,虽有士兵对河道进行巡逻,但巡逻时间、范围有限。经验丰富的船户则能够轻易避开巡逻,将船划到僻静无人处作案。在偏远的河湖或深夜的江心,即便发生了命案,也难以第一时间被人发现。
行舟途中,船户与乘客的地位的不对等,导致乘客遇到危险时难以反抗。一旦舟船离岸,船户可以改变船的位置,但乘客不能随意下船。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仅受船户技术影响,更取决于船户的道德水准。舟船犯罪案例中的船户,有的“剽掠为生”[16]520,是抢劫惯犯;有的“为蠹于干巷镇久矣”[16]405,是当地市井无赖;有的“坐听撑驾”[15]708,将自己的船给劫匪使用。来自外地的商人、旅客不知船户底细,或被船户热情招揽,或被同谋牙人引诱,登上不可靠的舟船,遂踏入罪犯设下的圈套。
(三)来去踪迹不明
与陆路交通相比,水路交通具有踪迹不连贯的特点。舟船离岸后,不会产生车辙、马蹄印、脚印之类连贯的运动痕迹,因此难以判断去向,给侦破案件、追回赃物带来一定的难度。例如松江府一伙强盗“借名鱼贩,驾船流劫,仅三匝月而被害者已六”[16]573,不仅在本地作案,还流窜至湖州等周边地区,难以抓捕。
舟船犯罪的这一特殊性为罪犯逃避追捕提供了便利,也导致受害人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例如一官员倪某即将赴任,在南京置办行李,出发前夕让仆人将行李先搬到船中安放一晚。天亮后船已消失,仆人和行李都被拐走。官员本欲报案,友人劝阻道:“江边常有贼船……若不识者,误上他船,虽主人亦同被害……船贼又无名姓踪影,虽告何从追捕?不如罢休。”[17]66官员只好自认倒霉,放弃报案。
上述三个特征决定了舟船犯罪具有异于其他犯罪类型的隐蔽性和流动性,导致舟船犯罪成本降低,侦破舟船犯罪的成本提高。乘客搭乘舟船,尤其是携带财物外出经商,可能会在途中遇到各种危险。因此明人总结经验教训,概括出一系列要诀和对策,用以防范舟船犯罪。
三、民间防范措施
针对江南地区舟船犯罪频发这一问题,明朝政府虽采取设巡检司、修桥立栅等措施对江南河湖进行管理,但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处在了人治与法治、宽弛与严猛来回摇摆的状况中”[4]205,致使舟船犯罪成为江南痼疾。关于舟船犯罪案件的处罚,原则上应依律判决,不过现存判例判牍表明,实际处罚常受现实因素影响。
一方面,性质类似的舟船犯罪,最终可能获得截然不同的判决。例如《云间谳略》中刘二兄弟劫赵森案和王成、沈德劫陆佩案,两案同为松江府审理的案件,审判时间相隔不远,罪行皆为劫船,但最终前者定性为“抢”,后者定性为“盗”。前者持棍殴打受害者,“诚与截劫无异”[16]520,性质近乎于“盗”;却因“东方已曙,党与不伙,舟无凶仗,主未重伤”[16]520,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遂以抢夺律判处充军。后者则“手持刀斧,打伤破面”[16]539,将受害者打成重伤,情节严重,不能“饰盗为抢”[16]539,且人赃俱获,遂依律处斩。由此可见,司法实践并非完全依律判决,实际操作中往往受情节轻重与社会危害程度影响。
另一方面,舟船犯罪案件容易在追赃问题上受阻,甚至因此影响最终判决。罪犯作案后,或快速变卖赃物、挥霍赃银,或“半舟半水”[16]539,将部分赃银藏于水底淤泥中。例如丘二、鲍二谋杀毕时选一案,案发两年后官府才将凶手抓获,凶手鲍二被判斩刑。其同谋丘二已将赃银挥霍一空,本应与鲍二一同处斩,却因赃银数额不明而罪轻一等,只被判处绞刑。地方官员只能在判牍中写道:“(丘二)本应以谋财致命律与鲍二骈斩,姑以赃亡拟绞,幸哉!至所分各赃,两年内如火之销膏,止有缳颈以谢泉下人,必欲求其赃以实之,则凿矣。”[15]689实际上,面对与丘二类似的情况,官府与其说无意追赃,不如说是无力追赃。
明代江南舟船犯罪不仅频发,而且难以防范,案发后缉凶追赃也并非易事。对于江南地区的乘客而言,官府针对舟船犯罪采取的措施往往治标不治本,江湖之上仍然充满各种未知的风险,轻则误事破财,重则人财两空。既然官方力量尚不足恃,乘客在搭乘舟船时必须小心谨慎,以免遭遇不测。针对乘坐舟船时可能存在的隐患,民间归纳出一系列自保防范措施,并通过商书、谚语等形式广泛传播。
(一)慎雇舟船
埠头既指岸边上船、卸货的固定地点,也指这一地点的管理者。商人与埠头签订“写船”契约后,埠头负责雇佣合适的船只和脚夫。此外,埠头还有管理船户、保障安全的职能。“江南地区的经济和商业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埠头功不可没。”[8]34
明末程春宇所辑《士商类要》中的《船脚总论》等文,记载了商人防范舟船犯罪的经验。作者认为,只有经过可靠的牙人雇船,才算稳妥。乘客私雇船只,不知船户姓名底细,则是乘船大忌。“……雇船一事,必须投牙计处,询彼虚实,切忌贪小私雇,此乃为客之第一要务也。”[18]258《杜骗新书》也提醒乘客:“若自向江头讨船,彼此不相识,来历无可查,安得不致失误?”[17]66雇船前,应先登记船户姓名,验证其身份真伪。一方面,这样能防止歹人冒充船户拐人上船;另一方面,若有失窃、丢失货物等纠纷,也可找到当时所雇船户。
乘客在与船户成交之前,应仔细观察船内外情况,判断该船是否安全。“其看船之法,须是估梁头,算仓口,看灰缝干湿,观家伙齐整,方可成交。”[18]358新下水或新修理的船只、缺少工具或工具不匹配的船只,都属于可疑船只,不宜搭乘。
(二)结伴而行
如前文所述,独行乘客常常成为罪犯的目标,必须加倍谨慎小心。“大凡孤客搭船,切须提防贼艄谋害。昼宜略睡,夜方易醒。煮菜暖酒,尤防放毒。服宜朴素,勿太炫耀。”[17]47明代有“投早不投晚,耽迟莫耽错”[18]363的俗语,夜晚是舟船犯罪高发时段,若非行程紧急,应尽量选择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出行。如果不得不夜晚行船,乘客要尽量在白天小睡,晚上才容易听到动静,发觉异样。在船上用餐时,要仔细处理酒菜,避免被人投毒。
然而旅途疲惫,孤客难免百密一疏,给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与可信的熟人结伴而行是更好的出行策略。“凡出外必须要择的伴,庶几有辅。若路逢素非熟识之人,同舟同宿,未必他心似我。”[18]363商人携带货物乘船,上船、下船、卸货等事务多由仆人办理,故“要得智仆为吉也”[17]75。如前例所述,一个经验丰富的仆人,能够窥破船户谋害之意,挽救自己和主人的生命。“凡远行者,主若疏满,得一谨密家人,亦大有益。故旅以丧童仆为厉,以得童仆为吉。”[17]73同行仆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些罪犯利用孤客想要寻找旅伴的心理,有意接近攀谈,伺机下手。“搭船行李萧然,定是不良之辈……非拐子即掏摸、吊剪之流……若不识其奸,财本遭掳。”[18]362有的罪犯一早在船,装作好心邀请受害者顺路搭船;有的罪犯伪装成普通乘客,与同伙先后登舟,彼此装作陌生人,实则配合犯罪。因此船上偶遇的旅伴不可轻信,必须仔细观察,保持距离。
(三)言行谨慎
除了选择合适的同行者,乘客自身也须做到言行谨慎。携带财物者,应衣着朴素,防止露财。“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财帛,切宜谨密收藏。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细,显露被人瞧见,致起歹心,丧命倾财,殆由于此……出外为商,务宜素朴,若到口岸肆店,服饰整齐,小人必生窥觊,潜谋窃盗,不可不慎。”[18]362-363《杜骗新书》中《道士船中换转金》《炫耀衣妆启盗心》两个反例中,主角皆因上船后大意露财而受害。
乘客不仅自己要衣着朴素,乘船时还应看护好儿童。旅途中,不仅不能使儿童离开成人视线,而且不能为其佩戴贵重饰品。前述拐骗儿童行乞一案后,作者评论道:“人家子女幼稚,不可令其单行,亦不可带金银镯钱。”[17]134父母给儿童佩戴金银项圈等饰品,本意为保平安,却容易遭人觊觎,反而导致儿童受害。“童稚戒饰金银……小人窃见,利其财物,或毁体折肢采取,或连孩童抱去。”[18]362窃贼手段残忍,为快速取下饰品,往往伤害儿童手、耳等部位,甚至将其杀害。
乘客还应避免与陌生人交谈,以免被人知晓底细。“人前话语,务宜谦慎缄默,使人难以窥我虚实。若满口矜夸己胜,说短论长而不知止,此人必无内养,诚可嫌憎。”行船过程中,船舱内缺乏娱乐,乘客多闲聊打发时间。然而言多必失,与陌生人交浅言深,容易祸从口出。一些罪犯利用乘客旅途无聊的心理,故意上前搭讪,“或自相赌戏以煽诱,或置毒饼果以迷人”[18]362,导致旅客在不知不觉中深受其害。
(四)照看货物
商人乘船,还要提防货物丢失或受损。《士商类要》强调“客惟装卸之中,勤管要紧,沿途停泊,防慎为先”[18]359,揭露了窃贼盗窃粮、油、米、鱼、麻饼、腌猪、棉花、棉布、白糖、芦席、荆条等货物的种种手段,供读者参考防范。尽管如此,苏州、杭州、湖州等地的船只“载人居上层,行李藏于板下,苟不谨慎,多被窃取”[18]362,舟船结构导致人货分离,货易失窃,防不胜防。
各种货物中较为特殊的是铜、铁、铅、锡等金属器物,运输此类货物时必须令船户知晓。“若有铜铁秤锤,一切重物,不可收入箱笼及裹于包袱之内。倘付脚夫、船户挑载装仓,疑系财帛,遂起歹心,不可不慎。”[18]361船户若以铜铁为金银,则很可能变盗窃为抢劫、谋杀。《杜骗新书》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专门以《买铜物被艄谋死》《带镜船中引谋害》两例予以说明。
从船上卸货时,商人不仅要自己仔细检查,还需要经过船行,以免脚夫和船户勾结,趁乱挑走货物,或故意遗漏货物在船。“凡卸船,必由船行经纪,前途凶吉,得以知之……倘悭小希省牙用,自雇船只,人面生疏,歹者得以行事。”[18]363
(五)防范船户
行船过程中,乘客对船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船户是信任的。“若搭人载小船,不可出头露面,尤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客人。”[18]357不言而喻,作者认为被船户认出是商人,后果就是成为其犯罪目标。
明代相关文献中,不乏对船户这一职业的评价。江南地区舟船犯罪案件频发,导致乘客不得不对船户处处提防,甚至将大多数船户视作潜在罪犯。当时有“十个船家九个偷”[18]359一类的谚语,虽为夸张之辞,也反映出舟船犯罪的普遍性。《士商类要》认为,船户之中奸恶者远远多于良善者。“若论船户脚夫之奸恶,律罪充徒,理的当也。奈何掌法之官,不知有此弊端,每怜贫而轻宥,情法何勘。虽然船脚之奸,甚于窃盗,间有二三良善者,客人亦不可加之于刻剥也。”[18]359《杜骗新书》也认为“溪河本险危之地,舵公多蠢暴之徒”[17]71,应该严加防范。
舟船犯罪普遍存在,乘客对船户失去信任,导致双方关系紧张。例如鄞县船户周玄被殴死一案中,乘客陈某失窃,其仆陈金助因船户周玄曾要求涨船价而怀疑其盗窃,对其“唾詈不已,继以殴击”[15]691,且下手极重。处理此事的三个捕役为强迫周玄认罪,便与陈金助群殴周玄,最终将其打死。经查,周玄并未盗窃。这一案例既体现出乘客与船户关系紧张的情况,也折射出社会对船户的偏见。尽管《士商类要》作者对官方处理涉案船户时的态度十分不满,但现实中基层差役对此类案件的办理并不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怜贫而轻宥”[18]359。
四、余论
明代江南地区舟船犯罪频发,不仅与舟船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也存在交通、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
水上交通发达的区域交通特点是明代江南地区舟船犯罪频发的基础。江南为明朝财赋重地,为了漕运便利,政府对这一区域的众多河湖进行疏浚,将密布的水网转化为畅通的航道。沿河市镇、港埠众多,城市内部大小河流数不胜数,有着水上交通发达的特点。舟船不仅是江南常见的交通工具,还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民户家中的小型船只,可以为捕鱼、采菱、采莲等小规模水上劳作以及载物赶集等活动提供便利。民间对船只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地区民间造船业的发展,使非船户出身的犯罪分子易于获取船只。舟船的灵活性也赋予了船户和乘客较强的流动性,因而舟船犯罪案件难侦破,案犯难抓捕,赃物难追回。
经济形势的转变是明代江南地区舟船犯罪频发的土壤。随着江南市镇不断建设与发展,商业贸易日渐繁荣,市镇间的运输需求也在增加。舟船凭借其灵活省力的优势,成为行商辗转各地运输货物时常用的交通工具。江南地区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针对商人及其所携财物的犯罪由此增加。同时,政府财政支出逐渐增长,上供物料摊派扩大化,进而导致逃户增多,户役制度走向衰败。户役制度的衰败导致船户群体的来源、结构和行为发生变化。“官府对职业户的控制相对宽松,或者说驾船为业的并非都是户役系统中的船户。”[9]71一方面,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和同行竞争,迫使一些船户铤而走险;另一方面,以舟船载客者鱼龙混杂,罪犯常以船户身份进行掩护,以便寻找并接近受害者。江南地区人口稠密,载客舟船往往在行程中多次停靠市镇港埠,往来乘客亦复杂多变,不尽相识,罪犯可能混在其中,伺机下手。
社会风气的变迁是明代江南地区舟船犯罪频发的诱因。明中后期江南奢靡之风盛行,这种风气来源于城市的繁华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现象和从众性消费风气,导致更多人陷入经济困境,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同时,部分乘客出行时衣着光鲜,在行船途中轻易对陌生人夸耀财富,不免引起罪犯觊觎。
综上所述,复杂的水文环境导致地方管理体系难以实现全面覆盖,变化的经济形势消解了过往的水上秩序,严峻的社会分化更使“凶年有盗”[19]204成为常态。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显示着搭乘舟船时的潜在威胁,与此密切相关的船户群体职业信誉下降,整体形象逐渐恶化。尽管明人总结出了慎雇舟船、结伴而行、言行谨慎、照看货物、防范船户等防范经验,并通过商书、小说、谚语在民间广泛传播,然而上述自保措施,除“将船户的这种负面形象以一种固定的知识传递给了读者”[9]75之外,对根除明代江南舟船犯罪痼疾助益甚微。令人忧虑的水上治安状况导致乘客与船户之间信任缺失加剧,但许多乘客又常需取道江湖,故而将船户视作盗贼严加防范,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频发的舟船犯罪扰乱了水上交通与社会秩序,使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流动和商业贸易受到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中国水运史丛书[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1998.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编.中国水运史(远古-1840)[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21.
[3]于宝航.明代国内交通运输的嬗变[A]//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4]王日根,曹斌.明清河海盗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5]松浦章.明代内陆河运的盗贼:河盗、湖盗、江贼[J].地方文化研究,2019,(04):61-69.
[6]裴宏江.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的特殊文化功能[D].上海师范大学,2012.
[7]敖红艳.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9.
[8]钱晟.明清时期江南埠头与牙行[J].历史教学问题,2020,260(05):34-41+165-166.
[9]杨泉.明代的船户——以户役制度为背景的考察[D].东北师范大学,2018.
[10]邢钺莉.《三言》与明中后期运河商贸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11]陈宝良.“行路难”:明清商人行走江湖之险恶及其应对[J].明清论丛,2016,(01):1-38.
[12]张志华.明清时期的闽江航运与河道社会[D].厦门大学,2017.
[13]李明珠.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船户研究[D].聊城大学,2022.
[14]苏茂相.新镌官板律例临民宝镜[A]//杨一凡,徐立志.历代判例判牍:第4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5]李清.折狱新语[A]//杨一凡,徐立志.历代判例判牍:第4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6]毛一鹭.云间谳略[A]//杨一凡,徐立志.历代判例判牍:第4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7]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18]程春宇.士商类要[A]//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9]黄汴著,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0]张春彦.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基层社会犯罪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21]李敏.《杜骗新书》新论[D].安徽师范大学,2010.
[22]马后威.晚明骗行解析[D].安徽大学,2018.
作者简介:
陈程,女,汉族,浙江绍兴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