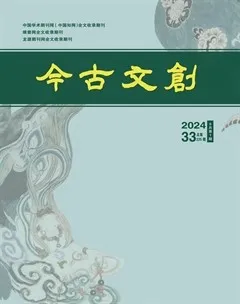俄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简史
【摘要】1820年,俄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浪漫主义时期。儿童写作也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开始以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情感看待儿童。孩子们受到重视,被认为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迷人而诗意的世界。“双重世界”的概念意味着日常生活与幻想世界并存,孩子可以毫不费力地跨越边界。这是幻想类型的基础,在浪漫主义时期,安东尼·波戈列尔斯基的《黑母鸡与地下王国》和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的《鼻烟盒里的小镇》等作品就是例证。这些是第一批获得经典地位的俄国儿童读物。这一时期,俄国童话的发展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文学史;浪漫主义;童话故事;俄国史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4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15
在浪漫主义时期,第一批几乎完全致力于儿童文学的俄国作家出现了。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安娜·宗塔格、彼得·福尔曼和维克托·布里亚诺夫都是真正的儿童作家,他们的作品为俄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渐渐地,人们意识到儿童文学应该独立于成人文学之外,于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形成了。一本儿童读物不仅应该具有启迪性,还应该具有文学性。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儿童读物的数量逐渐增加。虽然1801年至1825年期间总共只发行了约320种儿童读物,但在接下来的25年里,这一数字增加了一倍多,增至860种左右,增长速度接近每年30部。到1830年,俄国儿童文学原著的产量超过了翻译作品的数量。许多小说也进入了教科书,证明儿童文学现在已被视为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童话的道德教化功能
18世纪末,在民间故事短暂流行之后,这些故事或多或少地从儿童文学作品中消失了几十年。在俄国漫主义时代,民间故事以改编自民间传说和原创的艺术童话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些作品充分肯定了儿童们的想象力。约翰·穆萨乌斯在1811年至1812年期间出版的六卷本德国民间故事即为标志。1825年,查尔斯·佩罗童话故事的新译本问世,但关键的转折点是次年在《儿童对话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套“儿童故事”包括“荆棘丛”“兄弟和姐姐”“小红帽”“女巫”等。
人们对童话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认为童话应该具有道德传授作用,从当时出版的童话附带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作家的责任是向孩子们解释这些故事的道德教训”“不要盲目地翻译,而要像给你的女儿讲一个外国故事一样:这会让故事更加精致、清晰和简单”。安娜·宗塔格在翻译时并没有生搬硬套,她没有逐字翻译,而是以个人的、创造性的方式讲述童话。在《小红帽》中,当猎人打开狼的肚子时,“出来的是鲜花,然后是馅饼,然后一个牛奶罐滚了出来,牛奶洒了一地;他又一刀,一顶红帽子出现了,突然女孩自己活活跳了出来”,这样生动的话语有助于使儿童明白善与恶,好与坏。
儿童的知识和经验是在成长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获得的。儿童获得道德观念与生活经验的途径除了通过老师和家长,还可以通过童话中的形象来感悟。[1]通过阅读自己喜欢的童话,儿童通过直观清晰的童话形象可以知道,如果自己成为不听话的坏孩子,将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样他们心里自然就会抗拒和排斥这些负面形象,同时会同情、羡慕、模仿童话中正面健康的儿童形象。[2]这就是童话的道德教育意义所在。
二、俄国本土儿童文学的发展
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在欧洲的重要文学思潮,浪漫主义首先兴起于德国等国家,后来迅速在整个欧洲大陆流行起来[3]。1829年是俄国儿童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安东尼·波戈列尔斯基的《黑母鸡与地下王国》的出版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原创的、著名的俄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在此之前,儿童读物一直充满隐秘的道德说教,缺乏艺术性,缺少幻想和诗意,并且高度依赖翻译外国作品。这种枯燥的儿童读物很难吸引儿童的注意力。《黑母鸡与地下王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局面。
安东尼·波戈列尔斯基,一位浪漫主义故事作家。替身、奇怪的变形以及与恶灵的会面是他作品的主题。他创作了一个关于一个男孩和一个地下居民之间相遇的故事。波戈列尔斯基将《黑母鸡与地下王国》称为一个神奇的故事。他对作品的类型做出了开创性的选择,将现实场景与奇幻情节自由地混合在一起。一切都基于对孩子体验世界的方式的深入洞察。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阿廖沙,他住在18世纪末圣彼得堡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出于善意,他救了一只黑母鸡的命,结果发现这只黑母鸡是伪装的小人国。为了表达谢意,黑母鸡带着阿廖沙前往它的地下王国进行夜间旅行。在这里,男孩得到了一个护身符,可以实现许下的愿望。一个轻率的要求——不做任何家庭作业就能得到知识——暴露了阿廖沙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面。他从一个谦虚、勤奋的男孩,变成了一个自满的闲人。最终,他甚至食言,揭露了小人国的秘密世界。结果,阿廖沙不仅失去了他的奇妙护身符和他的朋友,还导致了隐秘世界的毁灭。
波戈列尔斯基的《黑母鸡与地下王国》被认为是一个警示故事。从与黑母鸡的友谊中,阿廖沙懂得了忠诚和勤奋的重要性。他在善与恶的选择中欺骗了自己,同时也欺骗了地上和地下的朋友,只有向黑母鸡承认自己的背叛,他才能摆脱自己的缺点。《黑母鸡与地下王国》因其生动形象的描写而成为俄国儿童文学的经典,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永恒的道德,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儿童。但书中也存在矛盾心理,使其对观众有双重吸引力。
阿廖沙的个人经历解释了这个故事中的奇幻事件。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他读了太多的侠义小说和太多的魔法故事,导致他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变得扭曲。他与黑母鸡切尔努什卡的友谊以及他从现实进入幻想世界的方式,是他为自己所缺乏的父母的爱和关怀寻找补偿的方式。长期以来,阿廖沙只生活在自己的梦想和幻想中,与学校和同学们越来越疏远。在书中,寄宿学校的德国老师扮演了阿廖沙的救世主,他狠狠地打了这个男孩,并迫使他承认他的夜间冒险只不过是幻想。从那时起,知识和科学取代了梦想,他周围圣彼得堡的美丽取代了他在地下世界遇到的可怜的仿制品。
切尔努什卡看似是阿廖沙的恩人,但在民间迷信中,黑母鸡一直与恶灵联系在一起,要么代表撒旦本人,要么充当他的中间人。母鸡确实想赢得男孩的灵魂,把他拖入地下,把他变成一个顺从自己意志的工具。阿廖沙因未能遵守不泄露地下朋友秘密的承诺而受到指责,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拯救他的唯一途径。只有与黑母鸡所代表的势力决裂,他才能摆脱自己的坏习惯和有害的幻想,重新赢得学校的认可。
这一时期的另一部重要奇幻故事——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的《鼻烟盒里的小镇》,也是基于双重世界的概念,其中一个孩子充当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纽带,沟通了两个世界。米沙对父亲的鼻烟盒感到好奇,在梦中,他进入了它迷人的世界,了解了它的不同组件如何运作和相互作用。所有的小部件都被赋予了个性化的人类特征,当男孩醒来后,他可以完美地向父亲解释盒子的机制。在故事中,男孩关于鼻烟壶的知识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而是借助梦境和生动的想象力获得的。
三、批评家别林斯基对该时期童话的影响
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给俄国儿童文学作家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涉及到对儿童的认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派诗人对儿童观最大的贡献在于肯定儿童的幻想[4]。1835年至1847年,别林斯基对俄国儿童读物,无论是小说、翻译作品、连环画还是杂志,进行了评论,指出了这时期儿童作品的可取之处与不足。别林斯基对俄国儿童文学的关注,促进了俄国儿童文学的良性发展。他在俄国现实主义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既定的事实,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对儿童文学的巨大兴趣。他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出版物上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系统地形成了自己对于儿童文学的观点。在对儿童读物的审视和评价中,他对儿童文学的具体特征和诉求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最终形成了一套儿童文学的理论。别林斯基作为俄国童话理论的奠基人,为俄国童话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5]。
别林斯基认为文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儿童读物是为了教育目的而写的,而教育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决定个人的命运。”专门为儿童写的书籍应该受到重视。在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别林斯基时代之前,儿童文学在出版商、评论家和家长眼中的地位一直很低。别林斯基提高了儿童读物作家的标准。他们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为儿童写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写作者必须生来就是一名儿童读物作家,人们不可能通过后天努力成为一名儿童读物作家。成为儿童读物作家需要与生俱来的天赋。”别林斯基在回顾1840年时,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期望:“儿童作家的形成条件有很多,甚至非常多:一个善良、有爱心、温柔、平静、天真单纯的灵魂,一个崇高、受过教育的心灵,一个对现实清醒的态度,不仅如此,生动的想象力,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中充满生动、诗意的幻想,能够以生动、欢快的形式呈现想要表达的一切都是需要的。不用说,对孩子的爱以及对童年的需求、特点和细微差别的深入了解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儿童作家不能回避社会问题。别林斯基在1848年与亚历山大·伊希莫娃的讨论中阐明了这一观点。在1847年出版的小册子《关于小说阅读的几句话和青少年阅读指南》中,亚历山大·伊希莫娃表达了她对法国小说在俄国大受欢迎的不满。在这些小说中,即使是无法控制自己本能的恶人,也被描绘得充满怜悯,有时甚至会得到读者的同情。在这些作品中,追随内心声音的想法被认为比家庭纽带更重要。亚历山大·伊希莫娃认为,文学应该为年轻读者提供好的榜样,教导他们热爱善良,鄙视邪恶。
别林斯基没有质疑亚历山大·伊希莫娃的观点,即儿童文学应该创造积极的理想,但他认为应该把孩子带出托儿所。至于题材的选择,他声称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不应该有区别。生活必须按其本来面目来描绘,“赤裸裸的现实生活,有欢乐和悲剧、丰富和贫穷、成功和苦难”。孩子们不仅应该接触经典作品,还应该接触当代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使孩子们对自己生活着的现实世界有更深的理解,同时教导孩子们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6]。
儿童文学应该以与成人文学相同的方式阅读和讨论。儿童读物必须是一件艺术品,而不仅仅是某些道德规则或说教原则的集合。在1847年的一篇文章中别林斯基阐述了他的观点:“唯一对儿童来说好的、有用的作品是成年人能够感兴趣地阅读并产生收获的作品。儿童作品不是为儿童而写的作品,而是为每个人而写的文学作品。”俄国童话的这些风格和特征既是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民族意识和审美精神的显现,也是俄国童话自立于世界民族童话之林的重要资本。[7]
四、浪漫主义时期俄国童话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浪漫主义时期,俄国童话取得了迅速的发展,首先是儿童读物发行量的增加,使得这一时期的儿童在阅读方面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其次是从事儿童读物写作的作家数量增加,大量知名的俄国作家如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享誉全球的大文豪在这一时期也投身于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之中,创造出了充满梦幻般的想象力与道德教诲意义的经典童话,如《王子与天鹅公主》《金鸡》等。别林斯基对这一时期童话作品的批判,也促进了俄国童话的发展。别林斯基的批判逐渐确立起俄国童话创造的原则,即儿童读物是为了教育目的而写的;儿童文学应该以与成人文学相同的方式阅读和讨论;儿童读物必须是一件艺术品,而不仅仅是某些道德规则或说教原则的集合;儿童作品不是为儿童而写的作品,而是为每个人而写的文学作品等。这些原则的确立,使俄国本土童话的发展进入到了春天。从此俄国国内的童话不仅仅是简单地翻译外国童话,而是开始了自我创造的过程,成为寻找真正“民间精神”的一部分。[8]
浪漫主义时期俄国童话的另一大贡献,就是肯定了儿童本身的想象力。浪漫主义时期俄国童话作家认为,要通过儿童的丰富想象力对儿童进行教育。[9]以充满梦幻般想象力的童话来对儿童进行教育是因为儿童教育与成年人的教育不同,儿童缺乏自制力,且易受到外部事物的影响,所以,对儿童进行教育要注意吸引儿童的注意力。童话中糖果的城堡、会飞行的扫把、王子与公主等主题,会激发儿童的兴趣,使孩子们乐于阅读。将道德教育与日常生活常识贯穿于童话故事构建之中,可以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使儿童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浪漫主义时期俄国童话的发展,使儿童文学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童话作品的主要受众是儿童,在此之前,从未有文学体裁是主要针对儿童的。童话这种文学体裁的迅速发展,使儿童教育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从此儿童作品的质量获得了提升。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投身于童话的创作之中,为儿童提供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五、结语
古老的文学体裁童话以其梦幻般的想象力和充满趣味的情节,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接受到美与爱的熏陶,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财富[10]。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说:“童话都是虚构的,童话对每个善良的人都有教育意义。”俄国童话凭借自己的魅力,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俄国童话中包含了俄罗斯人民的生产生活经验,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对邪恶的憎恨。童话中的道德教化意义也会启迪儿童们的心智,使儿童确立正确的道德观。毋庸置疑,浪漫主义时期俄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卢河梅.以漫画读物启智儿童心灵[J].文化产业,2024,(05):37-39.
[2]易丽君,王晓兰.理性的呼唤——从《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看童话的教化功能[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4):78-84.
[3]刘潇娴.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概览[J].语文建设,2017,(11):44-45.
[4]余春瑛.童话教化观念的文化根源[J].探索·研究,2008,(04):11-14.
[5]姜云雪.别林斯基论俄国文学的民族性[J].今古文创,2021,(45):33-34+39.
[6]林精华.别林斯基的茫然:现代俄国文学批评之形成与欧洲文化影响下的大众文学[J].文艺研究,2023,(12):76-93.
[7]刘文飞.俄国文学的风格和特质[J].江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6):105-113.
[8]王文毓.抚慰灵魂 追寻意义——论俄国文学的“童年叙事”[J].当代外国文学,2021,42(03):76-83.
[9]徐丽云.浅谈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J].文学艺术周刊,2023,(17):22-25.
[10]张洁,刘春芳.浪漫主义文学发轫的哲学背景[J].社会科学辑刊,2007,(06):261-265.
作者简介:
吕志炜,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