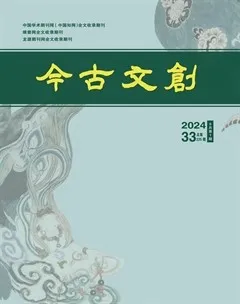论叶燮《原诗》中“冥漠恍惚之境” 的思想渊源
【摘要】叶燮在其诗论著作《原诗》中提出“冥漠恍惚之境”意境论思想。本文研究这一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通过文献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叶燮《原诗》中“冥漠恍惚之境”的意境论内涵,并从语义与内涵两方面对其进行含义阐释,研究发现“冥漠恍惚之境”有儒释道三方面思想渊源。讨论叶燮《原诗》“冥漠恍惚之境”思想渊源,旨在为中国古典诗学意境论的研究添砖加瓦。
【关键词】叶燮;《原诗》;意境论;冥漠恍惚之境;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10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著作,《原诗》具有鲜明的理论意识、开阔的史诗视野、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犀利的批评视角以及雄于论辩的特点。吕智敏称“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集中论述诗源、诗美、诗法的诗学专著”qDpKsKDbGrxxzcrbuBRjWg==。近些年与叶燮《原诗》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出原典自身备受重视。
一、研究背景及现状
(一)研究背景
作为继《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系统的诗论著作,叶燮《原诗》批判明末清初时期不良诗风,尤其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和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的性灵派诗论主张。它系统阐述了文艺的创作论、审美特征论、发展论、风格论等问题,在中国意境理论发展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6]118
《原诗》具有完备理论体系、思辨化话语模式和圆通运思方式,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它也在诗学历史流变、理性化对诗学历史进行分期建构、建立诗的批评标准等方面有全新突破。[10]在《原诗·内篇下》中,叶燮提出“冥漠恍惚之境”一语,并对其基于“理、事、情”的实践基础进行阐发,这使其在中国古代意境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具有可研究与挖掘的广阔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原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著作,它所具有的思辨性与体系性使其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中更是“凝聚了传统诗学的诸多精义”[1]15,我们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深入研究挖掘传统典籍中的价值,为增强全民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二)意境论的发展
“意境”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已有千年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最早描写意境这一词语的典籍为王昌龄的《诗格》,他认为“诗有三境”,第一个是“情境”,第二个是“物境”,而第三个就是“意境”,此“意境”主要指人内在的心灵意识世界,并非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至中唐时期,刘禹锡为意境正言,曰:“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诗人所言“境”生“象外”也是“象外之象”,前者之“象”是实写的“实境”,第二个“象”为虚写即“虚境”,由“手中之竹”而及“胸中之竹”,虚实相生,韵味无穷。[7]唐代司空图提出“三外说”阐释意境的特征;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情景”说,未言意境却处处散发意境;至清代叶燮《原诗》提出“冥漠恍惚之境”,“强调诗歌的艺术思维具有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的特征”[1]199。
清代神韵学式微,强调建构“清远”的意境特征有不重现实的流弊,叶燮的诗学理论因反复古而与之互补,并为促进清代中叶性灵派的兴盛发挥重要作用。《原诗》中的“冥漠恍惚之境”是以“理、事、情”为创作客体的论述,具有理论支撑与实践基础,促进了当时诗歌及诗论的健康发展。
(三)《原诗》意境论研究现状
王向荣和连丽丽在《“冥漠恍惚之境”:叶燮对诗歌最高审美理想的建构和阐释》一文中认为,叶燮《原诗》建构了一种处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相互运动中的“含蓄无垠,思致微渺”之最高审美理想,作者阐释了《原诗》中审美主客体参与审美活动时的独特性,认为生成审美客体的思维介质是“默会”,而审美主体能够表现出能动性和灵活性也是由于具有“神明”的独特品质。[5]李晓峰的文章:《叶燮“理、事、情”理论对中国意境论的贡献》,探究叶燮《原诗》对中国诗学意境论所做贡献,作者梳理“境”与“理、事、情”之间的关系,他首先从“情”的理论切入,将它放入自然景物与社会事物场域中研究,认为《原诗》中物之“情”理论与中国人体物、观物的审美体验过程相吻合,使诗歌意境中的人情与物情得到升华。[4]王向荣在《“触”与“衡” ——叶燮审美创作新论》一文中认为,“含蓄无垠,思致微渺”的“冥漠恍惚之境”产生于主客体之间、展现不受限制交融性的、具有高尚精神性的最高审美理想,“触”即为心物交融的状态,“衡”即为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由“触”与“衡”构成的是叶燮《原诗》的“审美范式和标准”。
综观以上与叶燮《原诗》意境相关的研究发现,研究者多集中于意境与审美互动和审美体验的研究,解析意境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阐释叶燮“冥漠恍惚之境”的最高审美理想。由现有研究发现,学界对于《原诗》意境的研究方向不够丰富,可将意境与《原诗》原文进行纵向链接阐释,挖掘“冥漠恍惚之境”的内在美学含义是有待相关学者开垦的沃土。
叶燮的《原诗》向来被学界视为中国古代诗话中理论色彩最浓厚、最有系统的著作。①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其研究日益深入,有关学者已在中国知网发表相关文章二百余篇,足见学界对其著作及相关理论的重视。现有文献对叶燮《原诗》意境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意境本体及影响意境生成的主客观因素方面,而对意境生成的背景及思想渊源进行纵向追溯式研究的文章较少。本文呼应学术语境中对典籍尤其是对诗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要求,呼应二十大报告“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研究“冥漠恍惚之境”的思想渊源,旨在为中国古代意境论的研究添砖加瓦。
二、“冥漠恍惚之境”含义阐释
杜甫在诗作《春宿左省》中写道:“月傍九霄多”,《原诗》论之认为这是一种唯有杜甫才能表达的独特意境之景,寻常人看见不过是普通的月色而已。可见其中一“多”字尽可概括杜甫眼前所见宫殿之前的月夜景象。“月傍九霄多”包含的若虚若实的审美体验便是叶燮所言“冥漠恍惚之境”。
(一)《原诗》中的意境理论
“冥漠恍惚之境”出现在《原诗·内篇(下)》中,内篇主要探讨诗文创作理论,在内篇中提到“境”的亦有以下几处:
“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 ②
“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 ③
“今日‘多’,不知月本来多乎? 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 ④
“意境”一词在中国诗学理论中是一个含义深厚的词语,由意境而及高远的格调、浓郁的气氛、无尽的遐想,最终达到只可意会的审美艺术精神之境况中。在叶燮的《原诗》之中,所论“境”之处并不多,结合语境可知这些“境”的含义似有模糊,可做优美无尽的“意境”解读,亦可做此情此景的情境解析,而唯有“冥漠恍惚之境”一语有更深刻的美学内涵,它不仅体现了意境赋予诗歌的精神美,也表现了审美理论中独有的理念与范畴。
(二)“冥漠恍惚之境”语义阐释
叶燮以“冥漠恍惚之境”为诗之“至”境,此处“冥漠”蒋寅注为“玄妙莫测”,即“境”具有不可捉摸的特征。《原诗》强调意境之妙处在于具有“含蓄无垠,思致微渺”的审美效果,为达到“至境”需调动人的多种感官,包含“可言不可言”“可解不可解”的精神感受和“泯端倪”“离形象”“绝议论”“穷思维”的情感理解过程,诗中的形式是能够被穷尽的,而形式之上深厚广阔的意义与旨趣是无法估量的。《原诗》以“境”为中心的诗之审美观几乎包含了“境”的全部效果、特征、手段和形成过程,“言浅”而“意深”是“境”的至妙所在。
叶燮所言“冥漠恍惚之境”针对“诗”所提出,最好的诗句在叶燮眼中是微妙而委婉、深厚而隐约的,不能够轻易被读者所琢磨。为使读者深入理解诗中之“境”的“冥漠恍惚”之美,叶燮列举杜甫集中四句诗“晰而剖之,以见其概”(蒋寅《原诗笺注》),即:一曰“碧瓦初寒外”,二曰“月傍九霄多”,三曰“晨钟云外湿”,四曰“高城秋自落”,诗句中以虚为实的拟物手法表现了作者具有的独特美感经验和在想象之中呈现的心理表象,“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意境感受方式只能“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蒋寅《原诗笺注》),杜甫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思维为读者理解“冥漠恍惚之境”提供诸多启发。
(三)基于“理、事、情”的含义阐释
叶燮所言意境论之通达与深刻在于他将“境”与“理、事、情”相结合,用诗之“境”论证其中的“理、事、情”。[4]47在“诗之至处”之“冥漠恍惚之境”后,叶燮又云:“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蒋寅《原诗笺注》)
叶燮“理、事、情”理论之独特在于:他能够用深妙的语言描绘日常之中无法用简单语言将其描绘的“理”和“事”,诗家之理与人们熟知的常理截然不同,既不能够用富有逻辑的表达阐释,也不能简单附和之,只能够通过“默会”的形式理解其中的奥义,说明诗中的艺术思维特征不具有逻辑性与理性。⑤“冥漠恍惚之境”是“理、事、情”相统一的想象性境界[7]35,杜甫四句诗的例子在于将超越常理的若虚若实的审美意象以诗人之理述之,使之只能“默会”,诗中意境并非写实,而是“得此意而通之”(蒋寅《原诗笺注》)的想象性描写。
意境于诗需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方知理至、事至、情至之语”(蒋寅《原诗笺注》)。叶燮着重与表达“理”之深刻内蕴,不是“理学”亦不是常理,而是在超越常理之上的具有诗歌独到趣味的“理”,是一种想象之中的富于艺术性表达的美学之原则。而在叶燮所举杜甫四句诗中也可见这“理”是不能用逻辑语言言明,也不能用理性思维去验证的“非常之理”。⑥而这正是叶燮笔下“冥漠恍惚之境”的根本特征所在,叶燮以“境”作为诗歌的艺术批评标准,实现了非理性思维中事物关系的重建,使得寻常事物具有了超越现实的艺术美,而美感也正是来源于诗人造境过程所形成的审美体验。[10]113
三、“冥漠恍惚之境”渊源追溯
叶燮在《原诗》中提出“冥漠恍惚之境”有其渊源所在。《原诗·内篇(上)》开篇曰:“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叶燮始终循着历史的路径构建他的意境论体系。
叶燮所生活的清朝时代背景使得他的思想中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叶燮与其父叶绍袁一样以儒者自居,常曰:“吾儒”,其中的理学氛围也十分深厚。[9]168明朝中叶后期,随着儒学的发展而呈现宋出明理学的衰败与“心学”的禅化,社会出现一股革新的实学思潮。在这一时期,叶燮的美学观承接了儒学发展的时代烙印,“理、事、情”中的“理”亦如朱熹的“理”,但更具体地包含了“事”与“情”在内,是“理”的实学化。由“冥漠恍惚之境”而及“理、事、情”,乃至所举宋诗四句,论述了诗人所造之境非“俗儒之作”,亦包含儒家思想的印记。
“叶燮学行宗宋人,讲理学,兼通佛老,工诗文,对创作、批评与自己的才能有清楚的意识。” ⑦佛教华严宗在明清之际较为流行,德国学者在卜松山述原诗时曾论及“理”和“事”两个概念,认为这两个概念具有相对关系,并且影响到了理学,在华严宗的体系里,“理”和“事”与“体”和“用”具有相同意义,都意味着“本体与事物”“真心与现象”“本体与现象”“自性与缘起”,形成两个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叶燮在《原诗》中论及的“事”具有较高的哲学意味,将“事”和“理”相关联而对比华严宗中的词汇用法,发现两者之间极其相似。叶燮在叙述与意境有关“理、事、情”时,确与华严宗“理事无碍观”有所关联。
叶燮将“境”与“理、事、情”相关联,突出无尽微妙的“诗家之理”,这种只能在“意象之表”“默会”的审美体验,只有在庄子所言“官知止而神遇行”的状态下才能被领悟[1]。从文本的行文特点也可见老子对叶燮的影响,如“然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之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蒋寅《原诗笺注》)两句,“以名言所绝之理为至理,以无是事为凡事之所出” ⑧,与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相合。而叶燮笔下由诗人以物而造的“冥漠恍惚之境”,似乎也是老庄审美观念展现的迷离倘恍、深邃奥秘、多样繁复、广漠混沌的宇宙万物形态的一种投射,老庄美学的“天人合一”审美意识无意中渗透进叶燮的诗论创作之中。[3]211
四、结语
出自《原诗·内篇下》的“冥漠恍惚之境”是叶燮提出的意境论观点,其中几乎包含了全部的诗歌艺术审美精神,作者通过强调诗歌为达到“至境”而调动人体的全部感官系统,在“可言与不可言”及“可解与不可解之会”的想象之境中感受意境的美妙。叶燮的意境理论建基于自身“理、事、情”的客观创作条件,并具有儒释道的思想渊源基础,在诗论创作上叶燮也遵循历史演变的诗学创作史观。《原诗》集中国美学之大成,它独特的美学体系、深妙的思维方式、富有逻辑的表达方式,使其成为中国诗论美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清)叶燮:《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第174页,第200页,第205页,第199页,第199-212页,第5页,第198页。
参考文献:
[1](清)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韩峰海.谈叶燮《原诗》的思想深度[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3):20-24+9.
[3]李天道.“大象无形”与中国美学“意境”之模糊心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05):206-211.
[4]李晓峰.叶燮“理、事、情”理论对中国意境论的贡献[J].中国文化研究,2010,(02):46-51.
[5]王向荣,连丽丽.“冥漠恍惚之境”:叶燮对诗歌最高审美理想的建构和阐释[J].绥化学院学报,2018,38(06):71-73.
[6]张长青.叶燮《原诗》的文艺美学思想[J].中国文学研究,1989,(02):19-26.
[7]章楚藩.“意境”史话[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4):28-38.
[8]赵铭善.论意境的概念及其三个规定性[J].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02):75-81+101.
[9]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D].复旦大学,2003.
[10]李晓峰.叶燮《原诗》研究[D].苏州大学,2006.
[11]戚娜.论叶燮《原诗》的诗论观及其价值[D].延边大学,2011.
[12]申钊.叶燮美学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