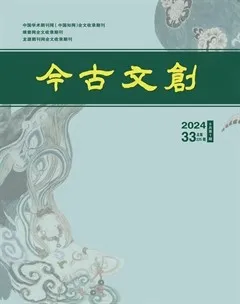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阈下《无性别的神》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摘要】《无性别的神》是央珍的代表作,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主要讲述主人公央吉卓玛的成长经历,以及她眼中的旧时代藏族女性的命运。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解读《无性别的神》,分析贵族阶层和被压迫阶层的女性形象,从女性人物的命运分析不公的社会制度、宗教的禁忌以及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切身地体会藏族女性寻求解放过程中内心世界的迷茫摸索和痛苦挣扎。
【关键词】女性意识;央珍;社会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2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07
《无性别的神》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以女性为书写中心的长篇小说[1]。其中承载着央珍对西藏大地的热爱,也饱含央珍对过去女性悲惨经历的同情与思考。旧时代的藏族妇女不仅受制于宗教制度,更受制于男权社会的统治,央珍描写了西藏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但不论哪个阶层,都逃不过社会制度的束缚。她们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而是藏族女性的普遍命运,受压迫无法获得解放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藏族女性无处寻得自我解放的路径。央珍在小说中对于女性生存环境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某个时代,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至今仍然存在。
女性主义(Feminism),是指女性为在社会和家庭中取得平等权利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的法国,目前,女性主义衍生出了众多派别,呈现多元化发展。20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想正式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期间受到广泛的关注,经过不断的发展,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随后传入西藏。西藏的藏族女性长久以来一直处于男性中心的文化结构中,始终依附于男性生存,女性逐渐失去自我意识,无法自主掌控命运,不可避免地沦为了“弱势群体”。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女性主义思想渗透进西藏人民的生活,这时候的5144624694b1531e35a6253033e9f6a04477841251c35ba6fdbb81bace6f71f1西藏小说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境况,这也促使了作家对女性形象的重新选择和多样化塑造。由于西藏社会对女性不断加深的尊重与重视,藏族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从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藩篱中挣脱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多藏族女性作家,她们将自觉的女性意识和民族身份建构融入文学创作中,表达藏族女性独特的心理体验,对不平等社会地位的呐喊以及对藏族女性身份再建构的思考。央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以现代藏族女性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融合自身特有的民族意识与女性意识,在小说中构造出一个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具有藏族特色的文学世界。
在以往的研究中,小说中对于藏族女性性别书写和身份建构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本文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与解读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意义。在小说中,作者央珍刻意回避了历史的宏大叙事,通过小女孩央吉卓玛纯真的视角讲述这一历史过程中主人公波折的成长经历,展现当时社会的风谲云诡[2]。
一、传统女性命运的抗争者
《无性别的神》主人公央吉卓玛是德康贵族家中的二小姐,出生后的第二年她的弟弟染上肺热病离世,又有云游僧说她命相不详,导致央吉卓玛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称为“没有福分的人”。从古至今,人们在面临厄运时,即使与女性没有直接联系,也总会将原因归结于女性,女性似乎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与厄运相伴而生。作者通过身边人对央吉卓玛的态度,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即使是贵族小姐也难逃“男尊女卑”制度的压迫。
小说开篇央吉卓玛失去了父亲,使央吉卓玛成了“半孤儿”,并且央吉卓玛通篇都是以儿童的形象出现,避免央吉卓玛受到夫权的桎梏。父亲和丈夫,这两个身份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通常象征着权威,央珍有意将央吉卓玛塑造为“缺父”“缺夫”的女性形象,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也为后来央吉卓玛觉醒女性意识,不断思考现存社会制度合理性,追求心中人人平等的理想环境提供现实条件。
在旧西藏时代,藏族女性被视为依附于男性生存的生育工具,除了能够提供性价值和生育价值外,并未被平等对待。在帕鲁庄园时,央吉卓玛干扰咒师施法,咒师说:“女人不能看法式、摸法袋,女人就是罪恶,女人的东西就是丑恶的,尤其是不会生育的贱妇和克死丈夫的寡妇。”[3]央珍设置这个情节来表现男性掌握“话语权”时,对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不断地强调女性在社会活动中“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央吉卓玛在贝西庄园看见女农奴拉姆被少爷用火膛中的牛粪火倒进脖子时,拉姆相比于男农奴不仅丧失了人身自由权,更失去了基本的人权,拉姆的经历给央吉卓玛带来极大的震撼。央吉卓玛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和拉姆一样无法自主地掌控命运,承受着社会带来的不平等。从德康庄园回拉萨途中“观圣湖”时,央吉卓玛深入思考是不是真的有命运?她对自己不吉利命运发出一系列追问。这表明了央吉卓玛对不公平社会的反思、对平等的渴望以及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同时,她的反叛精神和女性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初步觉醒。回到拉萨后母亲以让央吉卓玛摆脱尘世的轮回之苦的名义送入寺庙[3],寺庙的生活使得央吉卓玛对宗教和社会制度又有了新的思考,在这个阶段她不断觉醒的女性的自我意识。“铁匠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既然铁匠和屠夫是下等的贱民,为什么不管是黑头俗人还是身披袈裟的僧尼都吃屠夫杀的牛羊肉呢?”[3]央吉卓玛对于宗教文化规范的思考,反映了她的思想逐渐在冲破西藏传统文化规范和社会习俗的藩篱,为后来央吉卓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思想条件。在寺庙中师傅的关爱让央吉卓玛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福分的人,但知道母亲将自己送入寺庙是为了节省置办嫁妆的钱,央吉卓玛又感受到了消失已久的孤独。此后央吉卓玛彻底割裂了自己对家庭温情的期盼,本已找到归宿的心又变得无依无靠,但她并未放弃对幸福的追求。解放军到来后,央吉卓玛在解放军中发现女性也可以做医生并且男人也可以给女人斟茶倒水时,她想起了在帕鲁庄园咒师说的女人是脏物是罪恶;母亲说女人的责任是结婚生育,料理家务。[3]最后在解放军队伍中遇见拉姆,看见曾经受尽屈辱的拉姆,在解放军中被平等地对待,这给央吉卓玛加入解放军队伍打入一剂强心针,央吉卓玛坚定了去解放军那里学习的决心。这群来自异质世界的陌生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践行佛经上的众生平等,女性在此不用竭尽办法去争取平等自由,因为这本是女性一出生便被赋予的权利。[4]在解放军队伍中她第一次看见了佛经上所说的众生平等,央吉卓玛的女性意识彻底觉醒,她意识到这就是她追寻已久的理想生活,主人公央吉卓玛表现出了鲜明的自我意识,对于既定命运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央吉卓玛是西藏当代文学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构建了新时代的西藏女性形象,女性可以挣脱婚姻和家庭的枷锁,消解“女儿”“母亲”等种种社会身份的束缚,去追寻自我价值,摆脱“他者”处境,也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暴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对女性的戕害。
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旁观者
白珍太太是央吉卓玛的母亲,达瓦吉是帕鲁庄园庄主的养女。家中男性都相继去世的情况下,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她们面临共同的难题,家中没有男性则无法继承财产和贵族地位,噶厦会接管她们的所有财产。不论她们是否愿意,都必须安排入赘一名男性,才能保护自己应得的财产。她们是依附于男性生存的女性,是旧时代贵族妇女的典型代表。作为女性,她们承受着西藏旧时代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各种限制,但她们并未反抗,也没有独立意识,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平等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女性受害的旁观者。
白珍太太和达瓦吉同样具有典型的传统女性观念,她们将自己作为全面为男性主体服务的工具,以丈夫的话为行为准则,按照丈夫的要求塑造自己,她们是典型的被男权社会统治奴化的女性。白珍太太的第一任丈夫讨厌她吸鼻烟,她立马放弃多年爱好,第二任丈夫日日打牌不顾公事,也不打理家中事务,为了丈夫的前途,她请求母亲帮忙给丈夫捐官,还心甘情愿地在怀孕期间为丈夫处理工作事务。达瓦吉在央吉卓玛被自己丈夫处罚的时候,维护央吉卓玛说:“妹妹,快向老爷赔不是”[3],但在丈夫反驳她之后,达瓦吉也只能木然地点着头。知道丈夫苛待央吉卓玛后,给央吉卓玛拿了食物,但又怕被丈夫发现,嘱咐央吉卓玛“就在这里吃完,千万不要带回去”[3]。达瓦吉很心疼央吉卓玛,但在这个社会制度下,她没有话语权,只能唯丈夫马首是瞻。央珍塑造的西藏社会中的贵族女性形象,不仅揭露了贵族内部的腐朽没落,还进一步揭示了贵族女性的生存境况。在社会和家庭的束缚中,她们不仅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自主选择权,社会给她们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附于男性生活。
三、封建伦理下的屈辱者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下,主要的生产资料集中于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称为三大领主。三大领主的人口仅占西藏总人口的少数,而占西藏总人口多数的农奴却一贫如洗,必须忍受农奴主的剥削才能换来基本的生存。在广大农奴中的女性农奴又承受着较之于男性更为严重的压迫,央珍所塑造的益西拉姆和奶妈巴桑就是旧时代西藏女农奴的典型代表。
拉姆和奶妈巴桑具有西藏人民所特有的淳朴和温情,拉姆的出场就带着让人同情的色彩。为了哥哥的房租,拉姆成了贝西庄园的奴仆,不断忍受着农奴主的羞辱,即使有机会离开庄园,也为了哥哥留下来。巴桑作为央吉卓玛的奶妈,每当央吉卓玛被其他人称为“不吉利的人”奶妈总会站出来保护她,当德康家族败落时,奶妈带着央吉卓玛辗转多个庄园,却从未想过要抛弃央吉卓玛。她们淳朴、善良,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依旧努力生活,为了生存来到贵族家庭做奴仆,却丧失了基本的人权。
拉姆和巴桑同为在封建社会受尽苦难的女农奴,拉姆在落难时得到了解放军的帮助,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写,巴桑没有得到拯救,在德康庄园日复一日地推转经筒。她们虽然有着不一样的结局,但这仅仅是由于她们的境遇不同,小说前期二者均未觉醒女性意识。拉姆的悲惨经历是西藏解放前女性农奴的缩影,拉姆被人面兽心的少爷像牲畜一样玩弄,经常被要命地毒打。少爷用火膛中的牛粪火倒进她的脖子后,她受了很严重的伤,她没有反抗或逃走而是继续逆来顺受,央吉卓玛多次想要带她逃走,但拉姆都没有勇气接受。巴桑在德康家族没落时,尽心尽力地照顾央吉卓玛,但白珍太太接回女儿时发现央吉卓玛留着一头短发并且还说着土话,便咒骂巴桑带坏了女儿,并未对巴桑妥善央吉卓玛而心怀感恩。巴桑的儿子在运输钱粮的路途中不幸丧命,由于没有找到尸体,白珍太太便认定她的儿子私吞钱粮逃跑了,便惩罚巴桑去德康庄园推转经筒。这是长期的不平等制度与文化心理作用于个体的结果,从而导致对于不平等的高度认同。[5]拉姆和巴桑面对这些不平等的对待时并未抗争,也没有觉醒女性的自主意识,她们默认当时的社会制度,认为不平等的生活就是宿命。
四、封建社会中的智慧者
女性意识的觉醒并非仅仅指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的女性,而是在于女性发挥了本身独有的智慧,《无性别的神》中,央吉卓玛的德钦曲珍师傅便是具有女性智慧的代表,小说中多处展现了她的人生智慧。师傅带央吉卓玛上山采摘有刺的荨麻草,央吉卓玛疑惑:师傅的糌粑不够吃吗?师傅回答说:“够吃,但是我们不能暴殄天物,世上还有很多生灵在挨饿。”[3]德钦曲珍虽然身处于远离社会的寺庙之中,却仍有慈悲的济世情怀。在日常与央吉卓玛的相处之中也时时践行着“众生平等,不分贵贱”的思想,并未因为央吉卓玛的贵族小姐身份而让她不做杂事,德吉对央吉卓玛说:“你的师傅对所有人都很仁慈”[3]。师傅向央吉卓玛灌输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也成了央吉卓玛对理想生活的重要标准。
在解放军到来前,央吉卓玛对解放军队伍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央吉卓玛第一次下山找解放军,回到寺庙后师傅说:“宗教不是对真理的陈述,而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要靠自己去寻找。[3]”这更加坚定了央吉卓玛寻找理想生活的信念。央吉卓玛决定加入解放军队伍后,向师傅再次请假时,师傅已经洞悉央吉卓玛的目的,但师傅准许并且说:“我很赞赏你的精神,去吧,你去吧。”央吉卓玛与师傅道别时,也明白了师傅的用意,她的喉咙哽咽起来,只朝师傅张张嘴说不出来话。师傅平静地向她摇摇头。[3]师傅明白央吉卓玛去找解放军并且不会再回到寺院,她没有阻拦央吉卓玛,而是支持她去追求自己的信念。德钦曲珍以女性独有的智慧,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为陷入迷茫的央吉卓玛指引方向,也是她对于封建社会无声的反抗。师傅是央吉卓玛的人生导师,也是央吉卓玛最终坚定追求理想的引领者、帮助者、造就者。
五、结语
《无性别的神》中塑造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在不平等意识的社会性别观念和宗教社会习俗制约下,总是遭到压制和迫害。揭示了女性总是在面临个人生活道路选择和人生价值实现时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同时女性又没有觉醒自我意识,只得任人摆布。央珍以自觉的女性意识构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不断觉醒自我意识的今天,不平等性别观念仍然潜藏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女性在社会生存发展中仍旧存在着无法突破的桎梏与局限。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6]真正实现两性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魏春春.央珍小说创作心路历程论——以《无性别的神》的创作过程为考察中心[J].民族文学研究,2018,36(05):38-46.
[2]徐琴.评藏族作家央珍的小说《无性别的神》 [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9(04):106-109.
[3]央珍.无性别的神[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4]马歆怡.论央珍《无性别的神》中的仪式书写与成长体验[J].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3,(01):170-180.
[5]李美萍.别样的历史书写——央珍小说《无性别的神》分析》 [J].西藏研究,2015,(01).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罗茜,女,汉族,西藏拉萨人,西藏民族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