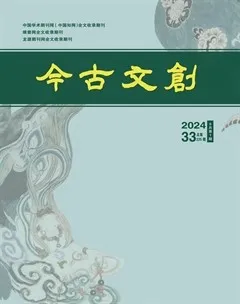小厦房里的疯女人
【摘要】回族作家马金莲是宁夏的一张文化名片,她以细腻质朴的笔触刻画了众多回族儿女的鲜活形象,2018年她凭借《1987年的浆水与酸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马金莲新作《花姨娘》通过叙述传统文化下花姨娘这一反叛者跌宕而又短暂的一生,展现出乡村女性大部分仍处于失语的状态,少数女性萌发出了积极反抗的女性意识。为此对小说中的父权文化以及在父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之间的异化与女性意识的觉醒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马金莲的这部作品。
【关键词】《花姨娘》;马金莲;女性意识;父权文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1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05
《花姨娘》是马金莲近几年众多作品中的一篇小说,作者通过“我”这一独特的男性视角,见证了花姨娘的命运的起伏跌宕。在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中,众多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抑或处于关系异化的状态,展现出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乡村女性仍然备受压抑。对此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揭示在庞大的父权文化之下,女性之间的异化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来自父权文化的凝视
在小说中,父权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小说的开篇就生动地描写了奶奶家的鸡群。奶奶撒出的粮食换来了母鸡们兢兢业业的奉献,在奶奶的精明下,没有一只偷懒不下蛋的母鸡。唯一的大公鸡英姿飒爽,叨伤隔壁挑衅的公鸡,宠爱自家的母鸡。在阴盛阳衰的鸡群里,貌似是这只英勇无畏的公鸡无私地守护着整个鸡群。实则不然,正是“阳衰”的公鸡统治着整个鸡群,正是“阴盛”的母鸡俯首帖耳的接受着规训,这个鸡群象征着当下父权社会中男女的地位与分工。作品中的母鸡,活脱脱的是一个下蛋的机器,硕大的屁股是为了更好地下蛋,圆润的体态和通红的鸡冠是为了取悦唯一的公鸡,母鸡丰满的体态与艳丽的颜色完全是为了繁殖而准备着。像小说里闫家梁的女人们一样,坚守妇德,不停地为男人们生产着。在鸡公鸡婆的分工中窥见现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女人成为男人的他者。描写鸡群是为了杀鸡迎接花姨娘,在一番激烈的追逐中,那只公鸡也终于为花姨娘的到来而献祭。花姨娘的出场,似一种含苞待放,又似花朵的舒展,总之迎合了奶奶以貌取人的观念。但是随着步调扭动的腰肢与嫩白细腻的长脖子,让奶奶在花姨娘与二爸相亲失败之后冠其以“妖女子”的名号。
在父权文化的主导下,男性都通过各种方式有意或无意地凝视着女性,凝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1]。小说通过“我”的视角描写花姨娘的外貌,“我们从不单单注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2]。这是作为男性的“我”对于花姨娘的观看,是父权文化对于女性的凝视与控制。幼时的“我”便因为沉醉在花姨娘的美貌与芬芳中,而无意识地去摸花姨娘的蛋蛋,这盛传不衰的笑话暴露出男性对于女性潜意识中的冲动与凝视。而十三岁的“我”将花姨娘的美丽与豌豆花相媲美,正大光明的窥视阳光下的花姨娘,感叹漂亮女人的美妙之处。而当花姨娘坐着飞机从外地赶回来的时候,作为成年人的“我”无需窥视,只需要坐在椅子上默默地观看,将花姨娘与她的三个姐姐进行对比,最后暗自庆幸岁月对美人是手下留情的。在我眼里花姨娘变成了一种景观,“我”都期待看见她,这是急切着去看那个景观有没有变化,每当看到花姨娘还是人群中最美的,“我”对那个景观的期待也就得到了满足。可是就是当“我”外出打工回到家中,还是想见花姨娘,可是这次的花姨娘却让“我”看她一眼,也需要鼓足勇气。没有一根头发,也没有颜色的脑瓜盖下,她那即将迸裂的眼睛认出来“我”是谁,并且要让“我”摸她的“蛋蛋”摸个够,这次我没有再举起肉乎乎的小爪子,而是仓皇狼狈的逃出门去。新疆男人将病了的花姨娘送回小红沟,不要了。对于男人来说,女人是一个物件,可以随意丢弃。这就是典型的父权文化下,女性被物化的结果。男人可以“断舍离”,女人却不行。在花姨娘从新疆飞回来的时候,花姨娘谈到她和青海男人离了。二姨娘提出疑问,反问花姨娘是否真的敢离,真的不怕吃亏。二姨夫在外与其他女人有了瓜葛,她不能像花姨娘那样一走了之,因为在她的思维当中女人就是为了男人而存在,和男人离婚,撇下孩子,女人就会无所事事,就会失去价值。在《观看之道》中,约翰·伯格这样写道:“女性把内在于她的观察者(surveyor)与被观察者(surveyed),看作构成女性身份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截然不同的因素。”[2]63不仅父权文化凝视着女性,女性自己也站在男性的立场去观看自己是否具有价值。在强大的父权制下,没有觉醒的女性是这个制度的帮闲。
二、女性群体之间的异化
“贾格尔认为,女性同自身性行为相异化、女性同自身相异化及女性之间相异化,均是女性异化的表现”[3]。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女性的压力无处释放,就把彼此作为发泄的对象,却没有注意到女性之间的情谊与共同利益,因此女性之间的关系变得扭曲,造成了女性群体之间的异化。
奶奶杀鸡的事情满城皆知,以为杀一只通人性的大公鸡来款待花姨娘,就可以将其与二爸的亲事板上钉钉,但是事与愿违。当花姨娘和二爸相亲失败之后,村里的女人们却虚情假意的前来道喜,得知事情真的没有结果之后,又口是心非地帮腔,哄好一个生气的女人办法就是无尽地贬低另外一个女人。村里的女人们以看客的姿态和轻飘飘的话语,在本来就觉得受了委屈的奶奶的心里,浇上了一勺又一勺的热油。从此之后,“妖女子”的帽子算是扣在了花姨娘的头上。转眼三年过去,花姨娘铁了心要嫁给喜家咀父母双亡还没有钱的喜喜子。娘家的姊妹几个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这门亲事,对花姨娘进行轮番攻击。“我”妈看似委屈地抱怨,大姨娘无情地附和,二姨娘满脸的嘲讽。在这些女人的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好这门亲事,因为没有一个人问过花姨娘真正的想法。当一个女人做出与世俗不同的决定,替世俗诘问她的也一定是女人。当外奶奶把花姨娘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告诉她亲家“我”的奶奶,奶奶得知花姨娘选中的不是“皇上”,而是一个家境极其不堪的“叫花子”,她心里的浊气也随之排出,还激动地拿出四碟子干果蜜饯来庆祝。两家的紧张关系也因为花姨娘的“不幸”而得到缓和。在那时候,一个女人看到另外一个女人的不幸,何况是一个让她心里憋闷好几年的女人,心里是何其的舒坦。但是花姨娘的“妖女”形象没有在奶奶的内心抹去,反而因为二爸外出打工的变得更加“浓墨重彩”。二爸的外出打工,让进门不久的二妈伤透了心,也让奶奶对花姨娘的恨意重新燃烧起来,“妖女子”的称呼不仅变成了“小妖精”,前面还加了更多的修饰词,“害死个人的”“不要脸的”“没良心的”“吃了我大公鸡不记好的”“丢人现眼的”以及“活活气死老子的”等。在花姨娘和喜喜子离婚后,二爸心中再次泛起了涟漪,二爸和二妈大吵一架,表面上没说是因为花姨娘,但是根儿上还是因为花姨娘。多年来,二妈和我妈之间也是生着一些不知名的气,归根结底花姨娘是我妈的妹妹,这样一来二妈便“欲加之罪”。但是这次吵架之后,彻夜的交谈又让妯娌二人的恩怨消解。二妈和“我”妈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年,却因为花姨娘这个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破坏行动的人,二人出现隔膜与误解,显然没有注意到两个女人之间的共同利益。
花姨娘离婚出走后第一次回家,就像奶奶杀鸡一样,满城皆知。因为这次花姨娘是有钱的花姨娘,是坐着飞机回来的花姨娘。在不得知花姨娘变有钱的消息之前,“我”妈对她的态度是淡淡的,是潦草的。当花姨娘给“我”妈打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途之后,“我”妈主动地、喜滋滋地炫耀她有个有钱的妹子,这个坐着飞机回来的妹子,可以抹平她脸上的皱纹,还可以治好她的牙疼。姐妹二人的关系因为花姨娘经济富足而解冻,即使花姨娘没有来我家来拜访,我妈还是拎着专门喂养的两只白母鸡,乐呵呵地赶到花姨娘家里去,最后带着一大包衣服和一沓子钱回来,赶紧换了一排又白又亮的假牙,逢人就呲着牙炫耀是妹子出的钱,仿佛姐妹两个人一直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这一排洁白无瑕的假牙真的功不可没,不仅缓解了牙疼,还让儿媳妇在婆婆面前挺起了腰杆。两姐妹因为花姨娘金钱上的富足,关系变得再一次紧密起来,可见在二人之间的亲情与友情已经被金钱异化。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中,女性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不再以父权文化的话语为准则,她们要为自己发声,为自己而活。小说中的花姨娘是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在那个看似自由恋爱的村庄里,媒妁之言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花姨娘却有着独立的思考,有着与世俗不同的眼光与想法。十七岁的花姨娘已经见过不少适龄男青年,但是都没能入得了她的眼。当奶奶为她杀了那只大公鸡,本来以为吃下鸡大腿的花姨娘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的儿媳妇,但是这次奶奶以貌取人的一招竟然败落。花姨娘没有收下那所谓的定金,反而将那张面值不小的钞票甩在二爸的身上。花姨娘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厚待和热情就将自己的理性抛之脑后,在家长对自己婚事的多番“强买强卖”后仍然勇于表明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的想法,坚决不做包办婚姻的牺牲品,花姨娘在婚恋自由中实现了自我超越。花姨娘选择的婚姻令众人都瞠目结舌,在“我”妈和两个姨娘的再三追问下,花姨娘却反问这三姐妹,自己嫁的男人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面对被反抛回来的问题,她们只觉得花姨娘的脑子不正常。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这三姐妹根本没有跳出男人、孩子和家庭想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她们从来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她们只得和世俗认同的男人一起生活,因为已经替她们做好了选择。围着灶台和厨房,围着男人和孩子,好也是一天,不好也是一天,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却从没有追问过她生来的意义是什么。花姨娘在这次追问中也追问了自己,这次的选择或许带有一些冲动,或许带有一些迷茫,但是这是她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别人或者谁的选择,她是为了自己才做出的选择。包括后来与喜喜子离婚,也是花姨娘为了自己做出的选择。小说还借助二爸之口,再一次说出了花姨娘的心声。女人不能为了男人苦熬接下来的后半辈子,即便那个男人是个残废,即便还有两个孩子,花姨娘在弃绝亲情中实现了自我超越。花姨娘为了一个女人的后半辈子离开了小红沟,当她再次回到小红沟的时候,已经又离过一次婚,再嫁了。第二次离婚是因为青海男人看到三个孩子稍微有点被怠慢就会对花姨娘大打出手,即便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花姨娘也不能让自己的独立人格受到一丝践踏,这是花姨娘在反抗男性中实现的自我超越。花姨娘一直都是向前看的,不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受到羁绊,也不会像兔子一样单纯地给男人一窝一窝地生孩子。花姨娘选择为新疆男人怀孩子,这不是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也不是为了拴住谁而生孩子,而是她选择了和新疆男人在一起,为了让感情变得更好才选择生一个属于她们两个人的孩子。
花姨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跳脱出传统对女性的禁锢,在本篇小说中的其他众多女性形象则与花姨娘形成鲜明的对比。花姨娘和“我”妈,这姐妹两人可谓是一体两面。如果说花姨娘勇于为自己发声,那么“我”妈便是处于失语的状态。尤其是在面对婆婆的各种刁钻与诘难中受尽闲气和委屈。马金莲的另外一篇小说《碎媳妇》中的主人公雪花,更是乡村女性失语的典型。雪花在沉默中答应这门婚事,嫁到婆家之后面对嫂子的蛮横和刁难,雪花忍气吞声,面对婆婆的冷眼,雪花也是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里,雪花生下的碎女缺少长辈们的疼爱,但是雪花还是默默地承受着。“女性世代生活在受男权制压迫的乡土社会中,来自男权社会的审视和压迫让她们在琐碎的生活中慢慢丧失了主体意识。”[4]本篇小说其他众多的女性形象和雪花一样,都深深地缺少自觉的女性意识。
当“我”最后一次见到花姨娘的时候,那是一个现实与理想激烈碰撞的结果,是惨烈,更是悲壮的。花姨娘变成了众人眼里的疯女人,被新疆男人送回来小红沟,被关在小厦房里,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兽,被无尽的黑暗吞噬着。小厦房里的花姨娘宛如《简·爱》中的伯沙·梅森被关在阁楼之上,那个“野兽的巢穴——妖怪的密室”[5]。罗切斯特说“这个疯子既狡猾又恶毒”[5],不仅捅伤了她的弟弟,还蓄意放火烧死他。花姨娘流掉当年反复用手摩挲过的肚子里的孩子,因为新疆男人有了外遇。小说中有大量的留白,没有交代出花姨娘疯掉的原因,到底是因为流产失去孩子而疯,还是受到了男人的虐待而疯,这不得而知。或者从头来想花姨娘到底真的疯了吗?如果她疯了,为什么还记得“我”,还记得那么多年前“我”要摸她的“蛋蛋”,是第一次离婚的时候抛下两个孩子所受的创伤吗?花姨娘是弱小的,她被关进的小厦房比“我”妈的年龄都大,并且阴冷阴冷的,后墙上的那道口子,是这个时代在花姨娘身上留下的一道伤。而外奶奶她们居住的房子热气扑脸,全方位显示着现代人的享受,这与花姨娘牲口圈一样的住处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着前卫思想的人被关在破旧的屋子里,像牲口一样养着,而那些固守传统思想的人却住进了时代的新屋。小厦房是父权文化的代表,里面囚禁着时代的反叛者。花姨娘是觉醒的,精神疯癫的她,发出的“邦邦邦”的声音,是与外界的对话,是她拒绝失语的表现。
四、结语
《花姨娘》这篇小说塑造了父权文化下的乡村女性面对压迫时很少能做出精神上的独立思考,思想超前的花姨娘似乎与之格格不入,沉默与压抑是她们的常态,随波逐流和盲目顺从是她们的本能。花姨娘被囚禁在小厦房里却还发出的“邦邦”声音,这是在向寂静的农村女性世界发出声响,渴望自身的经历会引起旁观者的反思与追问。虽然小说中的男性被弱化边缘化,但对花姨娘念念不忘的二爸是男性觉醒的先锋,二爸一反常人想法的行为,这也是在引导男性的思考与觉醒,摆脱父权文化的桎梏。马金莲这篇小说真实再现了传统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女性意识,呼吁女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1]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9.
[2](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
[3]马绘茹,吕颖.试论马金莲小说《碎媳妇》中女性形象性别意识缺位现象[J].名作欣赏,2021,(23):32.
[4]彭晗聪.《天黑前的夏天》中凯特的异化与自我救赎[D].武汉轻工大学,2021.
[5](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371.
作者简介:
王曼,女,河北涿州人,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