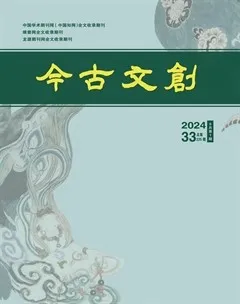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丝路古船》 : 现代海洋立场下的人物书写
【摘要】《丝路古船》以双线并行编排,明线摹写打击盗挖古船的侦察行动,暗线叙述船仔、老欧、池木乡、练丹青、郑天天等各人物的心境变化过程,交织构成了一部完整且精彩的打击“盗挖古船”案件。《丝路古船》体现出作者浓烈的海洋情结与坚定的现代海洋立场,通过摹写海洋与陆地之间的矛盾关系,呈现出强大的文学张力。本文聚焦现代海洋立场这一基点进行延伸,通过剖析作品如何通过对主要人物的书写,揭示隐藏在背后的现代海洋立场,并分析小说如何使海洋这一意象跳脱传统的单纯背景,成为行文内在线索的创新性。
【关键词】《丝路古船》;海洋立场;海洋文学;人物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1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04
海洋,作为重要的文学背景,具有其独特的魅力。现代海洋立场,即在新时代、新环境、新语境下,结合现代性思维,在认识与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所呈现出倾向海洋一端的地位与态度。《丝路古船》正是这样一部在现代海洋立场主导下应运而生的作品。小说以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将叙事布景分割为陆地与海洋,实行了有效的延展。文中的人物也依照场景之异被分割:以陆地为主战场的练丹青、钟细兵等人;以海洋为主战场的船仔、老欧、池木乡、阿兰等人;还有穿行于陆地与海洋两个场域间的郑天天。场域、人物、情节的交叉架构,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基于场域的分别,持不同的心态去阅读,从而丰富并充实了阅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阅读期待。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铺排,明显展现出海陆之间缠绕斗争、相依相克的关系。本文选取船仔、老欧、池木乡这三位小说中着墨较多且具有共性与异性的人物,并将他们分为三类形象进行分析,从中剖析李师江所彰显的现代海洋立场下人物书写的创新性。
一、船仔:纯净的海洋之子
《丝路古船》中的船仔是最能体现出作者海洋情结与海洋立场的代表。与许多作品中联结自然与人类二者的角色相似,如沈从文《边城》中由天与地灵气幻化孕育而生的“自然女儿”翠翠一样,船仔可以被认为是在海洋哺育下所成长起来的海洋之子,其生命中所体现出的本然性与壮美性,是海洋内聚的体现。他是海洋纯净本质的化身,代表着海洋的本性,即未受污染、清澈纯真、精美无瑕的本原海洋。
李师江在《丝路古船》的后记中,提到这一故事的蓝本取材于他的一个岛民朋友的真实经历。李师江称“写小说的目的也非常单纯,第一就是写一个好看得不得了的海上故事,第二,就是塑造一个海岛上自由而固执的灵魂。”[1]船仔正是“海岛上自由而固执的灵魂”。小说开篇船仔的初次登场,本身就带着一股子咸湿海风的气息。首先,在海边生活的人水性好,这是自然,但像船仔一样具有天然如此好水性的人实属罕见。船仔,似乎与晋代张华《博物志》中所记载的海洋族群“鲛人”[2]类似。这个氤氲着神话气息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眼前,这是李师江的高明之处:他借助对人物的描写,带领身处陆地的读者顺着船仔的视野仿佛也置身于大海的世界当中,使读者作为其中的参与者也进入了故事里,借船仔之眼,读者看到了神奇的龙鳗,看到了玄幻的深海,这是李师江诠释“在场性”这一概念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中,抒情者和叙述者始终与海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倪浓水据此指出:“‘遥望’而非‘在场’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描述的基本视角。海洋是一种想象和寄托的附着对象,一种‘思想性和审美性的空间’。”[3]从古至今,人们对“进入海洋”做了不同的努力,如何打破“望洋兴叹”这样的尴尬局面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层面,且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从这一角度上看,船仔这一人物的塑造,承续了这一历史传统。其次,船仔的性格也代表着海洋性格的一个剖面——自由、豁达、直接、纯洁。在古湖岛,男孩成年后,照惯例应该偷渡到美国去挣钱,这似乎是古湖岛男人的一项成年礼,也是标志他们长大成人的“里程碑”。
前往美国这样的行径似乎是逐大波随大流的无个性化表现,但事实上,这并非完全是为了塑造无个性者,相反,是通过世俗所为更加衬托出船仔身上所保有的纯净与空灵,加强了与世俗无个性者的对比度。船仔并不希望离开古湖岛去美国端盘子,他实际上舍不得这里的海。潜入海底,被海拥抱,邂逅呆萌的鱼群;偶尔遇到海底的龙鳗,能与它斗智斗勇,激战一番,这是船仔觉得舒适的生活。当少林跟船仔讨论挖掘到元青花瓷能卖出大价钱时,船仔觉得一万与一千万没什么区别,表现出对金钱的漠不关心。接着面对少林问他分到钱了之后想干吗时,船仔的回答仍然很是质朴:“我不分钱,我是来报恩的。”少林见他如此轴,索性直接问他,如果有一大笔钱最想干什么,船仔的回答是:“买条至少带两个发动机的大船”,“打鱼不打鱼无所谓,就是可以更自在,可以到鲸鱼出没的地方”。船仔以略带童话色彩的回答表明了自己内心于海洋的深度眷恋。
与一般渔民的心态完全不同,一般渔民秉承的是靠海吃海的维系方针,对海虽持有感激之情,但深层根因仍是企图依靠海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本质上仍然是基于自身获利的人类本位心态;而船仔则与此相异,从他的回答中可以嗅出他身上的海洋气息,是真正对这片大海爱得深沉,想要去探寻更加丰富的海洋魅力,以充盈自己的内心,体现出他对大海的关切,是真正的自然本位心态。
面对池木乡逼迫船仔父子二人成为“水鬼”替其挖掘古船,寻找元青花瓷的要求,船仔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因为他认为这似乎是对海洋的冒犯,同时也是对生命的亵渎。不同于父亲老欧始终将自己置于低位,船仔并不害怕凶狠暴虐的池木乡,且始终认为他与池木乡之间是平等的地位,坚持他们只是帮池木乡做事,自己与父亲并不是奴隶的坚定态度。面对池木乡的压制,船仔的内心丝毫没有动摇,没有害怕,但为何选择一味地忍让,其症结还是在自己的父亲老欧。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抗争而让父亲选择自己伤害自己,也不想让父亲因为自己而受到池木乡的虐待,所以他只能选择继续忍让池木乡。这是船仔作为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所保有的“情”与“义”,同时也是船仔海洋性格的两面涵盖:温柔隽永与刚烈无畏。
可见,小说从船仔的外貌、性格以及如何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三个方面表现出其为纯净的海洋之子。他纯净,善良,不谙世事;向往自由,热爱大海;骨子里缠绕着一股刚烈、顽强、正经的魂。在最后写给郑天天的信中,表露出了船仔对陆地的天生排斥与不信任,对“谎言”这种陆地产物的反感与逃避。倪浓水在提到“海洋”这一意象时,将海洋的描述分为:现实海洋与象征海洋,而后者显示出了更加强势的文化影响。“海洋的‘神圣-圣洁’寓意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所以每逢‘乱世’,总有人会萌生‘下海’之念:或者希望移居‘海上’,或者借‘海洋空间’来映射、反衬‘现实陆地’”[3]。李师江借“海洋之子”船仔这一人物,与陆地形成鲜明的对照,发起了对陆地宣战的先锋号角。
二、老欧:悲哀的海洋受缚者
老欧,主人公船仔的父亲。与海洋文学作品中普遍展现渔民不屈向上、奋发斗争的硬汉性格不同,李师江笔下的老欧更显出温顺纯良的一面。他淳朴善良、关怀家人。面对自己遭遇海难而去世的妻子,老欧担心她变成孤魂野鬼,纸钱烧得一年比一年多,还会嘟嘟囔囔地同妻子说话;为了船仔成年后能顺利出国,他想尽方法要赚到更多的钱,为此不惜危险也要前往马祖岛一带去捕捞梭子蟹。他恪守海事礼俗。作为有神论者,他对周围所有的事物都充满敬畏,特别是大海。虽然会受到船仔“整天伺候神鬼,就是不懂得伺候自己”的质疑,但老欧仍然默默恪守着“生活自有的一套法则”,始终坚定着对海神、妈祖的信仰,正因为此,他才有了面对大海的精神底气。
“海洋既有人可以掌握而产生美感的一面,又有人不能掌握而产生悲恐的一面,可以说这也是科学局限的一面和人生充满命运感的一面。”[4]人类的诞生虽然起源于海洋,但由于长期身处陆地,当置身海洋这一陌生场域时,往往会经历从不安到恐惧的心理变化,敬畏、恐惧、认命等情绪在此过程中逐渐上扬,促使人们对自然信仰、神秘力量进行反思、依赖,最终起到维稳自己内心的作用。但对神明的敬畏之心,亦会造成两面的影响。小说中,老欧坚信自己与船仔被池木乡所救是妈祖的神思,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更要知道如何回馈神思。因此在面对自己不想做的“盗挖”工作时,老欧依然选择听从池木乡的差遣,因为他认为,如果违抗他的意思,那就是与妈祖的神思作对,会遭遇不幸。老欧对池木乡的言听计从,表面上是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但究其思想根源,是深层次的信仰桎梏。
在染上“水鬼病”后,老欧的种种念想与行为,体现出他作为传统海上讨生者,在深层次信仰桎梏下所展现的强烈的海洋意识。他的首要愿望就是回家,因为他认为客死他乡,魂魄不归,这是比死本身更糟糕的事。他始终认为是因为挖到了海底的百年骷髅头,被鬼魂的怨气缠身才发病。他让船仔替他去桃花坞上的墓念《地藏经》,祈求能够得到鬼魂的原谅。就算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他还不忘吩咐船仔要继续听从池木乡的吩咐,继续下海帮他做事。此时,老欧受到深层思维中海事信仰的束缚,大脑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从客观而言,老欧的发病是因为没日没夜替池木乡卖命寻找古船所致,染上“水鬼病”只是迈向生命终结的导火索。老欧的一生,始于海,也终于海,一辈子被海洋与海事信仰所束缚,海洋受缚者终落得如此令人唏嘘的下场。
老欧的人物形象与海洋息息相关。一方面,老欧可以看作海洋的一面化身,他有着海洋沉稳、坚守、包容、隐忍的性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礁石一样木讷、沉默、坚硬。面对外界对他的欺侮和胁迫,他总能在内心找到一片栖息地,转变自己的思维,从而适应新的环境。而长期的海洋经验,以及父亲与丈夫双重身份的加持,更凸显出老欧身上的那股“海狼狠劲”。另一方面,老欧的身份是渔民,渔民对各种海事礼俗禁忌的敏感与恪守,是属于这个身份的鲜明烙印。
不管是渔民的本职还是后来的“水鬼”身份,与海洋的羁绊联系始终贯穿其中。老欧所从事的前后工作,经历了从主动亲近海洋到被动亵渎海洋的转变过程。在心态层面上,对海洋的亵渎行径不断拷打着老欧的内心,因为不能违背神思而选择继续“盗挖”,但“盗挖”的同时又是对海洋的亵渎,原本对信仰的无上尊敬转变为了对信仰的持续冒犯,这使老欧的内心备受煎熬,影响了他的思维与身体状况,一步一步迈向死亡。
李师江此前的海洋文学作品《黄金海岸》,精髓之处“在于人与海洋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围绕海洋所形成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在小说中获得了浓墨重彩的书写。”[5]如果说在《黄金海岸》中,海事习俗与海洋信仰起到了正向的助推作用,那在《丝路古船》中则转变为了反向的束缚。崇敬海洋的心态造成了亵渎海洋的结果,这无疑加重了文本表达的讽刺性。这一正一反所产生的张力与扩容,彰显了李师江对海事礼俗的辩证眼光。
透过老欧这一人物,展示了当原本站在海洋立场上的角色迈向另一极端时,所经受的灵魂拷打以及命运的最终沉沦。老欧与船仔这对父子,虽与海洋同脉,却走向了不一样的结局,于更深层面显示了以船仔为代表的新一代渔民和与老欧为代表的老一代渔民在对待海洋的态度、对陆地的抗性等方面的差异,彰显了李师江所立足的现代话语关照下的海洋立场,也启发读者进行思考:关于海洋与传统海事信仰,坚守的尺度应如何把握?
三、池木乡:海陆属性撕扯下的异化者
池木乡作为盗挖古船活动的二把手,是小说着墨较多的主要人物之一。笔者认为,李师江是有意将池木乡与船仔放置于两个极端进行书写。池木乡与船仔,都可视为海洋的化身,但各种原因的交叉,二者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为何说池木乡同样也是海洋的化身?第一,从池木乡的原始身份出发,池木乡出身海岛,同样也是渔民。受经济状况不佳所迫,再加上其本身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将来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但因为没有合理的渠道来实现自己所谓的“抱负”,才走上了非法走私这条“一时来钱快”的道路。走私,属于陆地习气侵蚀海洋的典型行径。池木乡在走私过程中被陆地所带来的污浊习气侵蚀,成为“海洋的叛徒”。第二,池木乡的性格暴戾,做事手段直接,常以蛮横凶恶的态度示人,也只有在面对自己的女人阿兰时,才会展现其宠溺的一面,当然这也是建立在阿兰没有影响到他利益谋取的前提下。小说中提到“女人上船,晦气一年”的航船忌讳,池木乡因为阿兰跑到船上,竟然大骂自己心爱的女人晦气,并让她赶紧从船上滚下来。种种行径都可窥见,池木乡身上属于海洋性格的另一剖面:海洋兽性。他为了聚拢团队,保证盗挖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先后将少林、老欧杀死,将郑天天囚禁于荒岛,甚至一度想要置其于死地,在这种种事件中,池木乡毫无人性悲悯之心可言。
但另一方面,池木乡在面对阿兰与阿兰的女儿之时,又不免让人意识到本质上他仍然是温热的人类,还尚存一丝人性的柔软地。池木乡的角色定位可视为“被陆地所污染的海洋之子”。阿米蒂奇指出,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陆地上,因而对陆地的依恋情绪比对海洋要深。这种心态被称为“陆地中心主义”。“长期以来,‘陆地中心主义’在人的大脑中根深蒂固,海洋被看成是与陆地对立的、险象丛生的、充满敌意的场所。”[6]但在小说中,相较于海洋,陆地更是险象环生、风险迭出的不洁危险之地。他刻着海洋兽性的烙印,在主动与被动间与陆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灵魂在陆地与海洋的矛盾场域中不断被撕扯摩擦,最终沦为了如此畸形的异化形态。
李师江立足于反向角度,通过对池木乡的书写,诠释了他坚定的海洋立场。通过陆地对人的异化,将陆地与海洋的矛盾聚焦于池木乡这一主体进行展开。池木乡的人格发展过程,象征着“陆地习性”与“海洋本性”从互相制衡阶段逐渐过渡到二者失衡的阶段。“陆地习性”指追求世俗欲望、必须坚持弱肉强食方针才能存活下来的心流体现;“海洋本性”则是自由无拘束、纯洁、不谙世事变迁的本原人格。“陆地习性”在此过程中占据上风,“海洋习性”逐渐被消磨殆尽,最终平衡完全被打破,池木乡也在此时完成了“异化”的全过程。
根据西方“万物链”的观念,每个生灵都有自己在固定的位置,不能随意更改,如果其中一环发生了异化,那整个宇宙的秩序就会紊乱,世界将会崩塌。在这条“万物链”中,人类因为具有部分的理性,与在其上位的天使有所类似,但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更是与“万物链”之下的兽类相似。人如果努力践行诸如忠诚、希望、节俭等美德,则会趋向天使;而如果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附着贪婪、嫉妒、暴怒等负面属性,就会使自己异化为野兽。为了陆地上美好的缱绻,任由自己无节制的“陆地欲望”不断膨胀而选择冒犯海洋,池木乡的“异化”已有端倪。在海陆属性相互撕扯的过程中,池木乡以诡异的形态进入海洋,背离了海洋的情感基点,最终迈向终结的深渊。在“万物链”中,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模糊,连作为人类所带有的部分理性也完全抛弃,彻底沦为了野兽,最终毫无节制地堕落下去。
四、现代海洋书写:回归生命本源的写作
“时代的认知装置和文化精神决定了文学中海洋书写的不同形态。”[7]在新时代、新环境、新语境下,李师江是如何结合现代创新思维,在人物书写这一环节来彰示现代海洋立场,创作出具有现代海洋立场的海洋作品呢?
李师江笔下的海洋已经被赋上了“泛浪漫主义与现代化”的意蕴象征。海洋,作为精神原乡,呼唤着爱与自由的回归。“大海之子”船仔爱海爱得深沉,由于海洋立场的强烈统摄、对自由的向往与远离复杂的淳朴心态,使他最终拒绝了郑天天对他的“补偿” ——让船仔在学校继续学习,之后投考体育专业的安排,同时也毅然决然终止了与郑天天青涩的无果邂逅。郑天天作为小说中穿行于陆地和海洋两个场域的人物,身上更多沾染的是陆地的气息。李师江非常巧妙地通过一种“离岸”行径,通过二者的交往,将带有陆地元素的郑天天与充溢着海洋元素的船仔融合起来,显示出一种重组还原的力量。而同时,海与岸也构成了一组指涉关系,并且依靠理性达成和谐,海的纯净最终收服了岸的繁杂。从海-岸关系的融合与对弈,上升到了生命复归本源的层面。安排具有海洋纯真品质的船仔带领郑天天回归大海,让幼时丧母的郑天天寻找到了回归子宫的感觉,从而体会到了海洋对她的疗愈效果。如小说写道:
郑天天好像回到子宫,被羊水包围着,温暖着,重力的消失,使得人极为放松,但是因为在水底下,思绪完全集中到眼前,心中万事消散,内心瞬间是前所未有的放松。是的,自己觉得那颗满是伤疤的心,此刻像海绵球,柔软死了。她猛然感觉到,自己被治愈了。没有潜过水的人,不晓得海底的妙处:那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也许是自己刚刚出生的那一天。
在这一层交往中,蕴含着两层复归的含义:一是人作为独立个体对生命母体的复归,二是人作为自然生灵对生命根源的复归。作为人类生命本能的对应物,海洋与母体在此刻联结在了一起,共同代表着生命孕育的场所。而在这段叙述中,人类也抛弃了智慧生物的高等身份,参与进了一众生灵之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李师江巧妙运用人物经历与人物性格的双重聚焦,不露声色地将海洋立场糅合至人物的内核之中,现代海洋立场下人物书写的创新之处可见一斑。
在陆地上的经历让安于纯净大海已久的船仔需要反复去消化这段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与郑天天的无果邂逅,船仔浅尝到了短暂的欢愉,但更多的还是体会到了人世的险恶,最终在陆地与海洋的两端选择了背向陆地,重归大海。这是李师江为船仔铺设的最美结局,也是人类归于海洋这一最终结局的艺术想象延伸。小说最后安排了时隔多年后,船仔短暂重归陆地与钟细兵相遇。已近中年的船仔仍然是孤身一人,而且总觉得人们会欺骗他,对人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选择不相信任何人,强行遗忘过去、强行抽离记忆的笼罩,以至于“说话”这件事情对船仔来说都十分困难。经过“丝路古船盗挖事件”后的船仔,被“失语”与“失忆”双重捆绑,其当时的状态就像在鱼缸中的金鱼一般,宽广的海洋实际上是船仔身处小小“鱼缸”的放大投影。
诚然,在现代话语体系下的海洋文学、海洋书写等基于海洋为理论背景的创作与研究逐渐被纳入学科交叉视野,并产出了丰富的成果。在此过程中,各路作家也逐渐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内核立场。海洋立场作为现今全球化视野下尚可继续深入挖掘的文化心态,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度与拓展辐射性。“海洋既是一个充满现代性魅力的理想他者,亦是现代中国自我体认和自我想象的未来形象。”[8]在中国当代文学,像《丝路古船》这样通过人物书写来进行具象化诠释海洋立场的写作依然可以作为继续延展的优质创作领域,对于构建现代化海洋意识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值得我们继续探索下去。
参考文献:
[1]李师江.丝路古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2](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倪浓水.中国海洋文学十六讲(修订版)[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
[4]张法.怎样建构中国型海洋美学[J].求是学刊,2014,41(03):115-123.
[5]周荣.海洋风景与地方传统的审美书写——以南北方地域经验为视角[J].海峡文艺评论,2023,(03):18-22.
[6]王松林.“蓝色诗学”:跨学科视域中的海洋文学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46(03):35-43.
[7]周荣.海洋风景与地方传统的审美书写——以南北方地域经验为视角[J].海峡文艺评论,2023,(03):19.
[8]彭松.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海洋热[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09):124-133.
作者简介:
李昌达,男,汉族,广东汕头人,福建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