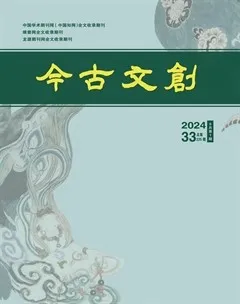从《野草》中不同的“自我” 意象看鲁迅的抗争精神
【摘要】《野草》隐含着鲁迅的抗争意识,用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和极具想象力的意象记录了诗人的自我探寻历程。《野草》中的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通过对自我及存在的“碎片”地拼凑和组合,呈现了诗人完整的精神世界。将《野草》放置于它所形成的历史条件中分析尤为重要,了解鲁迅所处的现实背景和人生遭际更能感受其内心的苦闷、寂寞、怆然,更深刻体悟诗人孤注一掷的反抗。通过对鲁迅生命中“抗争精神”的挖掘,感受他作为先锋者和探索者的艰辛与不屈,体悟鲁迅对生死问题的彻悟。
【关键词】《野草》;鲁迅;意象;抗争精神;生命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03
《野草》是鲁迅表达其内心复杂思想的一个特殊的精神产物,以形式独特的散文诗集面世,道出了诗人感性而挣扎的灵魂冲突。受西方象征主义思想的激发,鲁迅早在1919年就发表了散文诗集《自言自语》,其中就有《野草》集中某些篇目的原型。《野草》所带有的象征主义色彩不仅是鲁迅在创作技法上的运用,更是他超越现实与死亡对话时的自觉选择。鲁迅对于生命中对立命题的思索通过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用做出不同选择的“自我”来暗示现实处境中生存的困境。本文从《野草》的成因出发,关注鲁迅在创作前与创作中的精神历程,探讨其“反抗哲学”的生成,发掘诗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①的人生哲学。
一、自我和意象:《野草》的成因
(一)危机与治疗
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鲁迅在创作《野草》之际遭遇的精神危机,已被学界所注意。钱理群认为从《呐喊》到《彷徨》《野草》,表明了鲁迅的心理状况“从启蒙的外部危机转化为自己生命的内部危机” ②。汪卫东则将鲁迅精神危机的时间定格在了1923年,认为该年“应是鲁迅人生的最低点……就是鲁迅第二次绝望的标志。” ③细数鲁迅在这个时期所经历的困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新月派”的围剿、数起政治惨案、兄弟决裂等,使鲁迅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都发生着巨变。鲁迅于文艺刊物上的失意,可以追溯到创办《新生》的失败,当自己的“呐喊”再一次没了“着落”,那熟悉的荒原放逐感再一次袭来,悲观的思绪将鲁迅导向了自我怀疑与反省。而1923年7月的一封兄弟“绝交信”,更是直接打击了鲁迅的家族精神寄托,改变了对隐含在情义和温情背后的人性的看法。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原本激昂的战叫已然衰微,“五四”落潮带给鲁迅深刻的怀疑和失落,时代风向的飘忽不定也让他踌躇难行。鲁迅的心灵深处存在的两难困境与心结,以潜意识的写作来释放,难以与人言说的心绪纠葛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治疗”。鲁迅通过《野草》的创作,不仅是对自己内心的清理,也是对自己心灵世界的一种认识与梳理。
(二)释放与对抗
鲁迅于精神危机中创作出了《野草》集,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其中,把处于矛盾、分裂、痛苦中的自我投射在诗里,塑造了一系列带有主观倾向的自我意象。张洁宇把《野草》看作是鲁迅的一组“自画像”,认为其中存在着观察者鲁迅和一个被观察的“自我”。张洁宇采用画家与模特之间的关系言说,诗人“我”既是画家也是模特,在观察的同时也在被观察,由此构成了既同一又分裂的关系。鲁迅以文字自画像的形式解剖自己,抒写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自我,创造一种对自我的全面且清醒的认知。
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④具有强劲生命力的野草生长于滚滚地火之上,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它们自有一方天地。尽管地火将一切烧尽,直到无可腐朽,“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⑤鲁迅在《野草》的自我生命体味过程中,参悟到了人生的哲学,他要以一种无所畏惧的姿态面对黑暗和死亡,以一种由死观生的抗争精神来探索生命的意义。
二、抗争精神的意象表现
(一)孤独抗争
《秋夜》描写了出现在诗人“后园”里的诸多意象,“枣树”作为从开篇一直到结尾都出现的形象,成了诗中的关键所指。枣树是果敢和睿智的,他敢于发起挑战,善于自我保护,他也明白小粉红花的梦纯真但虚妄。枣树以战士的姿态直立于天地之间,挣脱一切负累,因为当叶子落尽,只剩光秃的枝干时,枣树才露出他本来的面貌。即使只有枝干,但他依旧“欠伸得很舒服”,没有了叶子的牵累,他才更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在这里,读者不仅能观察到枣树与天空对峙的场面,还可以从意象的选择上看出诗人的情感指向。枣树的形象是被诗人所认同的,充分显示出其作为精神界战士的抗争精神,隐喻着现实世界里的启蒙者,是与“黑夜”意象群相对抗的意象群的核心代表。
《影的告别》是《野草》的第二首散文诗。这首诗可以说是整部《野草》中自我分裂倾向最明显的一篇,“影”可以看作是获得了某种主体性的存在物,通过“影”的告别暗示了“形”与“影”的对立。从这一点上可以推断出,“形”是一个未觉醒的个体,也正因为如此,“影”才会如此坚决地与“形”道别。“影”孤独地在世上游旋,还要防备随时可能来临的死亡,如同先觉者感受到无路可走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觉醒的“影”指向了鲁迅本人,“影”的徘徊隐喻着诗人的彷徨和犹疑。但是“影”一直是清醒的,他辨别出虚假与真实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影”选择了黑暗的归宿,他愿意独自承担这黑暗,“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⑥“影”主动背负着黑暗,其强烈的生命意志使个体的生命也极具价值意义。鲁迅通过“影”的自我放逐来实现对现实的反叛,体现了自我承担和自我牺牲的某种英雄主义倾向。
(二)韧性抗争
在写作《这样的战士》之前,鲁迅就已在社会文化论战中独自作战,身心疲惫: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学衡》派论战、与胡适的“整理国故”派论战、与章士钊的《甲寅》杂志论战、与“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论战等等,《新青年》伙伴的分道扬镳更加重了鲁迅的生命孤独感,但无论情形如何,他依旧举起那投枪,作永不妥协的战斗。在《这样的战士》中,我们看到了鲁迅的战斗激情,他那激昂的、永不妥协的韧性抗争是面对敌人的态度,而诗中的敌人开始有了明晰的对象:慈善家、学者、文士……学问、道德、国粹……在战士这面看来,他们是狡猾的,使用的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用“点头”使抗争者无处着力;他们也是虚伪的,偏心却自证心在胸膛中央,有时将自己也欺骗过去。但是,具有高度警觉的战士识破了敌人的伪饰,他举起投枪然后正中敌人的心窝。也许投向了无物,也许未伤及敌人分毫,但战士要以这种姿态扰乱敌人的心绪,他也用决绝的态度作自我的抗争,在自我悲剧命运的承担中把握自我、超越自我。
《过客》中“前面的声音”是过客的引向标和继续求索的支撑力量,它激发了过客的探索欲望,也是蕴藏在过客心灵世界中的一种人生信念。过客就如“枣树”一般,女孩的布施是压弯枣树枝干的叶子和果实,只有一个无所牵挂的战士才能使出他的全部力气,把战斗精神贯彻到底。切断情感的羁绊,过客孤傲地前进,他得知前方应该是坟,坟之后也许没有路,这样行走下去就是走向死亡,然而走向死亡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死亡的反抗和超越。可以这样理解,“死亡”代表终结,“走”却留了下来,“走”这一行动留下了坚实的“足迹”,这是有触感的、可以被明确把握到的,凸显了某种肯定与恒久。因此,“走”的过程就是使生命充实、使之饱满的过程。过客“走”之精神反映了鲁迅的生命哲学观,尽管走的过程会历经险阻、走的终点不过是死亡,但是不能停滞,要以永远的“走”的姿态抗争生命的终局,这就是“过客”精神。就此,死亡的威胁和带来的恐怖再不能将鲁迅捆缚,呼唤过客继续走的“前面的声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光明与理想,而是鲁迅灵魂深处奔流不息的生命追寻。
(三)死亡抗争
死亡的意象贯穿了整部《野草》:有秋夜里主动赴死的小青虫、沉没于黑暗的“影”、复仇的鲜血和杀戮、苏醒的死火、只有知觉的死尸、道路前方的“坟”和坟上的墓碣文。鲁迅采用一系列意象来对“生与死”的哲学命题进行探讨,并且通过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刻思索,对“死亡”有了新的诠释和概述。
《死火》中有这样一个生死两难的处境:“死火”继续待在冰谷中,他将冻灭;若走出冰谷永得燃烧,他将烧完。这是作者绝望且悲凉的生命哲学在“死火”意象上的凄美演绎,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死亡是必须面对的终极命运。但是,走向死亡的人生中仍然有主动选择,“死火”忽地跃起于冰谷外,他不甘心悄无声息地冻灭,选择在燃烧的炽热中把握自我的存在。“行动”肯定了人生的价值,正如“过客”明知前方有的不过是“坟”,却依然坚定地向前走,因为他清楚死亡无法摆脱,而他也有面对的勇气。诗人明白生之悲哀,但又在沉痛与悲哀中获得了某种超脱。
墓碣文实是逝者的墓志铭,鲁迅写作《墓碣文》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告白,这个告白是他直面死亡,在与死亡的“对谈”中完成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⑦墓碣的阳面由四个充满悖论的排比句让“游魂”的形象再次浮现,而这“游魂”化作毒蛇啃噬自身,造成了自我的灭亡。墓碣的背面是墓主人空洞的尸身,他的死因不是他人造成的,而是在自我解剖、噬其“本味”中悲惨地死去。墓主人和“长蛇”一样,都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为了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选择了更为惨痛的自我解剖。这两个形象都指向了在绝望挣扎中的灵魂,毒蛇的自啮、墓主人欲知本味,都象征着鲁迅自我审视、对生命底色的探寻与追问。死尸自啮而亡,然而“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⑧“成尘”首先指向了“有”,死尸的“成尘”证明他生命的实有而非虚空。死尸的出现是对过去生命的一种肯定,于是“死亡”并不呈现出绝对的黑暗。在诗的最后“我”还是逃离死尸,也即逃离死亡,这里表现了诗人对“死亡”的否定态度,但也透露了“我”对墓主人这种死亡的赞同。因为他的死亡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于是“我”要离开此地、也即离开梦境,回到真实的世界与属于自己的黑暗做斗争。旧的存在应该灭亡,否则无法促成新生,墓主人的死亡是抗争的表现,可以看作有光明内在于黑暗之中。
三、思考与回顾
(一)冷静的审视
要以何种方式去战斗,鲁迅对此有深刻的思索。在《野草》里有许多象征着外部混沌环境的意象,如闪着鬼眼、又高又静穆的天空、四面的灰土、所谓世界的造物主等等,这些意象的设置让《野草》不只是表达出诗人在个体存在中的矛盾,而且反映了这些矛盾或多或少与外部世界牵连。正是在现实处境的重压下,诗人对正义斗争的方式进行摸索和探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中心命题就是对斗争方式的思考。“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 ⑨“只要这样”是奴才的自我麻痹和无所作为,“只能这样”则体现出奴才无法依靠自身来实现“觉醒”的无奈。诗人并非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批判奴才的落后,而是在思考奴才是否有获得觉醒的途径和机会。
从《野草》的整体性来看,鲁迅的斗争精神绝不是不顾一切、蒙头直进的冲刺,妄想将敌人一击即溃并不符合社会现实,而改革者的悲剧命运也在使鲁迅时刻警惕——取胜的道路还很漫长。那么如若反抗的力量还很弱小,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先得是正视现实,反对瞒与骗的自欺欺人,反对闭着眼的“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⑩。正视现实才能变革现实,“正视”显现着主体的巨大勇气和胆识,这是一种建立在人之主体性之上的担当。
(二)走向“新生”
《野草》的最后两首诗是《淡淡的血痕中》和《一觉》,这两篇写于结尾的“呐喊”之诗,使《野草》在历经失落、悲哀、绝望、虚无后重新定下了积极的尾调。需要注意到两首诗的写作时间——距离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不到一个月,青年们的受难和惨死对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诗中不仅可见鲁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还可见他在悲愤洗礼下向着光明前行的愈发清晰的信念。
在这两首诗中明显有“他者”的出现,这表明诗人的写作目的不再纯粹是对自我困境的反思,因为在现实的斗争中,诗人看到了真正投身革命的启蒙战士,他们或将是劈开一切的希望。鲁迅对青年启蒙者的觉醒和奋起发出欣慰的感叹,在《一觉》中引用具有“点睛”之效的“野蓟”意象,这是鲁迅与托尔斯泰在“以生命之力为美”的观念上发生的强烈共鸣,是对神圣不可摧折的“生命之力”的惊奇和感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纯真又愤怒的青年魂灵的感召下,鲁迅或许又重新找到战斗的同盟者。
四、结语
对鲁迅而言,他的生命体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个人情感、社会现实、思想探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在反思过程中,这些因素又会慢慢渗透到《野草》的艺术创作中,再加之象征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主客观结合的抒情体式。《野草》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代表了先觉者审视自我的不同侧面,在多数此类形象中我们探求到了鲁迅的抗争精神和生命哲学——无论生着还是死去,他要与一切不平对抗到底。“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5ea882fc47d86a96cf4c7a8f2a7fd96f992d521ffd75844a751c5fb29f2ee340”通过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鲁迅把生命支点放在了“空无”之上,把生命的脚步迈进坚实的土地里,像“过客”一样永不止息地向前走。因为求生或怕死而止步不前没有任何意义,“粗暴的魂灵”需要出现也正在出现!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⑨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钱理群:《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页。
③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⑩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1]张洁宇.审视,并被审视——作为鲁迅“自画像”的《野草》[J].文艺研究,2011,(12):67-76.
[2]任毅,陈国恩.《野草》:焦虑及反抗哲学的实现形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8):43-51.
[3]蒋济永,孙璐璐.鲁迅的精神危机与《野草》的书写治疗[J].广东社会科学,2020,(04):171-177.
[4]孙歌.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散文诗集《野草》析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9(01):47-61.
[5]李玉明.关于鲁迅《野草》的几个意象的解析(一)[J].东岳论丛,2005,(02):1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