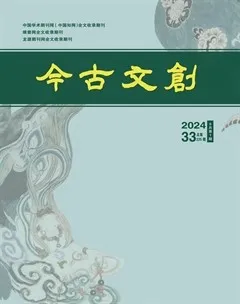论《雷雨》人物的双重悲剧意蕴
【摘要】《雷雨》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成名作,也是开创中国现代话剧的基石之一。剧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或死或疯的结局,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家庭和阶级的多重矛盾,既批判了旧时代的悲剧性,也叩问人类存在的意义。本文将从剧作的时代背景和悲剧内核出发,探索剧作人物的双重悲剧意蕴。
【关键词】《雷雨》;死亡意识;现代悲剧;存在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02
《雷雨》是曹禺的现实主义之作,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悲剧意识的重要奠基。作品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描写了一个封建主义旧家庭延绵两代人、引发劳资冲突的情感纠葛,并最终走向覆灭的故事。剧作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或死或疯,或孤独地苟活下来,忏悔身为始作俑者的罪孽。他们的悲剧命运来源于个人的过失和他人的戕害,来源于旧时代结构性压迫,也来源于超越时代的个体存在危机。因此,《雷雨》的悲剧意蕴既有时代性的特质,也蕴含着人类个体的存在主义危机。
一、无路可逃的历史性悲剧
《雷雨》遵循戏剧创作的“三一律”,情节设置十分巧妙。周公馆内的矛盾暗流涌动三十年,却在短短一天内突然爆发,将戏剧冲突推向白热化。各个人物的命运也在如此尖锐的矛盾下,进入到无法避免的悲剧螺旋。
剧作涉及两代人,人物关系非常复杂。按照人物的代际关系来划分,上一代人有:周朴园、蘩漪、梅侍萍和鲁贵;下一代人有:周冲、周萍、四凤和鲁大海。其中,周朴园和蘩漪可以被视为作品的“悲剧核心”。所谓“悲剧核心”,一则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也应当是最后承担者;二则是作品悲剧性的最集中体现。
(一)周朴园:从受害走向加害
周朴园是串联两代人和公馆内外的核心人物。在内,周朴园是周公馆不可撼动的绝对主宰者。他对待妻子独断专行,严苛地要求两个儿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大家长。他病态的控制欲使蘩漪绝望,进而引发了继母和继子之间的不伦之恋;他多年前无情地抛弃梅侍萍,让自己的亲生骨肉鲁大海流落在外,还间接造就了四凤和周萍的爱情悲剧。在外,周朴园是血腥冷酷的官僚资本家。他故意让承包的江堤出险,淹死了三百多名小工,贪污了他们的死亡赔偿金,狠狠吃一笔人血馒头;他勾结警察,官商相护,血腥镇压罢工,还毒打前来谈判的工人代表鲁大海。他是全剧封建性和资本主义剥削性的集中体现,是其他角色压迫的直接和主要来源。倘若没有周朴园,周萍不会和蘩漪发生不伦之恋,和四凤的爱情也不会不明就里地走向悲剧;堤坝上的工人们不会无辜罹难,当年的儿子,如今的工人代表鲁大海也不Sipv89U2zGDwjMhkEEud3w==会闯入周公馆,直接引爆埋藏三十年的所有矛盾。尽管故事展现的是“周公馆世界”的坍塌,但毁灭的祸根却是由周朴园在“外部世界”种下的。
同时,作为始作俑者,周朴园也同样是封建家长制的受害者。三十年前,还是少爷的周朴园,爱上了低微的女佣梅侍萍。当年的两人感情甚笃,并且受到了周公馆长辈的默许,生下了两个孩子。但梅侍萍没有逃脱被始乱终弃的命运,最终抱着刚出生的鲁大海被赶出了公馆,成了周家家族联姻的牺牲品。这一次冲突是封建家长制对周朴园的驯化与打压,他选择了向既有规则低头。三十年后,周朴园最终成为周公馆的掌权人,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身份转变。
毫无疑问,周朴园是封建父权制的异化品,但这个异化品也会怀念曾经残存的美好人性,怀念少年时与梅侍萍的感情。对此,作者曹禺这样评价道:“他两次婚姻都不如意……回想起来,还是和侍萍相处的日子,在他罪恶生涯中多少给他留下了些美好的记忆。”周朴园的存在和堕落,本身就是吃人旧社会的最好例证。
(二)蘩漪:从反抗走向毁灭
蘩漪身上充满了时代赋予的多重矛盾,并且比周朴园更复杂、更尖锐。这既造就了角色本身“既病态又崇高”的人格魅力,也是她悲剧结局的根源。蘩漪接受过一些“五四”新思想的熏陶,个性张扬自我,向往平等的爱情。可是她却生活在周公馆无比压抑的空气中,多年来不得不屈从周朴园的压制。蘩漪的生命力已经被压抑到扭曲,继子周萍是她脱离苦海的最后希望。她病态地追求周萍,不顾伦理与实际,只为抓住救命稻草。极端的抗争固然可能招致灭亡,但却是蘩漪唯一可以做出的反抗。一些读者常常批判她的冲动与浅薄,可曹禺却在《雷雨序》中无不悲悯地写道:“蘩漪的可爱正是来自她的不可爱之处。”
但这种“可爱”无疑是危险的。蘩漪,这位性格刚烈的女子,在周公馆的压抑氛围中不甘心默默凋零。她以生命为筹码,坚定地选择了反抗与报复。在这种决心的驱使下,她自然不会顾及那些无辜者的命运。她诱导周萍陷入不伦之恋,期待他能带自己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然而,周萍的懦弱与无能,使他无法回应蘩漪的期望,转而将感情投向了四凤。面对情人的背叛,蘩漪因爱生恨,阻挠二人私奔,并当众捅破了自己和周萍的私情。甚至连她的亲生儿子周冲,都被当作阻挠周萍与四凤爱情的工具人;承认与继子私情的那一瞬间,蘩漪也无情地撕毁了自己母亲的形象,丝毫不顾及儿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她的极端反抗葬送了她最爱的儿子,更葬送了自己。
作为《雷雨》的悲剧核心人物,周朴园和蘩漪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对人性的毁灭。其他角色虽然不是核心,却也都充满旧时代悲剧性的烙印。例如梅侍萍和四凤这对母女,她们是社会底层劳动女性的写照,勤劳、善良、朴实,却又先后陷入与豪门阔少的情感泥沼,难逃始乱终弃的命运。三十年后的四凤与周萍,和三十年前的梅侍萍和周朴园形成对照,都是一对为世俗所不容、被时代所不容的悲剧爱侣。周冲是曹禺理想化人格的外现,单纯美好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他仍然背负着家族带给他的原罪,戏剧的结尾,当他试图和鲁大海以拉手的方式化解恩怨时,却被后者无情拒绝了。他们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却被旧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划开了血海深仇。
二、人类生存的悲剧性内核
《雷雨》角色走向毁灭的结局,不仅仅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也蕴含着某种人类生存永恒的悲剧性内核。这将剧作的悲剧审美从单一的鞭挞旧时代、旧家庭,上升到了对生命意义和存在性命题的叩问。这是对剧作所依托时代局限性的超越,也是悲剧内核从个性向共性的提炼升华。即便跳出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仍然充满种种不可预知与不能把握,这样永恒的悲剧性赋予作品更深一层的哲学意蕴,使《雷雨》区别于同时代其他批判旧社会的作品。
在情节创作上,曹禺突破了一般的“性格悲剧”或者“时代悲剧”,将探索的笔锋指向生命的终极答案。早年人生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宇宙的苍凉与个体的渺小,以为人无法把握住命运,无法与未知抗衡,最终导致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永恒悲剧性。《雷雨》诸人中,性格、身份所代表的阶级各不相同,但曹禺却无一例外地赋予了这些角色以悲剧结局。他在序中这样写道:“《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曹禺的生命观是悲悯的,涵盖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生命状态,平等地赋予他们存在主义困境。这样的无差别处理,充满了某种宗教意味。在这层意义上,周朴园、梅侍萍、蘩漪、周冲、周萍和四凤,导致他们悲剧的并不是特定的时代或者事件,而是某种不可逃脱的宿命,是充满必然性的。
因为无法认知自身的存在,所以也难以超越悲剧性结局。全剧八个角色,各自有各自的所求和欲望;并且越求不得,渴望就越强烈,宣泄的手段就越极端,彼此纠葛成一个命运的漩涡,所有人都在求而不得的渴望里沉沦。以蘩漪为例,作为一个骄傲又接受过新式思想的上层女性,她渴望爱与被爱,渴望独立自由的人格;但在周公馆极致压抑的氛围里,她连为人最基本的自主和自尊都被剥夺了,于是转而将被压抑的渴望投向软弱的周萍。蘩漪爱上周萍,并不仅仅是渴望救命稻草,更是对周朴园压迫的转嫁。她以为周萍是一艘易于掌控的方舟,可以载着她泅渡苦海,却万万没想到周萍会爱上四凤。这不仅仅是两女争夺一男的俗套戏码,更是对蘩漪生存希望的最终毁灭,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因而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烈爆发。
再说周萍。在戏剧序幕的独白里,他就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与纠结。周萍从小失母,生活在周朴园封建大家长绝对的专制之下,造就了他软弱逃避的性格,进而酝酿出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与其说这场不伦之恋是出于周萍对蘩漪的爱,不如说是出于对父亲的反抗,尽管是见不得人的、窝囊的反抗。发生关系后,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背负上了沉重的罪孽感,急于寻求一个赎罪和解脱。于是他将这一愿望投射向单纯美好的四凤,渴求得到救赎,但这不过是父母三十年前爱情悲剧的重演罢了。周萍是个软弱的男人,既没有勇气反抗父亲,更不敢冲破家庭牢笼,放弃周家大少爷的身份与四凤私奔。四凤不是他的救赎,只是黑暗中一丝微弱的希望罢了。后来二人兄妹身份曝光,四凤惨死于雷雨中,连这最后的光芒也泯灭了。走投无路的周萍,最终不得已选择自杀。
其他角色的剧情走向,同样遵循“渴求—求而不得—激烈爆发—崩塌”的模式。周朴园几十年来苦心维护家庭的秩序,周公馆却在一夜之间埋葬了三个冤魂;梅侍萍早年被爱人始乱终弃,在底层挣扎多年不过是想求得一个命运的公平,却最终成了教堂医院里痴呆的鲁妈。在《雷雨》的世界里,卑微者如梅侍萍、四凤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看似高高在上、掌控他者的周朴园,最终也无法逃脱命运的回旋镖。所有角色仿佛都陷入了绝境,并非是改变某个决策所能避免的,而是欲望在现实围剿下的必然失败。《雷雨》的戏剧冲突,不仅是父辈与子辈的冲突、上层社会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更是个体与不可知命运的冲突。所有的抗争都付诸徒劳,所有的愿望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是《雷雨》永恒的悲剧性美感。
三、诞生于旧时代“雷雨”中的中国现代悲剧
《雷雨》的悲剧意蕴是极其丰富的。这是因为它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悲剧的情感内核,更成功借鉴了西方悲剧的本质特征。它不仅仅局限在对特定制度或时代的鞭挞,局限在对个体悲剧性命运的勾勒,更上升到了人类存在意义的高度。这是《雷雨》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悲剧的开山之作的原因。
(一)继承:旧式伦理困境的延续
《雷雨》是一出旧家庭的问题剧,也可以说是一出情感与伦理博弈的戏剧。故事中有两对经典的“少爷与丫鬟”的文学形象,本来就极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色,典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晴雯。少爷和丫鬟间颇具矛盾与张力的关系,作为文学意象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创作中,不乏这一组经典的文学形象的身影。例如在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中,受到新思想熏陶的开明少爷觉慧爱上了丫鬟鸣凤,但这份感情只停留在了浅薄的怜悯和感动。当鸣凤要被高老爷许配给老男人做小妾时,觉慧不敢站出来为了鸣凤的命运抗争,最终导致鸣凤悲惨地投湖自尽。再如张爱玲的作品《郁金香》中,陈宝初和陈宝余两位少爷都先后对丫鬟金香产生过爱恋,却没有一人以实际行动为她负责。对比《雷雨》中的两位少爷和丫鬟,可以归纳出他们爱情悲剧的共同根源:阶级的悬殊对立,以及“少爷”本人的自私幼稚,软弱而无担当。“少爷丫鬟”叙事的经久不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父权社会下女性个体必然依附于男性的事实。周朴园的资本家身份,其实也是由大地主转型而来的,因而言行举止都充满了封建地主的习气。即便是作品中的“进步少爷”,也不会为了丫鬟放弃巨大的利益,而是一边喊着“恋爱自由”“人格平等”,一边对“心爱的女子”袖手旁观。这可以归结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是“五四”运动退潮后,一代新青年思想上“何去何从”的迷惘。
此外,《雷雨》中周萍和鲁大海对周朴园的反抗,同样可以视作封建父子关系的“颠覆性继承”。作为20世纪30年代话剧创作的代表,《雷雨》挖掘了一代青年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困境,也探讨了诸如“娜拉出走之后”的社会问题。这是《雷雨》起初被当作社会问题剧看待的原因,也反映了剧作对传统悲剧范式的继承。
(二)开创:现代与传统悲剧的分野
但《雷雨》也实现了对传统悲剧的超越,开启了中国现代戏剧创作的新纪元。《雷雨》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形式上,因为严格遵守“三一律”而被称为“最像戏剧的戏剧”。三十年的冲突在一天之内集中爆发,情节发生的时间紧凑、地点集中,故事前后连贯,角色行为的内在逻辑完整可信。除此之外,《雷雨》也拥有更为现代的悲剧内核,即悲剧本身的不可解与不可避免。在传统悲剧中普遍存在着“完美受害者”的形象,他们的悲剧来源于社会的不公和强者的恶,最终往往诉诸更强者或神秘力量。例如《窦娥冤》中,窦娥化为鬼魂为自己申冤;《铡美案》中,包拯以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出来主持正义。这样的冲突是可以被解决的,而且主人公往往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在这点上,《雷雨》做出了大胆的创新。譬如在角色设置上,《雷雨》的角色无不契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过失论,即不存在所谓的“完美受害者”。无论是周朴园、蘩漪,还是梅侍萍、周萍,他们的悲剧或是源自自身有错在先,或是源自性格本身的缺陷,源自他们既不能控制欲望,更不能宰治自身命运。在曹禺看来,这样的悲剧是超越时代的,是人类生存本身的不幸。《雷雨》的创作与其说是批判某人某事,不如说是对个体存在的关怀与悲悯。
总而言之,《雷雨》的意义不仅在于批判那个时代,更在于对生命本身存在的哲学性探讨;《雷雨》不仅诞生于充满矛盾与变革的旧社会,更诞生于人类对自身缺憾的永恒性求索。《雷雨》的悲剧魅力,亟待更多更新颖的解读。
参考文献:
[1]陈彦彤.以《雷雨》为例新解“三一律”的中国化运用[J].参花(中),2023,(01):119-121.
[2]袁佳颖.浅谈中篇弹词《雷雨》对蘩漪形象的重塑[J].曲艺,2022,(12):57-59.
[3]和傲洁.曹禺《雷雨》戏剧人物蘩漪形象分析[J].今古文创,2022,(41):8-10.
[4sbYLw2ByohrcZwBb+yNEIg==]徐芳.高中《雷雨》课堂叙述设计与教师教学策略分析[J].语文世界(中学生之窗),2022,(09):62-63.
[5]王延松.试论《雷雨》悲剧人物的出场、在场与退场——以2007年新解读版《雷雨》为例[J].戏剧艺术,2022,(04):94-107+180.
[6]毛志宏.《雷雨》中人物反抗性分析与阐述[J].作家天地,2022,(23):8-10.
[7]谢淑婷.爱恋中沉沦,悲剧中挣扎——《雷雨》的爱恋悲剧意蕴解读[J].戏剧之家,2021,(35):51-52.
[8]李伊晴,沈祺.《雷雨》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分析[J].戏剧文学,2020,(08):76-80.
[9]柳靖.曹禺《雷雨》悲剧意蕴的多维解读[J].大众文艺,2020,(03):40-41.
[10]王卉.话剧《雷雨》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浅析[J].戏剧之家,2018,(28):32.
作者简介:
陈思妤,浙江树人学院,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