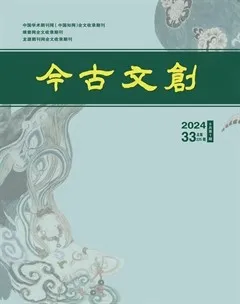论班维尔小说《海》中的自我建构
【摘要】爱尔兰当代作家约翰·班维尔的作品《海》是一部有关记忆、生命和寻找“自我”的小说。小说对现实与过去的再现并置,形成主人公马克斯对自我的再认识,暗示了班维尔对死亡、生命等存在问题的审视。本文着眼于马克斯在人生历程中自我意识的成长,探讨马克斯在亲眼见证死亡后如何形成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怎样处理记忆与生命的深层关系。
【关键词】班维尔;《海》;自我;记忆
【中图分类号】I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3-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3.001
2005年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创作的作品《海》(The Sea,2005)讲述了艺术史家马克斯·莫顿(Max Morden)因妻子离世,遭受重创后返回童年记忆地寻求心灵疗愈的故事。小说三线交织,在回忆和现实间勾绘出一幅主人公从童年旅居地巴厘来斯到英国伦敦再回到旅居地重新出发的人生地图,形象记录了其探寻“自我”、找寻生命意义的成长轨迹。根据心理学的观点,“自我”从外部世界独立出来的过程,可称为“个性化”:“经由这一过程,个人逐渐变成一个在心理上‘不可分的’(in-dividual),即一个独立的、连续的统一体或‘整体’”[1]33。荣格所谓的“整体”,即本文所探讨的“自我”(self)。《海》中马克斯“自我”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幼时他身处在“夏日世界”中自我意识开始萌发;成年后在“梦幻伦敦”遭受打击致使自我异化;老年回归“疗愈之地”获得心灵顿悟并逐渐明确自我定位。随着情绪、经历、经验、记忆等认知状态的完成,一个整体性的自我才得以显现。因此,本文拟以马克斯成长过程中所处的外部环境为切入点,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讨马克斯在亲眼见证死亡后如何形成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怎样处理记忆与生命的深层关系。
一、“夏日世界”:童年时期马克斯的自我分裂
马克斯自我意识萌芽时,童年期难以逃脱的“他者”力量,将他置于不真实的自我体验中。无法依靠的家庭和并未成熟的心智,使小马克斯对自我的探索和追寻摇摇晃晃,迷失在自我分裂而不自知的迷宫中。
在小马克斯建构自我的过程中,对其影响最深的是度假区人分三六九等的阶级观念。八月风景正盛时巴厘来斯会迎来一批从英格兰或欧洲大陆来的旅居客。这些聚集在海边共享阳光、沙滩的外来人员,因身份、地位、钱财的不同组合成一个贫富等级分明的“夏日世界”,“这个夏日世界的结构像金字塔一样稳定而难以攀登”[2]83。拥有独栋别墅雪松屋的格雷斯一家位于“夏日世界”的顶端,下一层是居住在海滨旅馆的旅客,再下一层是租房的旅客,最底层是生活在场院小木屋的马克斯一家。海边度假村给予底层旅居客一定的生活空间,制造出他们享受悠闲度假生活的假象,却没有提高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显性残忍的阶级意识,在旅居者间形成心照不宣的约定:“住好房子的人不会跟住小屋的人混在一起”[2]83,勉强度日的马克斯一家不与开着黑色大汽车的格雷斯一家往来,只因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小马克斯自记事起就已明晰巴厘来斯的社会等级结构,称“那是神祇的时代”[2]3。他知晓结识格雷斯一家能满足他跨越阶级的想象,因此,将格雷斯一家对他的接纳视为“众神”的恩宠,是一种特殊的象征。
受阶级意识的驱使,仰望“众神”的马克斯逐渐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根据萨特的观点:“羞愧是一种对于自我存在的原始体验。因自我存在介入到另一个存在之中而感到的羞愧,不是由于‘我’犯下了某种错误,而是由于我‘落’入世界或者说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3]293打破阶级壁垒,介入到格雷斯一家关系中的马克斯,与父母的关系急转而下:“我真恨不能将我那丢人的父母从镜头上擦除——就像海水卷走泡沫——我那又肥又矮、素面朝天的母亲,我那身上仿佛堆满猪油的父亲”[2]28。在他眼中,父亲是个抛妻弃子、胆小的家伙,同样身为男性,但不能通过模仿他来获得稳固的自我意识,反而陷入其“不称职父亲”的困扰中,无法习得父亲应尽的社会责任。再者,作为家庭的一员,母亲也未对小马克斯产生正向影响。她作为父亲离去后马克斯唯一的依靠,却将苦闷和憎恨之情转移到儿子身上,面对马克斯亲近格雷斯一家的行为,她虽不明确制止,但言语间应激的认为马克斯会成为如父亲般离家出走的“背叛者”。父亲缺席,母亲冷漠的家庭模式,令格雷斯一家的神性光辉放大,促使马克斯一步步向他们靠近。
与格雷斯家成员克洛伊的相恋成为马克斯自我意识的真实起源。他直言:“在克洛伊那里,这个世界第一次作为一个客观的实体被呈现在我面前”[2]127。起初,马克斯对克洛伊的母亲康妮·格雷斯产生不可控的迷恋,视她为高高在上的女神。后来,源于审美或欣赏,巧妙伪装的马克斯在真实、倔强、牢固且不可捉摸的克洛伊面前摘掉面具,并初次体会到爱情的滋味。与克洛伊亲密接触后,马克斯觉得“我是我,同时又非我,我成了别的什么人,一个彻底的新人”。[2]110甜蜜的恋爱令马克斯产生焕新感,像提前进入大人世界般获得对自我的掌控权。从母亲到女儿的情感转移表明马克斯意在颠覆既定的阶级秩序,反驳由富人掌握的权力话语。然而意外发生,克洛伊和弟弟溺水而亡,马克斯“眼看着两个鲜活的生命突然间,令人惊骇地消失了”[2]186。间接造成克洛伊丧生的马克斯在完善自我、跨越阶级的期待中坠落,对死亡的恐惧占据其心房,掉入自我分裂的裂缝中。
马克斯在“夏日世界”的记忆是他晚年不断回忆起的美好,同时也是困扰他的梦魇。他在此阶段受阶级意识的影响和死亡的冲击,没能形成确切的自我意识,伴随在他居住环境中散不去的气味,成为象征他所在阶级的无形符号。融入格雷斯一家不过是他上演的一场自导自演的舞台剧,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尚未调和。
二、“梦幻伦敦”:成年后马克斯的自我异化
伦敦的经历是马克斯自我意识成长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他拥有了家庭和事业,获得稳定居所。不过,童年时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经验在他成年后得到延续,回忆如幽灵般萦绕在他周围,看不见它们的存在,却帮助他做出一个又一个决定。通过婚姻跨越阶级的马克斯并未如童年预想的那般,向着完美人生前进。死神再度卷土重来,内心不够坚定的他陷入“灵魂游荡”的状态,伴随此状态产生的消极意识也蔓延至他身体各处,马克斯陷入自我异化的境地。
马克斯与安娜的相遇,可视为他步入上流社会,描绘起人生蓝图的开端。安娜是贵族的后代,与她结合让马克斯如在梦中:“我跳进了安娜与他父亲的世界中,那里仿佛是另一种介质,我先前所了解的一切规则都不再通用,一切都闪闪发光,一切都不真实,或者是真实但看起来却像是虚假,就像查理公寓里那一篮完美的水果一样”。[2]80“安娜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斯欲望之下格雷斯家女人的代替,代表了马克斯渴望而不可得的高贵出身。”[4]同时,也是他在伦敦的精神支柱和融入外界的助力者:“最初我从安娜身上发现了满足自己想象力的途径”[2]80。随着安娜查出癌症,两人平静梦幻的生活被拆解,“癌症这种疾病是死刑的判决”[5]9,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开始占据主位。这种“畏死”情绪,在医院被无限放大。医院的治疗室表面看来秩序井然:整洁平整的床铺、按时送达的饭菜、随时待命以应对紧急情况的医疗小组。但安娜的影像记录却“像是在战时的战地医院,或者是在被攻占毁坏的城市中的伤亡病区拍的”[2]137。病患的伤口、缝合线、脓疮都不加掩饰的暴露在镜头前,隐藏的混乱和失调也随之浮现。真实且无奈的影像记录,成为安娜对死亡的控诉和卷宗,一沓沓冲洗好的胶片都是她思想的再表达。马克斯没有患病,却也产生疼痛幻觉,对自我生出厌恶之情。两人情感相连,生命却已错轨,驶向不同的两端,安娜的那端直连死亡:“狄阿斯已经相中了她,潜伏在她体内,见风就长,只待一朝分娩。”[2]14
厄运降临,马克斯的自我意识开始错乱,对于安娜即将离去的恐惧和残留在脑海中克洛伊死亡的阴霾,使他在这种无法作为的无力感下被扭曲了。多数时刻,另一个马克斯好像悬在头顶,以俯瞰的第三视角窥视着发生的不幸,“我像是从镜头里观望着房间的一切。”[2]14这种“灵魂游荡”的状态,透露出马克斯的脆弱和不得已的逃避,他的“眼睛深处蹲伏着一个疯狂绝望的侏儒”[2]15。安娜如稳固不可撼动的锚一般,对周围的事物产生稳定的影响力。她的骤然离世成为马克斯变化的媒介,秩序失调下,马克斯借助暴力、谩骂、愤怒来感受活着。死神来临,人人叫苦不迭,面临不可抗拒的消亡,阶级、金钱、地位都失去独特意义。“对他人死亡的感知以及死亡的恐惧的自我投射促使马克斯开启了对死亡的哲学和艺术探寻。”[6]
事实上,步入伦敦上流社会的马克斯实质上并未离开“夏日世界”,童年时处在社会底层的不安和患得患失感没有消失,他有着体面的工作、可供支配的金钱、贵族出身的妻子,却无法获得真正的自我认同。再次与死神交臂,他费力建构起的自我大厦即将坍塌,进入自我异化的困顿中,需要消解对死亡的恐惧并重新学习融入其他人的生活。
三、“疗愈之地”:老年马克斯的心灵顿悟
“回归之旅”看似倒退停滞,其实象征着新的开始。是一个梦将他拽回“雪松屋”,梦中重复的“上路”“走”等行为,揭示了马克斯潜意识里对返乡的执念,从梦中惊醒后,他做出回归雪松屋的决定:“我必须待在这里,现在对我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的地方,唯一的庇护所。”[2]119当马克斯寻求稳定的庇护所以期疗愈,怀念过去对于其回归的重要作用被揭示,也就是说,回归“雪松屋”可以被视为是在试图重建一个虚构的过去,马克斯寻访故地的行为,也是想在安全的边界内定位自我。
曾经伫立在雪松屋客厅不敢贸然进入的小马克斯与携带记忆归来的老马克斯汇合。他通过重游故地、寻访故人、敞开心扉畅谈,慢慢审视过去的自我。相比于小时候来到这栋房子时的局促和新奇,此次回归后记忆中精致典雅的客厅倒显得拥挤简陋,房屋前后的变化揭示出物是人非的事实。对于敏感细腻的马克斯而言,在童年记忆之地回忆过去,是一项交织痛苦与愉悦的重要仪式,“这种回忆的过程又打破了他们麻木运转的日常生活,迫使他们面对过去和他人,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沟通的机会和疗救的希望”。[7]作者有意拉长回忆的时间,能更加清晰的暴露马克斯内心的“自我”。也就是说,这种有意的停滞不仅仅是想让马克斯触景生情,也并非过往记忆的简单重现,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回想,帮助回忆者捋清困扰自我的矛盾线索,为曾经处在儿童视角下难解的疑惑,找到合理的解释。当“各个部分都和某个特殊的点发生了联系时,我们认识到了它的实质”。[8]172-173
随着他的到来,房主瓦瓦苏小姐被误会、身份被隐藏的源头也都予以揭露,有关克洛伊死亡的真相也浮出水面。原来,瓦瓦苏小姐就是过去格雷斯一家的家庭女教师罗斯,因误会间接造成克洛伊溺水而亡。小马克斯原本以为瓦瓦苏小姐(罗斯)与格雷斯先生有着不正当关系,为获得克洛伊认可,便将这个重要发现透露给克洛伊,不曾想克洛伊对罗斯(瓦瓦苏小姐)生出恨意,选择以自杀反抗一切。记忆拉回过去,那个初见时,只发出声响,未展露全貌的小女孩罗斯,此刻与马克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共同守护悲伤秘密:“我们都是些盛满了悲哀的小船,航行在压抑的静谧中,穿行过秋日的黑暗”[2]43。随着秘密的揭开和事件反转,读者比马克斯——主要的焦点人物知道更多信息,使得文本的记忆世界更加完整,令阅读产生惊喜感,同时又补全了马克斯视角下记忆缺失的部分,“我”的记忆和“他者”的记忆相辅相成。原来,瓦瓦苏小姐(罗斯)一直深爱的是格雷斯夫人,她痛失所爱之人,却仍旧坚强地守护着雪松屋。强大的女性力量让马克斯意识到,广袤的世界上,有无数个渺小的个体都在承受或多或少的痛苦,自己所经历的只是众多生活中的一种,生命的离去不过是这个世界又一次冷漠地耸耸肩罢了,只能不断练习与世界相处,在悲伤过后腾出心力,厘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此次回归,使马克斯明白了生命的复原完满和重建的意义,代价是生者要承受无尽的孤独和记忆之苦,“我们带着死者的记忆直到我们自己也死去,我们承担了一段携带者的角色,然后我们的携带者也将离开人世,依次循环至无穷世代”。[2]90不同于生理学意义上的死亡和社会学意义的死亡,逝者的记忆被抹杀才是最终的崩溃消亡,记忆能使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小说最后以“一个护士出来找我,于是我转身,跟她走了回去,就像走入大海”[2]200作结。大海是吞噬生命的无情坟墓,也是哺育生命新生之地,“走入大海”这一行为意味着马克斯投入宇宙怀抱与世界万物再次产生联系。
四、结语
《海》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回忆过去时不介入其他无关人员的视角,其实是一场暴露主体最隐蔽思想的内省行动,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自省的方式,来建立和审视自我。在后现代社会,网络文化席卷全球,年轻人多以孤僻来武装自己,在关注自身的同时忽略“他者”的存在,产生由逃避现实造成的多方病症。班维尔关注到死亡的不可抗拒性,以反面鞭策的方式促使个人与社会彼此相连,对当下人们走出自我迷失的状态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C·S·霍尔,V·J·诺贝德.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爱尔兰)约翰·班维尔.海[M].王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3]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O’CONNEL M.John Banville’s narcissistic fiction[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3:134.
[5]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6]伊惠娟.约翰·班维尔《海》中的疾病隐喻[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02):88-93.
[7]陈丽.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20世纪爱尔兰大房子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8]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王雨,男,汉族,文学博士,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徐煜欣,女,汉族,长春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