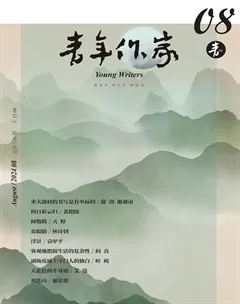彼其之子,美如玉
《诗经》摇曳着远古草木葱茏的枝叶,流转着日月顾盼多情的目光,飘荡着人们言笑歌哭的合声和踏歌起舞的欢欣,膜拜颂赞着天地山川化育万物的恩泽,三千年间一路跋涉而来,在漫长岁月的摧折和迢迢旅程的风霜磨蚀下,已是满面尘灰、音声含混、真假难辨。诗三百篇中的很多篇目在历史上也有多种多样甚至截然相反的解读。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通衢大道上,该如何倾听这穿越历史烟云飘飞而来的天籁一般的歌唱?
文学精灵舞蹁跹
《诗经》在未成“经”的周代,因其“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语),已被世人实质上尊奉为经;汉代之后,又被汉儒等弄得“作古正经”;称“经”以后更是被弄得“一本正经”。其在中国包括历史上的朝鲜,都以经学为主发挥作用,滋养着民众与社会乃至影响文化与政治的底色光泽。其经典一例是,西汉昌邑王刘贺登上帝位二十七天内荒淫无道作恶多端,被权臣霍光铁腕废黜,一大帮身边近臣因被认为未尽到劝谏之责而受到株连,其老师王式也在被诛之列。但王式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说自己为之朝夕传授《诗经》,篇篇都是在对他进行用心良苦的劝谏,怎么没有尽到责任呢?最后因之保命。而朝鲜,则因为经学上的争论,多次引发严酷的政治斗争。这说明,《诗经》是当时的重要的思想伦理政治教科书——当时“经”已成为时代共识,也是后世的普遍认知。
《诗经》对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有开拓性的贡献,在世界古典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以说,《诗经》一亮相就光彩照人,一发声就四方皆惊,历经岁月涤荡侵蚀和世人的取舍毁损,也未失其根本,而成为后世诗人们仰望的一隅星空,并成为中国诗歌长河的清莹源头,东亚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圭臬,最终愈久愈显愈远愈明,跻身殿堂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比肩希腊荷马史诗、英国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经典(著名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观点);可以说,《诗经》是古人嘹亮啼唱,人类初春原野绽放的绚丽花朵,世界文学宝库中光芒四射的硕大美玉。那些动人心曲的爱情、那些异乡征途的哀号悲泣、那些对抗御外侮的英雄礼赞、那些对国事民瘼锥心泣血的呐喊……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
要而言之,《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三个传统:一是现实主义传统。诗人们的思虑普遍关注现实,眼光瞄准现实,落笔映照现实。即使是告天祭祖这样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颂诗也着眼于为家国子孙祈福,福佑后人。就是对高高在上掌控人间命运的天,诗经中反映出的畏天——敬天——疑天——斥天的变迁,也着眼于天人的关系,究其实质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从内容看,诗经的内容既有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也有“贵者咏其忧乐,贱者抒其苦悲,智者虑其祸患,贤者思其得失。”这一点,从印度、希腊等国最早的诗歌以神话传说等超现实为重要甚至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明显差异。二是开创了咏物言志传统。也就是李山先生所说的“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艺术”(李山《风诗的情韵》),奠定了中国诗歌抒情风格的基本走向。三是开创了赋比兴传统。赋比兴成为影响中国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风雅比兴”也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主张、诗人创作的重要法度。
定格在历史深处的姿影
古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就是把《诗经》在内的六经都当作历史教科书来看。这虽以偏概全,但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从历史上看,《诗经》有巫史传统的影子,里面折射着深厚的历史因素。《诗经》中,有古人各具情态的婚恋、或苦或欣的生产劳作、愁苦劳禄的奔走行役、酢酬歌舞的欢会宴饮、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激动人心的杀伐征战、筚路蓝缕的祖先传说,雍雍肃肃的天地祖宗祭祀……这一帧帧影像无疑都是中华民族的动人身姿,散发出一个民族生机勃勃的气息,是极其珍贵的历史画卷。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的清明上河图,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简易百科全书。正如两位知名汉学家的评论所言,《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最出色的风俗画,也是一部无可争辩的文献”(【法】比奥),“《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俄】 费德林)。这显示出《诗经》珍贵的文学价值外,还有巨大的社会价值、认识价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
德之光
天帝看重之德和民意俯就之善是《诗经》在思想意识上所重视的两个方面,体现了当时统治阶层和民众对道德的尊崇与价值追求。
国家层面提倡以德治国,即“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时迈》);民众层面普遍重德尚德,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民》)。从《诗经》的发展来看,我认为,《诗经》体现出以下五个民族特性。
一是敬天尊祖。总体而言,天在《诗经》中不是自然概念,而是宗教性概念,被视为至高至大之神,主宰人类命运和家国祸福吉凶。而祖先则被周人纳入神的序列加以崇拜。敬天尊祖的一大表现是将敬奉天地祖宗视为国之大事和人之大德,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开启了中国人敬天法祖的传统。敬天法祖的观念应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载芟》)的农业社会的产物(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观点)。
二是以人为本。首先是托物言志,抒发自我的悲欢离合;其次是同情、关注他人的命运不幸;再者是反映社会的变迁。《诗经》从未放弃对民生的关注,从未离开对民瘼的牵挂,呈现出强烈的人本色彩、人伦情谊、人性意识、人文情怀。
三是厚德载物。《诗经》中对德的歌咏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对周先祖创业立国时艰苦奋斗、和谐万邦、大度包容、忠厚传家、孝亲友弟的精神的歌颂,对忠诚正直、忠君爱国等美德的歌咏以及对君子及君子之风的讴歌推举。
四是家国情怀。主要表现在战争诗徭役诗中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以及将士奔赴国难的大义和庙堂贤良讽谏体现出的忧国忧民情怀。
五是中庸和谐。激烈的情绪、疯狂的情感、极端的事件不是《诗经》表现的主要内容。有论者指出,诗经体现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强调“家国之和、上下之和、男女之和”(学者李山观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诗经》整体上的确体现出如孔子论《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节制有度。一言以蔽之:《诗经》反映了民族意识,润泽了民族气质,涵养了民族精神。
广阔的回响
《诗经》像涓涓流水一样深深浸润过中华大地,甚至异国他乡的土地和人民。据中国诗经学会原会长、已故著名诗经学学者夏传才在其著作《诗经讲座》中阐述,《诗经》至少在公元五世纪就开始向中东地区传播。公元五世纪中叶,日本雄略天皇奏表南朝刘宋皇帝,其中就引用了《诗经》。公元541年朝鲜半岛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博士讲授《诗经》,梁武帝派学者陆羽前往。新罗王朝765年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高丽王朝于958年定《诗经》为科考科目。公元781年设立在唐朝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撰写者景净为叙利亚人,碑文引《诗经》达二十余处。在越南,李朝十世开始以《诗经》为科考内容,士人无不熟诵《诗经》,十二世纪开始并现多种译本,其诗文中广泛引用有关《诗经》的典故。公元十七世纪《诗经》通过来华传教士译介到欧洲。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通过来华传教士传入北美。1852年俄罗斯出现《诗经》译本。由此可看出《诗经》传播之广之深甚至之全之细。而今,《诗经》已成为全世界诸多大学的开设课程,《诗经》已然成为全世界汉学之显学。
道阻且长
我认为,历代的中国学者,对《诗经》的研究和解读,在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为《诗经》研究作出开山架桥的贡献的同时,也有不少政治化、道德化、伦理化、主观化的解读,严重地误解和歪曲了诗篇的本义,遮蔽了诗篇的本来面目。美刺说、六经皆史论,甚至包括司马迁《史记》所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等论断,有部分合乎事实的合理成分,但更多的是让《诗经》被历史的尘土遮蔽得“不识庐山真面目”。对历史上《诗经》研究中的错误和偏颇,国外汉学大家葛兰言、白川静,国内钱锺书、闻一多等有诸多订正。葛兰言明白指出:“不言而喻,根据高尚的宗教思想的推敲,或以虔诚的稽古学者们再构的仪礼的法则和润色的事实来解释《诗经》的歌谣,是非常危险的。解释《诗经》应该尽可能地根据诗经本身来解释。”“《序》(指《毛诗序》——笔者注)中解说的性质完全是历史的道德的并且是象征的。” “倘若诸君依赖儒学旳注释书,依据书中象征性的解释,必然从始至终走错路”( [法]葛兰言《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高本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研究和注释诗经的学者,真是数以千计,而有关诗经的文献,也真是卷帙浩繁。然而在具有科学头脑的现代学者看来,大半都是没有价值的,可以置之不顾。因为总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些传道说教的浮词”(《董同龢<高本汉诗经注释〉》)。白川静则别具慧眼地指出,“将诗篇作为经书……古代文学所具有的民族精神的活泼胎动,由此反而遭到权威化,形式化,结果是阻碍了丰富的生命流动。诗篇迷失在谜一样的解释学迷途之中,失去了对于古代文学正当的理解之道,对于诗篇而言可以说是难以恢复的损失”( [日本]白川静《诗经的世界》)。我认为,造成这些谬见的原因,是汉儒戴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紧箍咒,而宋儒自带“儒术”的紧箍咒。千百年来少有质疑辩驳的原因则是学术上的述而不作和师承传统,正如孔夫子所提倡和标榜的“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一味尊古崇古,少有创新开拓。李白在《嘲鲁儒》一诗中对这种面对诗书等五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儒者作了辛辣嘲讽:“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一些穿靴戴帽甚至莫名其妙的解读让年轻朝气的诗篇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变得老气横秋,大大失真失本,乃至变成木乃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诗经》时应加以辨析的。
今天,我们触抚《诗经》,在凝固的文字里仍能撞见鲜活生命的蓬勃跃动,在静止的诗行里清晰地听见古人纯粹的话语、歌声、哭声与叹息,清晰地望见山川草木俯仰生姿,然后看见中华民族头顶日月,怀揣希望与梦想,从远古一路跋山涉水风尘仆仆而来。
【作者简介】雍也,本名雍峰,生于1970年2月,四川渠县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散文集《龙泉山笔记》、诗集《血脉中的驿路》、学术随笔集《回望诗经》等。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