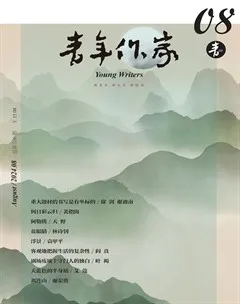一粒粮食的叙事
呼 唤
粮食的一声惊叫,唤醒了我模糊的记忆。
那年我到底几岁,不重要了。关键是我没眼力劲儿,点着了祖父的火药桶。
夜晚,煤油灯燃起来了,火焰在姐的瞳孔里顽皮地跳。淘气的我伸着脖子去吹,火苗前扑,一翻身又跳起来。这时我脚下不稳,摔倒在地。疼痛、委屈,在我无所顾忌的哭闹中,突然“啪”的一声爆响,一个热乎乎的东西不偏不倚地砸中了我的后脑勺。我的哭声瞬间凝固,继而变成惊恐的抽泣。
原来是祖父被搅得心烦意乱,大发脾气。正准备晚饭的母亲回了一句,祖父就一下掀翻了饭桌,那些刚出锅的玉米面窝头,惊慌失措地翻出竹筐,滚了一地。全家人谁也没吃一口饭。
据说,祖父白天在场院里干疯了,一个人站在高高的脱粒机旁扬场,扬出了六千多斤麦子。场院里,忙碌火辣的气氛让人恐慌。机器轰鸣飞旋,吞咽着麦捆。汗水混合着泥尘,从祖父铁打的脊背向下流,头发、眉毛、落腮胡子上都落满了长长短短的麦秸碎屑。一把麦子还没在簸箕里落稳,就被祖父抡开胳膊一扬抛到半空,麦糠顺风飘出去,麦粒雨“唰啦啦”落在地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上麦子,也没跟上祖父的速度。这救命的粮食没进仓,祖父心里始终不踏实。
祖父视粮食如命,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那是夏末的狂风骤雨后,暴涨的池塘映满火红的晚霞时,姐姐领着我和几个孩子嬉闹着跑进了池塘边的玉米地,那时候的玉米秸最甜。一转眼,十几棵玉米被掐头、去根、断腰,乱扔在地里。突然,我的脊背狠狠地挨了两棍。透过委屈的泪花,我看到了祖父暴怒的脸。我和姐姐哭哭啼啼,背着两道鲜红的血印进了家。这血印刺痛了母亲,她和祖父大吵一顿。祖父晚饭都没吃,一气之下卷了铺盖,独自搬到牛栏院住了。
平时,祖父最疼孩子。寒冷的冬夜,他厚厚的羊皮袄总盖在姐姐的那一头,姐姐夜里醒来,常热得满头汗。家里只有一个搪瓷汤壶,每晚睡觉前把我们的被窝暖好了,他才抱到自己的床上。因为粮食,祖父却狠心打了自己家的孩子。
一粒粮食沾染着泪花,就这样滞留在我清浅的记忆。年复一年,日子在琐碎庸常中旋转,随着我逐年长大,一步步远离了土地,粮食赐予的这点儿疼,早已融泥入水,浑然不觉。而今,碌碌半生,惶惑中猛然回首,萦绕耳畔的却是一粒粮食的呼唤。
那些清晨,我总是在麻雀的争吵声中醒来。金黄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斜织进屋子,切割着水泥灰墙皮。窗外“嚯啷啷”两声响,水桶落地,扁担钩子挠着水桶皮“叮当”乱响。不用出门看,是祖父挑着大铁桶回来了。祖父常年管理牛栏院,挑水、铡草、喂牛、打扫,一大早在牛栏院忙完这一整套活儿,早饿得前胸贴后背。他坐在雕着梅花鹿回头的老椅子上,大口吞咽着早饭。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地瓜粥、几张刚下热鏊子的玉米煎饼,随着早饭落肚,一家人一天的活计他也安排妥当了。最后,祖父指着院子里的藤篮,给我也布置了任务:放学后到西岭薅草,要薅满三篮子。
又是西岭的麦地?!那块狭长的山坡地,刨地难,养地难,耩地更难,全凭人力。去年国庆节期间趁着下了场地皮雨,祖父推着单腿耧子才播种了小麦。父亲拉耧杆,祖父扶耧把,中间的耧斗盛着拌了杀虫剂的麦种。耧斗前面的耧仓板可升降,调整麦种流量。耧板下的半圆孔中间有弧形细竹枝,一头拴在耧斗里,另一头拴在耧仓板上边的挑齿,竹枝中间拴着砖头磨成的耧子锤。祖父推着耧子摇耧,耧斗锤带动竹枝颤动打得耧斗板“梆梆”响,竹枝晃动的快慢掌握下种量的多少。
“谷耩浅,麦耩深,芝麻只盖半个身。”耩谷子,出苗要求“蚂蚁跟趟”,均匀适中。山岭地耩麦子那才叫费劲,土质薄,碎石多,犁头扎不下去。祖父双臂用力下按,耧腿吃土力度到位,种子深浅才到位。父亲两手紧攥耧把,粗麻绳套过头斜背在肩,埋头拉耧,既要注意步幅,保证麦苗出土笔管条直,还要保证行距均匀不浪费地力。这一垄一垄下来,是对体力,更是耐力的考验。
母亲则领着我和姐姐在后面拉石砘,把耩过的地碾压瓷实,保墒。太阳懒洋洋地滑下山头,冷风卷起沙尘满山坡闲逛的时候,这片山地的播种才宣告竣工。
那些沉睡的麦种被祖父长满老茧的手,翻来覆去摩挲过,再被暖融融湿润润的泥土拥抱着,开始复苏,萌动了。
寒露,麦芽像翠绿的绣花针一样一根根钻出黄褐色的土地,刺破了深秋的荒凉。那一畦一畦鲜亮的绿,蛰伏着一个季节的梦,经过了冰天雪地的拥抱,在春风荡漾的日子融化,才会拉开成长的序幕。几场绵密的春雨,不急不躁,洇透了大地。麦苗迎着春风一晃,再一晃,就蹿到了我的膝盖。那么多米蒿、面条棵、抓地秧和麦苗摽劲儿地长,我每天放学后挎着藤篮去薅,怎么也薅不净。我的个头也在猛蹿,裤腿拼接了一大截儿还是吊在脚踝骨上。
通向西坡的黄土路,坑坑洼洼的,那么长,一步一步量下去,量得我提不起精神。一下午,两个来回就耗尽了体力。我坐在门枕石上,磕出满鞋窠的黄土时,太阳像一颗黄澄澄的柿子挂在树梢,“咕咚”一声,跌下院墙就摔裂了,喷溅出漫天橙丽的霞光。我的肚子“咕噜噜”在唱空城计;觅食的鸡缩在柴草垛下“咕咕”呻唤;焦躁的猪顶着木栅栏门“哐啷啷”响;大黑狗四处嗅嗅,索性坐在喂食碗前眼巴巴地看着我,每一个空瘪的肚皮都循着粮食急切地呼唤,焦躁地等待。
但饥饿年代里的人们,真的难以从一粒粮食中走出。
那些年,我家住的老四合院像坠在鱼池街西头的秤砣,挤挤歪歪地装了三个家庭,老少三代二十余口人。一棵老石榴树、三棵老枣树立于各家门旁,自然划分出三个家庭的活动范围。一家风箱响,满院柴米香。谁家炒菜多点了两滴油,其他两家也闻得格外香。
早春二月,春姑娘的绿袖还没来得及舒展,院子里的红泥盆就泡满了嫩绿的柳芽儿和杨叶儿。东院里,凤莲姑的脸拉得比南瓜还长。早上一锅南瓜汤,稀水寡淡;中午一锅还是南瓜汤,照着愁眉耷拉眼。
凤莲娘掀开那些粮食瓮的盖垫,一个个空荡荡地盛不下她满肚子的愁怨怒火。她挥着笤帚,满院子追打凤莲爹——全家喝西北风也挡不住这老东西到处疯。凤莲爹紧跑几步,蹿上了平房顶。不承想,这房顶成了天然的舞台,他一瘸一拐,扭着台步唱起京剧《秦琼卖马》。凤莲爹才不理会自己被鬼子打瘸的腿,哪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扎堆儿纳鞋底儿、插花绣鞋垫儿,他就往哪里一站,扭着秧歌儿就唱。众人笑,惊得鸟雀冲天,他扭得就更欢畅。
凤莲娘索性搬开了梯子,冲天叫骂道饿死这个老不死的也不解恨。我母亲停下热鏊子,从秫秸盖垫上叠了一沓热煎饼抱到东堂屋,才堵住凤莲娘的嘴巴。
每逢夏秋打场晒粮,凤莲爹是生产队看守场院的主要人选。夜半三更,坡地里总是零零碎碎丢一片谷穗、半垄地瓜,往往队长开会时敲敲桌子,虚张声势吼几嗓子也就算了。底下就有人暗自耷拉了眼皮,总也盖不住羞臊的脸皮。而那年秋后,场院里一麻袋种子无缘无故消失,引起全村老少恐慌。一时间,大家互相猜疑,互提线索,互找人证,证明自己当晚的行踪。最后,所有的指责都落在凤莲爹头上,他被罚扣了一年的工分。深夜,凤莲爹黑沉着脸回到家,走进小东屋再没走出来。第二天一大早,家人发现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僵硬地躺在地上。一个空空的农药瓶子被仓皇的脚踢得无处躲藏。
喂养我们肚子的粮食,本来一腔柔情,重压之下,却是僵硬冷酷的刀。
一粒粮食从诞生起就与我们签订了生命契约。一万年前,一粒小小的稻米载入人类稻米文化史时,我们的祖先就参透了一粒粮食的硬度。从远古神农氏教民稼穑,到古代君主为祈求国事太平、五谷丰登,每年到郊外祭祀社稷;从冷兵器时代开疆扩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一粒粮食的身影随处可见,深陷浮浮沉沉的俗世尘埃,追随四季轮回,代代绵延,稳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
手捻一粒粮食,拂开浩渺的历史烟尘,饥饿阴影笼罩中的灾荒年里,是血腥填满了记忆的沟壑。“食胆至千”“双子宴”“两足羊”,当剥光的树皮、掘断的树根和涨坠肠胃的观音土也不能阻挡饥饿死神的吞噬时,“人相食”则是人间上演的最残忍的“喋血记”。
狗日的粮食!有多少咬牙切齿的诅咒,就有多少爱恨交加的呼唤。
韧 性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灌溉、施肥,吸收阳光、水分和土地的滋养,历时二百多个昼夜的生长,再经历收割、晾晒、制造、贩卖等程序,累积了多少能量和心血才能成就。它凝结了时间、步伐和印痕,才凝聚成一种坚韧,一种与时俱进的坚韧。
“龙王救万民哟/轻风细雨哟救万民/天旱着火了/地下青苗晒干了……”曾经陕北大地十年九旱,这苍凉的祈雨呼唤,震彻天宇。祈求神灵赐雨的法事活动,自商汤时代起在中华大地已绵延三千六百余年。商汤克夏后,大旱七年。商汤断发,祷于桑林。面对天灾,远古时期的人们无能为力,为取悦上天甚至“焚巫曝巫”,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追随历史的河流下行,来至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的年代,人们依旧把美好的期待寄托于天: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属龙日是楚雄彝族一年一度的传统祈雨节;五月十三日,关公磨刀水,是蒙古族盛大的祈雨,祭祀天地活动;每年六月,黔东南苗族要祭天求雨,唱芦笙,跳苗族飞歌;在山东,祈雨习俗主要有三类:祭神祈雨、敬龙祈雨、乐舞祈雨……人们或披发散肩或俯身叩拜,念之歌之舞之蹈之,以期感天地动鬼神。
公元1061年腊月,苏轼至凤翔赴任,直到第二年正月凤翔仍未下雨。麦田干涸,民声哀呼。他挥笔写就《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振振有词地和山神讲道理,与其说祈雨,倒不如说是责令其下雨。“今寻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菲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
可怜,苍天有眼,天降甘霖来。而今反观历代的祈雨图,或哀乞或反思或忏悔或威逼或利诱,人神交涉之间逸趣横生——这只不过是苦苦挣扎的人们与天地对话,求得心灵契合、精神安慰的寄托方式而已。
当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步伐迈进田野,灌溉的水管像血管一样畅通田野,一粒粮食的生长才恢复了足够的弹性和韧性,灌浆饱满,籽粒莹润。那沉甸甸的收获带来踏实和稳定,一粒粮食才能给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坚挺的信任和依赖。
还记得春日的旷野,风卷黄尘漫过,遮迷了我童稚的眼睛。胜利渠的水汩汩滔滔,奔涌而来,大人们轮流值夜班浇麦地。黑沉沉的夜幕匍匐下来,漫天的星星低低坠入遥远的天河,四周是空旷和死寂,清冷的寒风浸透了骨头。祖父一把铁锨,一只手电筒,在麦垄上不停地走动,查看水流,防备漏水,更不能打瞌睡让麦田浇过了头。走走停停,一会儿铲土堵漏洞,一会儿挖泥疏导水流。刚忙出一身汗,一阵冷风扫过去,又是一身寒。僵硬的手几乎握不住锨把,他不时用力把铁锨插进土埂,搓搓麻木的手。夜半更深,只有低压压的星星和满地“咕噜噜”的流水,与祖父贴心低语。
清晨,金黄的曙光笼罩着葱茏的麦田。凉风涌动,麦波起伏。祖父长长的身影抚摸过的每一畦麦苗都泪雨滂沱。
从记忆中走出,才发现年过半百的我,至今还没真正走进过一粒粮食。
今年大年初三,高脂肪高热量食物堆积,味蕾黏腻而慵懒。朋友送来的两袋糍粑“嚯”地调动起我的食欲。我照着网上的视频,把三个巴掌大的糍粑放进电饼铛,低温慢煎。那溜圆的面饼渐渐瘫软变形,像三只章鱼探出触角肆意伸张。煎至表面微黄,三个糍粑已彼此黏连成一家。出锅,粘白砂糖,入口却粘韧难嚼,在嘴里倒腾半天也切不断。我耐着性子消灭了一个,另两个境遇尴尬,遭受冷遇。另一袋糍粑至今冷藏在冰箱,若上体育课时拿去当铁饼,想必会落地见坑。
一粒粮食的坚韧真是让人惊叹。
糍粑一诞生就蒙上了硝烟战火的阴影,它在一座城墙的地基下悄然登场。战旗猎猎,喊杀震天。战马腾起的黄尘弥漫,吞没了吴国城墙。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局势即将完结,寒冬岁末又至,被越国围困的吴国城池中弹尽粮绝,人心惶惶。饥寒难耐中,人们想起伍子胥生前的嘱咐,悄悄拆墙挖地,发现城墙的地基竟都是熟糯米压制成的砖石。危难之际,粮食的坚韧填充进干瘪的胃肠,让吴国人挺直了意志的脊梁。伍子胥的“积粮防饥”之计,帮吴国军民度过了难关,此后每逢过年,人们都压制年糕以纪念伍子胥。
“正月元旦,啖年糕,曰年年糕”,黄河流域以黍米做年糕的风俗,倒与江南糍粑的寓意贴合。“年糕”随着大江南北的风霜雨雪潜入千家万户的除夕夜,风味早已与千年前不同。
“糍粑,系糯米饭就石槽中杵如泥,压成团,状如满月。”网络上这简约的注释显然不能填补一个北方人对糍粑的想象。走进千户苗寨,我才见到了“打糍粑”的现场。石臼中被捶打的糯米拖着黏丝与木锤缠裹着不肯脱离时,另一把木锤的救援形式悲壮而慷慨,径直砸入纠结和缠裹之中,同伴才有了脱身的机会。两把木锤如此一唱一和,糯米碎成糜状,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内里却绵软柔韧。
2016年的夏天,酷烈的阳光与那十口大锅下跃动的火焰,炙烤着挥汗如雨的工人。日均熬制的六七十锅的“糯米粥”与石灰搅拌成糯米灰浆,填补着年逾六百岁的残缺墙体。那是西昌古城大通门外唯存的九百二十米古墙,整个工程约用糯米五十吨!
一粒粮食如此卑微,鸟雀可随意啄食,鼠辈可恣意盗取,人们采摘摔打碾压,掉落在地也懒得弯腰捡拾。而千年前,古人的建筑工艺里却把一粒微小的粮食嵌入了历史漫长的骨骼之中。把糯米熬煮成汤,和石灰按照比例混合,可修筑防御城墙,以求御敌于外、保一方安宁;可建筑皇家陵墓,以期万寿无疆、永垂不朽;可建造佛地宝塔,享有佛光普照、圣洁润泽。这些被赋予神圣使命的墙体,承担起最沉重的承诺,经受着最艰巨的考验,经过了多次战争和地震,依旧苍然屹立。即便到了现在,那些古老建筑依然用推土机也难以推倒。
而在鲁中山区,则是小麦、玉米和小米在饭桌上唱主角。当年,为保护修缮曲阜内濒临倒塌的古墙,政府专门拨付了七千斤小米用于修复孔庙庙墙。
我时常流连于古老的岱庙。斑驳的青砖老墙内花香鸟语,古树葳蕤,藤萝迎风。那建制于唐代的石经幢,由六个拳头粗的铁箍环护着,受风化剥蚀的身体早已千疮百孔、遍体鳞伤;明嘉靖年间铸造的十三级铁塔,日军轰炸泰安市时被毁,尚存三级;明万历年间铸造的铜亭,遭劫掠后门窗尽失;还有层叠的殿宇楼阁、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终逃不出时光的锈蚀,黯然神伤。而威严的青砖古墙,在历史幽深的河流中缥缈沉浮,却依旧保持着生命的韧性,仅源于一粒粮食的滋养。
我抚摸着青苔密布的墙体,感受老砖缝隙内米浆与灰浆凝固的融合体的触感。它是如此清凉,如此细腻,沉默如铁的表面下蕴含着粮食的坚韧之心,在时光步履的碾压之下,历久弥坚。
灵 魂
酒杯立在木条桌,像一支初绽的郁金香。酒液红亮莹透,恰在酒杯鼓凸处切出弧面。一股糯米的暖香入口,酒液像甘露滑入咽喉、食管,浑身的毛孔也悠然张开。这是店家自酿的黑糯米酒。在镇远,几乎家家都自酿米酒。
我学会品咂一杯米酒的味道,是在镇远古城。与朋友坐进古城小小的酒坊里,伴着两千余岁的古城风韵,细品慢酌一杯浸透岁月的米酒,人生的长途短途、顺境逆旅、翻山过桥的诸多滋味,在舌尖渗透,弥散。
这酒坊不大,深藏于曲折交叉的狭窄巷口,店面仅能安放下三五张条桌,苍老的木桌木凳虽被常年擦拭,那清晰的纹路犹在话说当年。一排排货架靠墙而立,各种款式的酒坛列队井然:糯米酒、黑米酒、高粱酒、蓝莓米酒、桂花米酒、杨梅米酒、桃花米酒、玫瑰米酒。每一款酒都在深色的陶坛内酝酿日月情怀,单等掀开盖子的瞬间,所有的美好期待随酒香袅袅浮出,安抚一颗虔诚之心。一颗粮食的灵魂就寄托于此。
“汤液醪醴,皆酒之属”,自古以来,以五谷熬煮成的清液,滋养五脏,即为汤液;五谷熬煮后再发酵酿造,治愈五脏疾病,则为醪醴。一粒粮食从生长到收割再到酿造,须有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加持,才得以提炼成酒。
而“酒坊”,总让人联想到那些经典的场景:红艳的高粱在漫天霞彩下摇曳;劈柴柈子火焰熊熊,锅里沸水翻滚,蒸汽在大甑里曲折上升的咝咝声与伙计们的喘息声混成一片;那白锡做的酒流子上汪着一片亮,缓缓凝聚,终于凝成几颗明亮的水珠,像眼泪一样滚到酒篓里。最惊心动魄的还是《酒神曲》,那气运丹田、声震天宇的几嗓子喊,一经传出便成为酒的生命绝唱。这提取了红高粱灵魂的酒,在摆脱“肉身”,跳出蒸馏器的瞬间,轻而易举就俘获了人心。
酒杯旋转,透过亮红的酒液,朋友看着我灿然一笑,说起被粮食的灵魂俘获的刹那。
多年前,他曾拜访一位酿酒老人。老人把他领到蒸馏器旁,递过一个接酒的玻璃壶,然后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柔细的酒液从蒸馏器下的细管缓缓流出,浓香扑鼻。蒸馏器顶部猪尾巴似的甩出一根管,有酒液滴下。朋友是喜文弄字、率性爱酒之人。他捧壶倾听,酒滴轻落,溅起温柔的酒韵,如一层层涟漪漾开,心底悄然涌起沉醉的感觉,眼睛竟也不觉间湿润了。还没接满,他就已双腿僵硬,胳膊泛酸,似乎撑不住越来越重的玻璃壶。临走时,他把下乡走访时从老中医那里淘来的疗腿草药,连夜送给了老人。老人祖传的酿酒工艺完全可以申请省级非遗。
他灌满两瓶,宝贝似的揽在怀里,一路微醺着带回家,密封了,放进储藏间的角落,也把一个微妙的期待悄悄存在了那里。那天收拾东西时骤然想起这酒,沉淀在他心底的那个瞬间怦然灼亮,脑门却“嗖”地冒出一层汗珠。他急忙搬开那些堆放的杂物,捧起酒瓶,发现轻飘飘的,不由得心里一颤。他双手摇晃着,耳朵贴近酒瓶,走到阳光下,期待多年前那份沉甸甸的虔诚依然满瓶。他打开瓶盖,心头浓重的惋惜被飘摇的气球扯起来,“腾”地飞上了半空,弥散如烟。
一粒粮食的灵魂在孤寂中脱身而去了。尽管酿酒的老人在清洗、浸泡、蒸熟、冷却、拌曲、冷却、发酵、蒸馏的八道工序中,虔诚地掺入了一份敬畏一份期盼和一份耐心,也掺入了他们纯粹的情谊,但粮食的灵魂寄托于酒中,漫漫时光中它与空气氧化,又经历了生涩、成长、成熟、老态甚至死亡的抛物线式生命过程。
从回忆来到现实,朋友慢慢地啜了一口黑米酒,“要喝啊,还得是地头酒。”他一声慨叹,又煞有介事地闭紧了嘴巴。我沉默不语,期待他的下文。
没料到,随着他的一声朗笑,接上了“要吃啊,还得是地头饭”。我的记忆陡然像顽皮的鱼儿,轻轻点水,“哗”的一声跃上老家的西山梁。夏收抢农时,秋收马拉松。紧绷弦,闷头赶,收麦子可是“龙口抢食”的活儿。
记得小时候天一摩挲眼儿,一家老少就踩着晨露下了地。祖父“啪”,一口唾液在两掌搓热,那把打磨得锃亮的镰刀就黏在了手心。左手向怀里搂过麦子,镰刀寒光一闪,麦秆贴着地皮齐唰唰倒在脚边。埋头弯腰,一气儿割到地头,来不及直起腰歇口气,掉头又是几趟来回。等半块地躺满了麦捆子,太阳才悠悠地攀上树梢,牵着村里的炊烟袅袅婷婷地浮起来,农家的早饭才老牛拉破车一样慢吞吞地生火热灶。
我早就饿得两眼发花。一次次揉搓酸胀的眼,目不转睛地看着山下那条黄土路。终于,影影绰绰的身影冒出来,越走越近,挎竹篮提暖瓶。我眼神不错,站在地头看走路姿势基本能猜定是哪家的送饭人。
太阳在脑袋上方滴溜溜看着,软软的煎饼卷了脆甜的大葱,和着暖暖的山风、醉熟的麦香,一口口填进肚子的感觉踏实而满足。吃过地头饭,午后的阳光旋起金黄的光圈,猛烈地罩住了整个大地。闷热的空气下,一切都懒怠起来。干涸的水壶躺在地头,遍身灼热发起高烧。暖水瓶哑了喉咙,拔下软木塞,空空的胸腔 “嗡嗡”混响。麦芒扎透了衣服,浑身刺痒。我蹲在满地的麦茬间,头昏昏沉沉,眼前碎光闪闪飘忽不定。旧草帽像紧箍咒一样勒住了我的头皮,滚滚的汗珠砸进土地。干燥的嘴唇泛起一层白皮,汗衫湿透了,紧贴脊背。西斜的太阳终于被棉絮一样的薄云罩住,一阵风掠过,再猛一抬头,西山梁昏沉沉的要瞌睡了,乌鸦盘旋着翅膀一抖,天终于黑了。
已经过去多年,农忙的记忆却依然在我脑海中清晰如昨。“年头熬到年尾,头顶星光脚踩月影,那年月,人就是这么累死累活。到最后,还不是都一样?地头上会齐。”朋友说着朗笑了几声。那笑声清亮几乎穿透了天花板,但笑过沉淀下一星半点儿别样的滋味,冷不丁让人抓个正着。 “人这一辈子吃过几碗干饭,有数。总有一天要坐在地头算总账,那壶酒,端在手上滋味怎么样?踏实不踏实,每个人心里有数。”朋友的话有些硌牙,把人的灵魂嫁接于一杯酒、一粒粮食的灵魂之中。
但说起来惭愧,我们的祖先最初种粮并不是为了填饥,而是为了酿酒。一万年前,人类赖以生存的主食是肉类而非谷物。当人们发现采集来的野生谷物可以酿酒时,才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以保证酿酒原料的供应。高粱、大米、糯米、黍米、豌豆、玉米、小麦等富含淀粉和糖分的粮食,随着人类前行的步伐,陆续被开发为酿酒原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酿酒池。一粒粮食的灵魂在翻炒、蒸馏的热浪中滴沥析出。
一般来说,一百斤粮食可出五十斤左右的清香型白酒,或出四十斤左右的浓香型白酒,或出二十到三十斤酱香型白酒。而我国每年酿酒消耗的小麦有一千五百万吨之多,甚至二百万吨。那么,再加上高粱、大米、糯米、豌豆等其他粮食,每年要消耗多少呢?酒与粮食一路携手走来,有太多扯不断的恩怨情仇:酒自诞生时就面临着一次灭顶之灾,大禹尝了仪狄进奉的酒,干脆诏令不再酿酒;周王室为稳固政权,颁出史上第一个成文的禁酒令——《酒诰》;秦汉时期,对酒征收十倍的赋税以控制酒的酿造量;烽火连连的三国,曹操因缺粮而下决心禁酒,刘备筹军粮见到农家的酿酒工具都想治罪;元明之际,但凡种植酿酒用的糯米,一律处死;清乾隆年间,内阁学士方苞针对贫穷的西北五省(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提议禁酒,因为它们每年用于酿酒的粮食高达数百万吨,且酒后犯罪率太高。
酒无处不在,已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缝隙,填充着生活的边角旮旯。酒在生活中扮演了那么多角色,自古以来,上至君王帝显,下至平民百姓,以它敬天地祭鬼神,又拿它作日子的润滑剂、人际关系的调控剂。当一个人的欲望难以满足,情感歇斯底里喷发时,酒无疑也充当了催化剂,酒盖了脸,那块遮羞布何以挂得住?倘若没有酒,人类的文明将重新改写。酒已浸润了社会每个角色的灵魂。
今年夏初的傍晚,我乘机从贵州返回,恰好盘旋于济南上空,我迎着夕阳灼亮的金光捕捉窗外的风景。粗犷的黄河画出一条硕大的土黄色S弯,静静地流过广袤的麦野。那些平整的麦田棋盘一样,块块片片连缀一起,向着浩渺的远方铺展开去,一望无际。齐鲁大地麦浪滚滚,开镰收割在即。
一股热流在胸口荡起,一种期待在心头隐隐升腾,我仿佛听到“布谷”“布谷”,声声清脆的啼鸣震得四野清宁,田野里涌荡翻滚的麦浪正发出金黄的呼唤。
【作者简介】冉令香,山东泰安人,教师;作品发表于《青年作家》《作品》《散文海外版》等刊,著有散文集《蓝岸》等三部,曾获齐鲁散文奖等;现居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