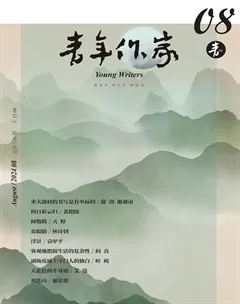天蓝色的半身裙
少女时期我曾有过一次危险的经历。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舒朗的夏夜,我和W手挽手去街上闲逛。我穿着白色大翻领衬衣,喇叭袖口镶有一圈蕾丝,轻盈飘逸,手腕在袖口若隐若现,就像中世纪欧洲的贵族小姐。想到这里,我不禁为之飘飘然。这也是我当天装扮最为中意的地方。除此之外,是缀着荷叶边的半身裙,洗得有点旧了。对了,我脖子上还有一条鸡心吊坠的银项链,它闪耀着星河般的光辉,任何一位少女戴着它都会为之雀跃,愈加光彩照人。
但这一切在W面前都黯然失色。W走在我右边,像一颗发光的、香气扑鼻的苹果。那段时期她长得飞快,个子已超过我半头,短发在晚风的抚慰下调皮地反复扑打脸颊,W只得不断将它们拢到耳后。有好几次,我转过头和她说话,恰巧被路边商店的灯光晃到眼睛,W的轮廓在逆光中恍若女神。
她没有项链,她的白衬衣也没有喇叭与蕾丝,但她太好看了,加上说话声清脆响亮,惹得路人频频侧目。我开始感到不自在。其中既有被众人打量的腼腆,又有对她过分高调的不满。她比我漂亮多了。举个例子,她的牙齿又白又小又整齐,可以毫无顾忌地大笑,我却不敢,因为我上排两颗门牙长成了一本书打开一半的样子。在和我聊到她表哥把收到的情书折成纸飞机却意外着陆到教导主任脑袋上时,W笑得整个身体像一块竖立的波浪前后起伏。由于我们的胳膊自始至终缠绕在一起,在她的带动下,我也只好吃力地跟着摇晃。我的不自在由此到达了顶峰,继而生出些恼怒。我希望W赶紧笑完,然后我要迅速夺取话语权,问问她那个后妈最近又有什么新花样。
老实说,我有点喜欢听W骂她后妈,听她不假思索地吐出粗话。有时她甚至会不间断地说出一连串。W太放肆了。我一个脏字也不敢说,不过也没关系,光是听她说,我就已经体验到足够多的负罪感以及青春期叛逆的奇妙乐趣。
W是我的邻居,我们认识时还不到五岁。当时每天聚在一起的孩子有七八个,除了我俩之外都是男孩,但要论翻墙打架那些冒险行为,W样样都不比他们逊色,这样一来,胆小谨慎的我便成了其中的异类。但我没有别的玩伴,只能坚持跟他们一伙,哪怕大部分时间都充当观众,也要从傍晚熬到天黑。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出点子。那个时候伙伴们年龄渐渐大了,眨眼间都背起书包成了小学生,不再满足于疯跑瞎闹,时常坐在低矮的院墙上发呆。这种无所事事太难忍受了,于是我站出来提议,不如举行一场联欢晚会,接着就开始安排这个表演东西,那个扮演南北。为了方便小合唱站成阶梯队形,我把舞台选在楼道里。结果楼道里灯坏了,我又临时宣布晚会暂停,鼓动大伙赶紧回家找手电筒。晚会最终演绎成一场扮鬼狂欢。每个人都用手电筒抵住下巴颏,蹲在黑暗处,一有人经过,就立即按亮灯泡,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不出意料地引来一通通热闹非凡的臭骂。
虽然吓唬人不是我的主意,但光线从下往上照出鬼脸的招是我出的,那次大伙玩得特别过瘾,都认为应该归功于我,从此我就成了小团体的“军师”。
我们就这样天天玩,一直玩到五年级。有一回,小伙伴发现隔壁单元有人养了一条狼狗,不等我这个“军师”发号施令,W就提议去敲他家的门,门一开狗自然会跑出来,到时候将那狗驯服,大家轮流骑狗玩。最关键是,有了“坐骑”,就可以向对面居民楼发动“战争”,毕竟对面楼的小孩嚣张很长时间了。众人听罢士气高涨,纷纷表示赞同。而我扭头就走。我生来怕狗,光是听到狗叫腿就发软,对于驯狗骑狗这种近距离的危险游戏,我连当观众的勇气都没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独自下楼,怕突然窜出个摇尾巴的不速之客。
有一天,W来我家,说出两件可怖的事情。一是她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要在医院里住三个月;二是她自己得了更严重的病,可能很快就要死了。我问她什么病,她说流血。直到现在,我还对当时的心惊胆战记忆犹新,我们把房门关上,又咔嚓上了锁,W站在屋子中央像一只鸵鸟那样静止了几秒钟,然后咬咬牙,刷地脱下裤子。我探过头去,天哪!真的是血,猩红色的一大摊。我的腿立马软了,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她仍然是健康的样子,圆脸红扑扑的,嘴唇边有颗痣,眼珠子是棕色的,头发颜色也是,看上去总有些像外国人。我无比惆怅地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她像外国人才得了那种可怕的病?那天我不太确定她有没有带病坚持驯狗,我黯然神伤地坐在窗户边上,还像往常那样倾听楼下的动静,小伙伴不断发出短促的命令,笑声与尖叫声中依然夹杂着兴奋的犬吠,我却再也无法感知其中的欢欣。
又过了一阵,天气热了起来。W在星期天的下午找到我,邀请我去她家玩。她家里一个人也没有,特别干净整洁,有种让人害怕的冷清。后来我才明白,房子空着的时间长了就是这种感觉。W告诉我,实际上她没有生病,流血是一种正常现象,每个女生都会这样。我马上反驳,我就没有,难道我不正常吗?她看看我,不太确定地说,那我再问问我小姨,月经知识都是她教给我的。W说她妈妈得的是癌症,一直住在医院里出不来,她爸爸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照顾病人,只好把她托付给小姨子。原来这段时间W一直住在小姨家,也不知道她把驯狗的任务交给了谁。说起她小姨我倒是见过,香香的,烫着大波浪,涂着红嘴巴,是个时髦极了的美人儿。W是回来换衣服的,天气热了,该穿裙子了。我看着她从一个大手提包里一件一件地取出薄毛衣、运动衫、灯芯绒长裤,然后分类放进衣柜不同的隔层,再踩着凳子从衣柜顶端拽出个布袋子,里面是夏天的衣服。她把每一样都用力地抖落开来,一一审视,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霉味。W做事情的样子越来越像个大人了,我默默地想。果然,家里出了事,人就会长大得快一些。
我渐渐明白了W的意图,她在向我炫耀。那些衣服样式新潮,很多布料摸上去丝滑冰凉,有种神秘的陌生感。是小姨给我的,W一边忙活一边说,她的衣服太多了,穿不尽。五花八门的裙衫摆满了床铺,时装发布会进入自由鉴赏阶段,W开始试穿起来,但她的身体暂时还驾驭不了成年女性的尺码,不是领口太低就是腰身太宽大。看来还得再等一年,她失望地叹了口气。我小心拎起其中一条天蓝色的半身裙,被它深深吸引。
我要说的就是这条天蓝色的半身裙。它有巴掌宽的松紧腰带和华丽的裙摆,我猜想穿上这条裙子转起来肯定比海面上的波浪还要美。W两只手叉腰,一大截裙边拖到地上,仔细看,温馨的棉布上还缀着点点花蕊。那个时候我虽然瘦,个子倒是高一些,便提出想要试一下,或许它的长度正适合我来穿。但W拒绝了我。我会长高的,总有一天能穿上它,W认真地说道,像是给我的解释,又像在自言自语。
她说得没错。一年后,也就是我要说的那个舒朗的夏夜,她果真穿上了。她把衬衣的下摆掖进去,裙子腰带往里折了一圈,裙边终于离开了地面。就这样,W穿着天蓝色的半身裙和我一起走在街上,她实在太好看了,我简直为之发狂。我甚至在考虑等她笑完表哥的事,切入后妈话题之前要不要赞美她一番,我想作为闺蜜,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应当让她知道这个该死的真相。
就在犹豫的时候,一个皮肤黝黑的瘦小个突然冒了出来,肩头摇摇晃晃地带着几分挑衅。还要装不认识吗?瘦小个嬉皮笑脸地问。W猛地收住笑声,没有回答,但我感觉到了她的警惕。因为我们手臂缠在一起,我明显感受到她那边绷紧了,步子也正以不易察觉的幅度加快。我偷偷打量那个人,的确像在哪里见过,是在学校门口吗?可他看起来完全没有学生样,痞里痞气,走路还甩脑袋。
咳,我说,我们是不是该把账算清楚?瘦小个紧跟我们的步伐,一个劲往W身上凑,W就朝我这边躲,被动的我只好一挪再挪,眼看三个人就要并排着走到马路中央去了。好在车不多。我们已经走过了闹市区,灯光渐渐稀疏。
算什么账,我又不认识你。W终于开口,同时伸直胳膊将对方往反方向推了一把,但她的身体抖得厉害,缀着细小花蕊的裙摆在急促的脚步的搅动下不断扫打在我的小腿上。我记得电视里跳探戈的女人,也是这样的大摆裙,猛打方向,舞步犀利。可惜瘦小个并不是一位绅士的舞伴,当裙摆扫打他的小腿,只会成为激怒他的催化剂。
说起来那本是个无所事事的夜晚。我和W只是结伴去街上边走边聊天,顺便看看世界,我们各自的精心打扮并不为了谁。但这个说法又多少有些不诚实,好看的衣服穿在身上,谁敢对天发誓,没有一丁点虚荣心,没有一丁点获得陌生人赞美的期许?但绝不是被瘦小个这样的人赞美。他猝不及防,被W推得失去平衡,柴火棍般的身体栽倒在地,脸上写着几个字:给我等着。我惊恐极了,感觉大祸临头。W倒是镇定了许多,只踟蹰了两秒钟,之后,我就从我们挽在一起的胳膊上接收到新的信号:赶紧走。
可我的腿软了,像遭到恶狗追咬,想跑却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喇叭袖和海浪裙摆就成了可笑的累赘,它们还在优美地演绎着曲线魔术,殊不知自己的主人正狼狈奔逃。瘦小个很快追了上来,他果然发怒了,歪着嘴,喉咙口发出浑浊的颤音,随后我闻到一股呛鼻的烟味儿。
和一个年龄差不了太多的抽烟男生走在一起,对13岁的我来说,是件令我双腿发软的事情。首先,这意味着危险,其次,路人会将我们视为同伴。更糟糕的是,当我们拐到一条倾斜的小街,没走几步,抽烟的男生又增加了一个。瘦小个打了个干瘪的响指,变戏法一般,戴破洞帽子的男生就出现了,两人坏笑着,作势用拳头相互攻击对方的小腹。
这是我从未见识过的情形。破洞帽子加入了我们,他走在我这边,个头和电线杆上贴广告的高度差不多,他身上浓烈的汗味熏得我头晕目眩。我悄悄对着W的耳朵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害怕。W没有理会我,她全身心投入在与瘦小个的谈判中。他们说话声音好似苍蝇蚊子,我只能听到间杂其中的脏话,因为它们总是那么字正腔圆、情绪饱满,并且理直气壮。
你叫什么名字?破洞帽子微微俯下身,语气礼貌且真诚——尽管我极力排斥这种好感——但我听到的的确如此。我回看了他一眼,很快拨正脑袋,两眼直视着前方的虚空——我想绝不能说,又担心此举招致祸端。好在破洞帽子没有再问,他保持那个俯姿走了几步,就重新直起腰,鼻子里喷出一股烟雾。他冰凉发黏的胳膊不时碰到我的左臂,这种接触令我恶心、反感,但我无法判断他是否有意,也没胆量抗议,只能尽量躲避。我右侧的谈判还在继续,大概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W的语气缓和了许多,瘦小个还笑了几声。小街斜坡向上,两边的店铺早已打烊,昏暗夜色中只剩下我们四个。我们的腿不知疲倦地走啊走啊,并排步入弯曲的巷道,在里面拐来拐去,完全搞不清究竟是谁在控制方向,也不知道有没有目的地。来自两边的挤压越发肆无忌惮,我紧贴着W的胳膊已经麻木。
谈判终于结束,说话声也恢复了正常分贝,内容不再保密。W正在介绍我,重点例举了我哪些功课好以及我比她漂亮的地方。怎么样?我朋友是不是很XX!W问他们,用无比得意的口吻。我惊呆了,没想到W会用一句脏话来形容我。确实XX!两个男生绕到正面仔细打量我之后,对W的评价表示赞同。他们三个大笑起来,俨然成了一伙。如果说之前我的害怕因为还有W的胳膊可以依靠至少能维系表面的镇定,而眼下,W的叛变将我的害怕瞬间升级为恐惧。在他们的笑声中,我彻底陷入了悲伤与绝望,任何伪装都失去了意义。我们还在继续往前走,左拐,右拐,没完没了。W的裙子成了一块碍事的破布,它来势汹汹,带着W的坏脑筋,几乎裹缠住我整个身体,正如我身临绝境。
我没想到天蓝色的半身裙会变成这个样子。
遥想那个星期天的下午,W慷慨地把其他衣服堆到我身上。这些你都可以随便试,W笃定道,甚至带着将其中一件送给我的决心,唯独不肯让我再碰那条天蓝色的裙子。很快迎来了暑假,暑假过后我们升到了六年级。W的妈妈是六年级上学期快过元旦节的时候去世的。我正在吃晚饭,楼下传来阵阵嘈杂,有人大声呼喊,还有乐队吹奏。终究熬不过一年!妈妈叹了口气,停下筷子掰起指头算。九个多月,不到十个月。她补充道。我突然明白了,赶紧跑下楼。楼前的通道搭起了两个大棚,很多人聚在里面,说话的,哭的,都忙碌着。隔壁单元的狼狗也加入了悼念,它趴在大棚边上,耷拉着脑袋。我顿时腿软,但为了更重要的事,我命令自己必须暂时克服怕狗的毛病。我在乱糟糟的人群中觅到一个少女背影,头戴白帽穿披白衣,跟随道士的指令时立时跪。后来我看清了棚内悬挂的黑白照,正是W的妈妈。她微微笑着,好像当初拍照时就预知了用途,眼神中流露出几分痛楚与不舍。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她们家的姊妹个个身材高挑,性格泼辣,唯独阿姨温柔和气。更令我悲痛的是,从今往后,W就没有妈妈了。我把这个情形代入自己身上想了想,如果我没有妈妈,那会怎么样?简直比死还要可怕。于是我放任泪水,哭得抽搐起来。
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答案,没了妈妈会有后妈。W的妈妈去世不到半年,她爸爸就找了后妈。头天领到家里做了顿红烧排骨给她吃,第二天就带着小女儿住进来了。W为此哭了一晚上,枕巾湿透了,她说她尝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她无法理解爸爸这么快就把妈妈抛在脑后,和一个认识不到半年的女人结了婚。W口中的脏话一开始应该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据知情者透露,在她妈妈病重期间,她爸爸就和那个女人好上了。简直就是XX!W悲愤地骂道,带着明显的模仿痕迹。
后妈要求她学做家务,给她演示如何煮饭炒菜,却从不肯让T也就是自己的亲女儿进厨房,因为油烟呛到了会头晕。那个时候刚上初一不久,W已经能熟练使用各种厨具,她拿水壶烧水,从橱柜里取出一只大碗,挑了一块猪油,又添加了好几样调料,她还动用了菜刀和砧板,切出一小堆葱花,最后开水冲进碗中,屋子里充满了浓烈的香味——W自己发明的汤。我看着她靠在水槽边大口喝下,随即把碗冲洗干净。
然而,这并不是那一天最令我惊讶的事。
喝完热汤的W拿起茶几上的香烟,居然抽出一根来点燃了。我整个人都懵了。烟雾从她嘴里喷出来,她咳嗽了几声,不屈不挠地与那无形的魔鬼较量着。这么小抽烟!这肯定是不对的,我想阻止她,但又十分好奇想看她继续抽下去。两股势力始终在斗争。W就在我的注视下抽完了一根烟,她的脸颊微微泛红,与我对视了几秒钟之后笑了。我没有笑。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把脑袋捂进被子,在憋闷中替W找出许多悲情理由,以佐证她抽烟的合理性。
现在看来,那些理由都太过苍白。事情的真相是W变坏了,她早就变坏了,从她抽烟开始,不,甚至应该从她不肯给我试穿那条天蓝色的半身裙开始。
两个男生又掏出烟来,W提出她也要抽,瘦小个愣了一下,随即心领神会地笑着点点头。厉害厉害!破洞帽子俯下身来给她支打火机。我无法预料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但很明显他们在针对我。危险近在咫尺,我以一敌三,毫无胜算。想到这里,我不顾一切兀自挣扎起来,反复努力了多次,终于从W怀中抽出僵硬的右胳膊。我开始跑,在迷宫般的巷道里胡乱冲撞,我承认我又腿软了,但只要有一息尚存就不会停。
他们在附近低声喊我的名字,令人胆战心惊的呼喊从四面八方传来。他们一边喊一边笑,其中还夹杂着脏话,我从中辨出了W的声音。她在骂我,用以前骂她后妈的那些字眼和语气。我的泪水哗哗流淌,冲掉了先前试图凭借记忆返回小街的念头。我想即便一直迷路,回不了家,也要跑得远远的,离W越远越好。
但她一直跟着,无论我怎么左拐右拐都摆脱不了。快要跑不动的时候,我猛然发现前方是堵墙,要命!我竟然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惊慌失措间我瞥见暗影中有扇半掩的门,直觉告诉我不能犹豫了。我像泥鳅那样钻了进去,屋里是空洞的,只有放大了的黑,但那气息似曾相识,是久无人住的清冷。我倾斜着身体,肩头死死抵住门。外面很快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
咦?跑哪儿去了?
这里有门!
我一来就发现了,门是钉死的。她应该去了那边,我刚才好像晃到一个影子。放心吧,她跑不快,她是个胆小鬼!咱们赶紧追,一定能追上。
W说出那些话的时候,背就靠在门上,和我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天蓝色的裙边从木头缝隙里悄无声息地渗进来,我看到一种触目惊心的蓝,一种惨白的蓝,介于银色和灰色之间的、死亡临近时映在眼底的那种蓝。
黑暗中时间也会迷路,不然它不会那么慢。我不敢松懈抵着门板的右肩,但两条腿早已经失去支撑力,整个人蜷缩成蜗牛的样子。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晚漆黑的楼道,伙伴们分散在各个角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附近的鼻息。
赶紧出来,他们走远了。快!快!
W急切的声音出现在门外,她喘着粗气,门被弄出很大的动静,她正在想办法把门抠开。我将信将疑道,真的假的?说完马上后悔了,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他们的圈套,如今我已暴露。恍惚中我被卷入漩涡,身体躺平,四肢漂浮,越来越轻。
初三那个没有作业的暑假特别炎热,有一天我连吃了三根冰棍,下午肚子疼得打滚。傍晚时分,我抬头望天,发觉月亮不对劲,再一低头,就看见了红色。我第一反应就是要告诉W,我也是正常的。
高中我们不再同校,W读了中专,住校的那种。按她的话来说,终于可以摆脱那个女人了。高三寒假我们在街上偶遇,她从一群热闹的男男女女中走出来和我打招呼。我问她天蓝色的半身裙你还在穿吗?她说早就撕成破布条了。本来我还想问,那晚巷道里你为什么要骂我?出于某些说不清的缘由,我没有问出口。W有些心不在焉,她不停地转头,看向那群男女,我想我们早就不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之后W再无消息。
又过去了很多年。期间人生际遇带来的各种变化我从未仔细盘点。偶尔在街头巷尾,有天蓝色的身影闪过,我的心绪却仍然会为之波动。后来我带上了牙箍,想象有一天自己牙齿整齐,可以像W那样咧嘴笑,在晚风轻抚下猛然转身,天蓝色裙摆制造出一座小而壮观的海。当我终于从镜子里看到满意的牙齿,却又为缺少唇边的痣和棕色的眼珠子而忧愁。究竟是放不下W,还是放不下那条天蓝色的半身裙,我已无从分辨。然而人生如此漫长,长到它懒得提前通知我:终有重逢时。
有一年春暖花开时节,我从外地赶回老家处理事情,手续涉及的居委会就设在那条倾斜的小街上。奇怪的是,当我重回故地时却发现附近根本就没有巷道,我仔细找了一遍各色作坊商铺挤满了的街道两侧,仍不放心,又向摆摊的太婆打听。她接连摆手。我想,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没有。起身便听到有人喊我名字,我不禁心里一颤。
好巧不巧,喊我名字的人竟是W的爸爸。他当街立定,任凭来往行人从我们前后左右穿过。他大声表扬我读书读得好,考到很远的地方,并且去了更远的地方工作,作为曾经的邻居,他为我骄傲。语气中带着夸张的成分,我客气地谦虚着,用礼貌的频率打量他,将他同记忆里的印象一一比对。W的爸爸老了许多,原本略微泛红的鼻头彻底演化成了酒糟鼻,细软的头发一缕一缕抛洒在脑后。絮叨了一大堆,他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马上就要走。匆忙中又掉头回来说,有空去找W,你们可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W。
这只是个借口。实际上,是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毕竟,打听出她在哪里开了一家叫什么名字的租碟店并非难事。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认识W,其中又有很多人经常见到她。W的样子有了变化,但仍然是好看的。嘴唇边的痣大了不少,眼珠子还是棕色,但头发颜色不是了,染成了稻草黄,有时也染成酒红。她喜欢涂黑色眼影,我想,那样看上去就更像外国人了。W结婚了,男人比她矮,戴着眼镜,二婚,手里牵着和前妻生的小女孩。W说,那不就是当年的我吗?我没法不对她好,每次我想冲她发火,就想起自己小时候。问题是那个男人看上去既不聪明也不愚蠢,根本配不上W。是的,我终于还是偷偷潜入了租碟店,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看W。
一开始W没有认出我来,我怀疑她是故意的。我在店里转来转去,像在认真找东西,又像个伺机而动的贼,过了许久,失去耐心的我站在第二排货架末端大声问道,老板,有没有某某某的演唱会呀?某某某是当年我们共同喜欢的歌星。W立马响亮又干脆地回答:没有!
然后她的身影出现了,陌生,又在意料当中。她似笑非笑,冲我挥挥手,示意我走到店铺外面去说话。我以为只是几句简短的寒暄,实际上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期间站一会儿又蹲一会儿,或者在附近来回踱步,却没人提议找个能坐着交谈的地方。于是,那些重要的、涉及青春成长的话题就在车水马龙的街边进行到底了。
当年瘦小个追求W,W自然是看不上。但她恨后妈,连带着后妈的女儿T。瘦小个便许诺替她收拾T,W不置可否,内心却又期待着,比如把她的书包扯个稀巴烂,比如使个绊子让她摔个狗啃屎,等她爬起来再给她两巴掌之类。有一天,T果然头发散乱着哭哭啼啼地回了家,W吓坏了,她意识到事情远远脱离了想象的样子。人的内心一旦出现了敌人,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敌意。她也因此意识到,和解是一件充满艰辛与魔幻色彩的事。首先,她得相信后妈的苛刻源于善意的初衷,因为女孩必须自立,学会独自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坚强冷静,她才能从容机敏地与瘦小个周旋,甚至在对方有增援的情形下临危不乱。但是,当她的同伴异常胆小,且在恐惧中丢失了智慧陷入悲伤中无法自拔,又该怎么办?
“那晚如果我被发现了,他们会做什么?”
“什么都不会做,他们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W狡黠一笑。
“你为什么不肯让我试那条裙子?”
“哪条裙子?”
“天蓝色的半身裙。”
W愣住了,她开始认真地回忆、思考,似乎要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我顿时紧张起来,然而W只是望着我,长叹一口气。
我始终没能穿上那条天蓝色的半身裙,这种遗憾以及遗憾带来的种种感受陪伴我走过了少女时代,或许,我也好,W也好,或者我们身边随便一个谁,都是经由对某件事物的执念去认识世界的。某种偏激的、忧伤的、好奇的、沉沦于困境中的情感指引着我们。当有一天,我们感到世界不再陌生,能足够从容地行走在人群中时,我们才有勇气随时停下来,谈论爱,谈论友谊,以及那些阻止我们速朽的东西。
【作者简介】艾蔻,本名周蕾,1981年7月出生于新疆库车,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诗歌、散文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作家》《十月》《解放军文艺》等刊。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现居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