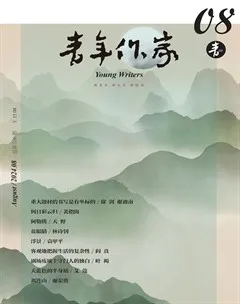剧场废墟上守门人的独白
摄像机架在高处,对准了舞台中央一位面对观众席的老人的背影。
既然已经进来了,那就请入座吧,请你们小心脚下,那边的地板都塌陷了,小心一点,别踩上去,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但是看看那边的洞,地板下面是几米高的钢架,掉进去会没命的,你们一定没见过,也不可能见过,在剧场建成的那一天,我悄悄从观众入口进来,从看台上走下来,看着几个人认真地跪在舞台上擦拭,洁净,走近了才能看到上面还点缀着细小的反光颗粒。舞台像月亮一样闪耀。也是在那几天里,舞台剧的主演依次入场,我把一盆芍药花摆在员工宿舍的窗台边,一位年轻人走到舞台上,在芍药开花的那天,他趁着初夏时积郁着的即将喷发而出的热浪穿上了一件粉白的T恤衫,鼓胀的肌肉把T恤撑起来再从袖口满溢而出,这一切都恰如其分。在这一年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肌肉和他的生命一样,和我颓败的芍药花一样,枯萎下去,被爱情用充满热情又不可动摇的丝线拉倒在地。看看他,在他干枯的躯体外面披了一层人造的肌肉,瘦削的脸上布满沟壑,嘴里喊着他一成不变的台词,“我要以血肉之躯射落九个太阳”,观众坐在露天看台上冻得瑟瑟发抖,不住地往自己的双手中哈气,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一次又一次做出拉弓射箭的动作。弓箭和他头上戴的羽饰早就被我收起来了,那天我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从宿舍里出来,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在检票口站了许久,剧场外墙上挂着的海报早就褪色了,固定在墙上的一角被风扯断耷拉下来,噼噼啪啪地拍打着墙面。我们在检票口站了许久,然后自顾自地进到剧场里,里面的一切都和刚建成的时候不同了,后面看台上的那些塑料座椅那时候就有不少已经损坏了,坐垫上雨后的水渍大都还没被清理掉,我们几个冲进后台,桌椅板凳还都放在原地,但大家都能明白,有些什么已经离开了,我们并没有时间犹豫,被彼此裹挟着,也被紧迫裹挟着。我们像一大片偏离方向的箭矢一样涌入化妆间和库房,把所有闪亮的,看起来昂贵的物件都揣进口袋,大件的就拿在手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把弓和那件羽毛装饰的头饰,饰演后羿的年轻人穿的那件浅棕色的人造肌肉就扔在一边,布满褶皱,这也是历经我们洗劫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东西,当然现在应该也不在了。我们抱着一叠叠的头盔和轻铠回宿舍里,一个个扮成士兵的样子,嬉笑着来回比画那些刀剑和长矛,这些东西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在剧场刚刚投入使用、这幕剧刚开演的那一段时间,观众络绎不绝。下午演一场,晚上演一场。我得守在门外直到散场,赶走那些没买到票,想在开场后碰碰运气的人,但我偶尔也收点小钱放进去几个人,这是我的权力,我一开始就没期望着这种权力能维持多久,不如说这种热乎的势头本身也没维持多久,后来开场后不久我们就能偷偷溜进去坐在后面看完整场演出,观众都凑在前排,舞台上的士兵们穿着后来被我们搬走的铠甲,戴着做成怪兽模样的长着獠牙的头盔,几乎露不出自己的脸,挥舞着手里的长矛,颇有气势地号叫着。舞台的上方和后方有许多块屏幕,卡在这些模拟成灰色岩壁的立柱之间,有时候会放映讲解背景的影片,更多的时候就是多角度展示那几颗太阳。演嫦娥的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我还知道在舞台剧现场说出或者唱出台词的另有其人,她本人的声音并不是那样的,一次演出结束后,我在离后台出口不远的观众出口处安排观众离场后四处转悠,偶然地碰到嫦娥和后羿一前一后地出来,在争执什么,我没想偷听他们的谈话,等到嫦娥离开了我才走出来,后羿披了件夹克在肩膀上,坐在台阶上,看上去有些沮丧,就像我说的,他确实是个年轻人,可能和我儿子年纪相仿,甚至还更小一点。我坐在他旁边,把一根烟递给他,他接过烟自己点上火抽了起来,虽然那时他一句话都没说,但后来我们慢慢熟络起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演员们一开始都住在不远处的小镇上,和剧场一样,是刚刚建起来的,里面几乎没有居民,各种设施都是专为接待游客建设的。来上班的第一天,我乘车路过那个小镇,里面的建筑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都挺时髦的,风格统一,都是砖红色的小楼,镇子的中央是个广场,地砖刚刚铺好,上面似乎要放一座很大的雕像,雕像用泡沫包裹着放在地台边上。镇子里没什么人,司机和我说现在整个镇上只有一家超市开始营业了,其他地方都得过一阵,我们如果需要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可以去这家超市,就不用总往市里跑了。给后羿递烟的那天晚上,小镇上应该有不少地方都已经启用了,因为我们坐在剧场的台阶上就能看到那里星星点点的灯火。总之那天晚上之后我们慢慢熟络起来了。他有时候会在两场戏之间来观众入口这边和我一起抽一根烟,聊一聊近况。和我想的差不多,他们的生活也基本和我这个年过六旬的人一样停滞着,演员们长期住在镇上的一家酒店里,不工作的时候也只能聚在房间里打打扑克,或者到镇上的酒馆里去喝那些供给游客的掺了色素的鸡尾酒。我已经无所谓了,可年轻人不能在这种地方一直待下去。我们熟起来的时候剧院不过刚开业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长是短我们都不好说,但是对我来说肯定是无所谓的,我的人生几乎已经结束了,面对什么新鲜事也几乎都提不起兴趣。那么长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好像是只过了一瞬间,虽然当时没问起来,但我知道后羿和嫦娥可能恋爱了。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到镇上的超市去买点生活必需品,看到他俩亲昵地坐在广场上的长椅上,那座雕像和我刚刚抵达那里的时候一样,依然被包裹着倒伏在地台边。镇子其实和我刚刚抵达的时候区别不大,只是多了些背着双肩包的游客,人也不是很多,在这种时间几乎停滞不前的场域里,人都会以自己意想不到的速度衰老,等再回到人群中时,往往会感到恍若隔世。我有些担心这个年轻人,一个像他这样充满热情的人,会比别人更快地被损耗,那个女孩和他不适合,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个女孩的眼神和表情里全都空荡荡的,在舞台上也是那样,所以才请了另一个人为她配音,她是不会被这种环境拖垮的,我熟悉这种人,把一切都封闭在自己的内部,就连一双眼睛都是看向自己的内心的,他们对外部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察觉,几乎没法扮演一个悲剧的主角,她的内心没有容纳他的热情的空间。恋爱的事他自然不会轻易和我讲,他有高傲的自我,有他不可辱没的自尊,表面上看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一样,穿着同样的戏服,做着同样的动作,说着同样的台词,可如果你仔细去看他偶尔会不自觉抽动的嘴角,去看他的日复一日逐渐失去光彩反而充满怒火的眼睛,你也会和我一样为他担忧。年轻人的生活不能这样过下去,他们需要家人、朋友、街道、城市,这些东西都是真真切切在那里的,是这个凭空冒出来的小镇和剧场给不了他们的。我儿子也是个热爱戏剧的孩子,在他离家之前,我常常听他谈起雅典、伊甸园、浴场、剧院,他向往那里的生活和爱情,可这个小镇绝不是那样的地方。入秋之后,客人慢慢少了,九月里整个剧院都很冷清,碰上周末最多只有几十个观众。演员们也慢慢有点懈怠了,士兵里面总有那么几个浑水摸鱼的,躲在后面打打闹闹,用刀剑来回比画,他们和我们小时候没什么两样,根本就不明白尊重为何物,和我们那时候一样,都是些没脑子的傻蛋,连自娱自乐的方式都没什么创意。我根本就用不着担心,他们有吃的、有住的,就能傻笑着把一天天挨过去,他们也察觉到了后羿和嫦娥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会跟在他们俩身后,从后台哄笑着走出来,这些一旦失去了同伴就会噤声的癞蛤蟆,自然不会明白,也不会理解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你瘦了。”我说。他确实是瘦了,他意志力的高墙也被削薄了,现在他不会没事儿就在空地上摆弄他的那些武术动作了,他干巴巴地站在那儿,若有所思地低着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劝他,我这么一个身无长物的老头,我说的话又怎么让人采信呢?你们看上面,从岩壁顶上垂下来的钢绳,还有那几个岩柱,抬头,往上看,看到它们中间的那些钢索了吗?嫦娥奔月的那一段舞台上的灯光变暗,灯光改为照到半空中,嫦娥就由这里的钢索拉上去,然后在月光似的灯光里,在这些岩柱之间穿梭,最后钢索会把她拉到屏幕缝隙间的那个岩壁背后,那后面有一道隐藏的楼梯,她就从那楼梯上下来然后趁着黑暗回到舞台中央,之后一束追光灯打在她身上,再由她来表演奔月后的孤寂。我一直都没弄清给她配音的那个演员是谁,但一定有这么一个人,就像我说过的,那个声音绝不是她自己的。嫦娥的那套纱裙,对了,我们并没有在后台找到那套纱裙,看质地的话如果找到了绝对能卖个好价钱,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一开始是那些士兵演员少了几个,后来扮演嫦娥姐妹的那几个演员好像也不那么全了,道具的修补也慢慢跟不上趟了,总的来说就是这部热热闹闹的舞台剧越来越寒酸了。一个休息日,可能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三,我到剧场里去打扫那些观众留下来的垃圾和被风刮进来的落叶,后羿仰靠在观众席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上,抬头看着那些关闭着的电子屏幕,他发现我来了,扭过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上带着那种直面灾难后人们脸上的那种表情,苍白且僵硬。他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异常,没等我开口问就自己说了出来,“她走了。”我那时候其实想问他,她走了,你为什么还在这儿?这个地方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吗?你这种年轻人也不至于找不到一个混份饭吃混点酒钱的工作。但我终究还是没说出口,我自己不也是情愿待在这里消磨掉生活中漫无目的的时间吗?而且他才是这出舞台剧的主角。我拿了一根烟递给他,整个剧场在那一刻显得那么庞大又空旷,观众席、舞台、模仿月球表面的外墙、两者间的空地,我们显得过分渺小,这些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被这些庞大的人造物给挟持起来了,这个以他为主角的剧场在这个瞬间,像一只大到没边又把他困在其中的鸟笼。但如你们所见,这个鸟笼并没把他困住太久,至少现在这里不能再困住任何一个人了,在劫掠了后台和仓库的那天晚上,我们很兴奋,但还是像平常一样到点就上床睡觉,可早上醒来的时候,整个宿舍空空荡荡,除了我躺在上面的那张木板床和上面的被褥,他们把桌椅都搬空了。我在四周转了转,我应该是附近的员工里唯一一个还没离开的人,不过这也不怪他们,我从一开始就瞧不起他们的自以为是和那种快活的态度,怎么着,他们都觉得这是一次短暂的带薪郊游,他们都以为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段插曲,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会愿意来这种荒无人烟的古怪地方工作?更不用说工钱原本给的就不多。苦难就是苦难,绝境就是绝境,这些都是刻在我们身上的烙印,不会被他们每天晚上三四个小时的牌局给洗刷掉,我从来没加入过他们的牌局,更讨厌看到他们为了几毛钱的胜负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那股穷劲儿。他们自然也不会喜欢我。大概在十几年以前,我儿子去罗马旅游,那天我早上一醒来他就给我拨来视频电话,他正在古罗马斗兽场的边上,人类的造物,过了上千年还伫立在原地,它主人的尸体早已经化为泥土,它的时代都已经死了。它已经目睹了无数个时代的死亡,可它的血腥味还没有散去,它还没有回到自然之中,还以那样破败的姿态苦苦支撑着。但我还是有信心,我们脚下的这座剧场不会成为遗迹。你们再看看这些虚伪的岩壁,看看它们表皮脱落后露出的内里锈蚀的钢架,看看这些在某一天突然轰然落地的昂贵的功放音响,看看它们砸出来的这些深坑。虚伪!虚伪!虚伪!这就是我的态度。它不会成为遗迹,它甚至没有成为遗迹的资格,它总有一天会被铲除,露出一片惨白的、多年来从未被阳光照耀过的土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十二月份,我们好几次都被通知休息,票已经卖不出去了,我们也没什么办法,我在电话里问我儿子,“你说到了你爸这个岁数再去了解戏剧是不是有点晚了?”他说:“没什么可着急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我那时候不该去相信这小子的鬼话,因为最后一出戏被演完的那天晚上之后,我在这里又待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傍晚,一个穿着牛仔夹克和牛仔裤的年轻人忽然出现,才带来了我儿子的消息。“叔叔,我终于找到了,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交给您,”他说,“叔叔,您叫我大光就行。”他把一叠剧本交给我——《植物学奥德赛》。如果事实正如这个叫做大光的孩子所说,那么这个剧本是在我儿子失踪之后写成的,他对这出戏剧的舞台布置做了详尽的规划,正中间是一个圆形的舞台,上面是一间植物研究所的布景,三个串联的房间,卧室、客厅和实验室,研究所外种植了一种能够快速长高的蕨类植物,在戏剧上演的几个小时内高度可以翻倍,圆形舞台的外围有木质的幕墙,上面细致地画出森林、山坡、山下的小镇,还有天空和太阳等场景,尽可能利用视觉错觉安排景物,利用景物线条的扭曲创造出广大的空间感,让身处舞台中的演员感觉自己身处自然之中,在幕墙上方遮盖可滚动的天蓝色、黑色、灰色三种颜色的幕布,随剧情的推进滚动,这种设置的关键之处在于让演员无法感觉到观众的存在,而观众只能靠幕墙上挖出的小洞来窥视演员的表演,至于情节反倒就没有布景这么复杂。一个年轻人误入自己所设的精神陷阱,开始在舞台上来回踱步并持续不断地独白,在一系列独白后他了解了自己的处境,没有选择设法逃离陷阱,而是开始精心照料其中的蕨类植物。我想他在写下这个剧本的时候没有想过某一天他的父亲也会读着他的稿子,面对和他一样空白的现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上演最后一出戏的那天早上,我从员工宿舍里出来,准备打个电话给老板问问工钱的事,我顺着原本被规划为工程用地的空地外围的铁丝网向剧场的方向走,工地从我来时就堆满了建材,到今天也依然没有动工的迹象,我沿路不停地试图拨通电话,但一直等我走到剧场跟前也没接通。我看到后羿靠在检票口外的墙上,双手揣在外套口袋里,低垂着头,一副脱力的样子,他看到我了,他抬起头来,“我梦到她死了,您说这正常吗?”他朝我走了一步,“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和她都穿着白色的紧身胶衣,在一个明亮的白色房间里操作一台黑色的机器,上面只有一个硕大的指示灯和两个按钮,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她那边,指示灯会慢慢变红,等我觉得到时候了,就按下面前的按钮,指示灯的红色就会慢慢褪去,再慢慢变成绿色,等到她觉得那绿色足够强烈了就再按下自己面前的按钮,让指示灯慢慢再变红,我们都很紧张,没有丝毫松懈的空间,似乎错过了那个时机就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我们重复做着这项工作,重复了很久,没有交谈,我隐约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可是手里的工作是那么紧迫,容不得马虎,我把十二分精神都投入到其中,不知道过了多久,指示灯忽然变成了白色,忽明忽暗地闪烁了几下,之后就熄灭了,我和她同时抬起头来望着对方,几秒之后,屋子里的灯也熄灭了,这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这间屋子的屋顶是完全透明的玻璃板,已经是晚上了,稀薄的月光照进来,让我们能依稀辨出彼此的模样,我们毫无迟疑地冲向彼此搂抱在一起激烈地接吻,我在梦里流下了眼泪,下一个瞬间,我从梦里醒来,发现自己正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不远处布置了一个小小的讲台,讲台上有她被白花拥簇着的遗像,而她本人正在讲台后面发表讲话,‘今天,我死了’,她说,脸上带着笑容,台下整齐地摆放着几十把黑色的折叠椅,来宾的细节被极度地简化了,只是些黑色的虚影,他们剧烈地鼓掌,随后她自己躺进了棺材里,棺材的盖子自动合上了,一条绳索凭空地降下来,把棺材牵引向空中,好像那棺材完全没有重量一样,跟着绳索不断升高,直到彻底看不见了。”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没有疯狂的血丝,他一句一顿地说完这一段话,疲劳溢出他的身体,感染了周边的空气,只剩下一个太阳了,不足以在冬日里温暖整片大地,我看着他微微发抖,朝空气中哈出白色的气,他不再需要扮演后羿了,可是我该去哪呢?我想,我甚至没有一个需要摆脱的虚像,却有太多注定不会有人回答,但又不得不追问的问题,梦境并不像现实一样无解,梦境更像是自动编排,却又胁迫我们成为演员的舞台剧,随着幕布拉上,有一些演员会永远退场,甚至我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终究会无处可寻,在其他人全都离开了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辆车停在了剧院门口,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检票员的位置上,几个人下来四处转了转,问我愿不愿意继续守在这里,我说我还能去哪呢?领头的那个人给了我一笔钱,之后就没再出现过,我看着远去的汽车,感觉这里也并不是那么虚假,无非是一座模仿月球的剧场,地球上没有哪里会比这座剧场更像真正的月球,人类伸出它的触手又收回,这里是人类留下的黏液,我正等着它被风干。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就终究会目睹那一天。有时候我会在远处的小镇那早已熄灭的灯光中,岩壁后的阴影里,舞台上的坑洞深处,瞥见一道黑色的身影一闪而过,像是不愿露面却又刻意彰显自己的存在,我想那可能是任何人或者任何物,也可能是我失踪的儿子,我来到这里的初衷无非是尝试跟随他的脚步。但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我既自责又懊恼,他朋友的那次来访只带给了我转瞬即逝的希望,我一度想象着生活就是一场隐秘的仪式,只要把合适的物件摆在合适的位置,我自己再说出合适的台词,献出生活的一切可能,命运就会从一个早晨骤然飞落,就像光明的总和。可我在这圆形的剧场里,一次又一次念出剧本里那些我早已烂熟于胸的独白,然后在木板床上等待一次奇妙的梦境的到来,我在那些演员中找寻,却始终没发现那张我所熟知的脸,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已经待了多久,我甚至幻想着,如果我现在回到城市中,是否会发现在我漫长又徒劳的等待中,连人类都早已溃退,可偶尔会从头顶掠过的飞机又一次次击碎了我绝无可能实现的幻想。生活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不能像回忆一样短暂?既然我儿子选择逃离城市,到森林中去,而我选择留在废墟里,那可能也只是因为我们明白,不这样做也只是会被城市所吞噬。那究竟哪里是人类的容身之所?或者说,哪里是人类精神的容身之所?在森林的中央独白,在月球表面独白,也丝毫不会扭转我们的命运,只是会把那些来自于未知的寒意传播出去,让它在自然之中扩散,最终进入人群。我甚至不记得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因为我们是相同的类型,会在张口之前完成对话的预演,在脑海中无数的对话结束后,我们早已错过了现实中对话的最后时机,我只能和这个荒诞的剧场作伴,恐怕它自己也不会想到,它作为光鲜的剧场的使命只有短短几个月,行使废墟使命的岁月却绵延不绝。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熟悉这个剧场,或者说这个废墟的每一个角落,它现在像是我身体的外延,如果我儿子知道了这里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会作何评价,会不会嘲笑他老爹这一次在他看来不着边际的尝试?远在我失去希望很久之后的一天,两个人忽然出现在检票口前,浑身都湿漉漉的。这里已经很久没有过访客了,他们的相貌令我感到陌生,但是他们俩个人却泰然自若地露出友善的微笑,我从那微笑中终于看出,他俩是当年扮演后羿与嫦娥的两位演员,岁月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后羿对我说,“我俩是游泳过来的,我们已经结婚了。”我对他们来之不易的婚姻表示由衷的祝贺,但对他们过来的交通方式疑惑不解。据后羿所说,他离开剧场大约是十五年之前,洪水的发生大约是在十年前,水量之大令人咋舌,处于低洼地带的小镇包括这个剧场都被洪水彻底淹没,他说据新闻报道,洪水发生的第二天搜救行动就迅速开展,在搜救中只发现几头淹死的牲口,而实际受灾与伤亡人数都为零。奇怪的事就在于这之后的几年中水位都并没有下降的趋势,直到今年,水位开始下降,一些地势稍高的地方开始露出水底的淤泥,他俩才决定在这个时候来他们当初相识的地方看看。我错愕地盯着他的脸,不明白这究竟是他出于何种目的开出的诡异玩笑,他难为情地笑了,他已经不再是主演了,我真不该搅和进这些年轻人的爱情里,他把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是一张手绘的明信片,正面是一张简笔画,画着一张呐喊着的男人的脸,旁边抄了一段话,“那些做梦而不哀叹其梦的人,那些潜入一片丰饶的无意识而不带回一丝乡愁的人,都是猪猡。梦是真的。所有的梦都是真的。——安托南·阿尔托”。“后羿”正心不在焉地看着别处,我怀疑他讲的那段奇怪的故事可能是寄信的那个人想出来的,明信片的背面写着,“叔叔,我找到他了。”落款是大光。我努力回忆那个年轻人的样子,他的面孔是模糊的,但是所有的行动都带着不可辩驳的气势,像是一首晦涩的诗歌,但坚持拒绝注解。我紧紧地捏着这张明信片,长出了一口气,这样的日子就要到头了,这些年里的每一天都并非难以忍受,但在漫长的时间里,微小的失落堆积成绝望,无数的绝望编织成地狱,终于,一纸短笺,宣告我即将“刑满释放”。从那一瞬间开始,我感觉那一天近了,更近了,回忆开始涌入我的脑中,如大雨倾盆,其中难解的问题远远多于答案。可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墓志铭是一个问句,仅就这一点来说,我知道我的戏剧还未落幕。在历经一幕漫长的独角戏后,下一幕应该是歌舞剧。正如我所说,这座剧场就像我的皮肤,我身体的外延,从你们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你们的气息,其中带有答案的氛围。这座剧场,到了今天,无论是作为废墟,还是作为剧场,似乎才真正结束了它的使命,我们作为演员,该往下一幕的舞台去了。
这时候老人似乎正要转过头来,镜头却突然移向观众席,对焦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几只脖子上挂着铃铛的迷路的山羊正迷茫地看向远方。
【作者简介】叶褐,生于1997年,内蒙古包头人。有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鹿鸣》等刊。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