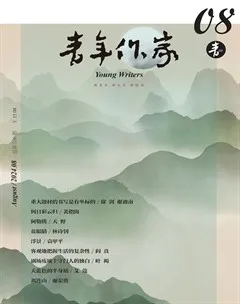客观地把握生活的复杂性
在今日中国,潮汕地区几乎成了一个文化特区。在这里,文化形态在时代风潮的冲击下,几乎完整地保留了自身的传统。家族文化、生育文化、女性文化、拜神文化……传统是如此地顽强,人们可以对它进行激烈的抨击。但你如果真正体验到了这种文化的感性状态,又不得不对它表示赞叹和尊重。我的学生袁甲平的这两篇小说,就真实地向读者呈现了这种生活原生态的复杂性。
《浮景》和《新妇》是两篇相互照应的小说。《新妇》的主人公惠玲和《浮景》的主人公贤妹都是潮汕家庭里的新妇,也就是儿媳妇。惠玲是一个传统潮汕女性,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早婚多育,勤劳能干,任劳任怨。而贤妹是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生,走出小镇,见过世面以后,又半推半就地重新回到传统新妇的人生轨道上来。
这两个小说乍一看会以为写的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但其实故事描述的就是当下的潮汕生活,也就是发生在大家普遍认为女性已经能够自主选择命运甚至掌握命运之后。因此,我们很容易用居高临下的视角,以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为范本,去审视潮汕地区的保守、落后、压抑。这两个小说中,族权、父权、夫权压迫无处不在,俨然就是社会进步的逆流,潮汕好像是一个急需被解放的地区。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从男女平权理论看,潮汕的性别文化肯定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潮汕妇女享誉海内外的温婉贤惠、勤劳顾家的美好品质,在对抗性的女权视角下,统统都是要被解放的内容。哪怕像贤妹的母亲这样生活得很稳定甚至很有幸福感的女性,她也没有人生选择权,只能说她把人生的规范动作都做到位了,且运气很不错。女性在婚恋、生育、工作、家庭等等问题上,需要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是个权利问题,而不是个利弊选择问题。潮汕的“男主外,女主内”,其实中国传统社会都是如此,这种模式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内和外,各占一半,女性本来就是“半边天”,有什么可解放的呢?今天潮汕地区,尤其是潮汕农商家庭,他们依然坚持的家庭、家族观念,从生存的角度看,不仅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且具有非常蓬勃的生命力。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生活不安稳,则自由毫无意义,用自由交换生活的确定性的故事比比皆是。
那么,在文学中我们能不能允许这样不“进步”的表达?能不能允许主人公选择用部分自由交换人生的确定性、交换一个更稳定的生活?我非常推崇“贴地而行”的写作方式,我的小说也都是“贴地而行”的。所谓“贴地而行”,就是生活是什么样子,作者就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记录生活。只有贴着生活的地面来行走,才会行走得踏实,从而不会走偏向“形而上”。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人不能按照概念去生活,文学不能把主人公当作某种社会理想的大喇叭。说到底,文学无法也无意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文学是用来触动情感,直击现实生命的痛点,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必须是具体而真实的人。
《新妇》的主人公惠玲是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媳。在传统潮汕家庭中,女儿依然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但长孙享有和儿子相同的继承权。也就是说,长房能够得到两份遗产。继承更多的家产,当然也要承担更多责任。惠玲嫁进门后,精心持家,又很快生育了两儿一女,并且还想继续生育,是一个标准儿媳。如果不是丈夫在抗洪时牺牲,她会有一个安稳且确定的人生。丈夫突然去世后,卢灶顺招了个外省打工人小张作为长子,也就是惠玲的丈夫。这种选择是完全符合传统规则的,是为了家族的完整和延续。惠玲当然不愿意。要注意的是,她恨这种安排并不是觉得自己有婚姻自由权,而是因为小张的外省打工人的身份让她感觉受辱。她想要一走了之,甚至已经悄悄出走。但半天后她就回来了,甚至没有耽误大家准时吃饭。这个细节证明,惠玲非常清楚,她没有经济能力,不接受公公的安排,就只能带着孩子改嫁,或者抛下孩子进入工厂,过一种无论如何也难以圆满的生活。在认清处境后,惠玲毅然将自己的全部情感杀死,投入新家庭。作为个体生命而言,这种选择是应该被理解,也应该被尊重的。
与惠玲相比,《浮景》的主人公贤妹是个现代知识女性。但这个形象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首先表现在她不是所谓“大女主”,始终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甚至在结婚后很快放弃了工作,回到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轨道上。这是父权对她的压制。说到底,贤妹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是因为父亲允许她出去读书,当父亲要求她回家时,她即便不情愿,已经刻入骨子的顺从也促使她没有激烈抗议。也因为这样的心理惯性,当她婚后面对种种压抑,不仅行动上不坚决,内心也十分摇摆。在面对丈夫、公婆甚至父母种种不合理的要求时,她最大的态度只是冷漠,然后便是逆来顺受。
这让我们哀其不幸的时候,一定会怒其不争。为什么不争呢?我们能不能要求每一个平凡人都为理想的社会奋斗?贤妹是一个并不具备超凡能力的女性,且传统文化在她的潜意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这两个因素让她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坚决。比如父亲让她大学毕业后回来当小学数学老师,她是个医学生,这个职业选择很不理想。但从现实的层面讲,贤妹自己并无能力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且独立在大城市生活下去,这让她没有办法坚定反抗父亲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有很多比她条件更差的人都在大城市里生活,她有什么不可以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且是个非常个人的问题,月收入多少钱才能在大都市生活,这有什么标准答案呢。贤妹不情不愿地顺从了父亲的安排,就像作者所说的,重新回到了古老命运的河流。
前些年潮汕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一个外地媳妇在电视台上哭诉嫁进门后婆婆天天要求她拖地,总共七八层楼,一千多平方。把家庭矛盾放到电视上说,让那个婆婆非常生气,但也非常困惑,她自己从七八岁开始帮母亲拖地,也当了几十年新妇,天天如此,从白灰地到红砖到水磨石再到瓷砖,房子越来越大,地面越铺越好,有那么大的地可拖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事吗?据统计,潮汕地区的离婚率只有万分之五,居全国最低。大家熟悉的潮汕故事里有潮商、宗族、祭祀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元素,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元素其实无不指向压抑。在巨大的生存、发展、文化压力面前,每个人都得交出自我。
比如,造成贤妹痛苦的“罪魁祸首”杰涛,他作为一个男性,并没有获得更大的自由。杰涛是家中的小儿子,在族权、父权逻辑下,长子要负担起全部家族兴衰责任,小儿子则不会被重点培养。杰涛被父母溺爱,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不被寄予希望。结婚以前,杰涛在哥哥厂里帮忙,结婚后,他想自立门户,但屡屡失败。杰涛遇到生意上的挫折,大哥、父亲都没有想指导他,而只是让他安分在家呆着,继续给哥哥帮忙。生活在父亲、兄长的羽翼下,是小儿子的福分,也是作为小儿子的本分。而杰涛和贤妹的关系恶化,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杰涛始终没有在贤妹这里得到作为丈夫的心理满足。实在过不下去了,杰涛可以离婚吗?他搬出家里,耍赖,惹祸,甚至有了外遇以后,杰涛也没有争取离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品格卑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深知背叛文化规则的代价。
在传统社会中,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名声比能力更重要,成也名声,败也名声。《新妇》里的外省人小张想要突破这个规律,以为自己生意做起来了就可以背叛文化规则,结果整个卢厝的人都不跟他生意来往了,当然也就可以想到,这一家人一定已经被排除在当地的生活圈之外。卢厝的文化规则一方面对人有强烈的约束和压迫,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强大的保护。越过了这个规则,就不再受规则保护。从这个角度看,《新妇》和《浮景》就不仅是女性题材的小说,而是关于潮汕生存文化的小说。在这两个小说里,作者没有让我们看到女性运动、女性解放,而是看到生存规则、文化规则对人的强大的改造能力。而客观来说,古老的潮汕文化规则在当代依然有效,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其复杂的价值状态,在这两篇小说中得到了真实的呈现。
同时,我也很高兴地看到,袁甲平已经具有了理解并描述生活复杂性的力量。在她的笔下,生活是一种客观状态,而不是一种主观意愿。这是一个青年作家获得写作成长空间的必要潜能。
【作者简介】阎真,著名作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曾在天涯》《因为女人》《活着之上》《如何是好》,理论著作《小说艺术讲稿》等多部;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