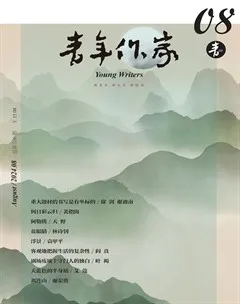新妇
卢灶顺的大新妇惠玲守寡时还不到三十岁,有两儿一女。她的丈夫是台风天为卢厝镇守江堤时,被大水冲走的。丈夫的坟墓因此立在江堤上,除了名号,还刻上了“为百姓安危牺牲,贡献彪炳千古”。坟堆和碑石都是单个一体完整的,没有为妻留下位置。一年后,卢灶顺决定招个人进来补长子的缺。虽然长房香火没断,但大新妇这么年轻,守寡到老是不可能的,要再嫁就得抓紧时间了。卢灶顺看得定,也紧锣密鼓地安排着。大新妇要是嫁出去,这两儿一女跟着会凄凉,不跟也凄凉。所以,不如就招进个儿子,新妇还是新妇。他不容拒绝地把想法告知惠玲。
顾不上礼节,惠玲对卢灶顺说:“那你得找个能当你儿子的。”
不多久,卢灶顺带回一个四川人小张,才二十五岁,没结过婚。媒姨跟着来的,对惠玲说尽好话。惠玲抱着小儿子一声不吭。
“你自己偷偷走吧。”灶顺的细新妇贤妹抓住午饭后收拾碗筷的机会,忍不住悄悄给惠玲出了个主意,还往惠玲手心里塞了一卷钱。贤妹用力地捏了捏惠玲的手心,说:“孩子给我。”
一整个下午,贤妹都没看到惠玲。但晚饭时候惠玲又回来了,带回来一只炸得金黄酥脆的童子鸡。贤妹接过餐盒,叹了口气,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招呼道:“大姆,可以吃饭了。”
灶顺大新妇没有反对,好事便着手开办了。所谓办事,只是让四川人小张拜了卢氏祖宗,并改姓卢。仪式结束,小张就是卢灶顺的长子了。他搬进了灶顺家。新婚之夜,灶顺大新妇极自然地把小女儿抱到床中央,自己爬进里面,兜着女儿的屁股,闭上眼睛。在新丈夫的脚悄悄伸过来时,惠玲猛地睁大了眼睛,瞪了他一眼,把那只脚“瞪”了回去。那是个随时准备同归于尽的眼神,吓得小张整夜都不敢关掉头上的灯泡。
半年后,惠玲怀孕了。她命令小张去跟卢灶顺说,必须分家了。卢灶顺招小张作儿子,家里却像多了个长工。卢灶顺喊他小张,灶顺嫂喊他小张,灶顺细儿子喊他小张,惠玲自己也喊他小张,甚至连灶顺的孙子们都喊他小张。小张已经不像刚进门时一样憨憨应着,惠玲难堪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掩藏不住。贤妹悄声对惠玲说:“不能让孩子们叫他小张,你这样叫也不合适。”惠玲吭了一声,尖利地反问道:“还得叫爸爸?”贤妹沉默了下,说:“叫叔也可以。”惠玲哼了一声,说:“娶我这寡妇倒是真划算,一下子房子、儿子全有了。”见贤妹还不走开,她冷笑道:“现在我还得给他生儿子,要不你来试试?”
贤妹一走开,惠玲的眼泪便掉下来了。她生卢灶顺的气,生小张的气,更生死鬼丈夫的气。她一秒钟的好脸色都不想给那个四川仔,但卢灶顺一家子对小张的看轻又让她压抑得简直要发疯。这家人既然看不起四川仔,为什么要招这么个人来?这个外省仔那么年轻,他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她看见小张不自在,心里畅快得想大笑。但事实上,惠玲几乎每天都在流眼泪,气得捶肚子,卢灶顺一家人凭什么这样做?凭什么呢?
卢灶顺拒绝分家,对小张说:“现在分家,你出门就得被人吐唾沫。别人当几十年新妇的,无论被公婆怎么刁难,都不敢说分家一个字,你这上门给人做儿子的,说这话不怕街市人骂?”
小张说:“老人、孩子该我养的,我肯定还是会养。”
灶顺反问道:“你拿什么养老婆孩子?我们两个老的要你养也是你的本分,但我自己还有儿子,不用你养。问题是,你拿什么养老婆孩子?”
小张干笑了两声,勉强保住了已经很难看的笑脸,回道:“穷就穷养,富就富养,不都这样吗?”
“你打算像你父母养你一样养我的孙子?”卢灶顺毫不客气地反问,“十二三岁赶出门去打工,娶不起老婆再像你一样被人招?”小张其实是十五岁出来打工的。
小张反驳道:“我十五岁才出来的。”
那天的晚饭,惠玲没煮。贤妹刚把碗筷摆齐,惠玲就坐下,端碗吃了起来。惠玲嫁进卢灶顺家快十年了,除年节外,她很少上桌和老人、男人一起吃饭,基本都是家人在吃的时候她喂孩子,等人家吃完了她才吃。现在,她不仅上了桌,还丝毫没有等其他人的意思。
贤妹在惠玲旁边站了好一会儿,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地偷声说:“别这样……”但惠玲只白了贤妹一眼。贤妹只好叫公婆吃饭。
卢灶顺进饭厅一看,气得直接回了房间,换灶顺嫂进来骂。惠玲当作什么都没听见,吃完了就回房间。贤妹在饭厅站着,大家都吃不下饭。接下来几天,惠玲都是这个样子,小张和两个儿子也被她赶出房间,小张睡到客房,两孩子被贤妹带到自己房间。
一个多月后的半夜,卢灶顺突然吼道:“分!分!留这些催命鬼在这收我的老狗命!”
贤妹再见到惠玲,是两年后了。惠玲一家分得了一座下山虎厝和一百七十万现金,楼房和生意存货都给了二房,也就是贤妹一家。这让贤妹即便是惠玲生孩子的时候,也不敢去看她。自古以来,分家产都是要长子长孙优先的,长孙当细子。说到底,还是认骨肉,还是有私心。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小张一家和卢灶顺一家的关系仅存于祠堂之中及族谱之上了。时年八节,也只有小张过来祭拜,连孩子都不来,何况是惠玲。
这天,贤妹去妇幼保健院上节育环,她连着生了两个儿子后,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任灶顺嫂怎么不高兴,也不愿意再生了。碰巧,惠玲刚在医院生了孩子。贤妹说:“呀,大姆!”惠玲也还挺高兴。惠玲和贤妹关系一直不错,她只比贤妹大四岁,因为贤妹上过大学,结婚晚,所以显得两妯娌年纪差很多。贤妹有文化,但一直很尊重大姆,把大姆当长辈一样敬重。
贤妹问:“大伯呢?”
惠玲说:“老五没人带,他在家带呗。”
贤妹吓一跳,这回出生的是惠玲和小张的第三个孩子。惠玲看出了贤妹的吃惊,问:“怎么?笑我没用?要不是老天爷积恶,我又不是没有儿子,又不是生不出儿子?”几月前,惠玲做B超的时候,知道肚子里还是个女孩,她和小张都很丧气。惠玲就像一个装满了番薯的鸟屎袋,从中一个接着一个地往外掏,圆滚滚的身体其实只是个空袋子,灌满空气,虚张声势。但小张还没有自己的儿子,惠玲还得再接再厉。
贤妹只好问:“还顺利吧?”
惠玲哼了一句,怒气冲冲地说:“哪有你顺利!”
“女孩也好。”贤妹没在意惠玲的态度,轻声安慰道。
“好的话你抱走,给你了!”惠玲心情似乎更坏了,安慰话换不来儿子,她也懒得跟贤妹客气应付。
贤妹叹了口气,说:“等阿妹大点了再生吧,你也调理下身体。”
“加紧点,早点生够,以后早点轻松。”惠玲突然变得垂头丧气,见贤妹为难着不知如何接话,就说:“带一个是带,带七个八个也是带,眼一闭牙一咬,就都一起长大了。我任务完成了,才不会一端起碗就觉得欠了谁的。”她又说,“你命好,两个儿子了,现在生男女都好,你才有底气说女孩也好。”
贤妹没有反驳,只劝道:“那也不能挨得太紧。”
“你不生,难道要留给别人生?”惠玲忍不住挖苦道。
“我也是学医的,你这样不顾自己身体,过些年有你受的。”贤妹还是不死心地劝道,虽然她很清楚说什么都是白说。
果然,惠玲一脸平静地回道:“人总是要往前看的。”也没明说往前看到底是什么意思,自己的身体就不是前面该看的事?
但卢灶顺家和惠玲的不幸还没有完。厄运进了命,就像蟑螂进屋,成群结队、生生不息,是除不尽的。
惠玲生到第七个孩子,终于是个男孩,大儿子卢木豪已经上初中了,一切好像都安稳下来了。谁知,刚上初中短短的一个学期,不知为何,原本懂事听话的儿子几乎成了个小流氓,逃课、飚摩托、拿铁水管跟人打群架、早恋……卢木豪迅速成了卢厝中学里一群野孩子们的头头。老师隔三岔五投诉,别的家长反反复复上门理论。卢木豪的继父小张不管,母亲惠玲道歉了又道歉,把儿子骂了又骂,并没有好转。有次吃饭的时候,惠玲气得拿筷子敲了下大儿子的手背,结果小伙子抓起高压锅盖就甩到母亲胳膊上。惠玲揉着瞬间红肿的手臂崩溃痛哭,卢木豪却头也不回地摔门出去了。惠玲下决心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去,再放他这样晃荡,要么会走上邪路,要么迟早得被人打残甚至打死。
到学校报名,学校要求惠玲交孩子的户口本复印件。惠玲的七个孩子都还没上户口,她和前面的老公没领过结婚证,和小张到现在也没有办结婚证。卢厝镇认的是礼俗,不到用时,证件都是多余的。小张的户口倒是已经迁过来了。卢灶顺凭借自己的人脉,又花了点钱,把小张改了卢姓,名正言顺地成了父子关系。
惠玲只好先回去,要小张去打结婚证。小张说:“可以,但我要改回姓张,你儿子姓什么随你,但我儿子肯定得姓张。”
这样要求,小张是有底气的。这几年,他跟着原来的老板学做生意,开了一家小小的丝花厂。他们一家早就搬出了卢灶顺分的下山虎老厝,在卢厝镇起了四间楼房,比杰涛分得的那四间还宽敞,地段也更好些。早在买下地的时候,他就想把姓氏还给卢灶顺了。
惠玲把小张的要求告诉卢灶顺。卢灶顺气得再次请来了族中的全部耆老,准备教训这个没长良心的外省仔。虽然小张松口允诺将来两边的祖宗都要拜,卢灶顺仍被屈辱激得怒不可遏。自己儿子生意越做越小,原本给人做工的外省继子却发了财,卢灶顺心里本来就很难消纳。有次他路过小张的丝花厂,进去看了看,随口提起说:“你们现在过得好了,要是可以,多少帮杰涛一点。”没想到,小张却认真地说:“要不把破房子还给你们?”卢灶顺听出了其中的威胁,却还强撑着笑容,说:“家都是你们年轻人打理了,做事凭本心,我们老人也就随便说说。”小张却再次认真地回答道:“那就本分点做个老人,多吃几年饭,别管那么多事。”卢灶顺气得差点甩出去巴掌,但还是攥紧了拳头,走了。最近一年,小张命令惠玲停止拜神,把守护卢厝镇风调雨顺的神圣事业说成“为了死鬼要熏死活人”,甚至连拜祖也时常不来上香了。卢灶顺正积压着气,准备找个机会去教训下这个外省仔,没想到他不仅不知收敛,还提出这样背天地良心的要求。
二楼,耆老们挤满了客厅,每张老得耷拉了的脸上都布满了替天行道的正义感。但事实上,耆老摆开阵势也只是劝、骂,讲诚信、讲仁义,再没有更多办法。卢灶顺气急败坏地质问:“这么多年,你都没回去过你外省老家,你现在究竟是想干什么?”
“这么多年,你们这本地话我再学也不像,挂着你们的姓总是心里不舒服。你们要是觉得亏了,我可以把以前你们的那座下山虎厝还你们,六年需要多少租金你们可以说说看,合情合理的,我一次性补清给你们。”小张点了根烟,跷起腿,神色一派悠闲地靠在椅背上,不紧不慢地回道。
“在我们卢厝,就得遵守卢厝人的规矩。做人不是拿市价就能换算清的,要有情有义。你娶了人家女人,让你从空脚白手的打工仔到今天有楼有厝,有妻有儿有女,你说租金脸不红吗?”年纪最大的耆老顿了顿脚,又顿了顿拐杖,手颤颤抖抖地,像随时要把拐杖挥过去。
“我不是卢厝人。你们还不让我活了?我做生意少过你们卢厝哪个人的钱?”小张却并不激动,也不理会对面那些老头子的愤怒。他经常说卢厝镇人有点事就叫出这帮连路都走不稳的老头是愚蠢的,而且没一点用。耆老讲起了从前的谁和谁如何如何,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小张歪在交椅上,换一条腿盘起,不着急搭话,半眯着眼睛,像快睡过去了,这让老人们很不自在,并且越说越气,有些不耐烦了。但以理动不了,以情也动不了的人,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耆老的权威是祖上开始就约定好的,显然小张并不在约定之内。
正当他们无可奈何,准备起身走人的时候,惠玲上楼来了。没有人叫她,她也不应该来的,但这会儿她就是出现在了客厅里。小张背对着楼梯口,听见惠玲的声音也没有回头。他摸出了烟盒,自己咬了一根,又把手伸向最近的老人,说:“抽根烟,歇会再说。”分了一圈烟后,他又递了一圈火,最后自己点上了,倒回椅背。惠玲站在他背后,没说话也没找地方坐下。
挨着小张的老人就说:“后生仔,娶得到这么好的女人,你得知道感恩。姓什么你们外省人对这个也不是那么看重,既然到我们卢厝镇做儿子了,老话说一诺千金,你也是生意人,应该懂才对啊。”
“一间破厝筒子就要千金?”小张斜乜了老头一眼,毫不掩饰地讽刺道。
“人家小嫂子给你生儿育女,家内上下打点得流流利利,这些是多少厝可以换来的?做人不能没良心,想想你们大山角里,有多少年纪比你大得多的还没有老婆,更别说儿女双全。你能做起生意,也是卢厝人牵你起来的。你今天所作,别说对不对得起灶顺一家,你对得起妻儿吗?”耆老们一直在强调良心。
可惜,小张显然是个没良心的人。他深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把烟缓缓地从鼻腔里吐出来,才睁开眼轻轻地问:“一个老寡妇?”
惠玲在小张背后,听到这话像吓了一跳,脸一下子又青又红,一会儿就全青了。她一脸不敢置信地瞪着丈夫的后脑勺,前面的人却是轻松得完全不为所动。惠玲又看了眼气急败坏的卢灶顺,像来时无声无息一样,又静静地晃悠悠飘下楼。已经管不得是否失礼了,身后乱得难以辨认词句的责骂让她几乎晕过去。惠玲紧紧抠着扶手,到了最后一级,瘫坐在楼梯上。
门一关,惠玲死死抱住贤妹,抑制不住哭腔、浑身颤抖地呜咽着:“他说我是老寡妇,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是老寡妇……”
贤妹也被这话吓了一跳,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只好挨着惠玲坐下来。惠玲扑到她身上,毫无顾忌地哭到破声。再也不顾及门外的人和耳朵,他们一定听得到的,但还能比被丈夫说成那样更丢人吗?惠玲胡乱地骂着那个已经死去多年的人,骂给她招来这个没良心砍头外省仔的老家伙,骂儿子,骂贤妹……贤妹静静听着,拍着她的背,也掉下了眼泪。
惠玲真的老了,和小张站一起简直像两代人。孩子一个接着一个从身体里掏出去,这会儿她趴着痛哭,就像个装满了空气的麻袋一样晃晃荡荡。眼前的人跟贤妹刚过门时记得的那个完全已经判若两人,靠近了甚至可以看见她耳垂下方的肉已经开始有些松弛,挂出几条浅浅的褶子来。而小张与当年瘦瘦小小的打工仔也已经判若两人,如今他膀阔腰圆,每天用发胶把头发梳得油亮。贤妹哀哀地叹了两口气,就不知道再说什么了。
“我也没做坏事啊!”惠玲哭了一会儿,抬起头,定定地看着贤妹说,“儿子不比人少,我也不败家,勤勤快快的,做祭拜神按时按日,比谁都诚心……”说着她又呜咽起来,问贤妹:“怎么命就是这么不好呢?
“唉……”贤妹又叹了口气,握着惠玲的手更捏紧了些,实在不知道怎么安慰。安慰得了运,还安慰得了命吗?既是命的事,就只能受着。惠玲不是能对抗命运的人,也不是敢跟命运鱼死网破的人。贤妹看得明白,所以没什么说的。她知道惠玲哭完了、冷静了就会回家,没有不回去的理由,也没有不回去的能耐。
抽抽搭搭的声音渐渐平息,惠玲从贤妹身上爬起来靠在墙上,刚才哭得太用力,出了一身汗。
贤妹见惠玲冷静了,就说:“你在这睡会儿吧,中午在这吃。”
近中午的时候耆老们颤颤巍巍地下来,走了。小张没有下来,卢灶顺也没有下来。灶顺嫂照例出去给两个孙子送午饭,肿着眼睛,匆匆忙忙地出门,匆匆忙忙地回来。贤妹的丈夫杰涛回来了。他已经听说,全卢厝镇的耆老都被父亲请过来了。
杰涛刚上楼,就看见父亲像垂死的人一样瘫在沙发上,小张也没好脸色,地上已经堆了一层烟头和烟灰。杰涛拧紧了眉,向灶顺嫂三两句问清了早上的事。他气得直接把小张踹倒在地,一脚踩在他胸口上。小张还没回过神,杰涛又咬着牙紧跟着踢了几脚。卢灶顺不得不起身喝住儿子,他一早上已经吼得喉咙都哑了。杰涛没有再动手,骂道:“破落外省仔也不抬眼照照自己,赚了几分钱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
“不改姓我不会去打结婚证,你们可以把那几个死父仔的户口入到自己户口本上,我的孩子要不跟我姓张,要不让你大儿媳妇来求你。”小张坐在地上,一脸讥笑地看着卢灶顺父子,故意用潮汕话字正腔圆地说了“死父仔”。
杰涛被激得捏紧了拳头上前要拎人,这回被小张躲开了。
整个早上没说一句话的灶顺嫂,眼泪已经不知道抹掉几回了,这会儿又止不住地往下流,“求你们了,积恶啊……丢掉祖宗脸啊,积恶……”她像哭丧一样拉长声喉哭道。
贤妹也上楼来了。换做往日,家里大人、丈夫都在场,她是不会开口说什么的。但现在惠玲还在楼下,贤妹觉得该说点什么。想了一会儿,说:“至少你不应该这样说大姆。”她突然不知道怎么称呼小张更合适。如果小张还是补灶顺长子位置的,那她该随孩子叫他大伯。但小张此时正在拒绝这个位置。贤妹只好不加称呼地说了这句话。
“她要是这么一句话就受不了,单这卢厝镇一天得死多少女人?你爸有钱有势,你才能天天那么多不情愿。”小张讽刺贤妹道。
贤妹正想说他伤了惠玲的心,杰涛却抢过话说:“你要不是卢厝人帮你,你现在连一口屎都扒不到嘴里!你还以为真是凭你的能力,你能塞满肠肚,坐在这里吐屎?”
“那卢厝人怎么不帮你?卢杰涛?”小张猛地站起来,尖利地说,“因为烂泥扶不上壁。”他似乎下定决心再不用客气了,把客厅的人都扫一遍,最后定在杰涛脸上,坚决却一点都不激动地说:“你要是心里不舒服,你们父子俩现在就可以去把人领回来。你们卢厝人能耐大,扶得起一个我四川仔,就扶得起两个三个,你卢灶顺的大新妇能嫁第二次,再嫁三、四、五、六个也没相干了,你们慢慢挑啊,挑到合心意的为止啊!”
“你这外省仔有没有点良心?”卢灶顺从沙发上跳起来,膝盖哐地一声撞翻了面前的小板凳。一丝灰白的头发掉到他眼睛前,但丝毫挡不住凶恶的眼神。
“跟你们用得着说人话吗?”小张迎上卢灶顺的眼光说道,他彻底失去了耐性。
卢灶顺抓起茶盅往小张脸上摔去,却被他轻易躲开了,茶盅砸在地上,茶叶和碎瓷片四散。小张捏紧了拳头,死死地贴着裤缝。卢灶顺在瓷茶盅的破碎声后,倒向沙发,垂着头,紧紧抿着嘴唇。灶顺嫂一下紧接一下地抹着眼泪,脸色比灯光还更白些,风湿发作似地瘫软着。
谁都没有心情再吃午饭。贤妹悄悄下楼,惠玲却已经走了。贤妹又叹口气,想着惠玲该是回家做饭了,家里还有七个孩子。
贤妹猜对了。下午,惠玲把孩子送进学校后,坐在幼儿园门口的花坛上,坐了整整三节课,她不想回去看到小张。孩子放学出来,她该带孩子回家了,却又走到卢灶顺家里。灶顺嫂也刚接回孙子,看了惠玲一眼,叹了口气,说:“你该回去买菜煮饭了。”“我回去会死的,”惠玲叫道,“要我就这样回去?他那么骂我!让我回去给他骂?”她直直地盯着灶顺嫂,眼神里满是恨和愤怒,但很快就又流下眼泪,呜咽着问:“你们让我跟他,现在却拿他一点办法没有?你们做大人的不用给我个说法?就拿他没一点办法吗?”
“那你打电话给他,就说阿弟们今天想住爷爷家,让他明天下午来接你。灵精点,谁都不信的话,你也得这么说。”灶顺嫂说完又叹了口气,现在她除了自己的叹息,什么都做不了主了。
她见惠玲没动作,又劝道:“身长棺材短,屈死也得刻苦领受。”隔了一会儿,灶顺嫂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完全不计前嫌地劝惠玲:“你自己命理不好,父母给你十足,你过得只剩三成,再怨天怨地也没有用。嫁人就跟去市场买猪肚一样,外面洗得清白,里面有屎没屎,得下手翻过来才知道。要吃就别怕臭!哪个夫妻年轻的时候不是捶破头壳的?难不成会比离了自己过更差吗?你真要离婚,还是想不开去找死路,他保管连眼皮都懒得跳一下。这四川仔前几年是赚不到钱才抬不起头,你以为他还真能随便给你揉捏?还是你想他一辈子缩头缩尾地给人打工?你十七八岁的时候赌气出走,人家得慌慌张张四处去找,现在你再这样试试,你前脚敢出去,他马上就敢找个补进去。你作娇,自己的男人不看,就给满街市人看了笑话。好过就睁着眼过,不好过就把眼睛闭着过,人又不是纸糊的,哪有人是骂不得的呢?”她见惠玲眼泪停住了,脸色却更死白,不忍心安慰道:“幸好还是在我们这,不是跟他去外省。骂你一句不会破皮流血,他也不敢真赶你走,那么多眼睛看着,他要在这赚钱,再坏也是要脸面的人……”
灶顺嫂絮叨完了,又把电话塞惠玲手里,要她打电话回去。惠玲捏紧了手心,深吸了好几口气,才拨了号码,语气平静地说:“阿弟要跟贤妹的儿子玩,今晚不回去了。”话还没说完,她听见了电话那端清晰的嗤笑,刚想开口,没拿电话的另一只手被灶顺嫂使劲地捏了一下。她挣开了灶顺嫂的手,用力地捏紧桌沿,指甲生生压裂了,几乎把自己的手指折断,才继续若无其事地说:“你去买点青菜,冰箱里还有排骨,用清补凉熬点汤。晚上让他们准时睡。”就像平常夫妻一样交代着,但惠玲说完赶紧挂掉电话。
晚饭之后,大人们没一个有好脸色,沉默地围坐着,连小孩子都不敢调皮了,安静地写作业。贤妹叫惠玲一起散步,透口气。但贤妹实在也想不出要讲点什么。她觉得即使已经吵开了,这些也还是惠玲的隐私,自己不该去安慰。
“大伯……”贤妹沉默了一会儿,犹豫着安慰道:“他可能也是生气乱说话,也不是故意这么说的。”
“不是故意?”惠玲回头看了贤妹一眼,嗤了一声,质问道:“随口说出的才更是心里想的。你以为他是个老实人?杰涛也不是个好货色,前几天半夜十二点多还载妹子从我家门前过。你说他们去做什么?我能听到的事,你还会听不到?你还不是得随他去浪荡?”
贤妹变了脸色,杰涛的事情她当然清楚,但被当面挑开还是第一次。
“只要没闹到实在过不下去,就都闭着眼睛过。要是都睁开眼过日子,有几人还过得下去?”惠玲反倒开始劝起了贤妹,“有了几个钱,外省仔也不会老实的。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想不破放不开,放得开的也没几个好过的。能跑能跳的时候,谁都要潇洒。等饭碗都端不到嘴边了,看还有没有那么潇洒,谁会给你端这碗饭去?”
惠玲看贤妹一脸不自在,一下子倒笑了起来——不是开心笑,而只是抽动喉咙像用力地吐气,常年骂孩子已经变得沙哑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就像刮铁片一样,冰凉刺耳。好像真有什么好笑的,她笑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又板起脸来,用教训的语气道:“饱鬼别不知道世上还有饿鬼。你指望一个连亲生父母都可以不要的人有良心?杰涛再怎么臭,还有爸管,还得在卢厝镇行踏,多少得要点脸面。妹子载来载去,你看得开,他不敢赶你走。这四川仔连父母都不要了,你以为他会听这个半路认来的老头的话?”
“你也别老是叫他四川仔,这太难听了。”贤妹劝道。
“难听?是叫错了?他还不欢喜做个本地人,要把姓还给人家呢,嫌我叫得难听,他怎么不嫌做的事难看?”惠玲站定,转身叫了起来,情绪又激动了。
贤妹不再接话,只听着惠玲接下去又说:“但老实跟你说,四川仔和卢灶顺的事我无所谓,姓张还是姓卢,我都无所谓,只要让孩子上户口出去读书。孩子去私立学校,那么多钱还要四川仔来给。他说的那话,怎么我也得让它过去。我得劝自己一点,老公敢发性说明也是有点本事了,总比一辈子给别人当狗,温驯得没出头之日强些。男人二三十,三四十的时候不安分,到了六七十还花得起来?坚持就是胜利!你说是不是?坚持就是胜利,我真的太大惊小怪了是不是?”
公园还没走到头,惠玲的态度已经转了几次,贤妹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像梦游一样地应道:“嗯,没经济独立不能轻易离婚。”
惠玲的脸色马上变得异常严厉,毫不客气地训斥道:“离婚?别读书读傻了!自由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连个气死你的人都没有!将来死了连个埋的地方都没有!我告诉你,脑子里千万不要留这种心思,死路一条。死了老公再嫁都没好下场,离婚的就更没好下场!你以为你离婚了,还会有人娶你吗?”她像听到了多么恐怖的东西,完全不顾及贤妹的面子,越说越急,越觉得自己义不容辞,掷地有声,完全失去了贤妹刚认识她时那温温柔柔的样子。
贤妹忍不住起了鸡皮疙瘩,搓了搓手,说:“有蚊子。我们回去吧。”
惠玲也没反对,一路上又嘟嘟囔囔说自己太大惊小怪了。
那一整夜,贤妹心里沉重得睡不着。惠玲随便收拾了个房间和儿子住下,不一会儿就均匀地打起了鼾。天刚亮,贤妹听见惠玲起床洗脸。等贤妹起来,母子三个已经回家去了。
但矛盾的起点本来就不是那句“老寡妇”,所以也不会因为惠玲回去而告终。小张是决心跟卢灶顺一家对峙到底了,他没有和惠玲去补结婚证,卢灶顺的孙子也迟迟上不了户口,自然也就不能送出去上学。惠玲求不了丈夫,正在学坏的也不是他的儿子,只好每天去求卢灶顺。也不知道是挨不过惠玲的哀求,还是怕长孙变成混混,卢灶顺最终还是抗不过小张。
小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张,再也不必为自己戴着卢姓却讲着一口水土不服的方言而感到羞耻。由于卢灶顺对他的要求没有一开始就表示配合,他也就不再遵守拜两边祖宗的约定,只答应让卢灶顺的孙子可以去拜祖。依然请耆老来作证人,他把下山虎老厝交还给卢灶顺,一并付清几年房租,按照市场价,一共八万九千八百元,连凑个圆数的情面都不留。杰涛气得当场一拳头打碎了小张的半颗门牙。
小张从地上爬起来,吐掉了血水,瞪大眼睛说:“补一颗牙四百。”说着从桌上的钱里抽了四百,放进裤兜。
杰涛捏紧拳头,扬手把桌上的钱全摔在小张胸口,叫道:“拿着,我把剩下的房钱全打掉!”
“打了手疼。”卢灶顺拉住儿子,心灰意冷地说。
小张扯回衣角,不紧不慢地抚平了,才说:“那我就只拿四百,走了。”他故意往前走了两步,把地上的钱踏了个遍才出去。
“自己捡走。”杰涛红着眼睛吼道。小张却已经下楼了。
“天上要滴下鸟屎,还有处说理啊?”卢灶顺低低地说,“明天我去找惠玲,他要是不肯养,我们就把阿大的孩子要回来自己养。”
杰涛没有听清父亲的话,依然愤愤不平,喘着粗气,骂道:“这外省仔过来的时候,连条破棉被都没有。现在就敢这样?”
“老话说知面知庞,不知肚腹。他刚才没还手,已经算客气的了。”卢灶顺叹着气,又说:“要是惠玲肯把阿弟送过来,你要是不肯养,我和你妈自己养。那间厝还得给他们,我和你妈死前,怎么也还能把孩子带成人……”
“要不再找找,看有没有整家人肯过继给我们的?”杰涛打断父亲看破世事的感叹,问道。
卢灶顺摇了摇头,说:“算了,把阿弟带大好了。家奴无定主。雇来拜祖的,你能世代雇下去?大弟十六了,我们也别求十足了。”
把孩子领回来的想法一提出,很快卢灶顺把大儿子的三个孩子都带了回来。他们的户口也不入小张那边,暂时挂在杰涛户下。灶顺长孙的名字是费了功夫起的:五行缺木,豪字辈,取名卢木豪。后面的孩子没有再看八字,木iAi1YU9iHQwVMozP7X2JNw==豪的弟弟就叫林豪,妹妹叫楚贤。录入户口的人却偏偏把木豪的“木”字打错了,成了“沐豪”。为此,卢灶顺气得差点砸了卢厝镇派出所。
其实,要是换个人或者换个时间,“沐豪”也就“沐豪”了。卢厝镇派出所经常出错,卢厝镇人并不在乎安名。比如,卢木豪的父辈,几乎大半人的名字都带着晓字,查了族谱却并不是晓字辈,这只是当年的一种潮流。但究竟是从何兴起这潮流,起名字的人都记不得了,也没人去细问。卢厝镇的每一个人到死后,都会按照辈序和生前品性重命名,把规范的名字刻入祠堂的神龛。生前的名字和政府登记的名字叫什么都不重要,只要顺口就行。家里人称呼,男孩亲昵点的叫法是狗仔或者猪仔,更多的就叫大弟、二弟,按年纪编号;大女儿都叫大妹,二女儿都叫细妹,万一还生了三女儿,要么就抢过二女儿的名字叫细妹,要么二女儿还叫细妹,三女儿叫尾妹,四姐妹以上的基本得叫招弟、来弟之类的了。家外的叫法也简单,俗话说:“大头好安名”,长什么样就叫什么,头大的叫大头,发色浅的叫红毛或者黄毛,皮肤黑的叫乌鬼,不会说话的叫阿哑,眼睛大的叫圆目,眼睛小的叫眯目,胖的叫肥仔,瘦的叫菜脯……即便父母有慎重安名,平日里连自己都会忘记大名的存在。要是父母不讲究,户口本可能就登记成了大头、乌鬼之类的名。在卢厝镇更加普遍的,就是一家之主的名字共享给全家人。谁都没问过灶顺嫂叫什么名字。
但卢灶顺的这个孙子是长孙,还是死了父亲、母亲改嫁了的长孙。卢灶顺接过户口本一看,反手就把本子摔在台上,质问办事员:“你眼睛被什么东西糊了是不是?先生算到我这孙子命中缺木,给起个好名字,你还把木抽走!”
“老伯,是名字打错了吗?”办事员听得有点懵,但见卢灶顺气白了脸,赶紧捡起来,翻开看了看,客气地问。
卢灶顺深吸一口气,抓起桌上的笔,把户口本抢过来,直接在“沐”字上重重地改了一个“木”,他手不停地抖,整个人像随时要倒下去一样,声音却十分洪亮:“要是有根木,他爸就不会淹死,老老小小就不会那么惨!”
办事员忙道歉:“对不起。我们太疏忽,木和沐同音,没检查好。”
“叫所长来!”卢灶顺叫道,“木和沐怎么是同音?没检查就把别人的名字乱写?我这是算好的,五行缺木,救命用的,你一个没检查就给我抽走了?还加了水,你嫌浸死他爸一个还不够是吗?”
办事员已经变了脸色,再次解释道:“这俩字在拼音里是同音字,现在已经录入电脑了,要不我帮你重做一本,这个改成曾用名,你看可以不?”
“谁曾用这名了?”卢灶顺又抢过户口本,这次直接冲大门外甩出去。
在卢灶顺的客厅扬眉吐气的那会儿,小张没有预料到,他在卢厝镇的生意会从那天开始,彻底萎缩下去。抛掉了姓氏,就没有浪子回头的余地。小张对抗卢灶顺的那场斗争,伤的是全卢厝镇人的颜面,再没有回转的可能。卢厝的耆老们在小张不承认他们的权威时,只能任着他奚落。但小张的言行,很快穿过卢灶顺家像纱布一样透明的客厅。
小张的生意大半是承包大厂里的半成品枝头,雇工人插上花朵,把成品丝花卖出去,从中获利。他还没从击败卢灶顺的得意中平静下心情,就一个枝头都拿不到了。按照往常,每月逢十,不出中午,合作的大厂就会安排三轮车把花枝送到小张厂里。到了送货的那天,小张等到晚上工人下夜班,还是没有等到货。小张已经习惯了卢厝的信用制度,对伙伴的失约有些气愤。谁知,第二天一早,几个老板亲自上了小张家门,但不是来送货,也不是解释为什么没送货,而是来结账。他们说以后都不生意来往了。小张追过去问,他们用潮汕人世世代代总结出来的经商俗谚回答他:“老实终久在,积恶无久耐。”他们还故意用方言说,难得多管闲事一回地帮卢灶顺出了口气。
小张求遍了从前的生意伙伴,但卢厝人早就硬下了心肠。小张对耆老们的轻蔑早传遍了卢厝,伤的是全体卢厝人的脸面,辱了卢厝全族和祖先。小张在本地商人圈里处处碰壁,只能跟外地人来往。可是卢厝已经没有多少外地老板了,再筛到丝花这行,就更少了。几个月后,小张在卢厝赚到的钱再也不会繁殖,所有的经营都奄奄一息。还没成为惠玲名副其实的丈夫时,他曾对卢灶顺说“穷就穷养,富就富养”,为了自己的姓氏,他真得把孩子穷养了。卢厝人要毁掉一个外地人在卢厝的事业是那么容易,这是小张硬气时完全没有设想过的。
被逼无奈,小张只能回头求卢灶顺。他忍下屈辱,挂满假笑,认了错,表达了想要改回卢姓并且再不胡思乱想的决心。但卢灶顺拒绝了他。小张又让惠玲去求贤妹,请贤妹说个情。贤妹看着几乎跟宗和嫂一样苍老的惠玲,答应了。可惜,她求不下这个情。她对公公说:“孩子还要吃穿读书。”卢灶顺大发一顿脾气,骂贤妹昏头,帮外人说话。
贤妹只好向惠玲道歉,偷偷给她点钱,更多的帮助也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