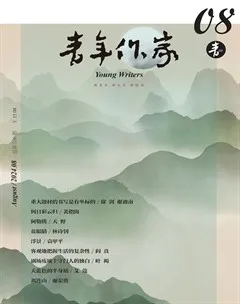记忆的容器
记忆力是古怪的能力。有时我觉得记忆像海,必须一头潜入其中,才能见到岸上所看不到的。有时我又觉得记忆像影子,猛然回首瞥见地上那块被拉长了的黑色,明白它一路跟来,应该是有话要说。
于是必须处理记忆,如同必须处理剩余的食物。放进冷冻柜,不见天日,逐渐被忘记,或是晾起来,看它在风中晃动,在形成固定形状之前,渗散出某种味道——我在不知不觉间做了后面这项工作。
三年前,研究生毕业作品,我需写出一部电影长片的完整剧本。时限紧张,坐在并不舒适的躺椅里苦想,点燃的香烟与鼠尾草,白雾弥漫,时间几乎不存在了。此时我的房门自动打开,遥远的小学同学露出他的半张脸,对我说,不如写一写我吧。
因此有了《蓝眼睛》这个故事。纠缠我许久的零碎记忆,或美丽或残酷,或确凿无疑,或面目模糊,终于有了将它们固定下来的容器。那个电影剧本最终得到蛮高的分数。之后是仓促的毕业手续,接连的忙碌,暂得的喘息。在深远的安静中,我仍听得到这个故事的呼唤。我逐渐领会到它的意思——剧本并非容纳这段记忆的最完美容器,我只有动手为它造一个新的,它才会真正安分下来。
我成长在城乡交界处,目睹了城市化的进程。我明白世界原本不是眼前的这个样子。崭新来自人为,洁净需要维持,土地始终沉默不语并不代表尘埃就永远消失了,因为我清晰记得它们飘舞在空中的模样。并不丑陋,也说不上好看。多年以后,我看见意大利修士安杰利科的画作,竟有一股久违的熟悉感。安杰利科画了一群又一群的天使,使用大片大片的灿烂金色来填充画面的空余。这金色,就是我记忆中故乡的尘埃的颜色。
逆着夕阳,农民工在尘埃中劳动,敲打,呼吸,行走,跳跃。建筑一旦完成,脚手架拆除,他们和尘埃一齐消失不见。我怀念他们的脸庞,某些珍贵而纯粹的东西只可能显现在这样的脸庞上。这篇小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怀念所写。如同扯起一张深海的网,必然会得到礼物一般的海草与贝类,小说在行进时总会遇上种种不请自来的细节。它们到底是真实经历,还是我的幻觉,中国古人说,欲辨已忘言,所以我想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真的曾经亲眼看见过山林间的孔雀。它被关在一栋红砖别墅内。那里没有人居住,地上堆满了落叶。我踮起脚,碰巧看见它。我和孔雀对视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如同落难的人,向我发出求助的目光,见我一筹莫展,它退缩回到了阴影里。我像是知道了一个不该知道的秘密,逃跑一般离开了山林。孔雀为何被关在那里?至今我仍然不清楚缘由。但我清清楚楚记得孔雀的眼神,那一道转瞬即逝的光是这篇小说的另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