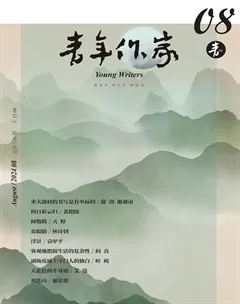蓝眼睛
一
草,并非一直像今天这样是绿色的。在我长大的年代,路边低矮的草被新鲜的尘埃覆盖,显得黯淡低沉。飞舞后落下的尘埃,来自于一辆又一辆土方车。那时经济好,像是蓄谋已久,村子的人们陆续开始盖房子。满载砂石的土方车到来,带着令人兴奋的轰鸣声。尘埃漫天,举目望去都变成黄色。黄色是幸福的颜色,它意味着一栋崭新的楼房要拔地而起了。
二〇〇四年,父亲雇了人,开始在老家的古宅边上建一栋五层楼高的房子。那年的暑假,我住进古宅,望见新盖的房子已经初具规模。灰白的外墙,紧贴竹子搭起的脚手架,有人行走在上面,“咔嚓咔嚓”地响。
我上到二楼,没有灯,光从四面八方的窗框闯入并照亮地面。我踢走碎石子,走到窗框边,听见楼下稀稀疏疏的敲打声,如同和尚漫不经心的诵经。
窗框外那棵龙眼树晃动起来,“哗啦啦”地响。我看见一个正在摘龙眼的少年,接着看见了他的眼睛。那双鹿一般的眼睛长在一张黧黑的脸庞上,使整张脸看起来更加苍老。这是我和向伟的初次相遇,他在房子的外头,我在房子里头。如此我们对望,不超过三秒钟,向伟就从龙眼树上一跃而下。落地声沉闷得如同夏日午后远方的雷鸣。
向伟来自西南山区,他的父亲就是负责盖我家房子的包工头。当年向伟的年纪理应上初二,但错过了注册时间,在他父亲的努力之下,寄读在本地小学五年级。因此开学后,我发现自己与他同班。
他很难管教,上课时摔门离开,说是去上厕所,就不再回来。直到体育课,我们才在篮球场再次遇见他。练习上篮时,他的口袋里掉出一个木制弹弓,有同学好心捡起还他。向伟接过弹弓,闭上一只眼,对那人比出射击的姿态,拉长了皮筋,说一声,“咻——”,接着像是为了证明并无恶意,他还咧开嘴笑一下。跟许多笑的下场一样,这个笑也遭到了误解。那天放学后,我把国旗降下来,扛着国旗走在走廊上。我看见向伟朝我跑过来,面色慌张,一闪而过,先我一步跳进了器材室。我瞥见走廊的尽头,是一拨追赶他的人。若无其事,我也进入了这个终日都很暗的空间。那时向伟蹲在墙角,我们再一次看着对方,就像两只动物在冬天的洞穴相遇。我们都没有说话。
门外传来闽南语粗话,然后好几个脑袋出现在门外。他们用闽南语问我:“在哪,那个臭巴子?”我打开皱巴巴的国旗,假装在整理,挡住了背后的那个角落。接着,我指往走廊的另一个方向,用闽南话回答:“他,往那里逃去了。”
像堵了许久终于决堤的水,他们往那个错误的方向跑过去。我看见他们手里握着长满刺的藤条,那是他们打架时常用的,当时遍地都是弯下腰一抓就有的武器。我身后传来声响,是向伟站了起来。他拍拍屁股的灰尘,推开器材室的窗户,脚踏上木箱。临走前他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就从窗户往外跳了出去。他逃跑的背影在窗框中,像是一幅平庸的风景画。
隔天早上,向伟背着一个崭新的挎包出现,那拨人再次围上来。挎包的拉链被拉下,里面露出一把开山刀。刀身是大小不一的圆圈,纹路像蛇皮,在教室里反射出一道白光。向伟把刀拿出来,亮了一下相,又塞回去,拉好挎包拉链。他身边的那个圆圈也随之散开了。从此再没人敢招惹他。
当天晚上,我住在古宅,闻见了建筑工人们开火做饭的气味。就在那栋他们亲手建造的房子里,炉灶在地上支起,不新鲜的鱼虾与酱油辣椒一起,合力造出呛鼻的味道。萤火虫们出来散步,在我眼前晃荡,陆续投入不远处的黑暗。
那片黑暗里走出了向伟,他额头的伤疤被月光照亮。向伟拿眼神跟我打招呼,我没说话。于是他问:“你几岁了?”我回答:“十二,马上满十三。”
我们一起走在月光下,路过一户养田鸡的人家,发出“咕咕咕”“呱呱呱”的叫声。又路过一片相思树林,草木的味道,混合挂在树上的猫狗尸体所发出的恶臭。我们闷头往前走,来到一片山坡,空气才变得干净。我们在月光下玩单脚跳的游戏,努力踩地上对方的影子。
他们都把他当作怪物,我反而和他走得更近了。隔天我邀请他到家里,介绍书给他。他拿起书,一直抚摸封面,抚摸了很久,像是一种郑重的礼貌。看书时他皱起眉头,很快又松开,叹一口气,说:“我投降了。”
向伟站起来,扫视我的房间,忽略成堆的书之后,看见了角落的鸟笼。里面空空的,水槽里有泛白的痕迹。他问我:“这鸟死掉了?”我说:“嗯,一只死了,另外一只飞走了。”他很认真地说:“恭喜你,交对朋友了。”
隔天他便带我掏鸟窝。我们在一片相思树林寻找了一下午,却没有找到半个鸟窝。他挠挠头,改教我爬树,教我如何双腿盘住树枝,如何踩在稳固的树杈上,如何碎步往前。他可能把我当成弟弟,不厌其烦,用那棵树做示范,忽上忽下,像搭电梯一样轻松。
接着他更认真了,说要教我打架。他抓我的身体讲解要点,譬如要击打对方的膝盖后方,那个往里凹的部位,对方就会跪下来。又譬如直接一个冲拳,打对方鼻子,鼻子很脆弱,血一流出来,对方的气势就会跟着往下坠。
跟学校课本的内容一样,他教我的这些东西,几乎不曾真正派上用场,更像是几则神话,驻留在我的脑中,偶尔发光,偶尔高歌,偶尔飞起在空中。
那年夏天,我们还去了好几次海边,都是在中午,阳光最猛烈的时候。大海是银白色的,沙滩滚烫,让人忍不住奔跑。我怕将身体丢进海水里,温暖包裹了我,还送来一股浓烈的腥味。
远处有抽砂的机器,呼天抢地,卖力地轰鸣。即使如此,我仍感觉整个世界非常安静,安静得没有尽头。那时向伟已经游出去很远了,他在海面上浮沉,吐口水,叫我过去。我划了两下,脚底的海水开始变凉,恐惧升上来,于是我掉头,回到了岸上。
沙滩仍然滚烫,我在沙滩上奔跑起来,沿着海边跑了一圈。烈日在上,烤着我的身体,令奔跑变成庆典的仪式,海面变成了闪烁的金色,好像宝石从天上掉落,漂浮在水面,然后拥有了呼吸的能力。海里的向伟只剩一个脑袋,他舒张身体,自在的,好像被海浪摆布,又好像接受施洗。涨潮前他终于上岸,眼睛明亮,晒黑的身体微微发光,如同刚刚捞上来的石头。
我们往回走,迎面来了四五个初中生,比我们高出两个头。他们脱衣服,准备下水。有人皱眉头,回头瞪我们一眼。我牵起单车,准备踩上去,背后来了一句闽南语,“好臭,哪里来的臭巴子。”向伟转头问我:“我他妈又被骂了?”那人看看向伟,又看看我,继续用闽南语说:“你明明不是巴子,为什么要跟臭巴子玩在一起?”
我沉默,然后沉默地蹲下,抓起一把沙子,朝他们砸过去,接着跳上单车用力踩下。那人吃进沙子,反倒吐出了粗话。他们试着追上我们。但滚动的车轮比迈开的双脚更快。石子砸过来,我们的笑声如同屏障,令石子只命中了地面。
生命与危险,蛮力与速度,令人着迷的畅快,当天正午的太阳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安全到家,满身的细沙。我们唱着歌,用角落的水龙头冲澡。从海里带回的沙子留在地上,连同水渍一起,组成了小小的海。天上有云朵路过,射出阳光,收回了这片短暂的海。
二
半个月不到,向伟去网吧打游戏,他正投入,嘴里念念有词,突然后脑勺被扇了一巴掌。他转头,看见是海滩上的那几个初中生。向伟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踢掉椅子,跌坐在地上。随后,依他的说法,他和他们打了几个来回,才从后门跑掉了。但眼看着他嘴角的瘀青,以及他怒不可遏的样子,我更相信当时他并没有还手的机会。
向伟说:“借我一把刀,我砍死他们,然后去自首。”我问:“你不是早就有一把很威武的刀?”他不好意思地承认:“其实那是找朋友借来的,已经还回去了。”思来想去,最终我和向伟走了很远的路,再一次去借那把刀。在一条溪流旁边,住着他的老乡们。他们用黑油毡和竹子搭起简易的工棚,远远望去,好像一条老狗身上耷拉着的层层皮肤,随便一阵风都可以轻易吹散。
刀借来了,我拿起来挥了挥,发觉刀光暗淡了,仔细一看,原来刀已经生锈了。向伟告诉我,上次他带去学校之前,其实特意抹了油。我问:“你有这个,那我用什么?”向伟愣一下,转身去借来另一个家伙,一个铁制的指虎。
我把指虎套在手上,握紧了,试着打了几拳。空气发出的声响让我顿时明白为何羚羊的头上会长角。向伟怕我的手指受伤,又找来布带,缠进指虎的空环里。缠绕时他皱起眉头,像是在做刺绣那样细致的手艺。
我戴着指虎,向伟背着开山刀,我们去网吧找那伙人。找了一圈,确认他们并不在。一台电脑的屏幕还亮着,向伟坐下了,点开了游戏。我站在旁边,看着他打。屏幕里的游戏人物叫八神庵,甩动肩膀,撒出紫黑色的花簇,连连命中对手。八神庵确实很帅气,操纵他的向伟似乎也变成英雄。他连赢好几局,脸上有了光彩。他看向我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是在靠着打游戏壮胆。我问:“你还报仇吗?”向伟猛吸一口气,起了身,说:“事不宜迟,我差点忘了。”
当时我们能够活动的范围并不大,小小的天地下仇人也容易寻找。我们远远望见他们躺在一个小山坡。和上次所见有些差别,有人染了头发,满头的金毛,比太阳还要扎眼。我和向伟站住,进行观察。他们正在分烟抽,有人呛到了,努力以豪迈的样子吐痰。还有一个拿着美工刀,用刀背,在小臂上为自己刺青。温柔的阳光下,他全心全意地伤害自己的身体,令我们不得不屏息,像是一旦打破这宁静,那人就会立刻受伤。
我和向伟看了看对方,点点头,向山坡走去。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们的出现,但也懒得站起来。向伟还没来得及把刀掏出来,我的指虎就掉在地上。我弯腰捡起,发现胸口已经流了血。我不顾一切,用戴着指虎的拳头胡乱挥舞,“啊啊啊”乱叫,终于谁也没有打到。
若遇到疯子,最好是走开。他们拿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四下散开了。我筋疲力尽,喘着粗气停下。向伟看着我,指我的鼻子说:“流血了。”我仰头,天空映进来,铁锈味道的液体在鼻腔流淌。我把指虎甩开,才看见手指的关节也出了血。
等待我的鼻血止住了,我们才回家。向伟父亲已经得知儿子借刀的消息,手里抓好了皮带,看见向伟就骂,“听说你要去杀人,你是准备专门当畜牲吗?”向伟不疾不徐地说:“你今天要是敢打我,我也跟你来真的。”说完他拉开挎包的拉链,露出刀光,故伎重演。向伟父亲愣住了,很久没有说话。接着他站起来,在口袋摸摸,掏出皮带的钢扣,装上去,举起来朝向伟打去。那天晚上向伟被打得很惨,我听见他的哀嚎与求情,过了很久才停止。
隔天向伟不见了。我试着寻找,去海边,去泳池、水库、学校、小卖部,没有人看到他。我开始幻想他已经死了,昨天夜里就被打死了,尸体说不定就埋在地基里,不久后,我住进那栋楼里,夜里有人长久地唤我的名字,我醒来,满地的白光,向伟站在窗前,脸上那道伤疤正在滴血。类似的幻想越频繁,我越感觉愧疚,是我害死了向伟。
不过幸好他是活着的。某个早上,我被“哐哐”声吵醒,睁开眼,向伟就站在窗户外面。我打开窗户,问他究竟去了哪里。向伟说:“先让我进来。”于是他从窗户跳进我的房间,我注意到他衣服发黑,身体也散发出酸臭的霉味。他扫视我的房间问:“那个鸟笼呢?”我又问一遍:“你去了哪里?”他才告诉我,这段时间他其实住在山里。
向伟说,那天夜里,父亲喝酒后又来了兴致,抓起皮带想再打他一顿,这回他跑开了。月色中,他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却找不到安身地。他从围墙跳进学校,在双杠上甩了几把,微微出汗。不知不觉,他走到了大理石堆场,找到一块无人占用的大理石,躺下了。他听着夏夜的虫鸣,就此睡着了。
隔天太阳出来,带来光亮的同时,也把石头照得发烫。他只好继续迁徙。他走进一片山林,里面阴凉,安静,还有些野果,味道类似桑葚。于是他白天待在山林,夜晚睡在堆场的石块,流汗了,去河里洗澡;没钱了,就去拣废铁、偷井盖,或者去网吧打游戏,靠比赛赢钱。他说:“我现在就跟天上的鸟儿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我惊讶他已经变成了野人,在短短两个礼拜内。尽管太阳是同一颗太阳,月亮也是同一颗月亮,但照到底下,人们却身处不同的情境,这像是世界给出的谜语,我至今仍不知晓答案。
向伟说:“哎,来,有个礼物送给你。”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捧着送到我面前,手掌打开,是一只雏鸟。灰白色的毛,渗出一丝蓝绿色。向伟说:“在山林里捡到的。”我接过问:“这是什么鸟,该怎么养?”向伟说:“随便养,死了也没事。”说完他从窗户跳出去,离开了。这只雏鸟在我的手掌里,重量微不足道,但有一双难以忽视的眼睛。它在桌上试探着走动,我看着它的眼睛,仿佛看见向伟的眼睛。
我开始养这只鸟,我不知道它的品种,也没有取名。当时我们好像不在乎这一套,就只是养一只鸟。我喂它吃菜叶、玉米、花生。生命的力量超乎想象,它长得很快。它试图探索眼前的世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终于有一天被我母亲发现了。那时她刚丢了工作,赋闲在家,需要清静,因此当她明白我房间那股怪味的由来,便生气地要求丢掉它。
我去找向伟,告诉他我养不了了,是否一起丢掉它。他挠头,叫我跟他走。一路上我们捡了些石头、硬纸板,还停下喝了汽水,然后来到大马路。汽车和土方车呼啸而过,掀起熟悉的尘埃。
我们走在黄色里,直到前方出现一个加油站。我们绕到加油站后头,拨开铁丝网,从缝隙钻进去。地上有层层叠叠的落叶,踩上就碎了。这里都是龙眼树,大片的树荫,蜘蛛网忽明忽暗。此时,怀里的那只鸟发出了“咕咕”声,像是宣布它很满意。
在一棵藤蔓缠绕的树下,地面平坦,我们用纸板和石头围出一道墙,将雏鸟放下,让它适应这个新住所。它探头探脑,细嗅土地的味道。我看着雏鸟的样子,又看看向伟,对他说,你们两个长得挺像。
向伟说:“错了,这东西需要人养,我不一样,我早就是野生的了。”我们分工,我负责收集菜叶、玉米、饭粒,向伟负责将围墙修得更坚固,到后来鸟窝还有了一个屋顶。
这里变成我们的秘密。我们花漫长的时间待在这里。我在树荫下读小说、背诗词,向伟在树上听着,有时直接睡着了。光的影子在地上,往同一个方向挪动,不紧不慢,黑色忽然就落下来。第二天,影子重来一遍昨日的游戏,没有意外,结局都是夜的降临。如此好多天过去,那只雏鸟越长越大,逐渐变成鸡的模样,陡然多出了一条长尾巴。我们意识到,向伟捡到的不是鸟,或许是一只山鸡。
暑假快结束,树上的向伟说:“再养大一点,我们就一起放生这只山鸡。”我答应了,然后我告诉他,以后我来这里的时间会变少,因为爸妈好像要我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上补习班?”向伟问。我说:“不太懂,但好像是要我考市区的一所初中。”
向伟没有回应。然后蝉鸣响起,尽力拉长了自身。又过了半个月,我家的房子已经完工,向伟一家人,连同他的老乡们,准备去到下一个工地。临走前,我父亲包红包给他们,挥手祝福,然后低下头,对我说:“野成那个样子,别跟向伟玩在一起了。”
身不由己,我很快就无暇顾及向伟了。开学后,我晚上去补习班上课,我和样子体面、皮肤白皙的孩子们坐在一起,第一次有了自卑的感觉。眼前的题目,好像烈日下的那一大片海水,一不小心就会将我淹死,我再一次感受到无边无际的寒意。
我奔跑在马路上,看见加油站,绕到后面,进入我俩的秘密基地。拨开树枝,向伟背对我,我叫他名字。他转头过来,已经长出了胡茬儿,对我比“嘘”的手势。他用眼神示意,要我跟着他看,我循着向伟的目光看过去。
在山林的深处,有一个老人,正环抱着一棵树,均匀喘着气。他喘了好一阵子,然后突然大叫一声,“啊——啊——”,一如山洪在夜间爆发,一举宣泄累积已久的郁闷。
我知道这个老人,他平常走在路上,嘴里总念叨,“错了,我做错了”。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可怜的疯子,没料想他还有这样的秘密。我顾不上答案,我只是心急地问向伟:“那只山鸡呢?我们的山鸡呢?”向伟不动声色,指向头顶的树梢。
我抬头,看见停在树枝上的,是一只尾巴很长的鸟。阳光遮住了视线,我走过去,认真看了几遍,确认那些蓝绿色的羽毛并非光的折射,而是它真正的样子。
我本想大喊,孔雀!怎么变成一只孔雀了?但我忍住了没有出声。因为当时的山林安静无比,那位老人像是被什么更大的东西接纳了,已经和那棵树融为一体,连呼吸都变得平稳许多。在这诡异的宁静中,我仰头望着树上的孔雀,呆呆地盯着它,仿佛它是天上来的。
三
那年的立秋,土地拆迁办公室的人来到村子,他们带着卷尺,穿着白衬衫,在空中比画。接着消息传出来,我们这片地要被征用了。其中也包括我家那栋五层的楼房。
与此同时,向伟一家则谈不上幸运。他父亲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折了腿,对方不肯赔钱,于是他拿着刀,连同老乡们,在夜里来到那户人家的门口,在地上静坐。第二天中午他拿到五万块。两万用来付医药费,剩下的准备分给一同前去的老乡们,但被他们谢绝了。
因为腿伤严重,向伟父亲决定回老家,用那笔赔偿金买一块地,计划种水果。这是我从向伟口中听到的最后的消息。那时他在树上,我在地上,我们互相看对方,明白似乎有些残忍的东西发生了,如同鞋底的石子,别人看不到,当事人心知肚明。孔雀发出叫声,像是面容难看的婴儿尽力的哭泣。
我父亲用征地赔偿的那笔钱买了市区的房子,我第一次住进了小区。客厅和房间,摆满未拆封的电器,它们被乳白色的塑料膜套住,与书桌前的我对望。风扇摇着头,把塑料膜吹得“哗啦哗啦”响,像是台风前夕的景象。
几天后,我参加那场考试。题目如同咒语,我胡乱应和,完全不知道这些咒语会将我带到何处。出了考场,阳光来势凶猛,试图把天与地照成同一种颜色。接着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类似臭掉的杧果。我想起了向伟。我试着想象回到老家的他,如何在果树林里穿梭、跳跃、流汗,以及苦笑。
我被录取了,往后要到市中心上学。我特地去了一趟山林,孔雀当然已经不在那里。那块我坐着看书的地方,被流土覆盖,还有雨水的痕迹,仿佛我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是幻觉,不曾存在。我蹲下来,走了几步,试图以孔雀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然后我模仿那位老人,大喊了一声。回声消失之前我站起来,我很确切地知道,我身上的某一部分已经消失了。
但命运没有放过我。我初二那年,某天经过巷口,有人叫我过去,说来帮个忙。我照做了,但一进去我就被人群围住。他们说,“小帅哥,跟你借点钱花花。”我明白自己遇上了勒索,没有犹豫,低头拉开书包的拉链,拿出了钱包。我展示里面不多的钞票,等待回应时,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眼前的人正是向伟,他戴着墨镜,嘴角有笑容,接着他把脸撇到一边,假装不认识我。
我扯出了一张五十块,递出去。没有人接那张钞票。一只手拍到我的肩膀上。向伟的脸凑过来,摘下墨镜,“哈哈哈,骗到你了,我跟他们打赌,赌你不会掏钱。”我还没反应过来,向伟接着说,“上个礼拜我就在这看到你了,哈哈哈哈,你怎么了?胆子变小了。”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借口,我告诉他,我上课要迟到了,我先走了。我转身跑掉,没人阻拦我。
一股不安感找上我,直到下课。我走出校门,遮阳伞下有一台摩托车,向伟坐上面,一边抽烟,一边与我挥手。他拍拍坐垫,我上了车。这是一台动静很大的摩托车,路上的人转头看我们,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城里的绿化建设很好,草已经是有希望的那种绿色了,在风中堂堂正正地摇摆。向伟带我来到另一个巷子。他说,“现在最流行的,溜冰场,来过没有?”
买票,租鞋,场内满是烟味,五彩的光来自天花板的彩球。向伟踩着地上不断变幻的光,走向一群人,点头致意,然后介绍我,“这是西拿,我以前最好的朋友,高材生。”因为那一句介绍,我也与他们点头致意。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紫色,是他们头发的颜色,一只或两只眼睛,透过帘子一般的刘海偷看我,仿佛小兽躲在洞穴里张望外面的世界。
随着向伟喊一声“一起来噢”,灯球就此变幻了颜色。歌曲是那首《金色年华》,鼓点浓重,声嘶力竭,意外好听,不顾一切的狂欢。溜冰的向伟,舒展身体,还伸出手来点烟,如同孤独地滑翔的鸟。他眼看着我还在缓慢挪动,就先溜到前面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海里的他,就此明白有些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在那一瞬间,我确认时间只是幻觉而已。
滑冰到一半,派出所的人在外面敲门,我们像老鼠一样从后门跑掉,来到巷子的尽头。向伟像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喘喘气,什么也没解释,带我翻过围墙,继续往前走。他用摩托车载我回去。在路上我忍不住问:“你现在住哪里?”他回答:“今天住这里,明天住那里。”我说:“你还是像鸟一样。”
他笑了,然后在风声中说:“讲到鸟,你还记得那只变成孔雀的鸟吗?”“当然记得,它已经死掉了不是吗?”向伟说:“死,哪有那么容易死?它活得很好,改天带给你看。”他扭下油门,劈开风,闯过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隔了一周,我走出校门,看见向伟朝我招手,叫我过去。我跟在他身后,来到附近的公园。在梧桐树的树荫里,地上有一个笼子,被麻布盖着。
向伟对我一笑,说:“记得我吗,还记得我吗?”然后扯掉了那块布。是那只孔雀,它低着头,正在啄地上的草。它瘦得像一只落难的山鸡,好像经受了风吹雨打,但努力活了下来。
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又想问,你怎么养的?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沉默像一条河,横亘在我和向伟之间。有散步的老人走过来,看着孔雀,缓慢地弯腰,伸手摸它的尾巴。向伟没有阻止。老人闻了闻手指说:“挺漂亮,也挺臭的。”向伟不满地“啧”了一声。老人抬起头,问:“多少钱一斤?怎么煮比较好,红烧还是煲汤?”
向伟载我和孔雀一起去吃饭。结束后,他载我回家,在小区门口,他突然叫住我。我见他有话要说,便问他要不要去我家玩。向伟说:“真好命,你住的地方越来越好了。”我说:“什么话,我们都差不多的。”向伟摆摆手,说:“骗人,我知道你爸不喜欢我。”
我试着解释,向伟打断我,说:“其实吧,我要回老家了,这里混不下去了。”我问:“你爸还好吗?”他说:“就那样呗,在办残疾人证。”我沉默。向伟说:“这只鸟交给你,行不行?”我说:“可以,那你还回来吗?”向伟说:“这里比较欢迎我这种人了,我就会回来。”
我们一起把笼子搬进小区,放在草地上,打开栅门,把孔雀放了出来。孔雀好像很熟悉这里,循着水声,走到水池边看了看,然后低头,又开始啄地上的草。
向伟突然说:“那我走了噢。”我跟他加了QQ,然后挥手告别。向伟走进黑暗里,然后又走出来。他拿那双我很熟悉的眼睛看向我,像是终于下了决心,说:“你那边有钱吗?”我愣了一下。向伟说:“我想买车票,钱不够。”“要多少?”“跟你借八百,一定还你。”我叫他跟我上楼拿。他坚持在楼下等,然后又补了一句,“不然跟你要个一千块好了。”
我回到家里,找到六百块,然后又去父母的卧室,打开抽屉,凑齐了一千块。我往楼下走,停住了脚步,又走回家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觉镜子有些脏。我把那些钱放回原本的位置,手里只留下三百块。下楼的时候,我反复练习了语气,“哎呀,我只找到三百块,真抱歉,三百块够吗?”
我来到路灯下,那里没有人。我喊向伟的名字。那只孔雀从草丛里钻出来,发出“咕咕”声。我继续寻找向伟,一直到小区门口。保安告诉我,你那个朋友骑摩托车走了。不知为何,我感到口渴。地上躺着一根孔雀的羽毛。我捡起它,发觉自己的手心出了汗。
那天晚上,月光亮得不可思议。我站在窗户往外望,底下的那些土地,现在整齐干净,但我知道它们以前是什么样的。尘埃的漫天,货车的呼啸,向伟和孔雀,还有我,都是确凿无疑的记忆。正是它们的确凿令我恍惚。灯光明亮的教室,我正襟危坐,面对无边无际的习题,在竞争中学会了谨慎与自保。
草已经变成绿色,山林已经被马路切开,萤火虫已经躲到无人过问的角落,山林里的老人已经死去,新的小朋友们出生了,广告与标语也已经换成了新的,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也已经规划好了。
那天深夜,我坐在书桌前伸懒腰,往窗外瞥了一眼,那只孔雀身姿笨拙,走到路灯下,圆形的灯光在地上照出一个暖黄色的舞台。孔雀在舞台中央站了许久,突然它耸起屁股,好像在发抖,就此打开了尾巴。我呆呆地看,以为看见了幻觉。它支撑着那把绽放了的巨大尾巴,拖着蓝绿色,离开了舞台,旁若无人地,决绝地,没入黑暗中。
那晚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梦里五颜六色的光旋转移动,带我去遥远的深处。隔天中午我才被母亲叫醒。她问我:“那只孔雀,是不是你养的?”我点头,她说:“赶紧去处理,小区的物业在等你。”我迷迷糊糊下了楼。围观的人群很多,还有一个小孩在哭泣。我走过去,清洁工说:“我就记得是你养的,你来说说看,现在该怎么处理?”
我拨开人群。巴掌大小的血迹,那只孔雀倒在地上,它应该是刚死没多久,因为那抹血迹称得上新鲜。旁边的人议论纷纷,说,“就不应该养这种东西,臭死人了,叫声也真难听。”另一个说,“谁放它进来的?”
我抬头盯着他们的脸看,他们不再说话。在这份短暂的安静里,我看着那具孔雀尸体,试着目送它离开。孔雀的尾巴,那一大片花纹,一个又一个蓝绿色的圆圈,犹如无数双眼睛死盯着我,像是在不甘地质问。
不知看了有多久,最后我站起来,打了一个寒颤。起风了,这里不再有尘埃。
【作者简介】 林诗钊,曾用笔名林西拿,生于1993年,福建厦门人;写小说,也写电影剧本。小说发表于《江南》、《ONE.一个》,现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当代视觉文化博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