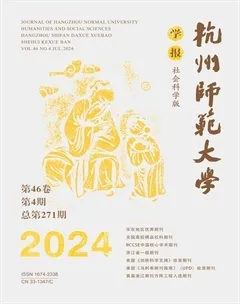从后现代史学论顾颉刚层累说 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摘 要: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后,在史学界引起两次批判,这两次批判多将顾颉刚视为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顾颉刚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在理论上有相似性,所以层累说所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也常与后现代史学遭受的批判有相同之处。虽然顾颉刚有许多与后现代史学相近的看法,但他相信各个时代所建构的历史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意识”,由此可以建立一种“近真”的历史,从而也比后现代史学更能维护史学研究的尊严。从当代史学史的发展而言,顾颉刚的观点早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这不但表现了中国史学见解的自主性,也更早地将中国史学带入了当代的研究趋势之中。因此,层累说可说是让中国的史学界比西方更早接受了后现代史观的冲击,也让传统的史学家借之反思而可顺接后现代史观所引发的启示。
关键词:顾颉刚;层累说;疑古学派;后现代史学;海登·怀特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4)04-0014-10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4.04.002
一、前言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顾颉刚(1893—1980)于1923年提出的著名观点①,依此观点他在1926年编著的《古史辨》质疑了先秦、秦汉典籍所记述的三代历史,因而以“东周以上无(信)史”在学界引起极大的震荡。支持《古史辨》之研究的学者如胡适(1901—1995)称誉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而钱玄同(1887—1939)甚至为此易名“疑古玄同”,他们都认为《古史辨》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的契机。
然而在1952年,批判胡适与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风潮兴起,其中包括了曾经参与古史辨活动的童书业(1908—1968)和杨向奎(1910—2000)。批判的论点大多是站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将胡适视为是“唯心论”“实验主义”与“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视顾颉刚为现代版的公羊派学者,认为他混合了公羊学、清代考据的疑古学,并且接续了胡适的工作,进行着“推翻古史的计划”。②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些学者的批判态度虽然相对以往有所改变,但在1995年李学勤(1933—2019)出版了《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并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后,学界再度出现了否定古史辨运动的声音。 如廖名春认为:“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倍受外国霸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见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陈明主编《原道——文化建设论集》第4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走出疑古时代》的书名来自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信古、疑古、释古”三种研究趋势 冯友兰言:“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级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见冯友兰《冯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6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第1页。" ,李学勤将“信古、疑古、释古”解释为三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阶段,因此有走出“疑古”、到达“释古”的说法。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在于1993年郭店楚简的出土推翻了过去很多伪书说的观点,因此李学勤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郭沫若的考古方法论,认为必须结合文献和考古反思中国古代文明,唯有“走出疑古”才能避免古书的“冤假错案”。[1](《导论》)李学勤及其支持者虽然没有完全否定“疑古”的“进步意义”,但大多认为“古史辨派的失误是其方法论导致的必然结果”,多将“疑古”等同于“怀疑古书的真伪”,并且认为古史辨派“简单用古书出现的早晚来判断历史事实的真伪”。 如梁涛认为:“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即是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的原因所在,而古史辨派由这种记录、描述的不同,转而怀疑事实本身的‘有无’与‘真伪’,这可以说是导致其片面‘疑古’,并最终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见梁涛《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二十一世纪》,2005年2月号,第134页。
如果是站在乾嘉考据学、清代公羊学、胡适科学史学及五四反传统思潮的脉络来批判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似乎会导向“这个运动最大的盲点之一是把书的真伪与书中所记载史事的真伪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伪书中便不可能有真史料”的结论[2](P.296),而“走出疑古”的批判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以考古的成果来加强这种论述,认为考古的实物有助于重建上古的信史。然而,如果跳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疑古脉络以及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信史的观点,改从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去看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则可以看到他的理论方法,已经具有后现代史学的观点。因此,从后现代史学的理论来看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或许更能看到顾颉刚对中国史学理论的贡献。
二、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之同
近代中国史学对方法的提倡,起于梁启超在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3](PP.3-7)梁氏之后,代表西方实证史学的著作因其“科学方法”大受欢迎,其中包括由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引领的兰克学派,他们重视原始的一手资料,更重视事件目击者所记录的书信和档案。由于兰克学派主张对所采纳的数据源作严格的考证,所以人们称兰克的史学为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科学的史学。兰克学派对西方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占有主导地位。[4]其方法论对中国五四之后的史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傅斯年即对兰克(当时译作“软克”)十分推崇。[5](P.276)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陈独秀与胡适、顾颉刚的疑古态度,都体现了西方追求理性与科学方法的精神,而傅斯年也明白地指出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论”具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 见杨国荣《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史林》,1998年第3期,第91—101页。又如汪荣祖认为兰克的科学方法与历史求真“引发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风潮”,“胡适更将讲究考据的清代朴学与西方科学(实证)方法相比符,强调史料乃是考证真相的命脉,顾颉刚受到胡适的影响,从辨伪入手,以建设真实可靠的古史”,“顾氏于疑古之余,借此提倡西方人所谓的信史,而信史之建立必须依赖可靠之原手档案史料,遂引发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之说”。见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56期,第148、150页。 换言之,顾颉刚一向是被列入梁启超“新史学”[6](PP.1-32)之下,作为重视“史料”、重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关系的实证史学的代表。就此一学术系谱而言,顾颉刚似乎完全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后现代史学无关 依黄进兴的意见,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如下:“时序上,发轫于上一世纪50年代的建筑、艺术与文学的评论,60年代则在思想与哲学园地发荣滋长,70年代以降,便席卷社会科学;而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史学则殿其后,方受波及。”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第3页。,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梁启超“新史学”是“现代性”中“科学理性”所孕育的产物,后现代史学则有“反现代性”与“反实证主义方法”的倾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主要在两方面:其一是消解“后设叙述”,其二是“语言的转向”。 有关“后设叙述”与“语言的转向”,参见黄进兴《历史的转向:现代史学的破与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38—140页。“后设叙述”是指“一套能整合、调解叙事与叙事间关系的系统性框架”,因为有了这套框架,分门别类的叙述活动才能够被编写到同一个故事之下,各不相关的语言才能汇总成同一个社会组织,而形成了“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因此,对“后设叙述”的消解,在史学上即是质疑具有本质论色彩、线性发展与目的论的民族史观和进步史观。“语言的转向”是指从语言符号上对史实进行一系列的回溯,由史实回溯到语言,再从语言回溯到文本(Text),最后由文本回溯到符号(Sign)。依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语言作为任意(Arbitrary)的符号”的原则,语言符号与其表达的事物并没有自然、必然的关系,语言只是社会文化的建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打破了“先有一个具备系统的物质世界,然后人们得以命名这世界的事物,以进行语言沟通”的观念。对索绪尔而言,语言只是一套用以建构事物之意义的符号,而且语言还筛选了什么事物需要被命名,什么事物不需要被命名。“语言的转向”否定了语言的意义与史实的必然关系,凸显了史实是一种语言符号的建构,这种看法促成了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在1973年出版之《后设史学》(Metahistory)所高举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 有关“叙事转向”,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3章《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以及第5章第156—162页、第6章第185—201页。怀特扛起“历史若文学”的大旗[7](P.55),指出历史与文学都是一种叙事的表达,这除了有泯去文、史分隔畛域的意义之外,也认为历史与文学的“论述”(Discourse),它的基点在于“转义理论”(A theory of tropes或tropology)。“转义”简单而言便是隐喻(Metaphor)、换喻(Synecdoche)、提喻(Metonymy)、讽喻(Irony)。怀特主张史学与文学的表意均需通过自然语言,故无所逃于譬喻的转义作用,所以史书会呈现出和诗、小说、戏剧同样的语艺模式。因此,对怀特而言,“过去”本不具任何意义,“历史”之有意义纯为史学家的语艺行为,而这正是历史虚构性的真谛,也是“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极致。
不难看出,支持“走出疑古”的学者,对顾颉刚的批判有一部分的理由在于他的理论不能建立民族史观 如前述廖名春的观点。李学勤亦言:“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特别是炎黄二帝的传说,不能单纯看成神话故事。这些传说确乎带有神话的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历史的质素、核心,就会抹煞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上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民族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 :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4、217页。又如宋健言:“爱国需要读史。人们说,无论是学社会科学的,学自然科学的,都应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五千年历史进程的炼凝荟萃而成。”见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文史哲》,1998年第6期,第5页。,这是由于顾颉刚的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同样具有质疑古书中“大叙述”的意义。顾颉刚的层累说是从歌谣、戏曲中悟出的。所以他也说:“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作为系统的叙述。”[8](P.61)基于这种想法,他对孟姜女故事的演变进行研究 顾颉刚有《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原刊《歌谣周刊》第69号,1924年11月)与《孟姜女故事研究》(原刊《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1927年)二文,可见于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顾颉刚言:“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见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2页。,指出“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9](P.70),“懂得了这件故事的情状,再去看传说中的古史,便可见出它们的意义和变化是一样的”[9](P.72)。由此可见,顾颉刚认为古代学者编定古史与歌谣、戏曲的作者编定故事具有相同的情状,这种情状概括而言是:古史与故事都“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的要求的。我们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过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种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的需要”[9](P.72)。顾颉刚的看法说明了古史与文学的叙事都有“后设叙述”,也与怀特所说的“历史若文学”有相近之处。
怀特认为“编年记事”(Chronicle)与“故事”均取资于未经处理的历史素材(Primitive element),经过编选、排比,使之首尾一致而富有意义,由于编年记事与故事都借助自然语言中譬喻的转义作用,它不是科学的形式语言,所以编年记事与故事都具有虚构性,也都有以叙述体论述形式的言辞结构。[10](P.ix)由此,怀特指出历史作品包含了认知的、审美的与道德的三个显性层面,这三个层面的解释策略统由“形式论证”(Formal argument)、“情节编织”(Emplotment)与“意识形态”(Ideology)交互运作而成,因此所谓的史学风格便是“论证”“布局”与“意识形态”诸模式的结合。 怀特认为“布局模式”有“传奇”“悲剧”“喜剧”“讥讽”等,分别对应“论证模式”中的“形式”“机械”“有机”“语境”,以及“意识形态的涵蕴模式”中的“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69页;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29。顾颉刚的观点虽然没有像怀特一般的整齐理论,但他说“就这件故事(孟姜女)的意义上回看民众与士流的思想的分别。杞梁妻的故事,最先为却郊吊;这原是知礼的智识分子所愿意颂扬的一件故事。后来变为哭之哀,善哭而变俗,以至于痛哭崩城,投淄而死,就成了纵情任欲的民众所乐意称道的一件故事了”,“后来民众方面的故事日益发展,故事的意义也日益倾向于纵情任欲的方面流注去;她未嫁时是思春许愿的,见了男子是要求在杨柳树下配成双的,后来万里寻夫是经父母翁姑的苦劝而终不听的;秦始皇要娶她时,她又假意绸缪,要求三事,等到骗到了手之后而自杀。但这件故事回到智识分子方面时,就又变了一个面目,变得循规蹈矩了,她的婚姻是经父母配合的,丈夫行后她是奉事寡姑而不敢露出愁容的,姑死后是亲自负土成坟而后寻夫的。” [9](P.71)顾颉刚的上述说明与怀特所说“形式论证”(包含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决定论)、“情节编织”“意识形态”都有相似之处,如所谓的“知礼的智识分子”可视为儒家的意识形态,而在蔡邕的《琴操·杞梁妻叹》中也呈现了部分“鼓盆而歌”的道家意识。 顾颉刚论蔡邕的《杞梁妻叹》的曲词言:“她死了丈夫不哭,反去鼓琴,有类于庄子的妻死鼓盆而歌。”见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1册,第11—12页。意识形态的表现,在故事上是如此,在经学上更为明显,故顾颉刚说:“经过了二千余年的编造,能够成立一个系统,自然随处也有它的自卫的理由。”[11](P.187)
三、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之异
由于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相近的观点,所以它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也常与后现代史学遭受的批判有相同之处。针对历史知识的性质,传统的史家多持“对应论”(Theory of correspondence)的主张,认为史料和史著与过去的史实存有关联,除非有过硬的证据,应该先相信它们具有客观性,并努力从中“发现”(Discover)可信的史实;而后现代学者多持“建构论”(Theory of construction),认为史家无从知晓真实的过去,史家追求知识系统的“连贯性”(Coherence),只是在“建构”(Construction)或“创造”(Create)过去的历史。[7](P.159)“对应论”与“建构论”的针锋相对,也表现在顾颉刚及其批评者的论辩上。如顾颉刚认为《閟宫》说“缵禹之绪”明明是后稷在禹后,它却说是舜的同官。于此,刘掞藜批评顾颉刚不能照顾到全面的史料因而形成错误的解释。他说:“‘缵禹之绪’虽可证明弃的事业在禹后,但不能证明他们两个不同在舜的朝廷作官。因为禹是尽力乎沟洫的,后稷是从事于种植的,禹把沟洫治好了,使后稷得以种植,这种缵绪并不须在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12](P.90)又如胡堇人认为史官世代所传的史料以及出土重器的款识应可相信,“古史里比较稍近事实的地方却也不少,断不能一概抺煞”,如对禹的讨论“战国以前经传和诸子书中说禹的地方很多,实物也有‘峋嵝碑’”[13](P.93),依古籍及实物也可推论“尧舜以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13](P.95)。胡、刘二人相信史料、史著与史实的关联,看法近于“对应论”。
针对刘、胡的指教,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给出推翻信史的四个标准,分别是:(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指出古书中各个种族各有始祖,且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所以过去公认的古史所呈现的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的观点是后来建构的,不可能是古代的史实。而在古史中,古代常是以黄金时代来呈现,这是由于神话人物“人化”结果,故顾颉刚认为:这种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主看样的,庶不可受他们的欺骗”[14](PP.96-102)。由顾颉刚的回应,可以看到他是以古书中具有太多的“建构论”来否定古书所“论述”之古史的真实性。
然而,即使顾颉刚有太多与后现代史学相近的看法,但他因为相信古代“信史”的存在,所以也与后现代史学产生差异。如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他指出胡适的古史大旨“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14](PP.97-99)顾颉刚所谓的“信史”并不是大一统叙述下的“信史”,而是指“未经建构的原初的史料”;相对于“信史”,凡经“建构的历史叙事”,他称为“伪史”,而纪录、宣扬伪史者为“伪书”。因为反对疑古学派的论者大多认为疑古派学者“认为伪书中便不可能有真史料”,认为顾颉刚“始终认定他所做的工作是书的真伪,所以没有跨进一步探究历史的深层问题”[15](P.380),“古史辨实际上就是古书辨”[16]。这些意见似都以为顾颉刚否定古书的历史价值,所以顾颉刚所说的“伪书”是否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就成了必须先予辨明的问题。从顾颉刚的观点看来,他并没有否定“伪书”的研究价值,他认为“我们辨伪比从前人有一个好处:从前人必要拿自己放在一个家派里才敢说话,我们则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尽量发出,别人的长处择善而从,不受家派的节制”[17](P.26),而辨伪的工作也可以看到造伪的原因可能有“‘装架子’,如汉高算做唐尧的子孙,……有的是方士骗皇帝求利禄,如《封禅书》所载。有的是为抢做皇帝而造的符命。有的是学者的随情抑扬。有的是学者的好奇妄造”[18](P.29),由这些看法可知他认为“原初史料”之外,都是“建构的历史叙事”。由“建构的历史叙事”所形成的“历史文本”,不论是具有想象性因果逻辑的“史料的编排”、安置所处语境与意识形态(家法)的“历史故事”,虽然不能将我们带回到“历史的现场”或“历史的客观事件”中,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接触到某一时代或某些人所建构的“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指的是把现在生活中的现象与过去的某些现象连接在一起的心智状态,由于将过去与现在事物关联的方式不同,因而也产生出不同形式的历史意识。胡昌智在《历史知识与历史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一书中引用德国史家余琛(Jrn Rüsen)的观点,将历史意识区分为传统式(Traditional)、例证式(Exemplary)、演化式(Genetic)以及批判式(critical)等四类。“传统式”的历史意识视时间为生活的原始状态不断延续的结果,在此原始状态下,后人不断模仿前人的行为;“例证式”视某些行为规则(如君臣关系)可超越时空而不变;“演化式”认为时间是由各个改变“现状”的行为所组成;“批判式”批判演化式的时间观,认为时间的特性可能表现在新旧交替上,但也可能是忽然中断与突然开始的。这种对各时代历史意识的研究,即是他所说的类似于“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说:“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中编,第60页。的“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 顾颉刚说:“我所以敢于这样做,自有我的坚定的立足点——在客观上真实认识的古史——并不是仅仅要做翻案文章,这是我敢作诚信的自白的。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见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65页。。
从后现代史学的立场而言,“原初史料”也是语言建构下的产物,而“历史叙事”更是多元建构下的一端,所以“信史(原初史料)”与“伪史”都不具真实的意义,这种看法无疑否定了历史研究的意义。顾颉刚承认“伪史”“伪书”是建构性的“历史文本”,但他并不像后现代史学般否定历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辨伪的工作虽然不能让我们接近真实的历史,但分析“历史文本”仍可让我们认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识”,而领略“历史意识”在不同时、地、人皆可能产生不同的变化;而对“信史”的追求,虽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史实,但至少可以追究历史事件的最早状况,达到“近真”的目的。 顾颉刚在谈论古人“直遗”的作品或考古的成果时说:“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决无圆满的解决。”见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下编,第271—272页。因此不论是对古书的辨伪,或是对“信史”的追求,虽然都不能回溯到古代真正的史实,但都能体现史家的“求真”精神。 顾颉刚认为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之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中编,第59页。顾颉刚认为“求真”不能是基于政治或功利的目的,而纯粹是对学问“真实美感”的兴趣与对“真理”的爱好 顾颉刚说:“我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反过来说,我的不信任教师和古代的偶像,也就因为他们的本身不能给我以美感,从真理的爱好上不觉地激发了我的攻击的勇气。”见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98页。,不涉及任何实用上的目的。他说:“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与坏东西”[8](P.83),“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 [8](P.25)从学问追求的真与不真而言,“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19](P.273),在此情况如何能立一件事的真?对此质疑,顾颉刚有“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回应。“不立一真”并不是不去求真,而是反对在不知史料的“流变”下所妄断的“史料之真” 顾颉刚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从前人因为没有这种的眼光,所以一定要在许多传说之中‘别黑白而定一尊’,或者定最早的一个为真,斥种种后起的为伪;或者定最通行的一个为真,斥种种偶见的为伪;或者定人性最充足的一个为真,斥含有神话意味的为伪。这样做去,徒然弄得左右支吾。结果,这件故事割裂了,而所执定的一个却未必是真。”见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下编,第273页。,而其具体的操作是在“存疑”之后,继之以“订疑”,而后“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20](P.410)
四、“重写”的目的与态度
顾颉刚没有放弃信史的追求,在《古史辨》第1册出版后的1929年春,他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了《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由于认为三皇只是传说人物,是“儒家所奉的中心人物,是《尚书》一经中的最大偶像”,所以列了一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顾颉刚对本国史的“重写”,这是基于研究的进展所形成“重新认识”的要求,然而国民政府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而将其列为禁书,理由是在三皇五帝的问题上,“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摇动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换言之,国民政府认为“重写”的目的不在“认识古史”,而在“以古史进行教化”。顾颉刚得知政府禁书的原因后,在“惟恐自己作了民族的罪人”之下,作了这样的反省:“我们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筑在三皇五帝上的吗”[21](PP.45-46),“我们正应当把种种不自然的连络打断,从真诚上来结合”[21](P.47)。顾颉刚的回应显示他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也认为民族的自信力从未建立在对上古的历史成见上。
随着考古的发现与文献的出土,李学勤将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对立起来,似乎认为不“走出疑古”就无法有效开展出土文献研究,也就不能真正改写学术史,所以他在1992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概念,之后陆续有新的著作,如其所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学术史》、其弟子田旭东的《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田旭东在书的后序中说:“李先生当时与我谈,希望我的博士论文以学术史为主,重点总结二十世纪古史研究。” [22]这种“认真的总结”把20世纪古史研究高度简化成“疑古”和“新证”两条线,其中“古史重建”一线以王国维“新证”为始,而以其师所论的“释古”为终。李学勤在2013年的《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一文中,总结说明需要“重写”的原因在于:“‘古史辨’实际上就是古书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古书来了解古史”,“疑古思潮也有着严重的问题和缺陷,由于他们的辨伪工作做过了头,把许多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全部否定了,以致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16](P.2)为了弥补这种空白,李学勤认为必须借助20世纪考古的大发现以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达成“使一些古书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认可”“使一些古籍的属性和成书时代得到大致的确认”“使许多学术著作的价值得到新的、进一步的认识”“对古代时期的学术源流作出新的判断”“重新为战国时期某一诸侯国进行学术史定位”等目的。[16](P.1)
顾颉刚的“重写”是为了“重新认识古史”,而李学勤的“释古”也有“重新认识古史”的意义,如此他的论点为何要由批判古史辨开始?分析其用意,则可知他所谓“重写”的重点,有很大的部分在透过“重新估价古书”与“以考古发现补充古书之不足”来“重新估价古代文明” 李学勤曾指出:“只有摆脱疑古的局限,才能对古代文明作出更好的估价。”见李学勤《清路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此所以在立论上必须先抬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有关“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学者已有很好的反省,如陈淳认为:“如果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那么是否意味着考古材料中只有贵族的观点和活动才有价值,而其中蕴涵的大量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技术、艺术、信仰和平民文化的信息就没有意义?”[23](P.17)陈淳除了指出考古不能作为历史学或文字数据的附庸之外,也看到了“疑古辨伪的意义被人刻意贬低”,并认为贬抑疑古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历史和考古学者主要受传统国学熏陶,受传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很大关系。于是在面对新思维和新理念与传统方法发生冲突或产生质疑时,常常会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立场来加以评判”。[23](PP.22-23)陈淳的批评十分到位,但事实上只要由李学勤所提到的“马王堆帛书的发现得知汉初黄老道家的渊源在楚地,齐地的道家非其主源”以及考古数据可以为楚国在中国学术史上定位,也可以知道古书的可信度不能过度评价,而所谓“主流”与“非主流”也不能从古书与考古发现上来判断。
在李学勤倡议“写重”之后,与其理念相同者有梁涛的《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一文,而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的论点与之相异,曹文除了讨论出土文献的局限及在研究上的可能困惑外,对梁文也有很好的评论。[24]撇开这些论文的细节,如果只针对疑古思潮,梁文虽然强调“走出疑古”,但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许多疑古的论点,如“近些年大量战国古籍的出土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因此,古书形成时间的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不就是否定了“历史文本”与“真实历史”的关系?又,其言“老子的身世扑朔迷离,而其后代的世系却言之凿凿,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这不就是层累说造成的结果?“这里,重视实证,还是相信某种思想的理念、逻辑,不仅会导致不同的写法,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思想史的理解”,这不就承认了任何的思想史解释都是一种“建构”与“论述”?[25]梁文最后在批评何炳棣“《孙》为《老》源”的说法后,提出他对《孙子》与《老子》二书之关联的看法:“《孙》、《老》是一种同源共生关系,而不一定是时间的先后关系。另外,《孙子》是一部兵书,由于要游说君主,所以可能形成较早;《老子》则是一部哲学书,其内容起初只在少数人中流传,所以可能与《论语》一样,也是由老子的弟子、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但大概在战国早期已完成。不知何先生以为然否?”[25]这种反对何炳棣论点的说法,也是依托不同于何炳棣论点的条件所形成的新的建构,如此这两种建构论何者可以说自己的建构可近于“历史事实”呢?梁文在此,虽然以“讨论”以及“寻求同意”的语气做结,但读者从行文上看来,也不能明白他到底是想提出一种新看法,还是以此例子来呈现他在文中所说的“法官客观的身份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裁决”?
上文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重写”。顾颉刚的“重写”是在“疑古”之下“重新认识古史”;而“走出疑古,走向释古”的“重写”则在“以二重证据法裁决古书的真伪,以及古史的事实”,积极肯定被“疑古”否定之“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以进行他们所说的“释古”。由于“走出疑古”希望透过如法庭的终审判决书,使得“疑古”的罪过和“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这也给人“走向释古,建立信古”的疑虑。虽然“走出疑古”的学者澄清“走出疑古之后要以释古代替疑古,但释古完全不是倒退到信古。……相反的,对于传世文献应以更严格审慎的态度进行整理研究。我们不赞成预设的信,也不同意预设的疑,实事求是乃是我们力求达到的准则”[26](P.228),而这也使得“走出”失去了必须刻意标举的意义。故林沄说:“我们根本无须走出疑古时代,而应该在信古时代寿终正寝后,还要继续坚持疑古、释古并重的方针,来重建真实的中国古史。” [27](P.3)从后现代史学的立场而言,“走出疑古”的学者其实也在对“疑古”进行一种有“目的”的“建构”或“论述” 如廖名春指出:“否定尧舜禹,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古史辨学者却替侵略者干到了。”见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陈明主编《原道——文化建设论集》第4辑,第128页。这种对古史辨疑古思潮的批判,已经超出了学理层面,而进入了政治层面。另如前文所引林沄的意见,他也认为“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新意。其实在于‘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具体地说,是要把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为此,才提出所谓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为《五帝德》、《帝系姓》等古籍翻案”。见林沄《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第3页。,基于这种目的,他们也刻意对疑古学者进行“误读”的“重写”,即将“疑古”所强调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解读成一种明确否定古书所述古史之价值的结论,并在这种否定的结论上,进行新的肯定的“重写”。
五、结语
“疑古”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论语·子张》载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而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认为《尚书·武成》可信者只二三策,而武王伐纣“血流漂杵”更不可信 《孟子·尽心下》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可见孔、孟之时也能知道历史的描述有其政治性的建构,而儒家推崇古圣和三代之治的古史观,也不能为先秦诸子所接受。自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而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经典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因此,即使学者有疑古之说,其目的也可能在“圣道王功”,此所以顾颉刚认为他自己的“疑古”能超越儒家意识形态,而有不同于戴震(1724—1777)、崔述(1740—1816)之处。顾颉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掀起的疑古思潮,虽说是基于科学理念的指导,但他对所谓的科学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顾颉刚言:“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所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但是我常常自己疑惑,科学方法是这般简单的吗?只消有几个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处应用的吗?在这种种疑问之下,我总没有作肯定的回答的自信力。”见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94—95页。,因此他的辨伪、疑古只能说是出于一种“理性”的冲动 顾颉刚言:“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见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81页。 。而当他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并且指出民俗戏曲的故事与古史有相同的叙事结构和发展时,实已使得他的论点脱离了科学实证的史观而趋近于后现代的史观。实证的史观所求的是“客观”与“真”,而顾颉刚已经认知到“客观”与“真”的不可能,因此他很清楚地了解所能求的只是“少偏”与“近真”,也认为自己的研究结果不是可遵循的指导,而是可批判的对象。 顾颉刚言:“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但这是研究,不是服从。……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判,千万不要说‘承你考辨得很精细,我有所遵循了’这一类话!”见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81—82页。因此从当代史学史的立场来看顾颉刚的论点,实可以说顾颉刚的观点,让中国史学界比西方更早接受了后现代史观的冲击。
顾颉刚虽然没有建立任何的史学理论,但凭借着他对史料的独特看法,使得传统史学遭受到颠覆的梦魇。因此,即使他的研究方法引领了人们走出传统古史观的泥淖,但仍然使得传统史学家为之惊骇,故往往在哄传之下,抨击其论文的结论。如郭沫若一开始也曾对顾颉刚加以讥笑,而后才承认他道破了旧史料中的作伪之点。 郭沬若曾说:“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郭沫若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4—305页。然而,即使有许多讥笑与反驳,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 1884—1975)在读完顾颉刚《古史辨》的自序后,认为这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的记载”[28](P.335),将它译成英文在美国最重要的史学刊物《美国历史学报》(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引起当时西方的注意与震惊。顾颉刚在研究方法、视野、态度等方面的突破,打破了中国现代史学追随西方史学未能建立“自主性”的窘境。他挑战追求绝对历史真相的看法,不但早于西方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更早于20世纪70年代涌现的后现代风潮,这使得中国的研究者比西方史学界更早关注到连贯性的历史解释可能不是真正的史实,而其影响也扩及国外的学者,如宫崎巿定(1901—1995)的中国史研究明显受其影响。[29](P.95)
古史辨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了当代史学的重要内容,但在20世纪末,“走出疑古”的学者又掀起了对他们的批判,这种批判除了是基于建立民族史观的需要外,也与传统史学在意识上反对后现代史学的思潮有关。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诸如“文献不全真,亦非尽伪”“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岂能事事造伪”“文士哲人风采,宁为虚构?”“后现代主义最低限度将摧毁历史,甚至整个历史事业为之荡然以尽”是“历史虚无主义”及“盲目的怀疑论”等[30](PP.1-5),这些论点也都可以直接用来批判疑古派的说法。然而顾颉刚并不是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一个史学研究者,所以他的论点断然不会有摧毁历史及历史事业(Historical enterprise)或者认为“伪书”“伪史”不具有历史研究之价值的可能,因此批判他们以辨别真伪来否定古书,实是言过其实。疑古学派的学者既然不否定伪史、伪书的历史价值,在积累研究成果之后对过去的研究进行改写就有其必要,但改写的目的不应该再回到真伪与确定编年之上。以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史记·老子列传》罗列了老子生存时代的各种传说,并指出对《老子》文本可以有庄子、韩非截然不同的“论述”(Discourse),这已表明古代即使没有顾颉刚的层累说,没有后现代史学的理论,他们仍然知道要建立“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或客观的史实并不容易,因此若有人觉得利用考古的成果可以确认哪一条线索具有真实性,这无异于忽略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文物、文献的保存在不同的目的下所可能产生的诠释差异。
“走出疑古”的学者对“疑古”的第二次反思,虽然直接批判的是顾颉刚的研究方法,但也可以看成是传统史家对后现代史学的反弹,这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经过不同的论辩后,我们不但可以明确定位顾颉刚在史学上的贡献,也可以理解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并不是毁灭性的,而是建设性的。由于古代信息的流通较慢,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各种信息也不是处于公开透明的状态,所以人们对古书的权威性有较高的接受度。但在今日,借由数据及媒体的流通,我们可以快速地接收到信息,也能快速地看到同一“历史事件”(Historical accident)的诠释有不同的权力、文化群体及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且,当广播、电台被互联网取代之后,网络中接收或传输消息的各个节点(Node),虽然可以对媒体的信息有“不服从”的表现,但权威的统治者仍然可以透过不同的流量限制与流量操作来达成对信息解释的影响。由今观古,应该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古代的社会及古史、古书的内容,也可能隐藏着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经济文化群体的交涉和重塑。在此情况下,就可意会顾颉刚的层累说不但早一步地将中国的史学带入了当代的研究趋势,也让传统的史学家借之反思而可顺接后现代史观所引发的启示。
所谓“后现代”,并不是指“现代”已然结束后才兴起的一个思潮或文化现象。就当代的社会而言,无论是先进的国家或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仍然在追寻社会的现代化,因此“后现代”也可以视为是现代的延续。换言之,如果说现代的特性在于“理性化”,“后现代”即是对“现代”所后设的大理论、大叙述再度进行“理性化”的质疑与批判。这意谓“后现代”是对现代的本质、现代之所以为现代的“现代性”(Modernity)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在这种批判、质疑和否定之下,希望能形成一个新的展望,因此它也可以是一种“策略性” 的说法。 沈清松认为:“后现代这个观念一定要跟现代的观念连起来思考,它才有意义。如果单独的思考它,它就变成孤立的一个现象,在这孤立的情境下去谈后现代文学与艺术,可能就无法真正的了解其中内在的一种紧张关系”,“后现代离不开现代,而是根据与现代的关系来接受定义。换言之,这其中它一方面包含了对现代的延续;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对现代进行质疑、批判,甚至否定。”见沈清松《从现代到后现代》,《哲学杂志》,台北:哲学杂志社,1993年第4期,第4—25页。 古史辨的学术也是由“疑古”来进行否定的“策略”,因而其实质的内涵并不在于“辨伪”,而在于以理性去批判传统的史学系统,并以此探索新的史学体系。若我们能透视顾颉刚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所具有的策略与精神,就能更好地继承传统史学的遗产,展开对历史的重新考察。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
[2]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全集》第16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4] 王晴佳:《简论朗克与朗克史学》,《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孟真先生集(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
[6]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第2册,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
[7]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
[8] 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9]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11] 顾颉刚:《启示三则》,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中编,北京:朴社,1926年。
[12]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中编,北京:朴社,1926年。
[13]"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中编,北京:朴社,1926年。
[14]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中编,北京:朴社,1926年。
[15] 沈颂金:《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6] 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
[17] 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编,北京:朴社,1926年。
[18] 顾颉刚:《论伪史例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编,北京:朴社,1926年。
[19]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下编,北京:朴社,1926年。
[20]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21] 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中编,上海:上海书店,1937年。
[22] 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23] 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第6期。
[24] 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
[25] 梁涛:《疑古、释古与重写思想史》,《二十一世纪》,2005年2月号。
[26] 李学勤:《清路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
[27] 林沄:《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28]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2册下编,北京:朴社,1930年。
[29] 车行健、卢启聪整理:《顾颉刚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先生的疑经、辨史与采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21年第4期。
[30] 杜维运:《后现代主义的吊诡》,《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1期。
Gu Jiegang's "“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TSAI Chen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106319, China)
Abstract: After Gu Jiegang proposed the "“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 "in 1923, it caused two criticisms in the historical community. These two criticisms often regarded Gu Jiegang as a representative of "“ scientism ” "and "“ positivism ” . However, this paper compares Gu Jiegangs "“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 "with the views of postmodern historian Hayden White, and believes that the theories of the two have similarities. Therefore, the "“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 "is questioned by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nd often has the same criticisms as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Although Gu Jiegang has many views similar to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he believes that the history constructed in each era can reflect the "“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 "of that era, and from this, a "“ near-true ” "history can be established. It can be seen that Gu Jiegangs views are more able to maintain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than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it can be seen that Gu Jiegangs views are earlier than those of Western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which not only shows the autonomy of Chinese historical views, but also earlier bring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to contemporary research trends.As a result, the "“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 "not only allows the Chinese historical community to accept the impact of postmodern historical views earlier than the West, but also allows traditional historians to accept the enlightenment brought by postmodern historical views.
Key words: Gu Jiegang; Layered Fabrication Theory; School of Doubting Antiquity;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Hayden White
(责任编辑:蒋金珅)
作者简介:蔡振丰,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魏晋玄学、魏晋佛学、中国哲学史、东亚儒学研究。
①对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定义,顾颉刚自言有“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三个意思。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中编,北京:朴社,1926年,第60页。
②如童书业有《“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有《“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二人的意见可见于《文史哲》,195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