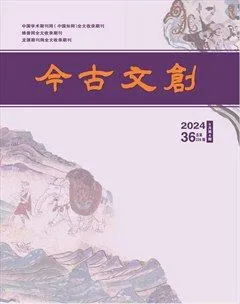侠之西行: 论侠客形象在郝译本《射雕英雄传》中的英雄化
【摘要】金庸武侠小说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传承与创新,在承袭传统武侠小说描写侠客惩奸除恶、施行仁义形象的同时,摒弃了一些消极因素,赋予其现代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庸武侠小说开始被译成英语、德语、日语、马来语等多种语言,传播至海外。以郝玉青译本《射雕英雄传》为例,虽然受到较多读者关注,在销量上有着不错的成绩,但译作中,侠客形象被泛化为英雄,丢失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究其原因,是侠形象在译介过程中并未被建构且被曲解,这在今后的武侠小说翻译过程中也值得注意。因此,在武侠小说译介过程中,不可让侠英雄化,而是需要建构独立的侠客形象,强化作品文化身份,使目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对侠客群体的独立概念。
【关键词】侠;英雄;《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10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3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英国学者郝玉青所翻译的《射雕英雄传》(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在英国市场获得较大反响。此外,西班牙、德国等国家也相继购买版权,目前,西班牙已推出由英文转译的西班牙文版本。从销量维度来看,《射雕英雄传》译介效果良好。但该译本存在不少误译,如“侠”的误译——郝玉青将“侠”这一概念翻译为“hero”,将二者等同。这在读者理解侠客形象与作品主旨精神的过程中会造成极大影响。被误译的侠义精神对原作及其彰显的侠文化的海外传播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本文将以英国译者郝玉青(Anna Holmwood)所译的新修版《射雕英雄传》中对侠客形象的翻译为例,对这一误译现象进行反思:译者为何在翻译过程中采取这种处理方式?“侠”的基本意涵是什么?在金庸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与“hero”的区别又有哪些,二者为何不能等同?下文将对侠之意涵及其在金庸作品中的呈现进行梳理,试析“侠”与“hero”两个概念的区别,以期在今后的译介过程中建构合理的侠客形象。
二、侠之意涵与金庸之侠
(一)原侠与武侠小说
侠这一群体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蠹》最早对侠进行评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对破坏法禁的侠深恶痛绝,将其划入国家蠹虫行列。而司马迁在其《史记·游侠列传》中从精神气质的角度,赞赏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品质。后世对侠的评价也大都承接二人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侠出于墨,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为陈澧,而鲁迅、闻一多等人也持同样态度。在此,本文采用王蔚丹、汪聚应的观点,对“侠出于墨”一观点进行驳斥。盖二者在行事目的、对私斗态度和组织纪律方面都大有不同,仅从表面相似的气质妄下论断不甚可取。汪聚应提出,侠起源于刺客,在由刺客向侠的过渡中,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其服务于权贵的依附性大大减弱,由“失位”进一步演变为民众的英雄,加之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侠。
侠客群体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而以其为底本的武侠小说也成为通俗小说中备受重视的一个流派。侠的形象也在武侠小说中得到进一步的理想化。武侠小说这一流派从古至今经历从“中国古代武侠小说”到“中国旧派武侠小说”再到“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演变。古代武侠小说中以歌颂侠客义士惩奸除恶、扶弱扬善、打富济贫、施仁行义等行为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大多数作品局限于忠君报国,斩奸除恶的固定程式。步入近代,受社会变革以及思潮的影响,侠形象糅合了各种思想理念,这在新旧派武侠小说中均有体现。
根据林保淳的研究,“旧派”源自民国初年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的说法,内容以通俗为主,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为代表人物,这一派的杰出作品有《蜀山剑侠传》《江湖奇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新派武侠小说则以梁羽生为开端,此外,还有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也为该派贡献大量经典作品,其中,当属金庸的作品最受欢迎。
相较于旧派武侠小说,新派在主题思想、人物刻画、情节结构、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旧派小说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难以放开手脚,而新派小说在这一方面则相对多元而自由。不少作品还对武侠小说惯有的复仇模式进行了批判。人物刻画方面,新派作家们也显得更为细腻。此外,在故事节奏上,新派小说也更加紧凑明快。在写作技巧方面,新派小说也有诸多创新之处。而这些革新之处,也构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现代性。在“侠”、武侠之“武”、侠客之“情”的刻画上,新派武侠小说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的模式,赋以了更为立体更为现代的定义。社会环境的变化,又使得新派武侠小说作者们进行反思,塑造非传统意义的侠客形象,对侠文化作新的诠释,完成从“武侠”到“反武侠”的蜕变,这在以金庸等人作品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金庸武侠小说之现代性
金庸武侠小说继承了悠久的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并以其作为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陈平原指出,金庸值得格外关注,主要不在于文化知识的丰富,而是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其贡献在于其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与“古今”。王一川认为,金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他的作品以通俗的手法表现出极深的意义,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体现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另一方面,金氏武侠又体现着反文化思想,渗透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重新认识。根据吕进等人的观点,金庸武侠小说经历了一个自然的“反武侠”发展过程,反映其对包括武侠人物身份和武侠小说主题的认识的渐变。“反武侠”的实质,既包含他对自我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也包含基于变革的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这在其中后期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如《笑傲江湖》中构建的尔虞我诈的江湖,反映出欲望使得侠义精神堕落,透露着金庸对武侠文化的深刻反省;再如《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的“反侠”和八面玲珑的形象成为对传统侠义信条的否定,也是对传统武侠小说规范的否定。
(三)金庸武侠小说之译介
从《射雕英雄传》到《鹿鼎记》,金庸对侠义精神的思考逐渐加深,从“赞侠”到“反武侠”,完成对侠义精神的现代性诠释。也正因此,承载现代意义的金氏武侠在海外也得到一定传播。然而,因其文化异质性,目前,金氏作品主要在中华文化圈得到广泛传播。
20世纪70年代起,金庸武侠小说便先后被译为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韩文、日文等文字,在亚洲地区广泛传播;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金庸武侠小说才开始在西方世界传播,被译为英、法、德文等。以英译本为例,目前,仅有《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鹿鼎记》被译成英文,且从销量角度而言,除郝玉青版《射雕英雄传》外,其余三部作品的译本在英语市场的接受程度一般。此外,郝玉青版《射雕英雄传》存在不少误译和删改现象,对原作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存在一定的误解与歪曲,对作品精神的传达反而起到阻碍作用。郝玉青译本中最严重的误译当属“侠”与“英雄”的混同,下文将以第一卷第二回中登场的江南七怪为例重点讨论,因为自此章始,作为该作品灵魂人物郭靖的七位启蒙导师、全书最为典型的侠客群体——江南七怪正式登场。而主人公郭靖所继承的侠义精神也自此章始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
三、侠的缺位与七怪之失侠
(一)侠与英雄之辩
郝玉青在其译作卷首部分对作品中登场的主要人物进行简介,并根据江湖门派或者势力将人物分类。江南七怪作为第一卷中较为重要的人物,自然也在其列。“江南七怪”这一称呼是七位侠客对自己的称呼,在《射雕英雄传》所描写的江湖中,人们称其为“江南七侠”,以示对七位侠义之士的敬畏。郝玉青将“江南七怪”这一称呼译为“Seven Freaks of the South”,考虑到七位侠客自谦的因素。但对于“江南”与“怪”字的翻译尚有欠缺,此处按下不表。更值得关注的是,郝玉青在翻译江湖人对七怪的敬称“江南七侠”时,将其译为“Seven Heros of the South”,将“侠”与“英雄”两个概念混同。
“英雄”二字可以释为才能勇武过人的人①,而在当代语境中,多指无私忘我,不辞艰险,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令人敬佩的人。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古代之侠起源于刺客,一度游离在社会边缘,是政客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得力工具,并在脱离权贵后经过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才逐渐成熟。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侠客“嫉恶如仇”“惩恶扬善”“豪爽夭矫”等品格,另一方面也具备了“道义模式”以外的武术本领。从精神品质来看,二者存在共通之处。以《射雕英雄传》主人公郭靖为例,尽管该书故事背景设定在南宋,但金庸在作品中引入颇具现代性的观念:生在江南、长在草原的主人公郭靖,已对民族矛盾有了自己的见解,不秉信“汉夷有别”,而持着“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他自然当得“大侠”之称,也当得“英雄”之号。
但所有侠客都当得“英雄”二字吗?《射雕英雄传》中有着“东邪”之称的黄药师便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侠客,也难以与“英雄”画上等号。尽管同全真教等所谓“正派人士”一样参与抗金,但他唾弃腐儒传统,且行事古怪多变。在得闻弟子陈玄风、梅超风二人偷盗《九阴真经》“叛出师门”后,迁怒于其他弟子。但与弟子重逢之际又授其旧伤医治之法,让一众弟子重归师门。这些行为不仅叛离传统意义上的侠道,也与英雄所为相去甚远。
侠与英雄,二者尽管有着交集,但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侠客代指一个社会群体,在金氏小说中,勇武过人,富有“任侠”精神的人士皆可划为此列。但要成为英雄,仅有见义勇为的气质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而武艺超群的特征也可在此时被剔除。侠义精神的彰显,往往伴随着“复仇”等流血行为,而成为英雄却不需要这一条件。英雄之于侠,恰如侠之于武人,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对其道德品质的褒扬。因此,侠可以成为英雄,但英雄不一定是侠。
(二)侠客、骑士、义警与七怪的失侠
在郝玉青译本中,凡是作品中被称为“侠”的角色,都被冠以“英雄”(hero)之称。英文中,“hero”一词指“a person who is admired for having done something very brave or having achieved something great”,即因做非常勇敢的事情或取得伟大成就而受到钦佩的人,其意与前文所指出的汉语中的“英雄”二字,在一般语境中可视作同义词,但仍然不能用以代指“侠”。
一般意义上的侠,即“武侠”,尤其是金氏《射雕英雄传》中所刻画的侠客,其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过人的武艺。而成为英雄并不需要这一点,这在英文语境中也是相同的。英文中的“knight”(骑士)形象常被用来与“侠”做对比,武侠小说也常被译为“Chivalry novels”,但二者在身份与精神内核等方面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武侠文化与西方骑士文化根植于两种文化土壤,有同质性的一面,也有不同之处。侠客群体源于刺客,起初是政客们实现政治目的的得力工具。而西方骑士则出身行伍,是保卫国家、开疆拓土的坚实后盾。随着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演化,骑士从战场中退出,成为效忠国王与教廷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阶级观念、宗教信仰驱使骑士伸张正义、除暴安良。骑士在社会中处于中上层,其所彰显的骑士精神也是贵族文化的代表。
从身份地位与内在动力来看,欧美超级英雄题材漫画中塑造的“义警”(vigilante)似乎更加贴合东方的侠客形象。欧美超英漫画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探讨了当时欧美社会备受关注的许多主题,如道德(ethics)、正义(justice)、犯罪(crime)和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超级英雄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特殊能力或先进的武器装备,还在于他们面对背叛、混乱和破坏性暴力时的大无畏精神。他们追求正义,捍卫手无寸铁的人,帮助那些无法自助之人,用正义力量战胜邪恶。超级英雄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法律合法性的“拷问”(interrogation)。超级英雄坚持不懈的义警精神是对正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基于当代大众对复仇文化的想象。这也与武侠小说中塑造的侠客形象不谋而合。或许是原作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缘故,以“vigilante”这一颇具现代色彩的词指代侠客群体不免会使读者感到割裂感,郝玉青在其译本中最终采用“hero”一词翻译“侠”。
然而,“hero”一词在指代上更具包容性,无法确指侠客群体。《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在听到丘处机称其为“江南七侠”时,连连自嘲:“都是怪物而已,‘七侠’甚么的,却不敢当”。“七怪”对“侠”字的敬重,正如侠客群体对“英雄”称号的敬重。英雄意味着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而流连闾巷、“不拘小节”的游侠们在面对“英雄”二字也得谨慎起来。无论是身份特质相仿的“knight”与“vigilante”,还是在核心价值观有相通之处的“hero”,似乎都不能与侠客气质完全吻合。
故此,在翻译过程中,“侠”绝不可被简单译为“knight”“vigilante”或者“hero”。西方文化中,本无“侠”的概念,因此,在武侠小说的译介过程中,必须建构“侠”形象,而不是将其归化,与“英雄”混为一谈。采取异化音译“侠”(Xia)
的方法,或许是建构“侠”形象的一个方向。邓高胜、叶小宝在其研究中指出,尽管起步晚、影响小,一些学者也在提倡以“Xia”异化音译“侠”。斯蒂芬·陶(Stephen Teo)也表示,不使用英语单词替代“侠”,而把“侠”的拼音当作一个新词,将“侠”从西方骑士印象中独立出来,虽然这种译法不方便英语读者理解,但是经过起初的解释和一段时间的使用后,会逐渐被认可与接受,并以新渡户稻造翻译“武士道”(bushido)成功进入英文语境的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综上,通过“侠”的汉语拼音构建独立的侠客形象并辅之以必要的解释与对比,是武侠小说译介过程中对侠文化进行正确诠释的可行之策。以此方法,既能强化作品的文化身份,也能使目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对侠客群体的独立概念。
四、结语
侠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在其演进过程中,不断地适应社会历史的变化,彰显其现代性。而刻画侠客形象的武侠小说便是侠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译介在传播侠文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侠”这一概念以及侠客形象的翻译在译介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尽管存在可以类比的形象,但侠客形象在翻译过程中应被单独建构,而不是成为“英雄”的代名词,流失其文化内涵。由“Hero”到“Xia”,尽管建构的道路漫长,但正如其译介本身,是一场艰难却甘之如饴的西行。
注释:
①见《汉书·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行宽仁之厚,总擥英雄,以诛秦、项。”
参考文献:
[1]Lorén G.El mejor libro de fantasy y ficción histórica de todos los tiempos según la revista Time,ambientada en la China del siglo XII.[EB/OL].https://laslecturasdeguillermo.wordpress.com/2021/09/01/el-nacimiento-de-un-heroe-leyendas-de-los-heroes-condor-1-de-jin-yong-seudonimo,2021-09-01.
[2]刘毅.《射雕英雄传》在西方的译介传播:行动者网络、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4(02):58-65+159-160.
[3]Holmwood A.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A Hero Born[M].MacLehose Press,2018:67.
[4]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709.
[5]韩兆琦译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7347.
[6]陈澧.东塾读书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23.
[7]鲁迅.鲁迅杂文精选[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15-116.
[8]郭沫若,朱自清,叶圣陶编.闻一多全集[M].上海:开明书店,1948:19.
[9]王慰丹.“侠出于墨”说辨[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05):173-174.
[10]汪聚应.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7(02):42-48.
[11]林保淳.武侠小说的旧派与新派[J].关东学刊,2019,33(03):98-123.
[12]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J].当代作家评论,1998,(05):25-31.
[13]王一川.重排大师座次[J].读书,1994,(02).
[14]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先生获北大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词[J].通俗文学评论,1997,(01).
[15]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J].文艺研究,2002,(02):65-73.
[16]罗永洲.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J].中国翻译,2011,32(03):51-55.
[17]叶铖铖,邓高胜.《射雕英雄传》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J].外国语言与文化,2019,3(01):115-124.
[18]金庸.射雕英雄传[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48-50.
[1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0]姜斐斐,高艳.西方骑士和中国侠的多元化解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3):324-327.
[21]Meade B,Castle T.“It’s What I Do that Defines Me” :Real Life Superheroes,Identity,and Vigilantism[J].Deviant Behavior,2022,43:9,1088-1102.
[22]金庸.射雕英雄传[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48-50.
[23]邓高胜,叶小宝.中国文化词“侠”之英译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0,31(03):117-126+160.
[24]Teo S.Chinese Martial Arts Cinema:The Wuxia Tradition[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2009.
[25](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26]郝世英.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考察[J].嘉兴学院学报,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