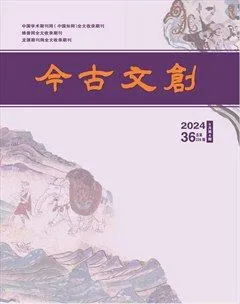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喜剧理论探析
【摘要】亚里士多德所提及俄瑞斯忒斯故事的喜剧版本反映出亚氏将思维惯性的打破作为喜剧性生成的基点。喜剧快感的生成则与求知的满足与观众在观看时暂时性的替代性满足相关。对喜剧性和喜剧快感的思考与亚氏本身的政治伦理思考密切相关,即强调行动力之重要性、塑造更好的公民个人素质。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喜剧;喜剧性;喜剧快感;政治伦理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8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25
在国内学界中,对亚里士多德喜剧理论专门研究数量较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对喜剧的论述之中假设了俄瑞斯忒斯的喜剧版本,这一点几乎被现有研究忽视,但该例子能够很好地对亚氏所思考的喜剧性和喜剧快感的生成论述作出补充。本文从喜剧性和喜剧快感的生成为切入点,以《诗学》为主要文本,同时结合亚氏的其他著作,对其喜剧理论进行分析,并借此指出其喜剧理论背后的伦理政治思考。
一、喜剧性
喜剧性的生成是喜剧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有学者将亚里士多德喜剧理论中喜剧性归纳成“高阶论”,即观众对摹仿对象居高临下的轻蔑而产生的快感,如石可“高阶论,或者说优越论,是最古老的说法,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些低于或者劣于我们的人或事会让我们发笑。这实质上是认为,喜剧性本质上是轻蔑的一种形式:前现代时期社会成员的‘尊严’即建立在等级社会中社会地位的比较上”[1]3-7。有学者则认为喜剧性是由滑稽动作而产生的,如陈中梅认为“喜剧的目的在于通过滑稽的表演和情景逗人发笑”[2]59。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所论的喜剧性生成不指向动作的夸张和变形。亚氏指出“一种通过表演来表现一切的摹仿是粗俗的。演员们以为不加些自己的噱头观众就欣赏不了,因此在表演时用了很多的动作”[2]190。由此可见,滑稽动作所产生的喜剧性非亚里士多德所赞同。
在论述喜剧时,亚氏以俄瑞斯忒斯为例进行分析“在喜剧中,传说中势不两立的仇敌,例如俄瑞斯忒斯和埃吉索斯,到剧终时成了朋友,一起退出,谁也没有杀害谁”[2]98。从中,能够分析出亚氏的思考所在:喜剧性的形成并非是观众与摹仿对象之间由于地位优劣对比而产生的轻蔑感,而是由思考惯性打破而生发出。悲剧版本中的俄瑞斯忒斯遵照阿波罗的神谕,杀死篡夺王位的埃吉索斯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完成复仇。俄瑞斯忒斯的悲剧性体现在他身上两种伦理的冲突。作为阿伽门农之子为父报仇具有正义性,但报仇要以牺牲母亲的生命为代价,弑母行为不具有正义性,因而俄瑞斯忒斯感到矛盾和痛苦。但杀死埃吉索斯则完全合乎其作为在家庭伦理层面上的儿子与作为国家伦理层面上的统帅之子身份的正义性。俄瑞斯忒斯遭遇了父亲被杀、王位被夺、母亲嫁给仇人的巨大耻辱。从情节上看,按照观众的思维惯性,俄瑞斯忒斯将完成最基本的复仇。但在亚氏所设想的喜剧场景中,俄瑞斯忒斯却选择与埃吉索斯和解,这使得观众思维集中之处被陡然打破,紧张感被解除。而从人物本身看,这个例子还暗指喜剧性来源喜剧人物自身“大”与“小”的不协调,即表面和实质的差异。里普斯指出“喜剧性乃是惊人的小……就是这样一种小,即装成大,吹成大,扮演大的角色;另一方面却仍然显得是一种小,一种相对无,或者化为乌有”[3]1256。俄瑞斯忒斯出身高贵,却并没有与其身份所适配的行动力,高贵的外壳之下实际埋藏着一个弱小的灵魂,使其最终做出和解的选择,与敌人成为朋友。观众对俄瑞斯忒斯的行动期待落空。从这双重思维惯性之打破中,喜剧性生成。而打破惯性要求创作者制造情节,激发观众理性。
亚氏认为荷马是第一位为喜剧勾勒出轮廓的诗人,他“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滑稽可笑的事物”[2]48。“戏剧化”意为“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2]163。亚氏更倾向通过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喜剧性。在对喜剧语言的论述中,亚氏认为喜剧语言的使用需要考虑的不应只是“笑”结果的生成,还需要考虑玩笑的“适度性”。他对比了现在和过去两种喜剧的不同“过去的喜剧用粗俗的语言取乐,现在的喜剧则是用有智慧的语言引人发笑,这两者在礼貌上有很大的区别”[4]124,并对现在的喜剧做出了肯定。依靠粗鄙的语言和夸张的动作所产生的笑是一次性的,满足的是人“无理性的欲念”,即未经思考而发生的欲念,此时人成为生理性快乐欲望的奴隶。而通过情节编制方式展示出来的喜剧性,亦需要观众借助理性进行思考和推理。因此,亚氏所思考的喜剧性生成与理性相关。
二、喜剧快感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能够“通过摹仿获得最初的知识”[2]48,并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这是他不抵制诗的原因之一。通过观看喜剧,观众获得知识并产生求知的快感。而“求知和好奇,一般来说,是使人愉快的;好奇意味着求知的欲念,因此好奇的对象就成了欲念的对象;求知意味着使人恢复自然状态”[5]180-181。自然状态“就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6]56,亦是亚氏所推崇之状态。借由喜剧,公民能够达到自然状态,恢复到本真的境地。
除求知快感外,喜剧快感与悲剧快感一样与卡塔西斯相关。《喜剧论纲》指出喜剧“借引起快感与笑来宣泄这些情感”[5]391。与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卡塔西斯)”[2]63不同,喜剧通过“宣泄”来消除紧张,达到情绪的平衡。亚里士多德认为“快感的反面是苦恼”[5]178。借助“笑”,观众能够得到情感的释放。旧喜剧中有“插曲”,歌队长常于插曲中代表诗人发表政治见解,所攻击的主要对象为政治权势人物或社会著名人士。而亚里士多德所处的中期喜剧时期是雅典遭受外敌压迫和内部动乱时期,人民无法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对政治缺乏关心,导致喜剧较少指涉政治,更多地选用市民生活为内容。因此,在此时期,公民处于动乱之中,面对自身困境,行动力也处于一个较小的时候,喜剧诗人则借助喜剧给经受苦难的人民坚持的勇气。
俄瑞斯忒斯选择放弃复仇,逃避了伦理规则的要求。利普斯认为愉悦感是由移情产生的,“这种联想、类比的方式为的是更好地理解对象,除了使我们回想起自己所经历的过程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回想起自己发出同样动作时的意象,以及伴随这种动作的情感体验”[7]374。观看者在观看喜剧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虚拟代入,将“我”放置到喜剧摹拟对象的身上。在现实生存世界,受到多种伦理责任的制约,人常常陷于左右为难的困局之中。脱离伦理道德思考的行为选择,恰恰是观众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实现的,而喜剧中低行动力的呈现,让观众产生了替代性满足的快感,并借由此释放了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焦虑。
除此之外,重大事情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化解,这种“化解”使得观众产生了轻松的快感。亚里士多德提到:“滑稽的事物,或包含谬误,或其貌不扬,但不会给人造成痛苦或带来伤害。现成的例子是喜剧演员的面具,它虽然又丑又怪,却不会让人看了感到痛苦”[2]58。换言之,喜剧式的快感不包含痛感,这与悲剧所引发的“恐惧和怜悯”不同。相比起悲剧,喜剧的快感是一种轻松的快感。如喜剧版本的俄瑞斯忒斯没有复仇,巨大的矛盾以简单的方式进行化解。
喜剧之快感生成还体现在大团圆之结局引发的替代性满足上。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结构时提到,好人和坏人分别受到赏惩的结构“这不是悲剧所提供的快感——此种快感更像是喜剧式的”[2]98。悲剧所呈现的人的有限性,不免让人怀疑对抗的意义所在。而好人和坏人分别受到奖惩的“大团圆式”结局的呈现,让人相信善良与正义能够最终获得胜利。科普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对喜剧快感的生成机制提出的“义愤”说中也同样提到喜剧快感有“在看到恶人遭到应有惩罚后产生的愉悦”[8]113。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一直实现,但喜剧的表演使得观众产生了替代性满足的快感。
三、喜剧的伦理政治指涉性
亚里士多德并不排斥喜剧,他认为:“快乐是灵魂的习惯”[3]23。亚氏提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3]3。“衡量政治和诗的优劣,标准不一样”[2]177,虽常被视为亚里士多德区隔艺术和政治伦理思考的证据,但将《诗学》作为完全脱离伦理道德思考的艺术创作指南的观点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古希腊以戏剧为媒介进行社会教化,公民在观看戏剧中培养基本的文化素质,反过来亦为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做准备。“模仿有这样点石成金的神奇力量,而且它的感染力对于知书达理的精英阶层和认知能力相当有限的大众阶层一并有效,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不失为哲学认知局限的一种补充。”[9]128喜剧作为戏剧技艺的一部分,必然逃不脱对“善”的思考。亚氏对产生快乐的喜剧之讨论也必然包含着伦理政治的思考。
前文提到喜剧性的生成,亚里士多德强调的并非是“动作”,而是注重情节的编制,情节又是对行动的摹仿。陈明珠关注到《诗学》第三章中多里斯人对喜剧发明权的宣称“他们把ποιεῖν[做、制作]称为δρᾶν[做],而雅典人却称之为πράττειν[做,行动]”,从词义上看,“δρᾶν(做动作)意义上的行动则只强调做,不强调做什么、为什么做”[10]121。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此不置可否,甚至暗含反讽。陈明珠借助玛高琉斯的注解,认为在《诗学》“通过众摹仿者作为所有行动者(πράττοντας)即事功活动者(ἐνεργοῦντας)”(1448a23-a24)这句话提示了ἐνεργοῦντας一词作为πράττοντας的同位语中意义的等同,而ἐνεργοῦντας是ἐνέργεια的同源词,ἐνέργεια的名词形式正是πρᾶξις,该词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伦理学语境中十分关键的术语,即“行动”。[11]218由此可看出《诗学》语境中的“行动”,实际上也指向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意义上的“行动”,即伦理德性的实践活动。陈明珠指出,喜剧摹仿的对象“卑俗低劣者”指向的是道德德性意义上的低劣,她引用玛高琉斯对亚氏的德性作出定义“城邦最微贱的成员也有其要去履行的职责,而德性正是使其得以好好履行其职责的那种东西”[11]217。喜剧人物存在具有其必要性“没有可笑的事物,严肃的事物就不可理解”[12]282。在观看喜剧的过程中,普通公民能够对自身的德性实践产生思考。
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比讽刺诗更高级,其原因是喜剧所能表现的普遍性“在喜剧里,这一点已清晰可见:诗人先按可然的原则编制情节,然后任意给人物起些名字,而不再像讽刺诗人那样写具体的个人”[2]81。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是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反思。讽刺、辱骂,更多地指向具体的人和事,在面对更为具体的人和事面前,观众作为旁观者容易产生“旁观者”心态,将辱骂和讽刺归纳到私人领域。喜剧所展示的这种非具体,能够摆脱对具体个体的道德批判,敞开到对集体伦理层面的思考。而“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13]8。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至高的善不在于拥有善的状态,而在于实现行动,具体的行动是人之性格的外显,也反过来促进性格的形成。喜剧呈现了最低行动力的可能性,观众通过“笑”这一否定性姿态对行动力不足和不勇敢的人进行否定。在对行动力不足的人的否定之中,人们认识到行动的重要性,从而实现德性认知与德性实践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必须把伴随着活动的快乐与痛苦看作是品质的表征”[13]39。当公民在观看喜剧时,伴随着观看行为的快乐同样是公民品质的表征,与公民德性相关。戈尔德希尔指出雅典及其民主制度依赖表演。雅典公民通过观看戏剧这一公民行为来进行“自我提升”。表演这一公民实践促进了民主的公共对话,促进了“民主的政治性主体”的构建。同时,公民身份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了个人主体性的形成。文森特·法伦格认为,“雅典人以表演性的方式维系着其民主性的公民身份”[14]4,甚至“雅典的公民身份也可以视为一种表演”[14]4。个人参与公共活动表现自己的公民身份,而共同的政治生活能够“使人好的、出色的生活实现活动同一般的活动通过某种共同的评价显示出实质的差别”[15]15。由于广场场域的特殊性,“笑”更容易传染。在观看中,公民为保持自身与周围公民的一致性,即使个人对喜剧无感,也容易表演出与周围一致的反应。在观看喜剧表演中,个体进行自我认知的教育和塑造。喜剧借由“笑”也强化了亚氏所重视的公民教育。通过喜剧,公民能够看到普遍性的缺陷所在,能够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在行动中促进城邦政治的完善,最终实现至善的“优良生活”。
亚里士多德喜剧理论背后指向其伦理政治的思考,暗藏了他的伦理政治的关切。观众在公共场域中,通过“笑”对行动力不足者进行否定,又从喜剧所展示的普遍性看到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当今许多喜剧中,存在着许多依靠粗鄙的语言和夸张的动作进行逗笑的情况,只让观众停留在生理性的“笑”之上,其实是另外一种悲剧。重返数千年前的现场,思考亚里士多德喜剧理论及其背后的伦理政治性思考,对当代喜剧创作亦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石可.喜剧的伦理边界[J].电影艺术,2017,(02).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3[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6]徐开来.亚里士多德论“自然” [J].社会科学研究,2001,(04).
[7]刘小枫选编.德语美学文选·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林琴.“义愤”与“蔑视”——论本·琼森的喜剧快感观[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6(02).
[9]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思想史·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陈明珠.“动作”还是“行动” ?——亚里士多德《诗术》的“戏剧性”论述[J].艺术学研究,2022,(04).
[11]陈明珠.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的伦理政治意涵[J].浙江学刊,2020,(04).
[12](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4](美)文森特·法伦格.古希腊的公民与自我[M].余慧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15]廖申白.《尼各马可伦理学》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