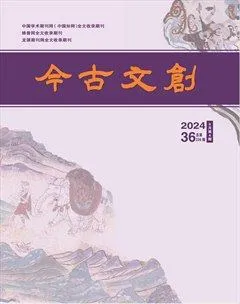《理想国》第十卷
【摘要】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和诗人,他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思想交流的火花。柏拉图关于诗的看法出现在他众多的作品之中,本文主要选取《理想国》第十卷进行探讨,由此可以了解柏拉图的一些重要哲学观点。
【关键词】柏拉图;诗;哲学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7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21
诗与哲学之争一直是西方历史上的重要议题。诗人和哲人分别为支持的观点而论战,诗和哲学在每个时代争论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争论的实质没有改变。关于诗与哲学之间的争论,并不仅仅是两种学科之间的争论,更是它们背后代表的理性与感性、诗意与逻辑、诗意思维与哲学思维之间的论战,这是两种认知方式的抗争。诗与哲学发生争论是因为诗人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是智慧的持有者,诗人尝试像哲人一样,试图对生活做出诗学的解释。而哲人则认为追求真理是自己的宗旨,他们把真理当作一生的追求。诗人为何会认为自己持有真理呢?因为诗产生于原始时代,其他的学问都发源于它,每个民族都有传统的诗歌、神话,在古代,历史家、政治家要借助诗需要借助诗作为载体来表现历史和政治。诗的地位远远领先于哲学,两者并不存在争论。公元前5世纪到前6世纪,诗处于主导地位,人们崇敬诗人,把诗人当成人类生活的导师。哲人笼罩在诗人的光环之下,哲学的表达需要借助诗歌的形式。诗里所描绘的故事被当成真理,相对诗人来说,哲人的声音就显得相当微弱,即使一部分哲人化身智者与诗人论战。赫拉克利特就认为诗人是没有智慧的,但诗人的地位还是不受影响。柏拉图也可以承认诗人的地位:“诗人可以说是我们的父亲,是智慧的向导。”[1]诗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局面在柏拉图《理想国》中被打破,柏拉图是反对诗和诗人的哲人中,立场最为鲜明的一位,他坚定地站在哲学一边,对于诗人和诗歌发出了猛烈的攻击。从此之后,诗与哲学的地位发生转化。
一、《理想国》卷二三关于诗的观点
在《理想国》第二、三卷就有对诗人进行批判的内容。在第二卷中,柏拉图提到,作为城邦的护卫者,需要接受心灵和身体上的教育。但是城邦中给儿童讲述的故事是虚假的,这些故事本质上是摹仿的产物—— “故事从整体上是假的”[2]。一个人在幼小时期最容易接受陶冶,这个时期最容易塑造儿童的心灵,因此需要给儿童讲好的故事。他认为传统诗歌教育在教育年轻人上存在着诸多问题,神的地位也不能被诗人所污蔑。神是善的原因,人们所能够知道有关于神的事情都是从诗人的描述里来,而《神谱》里却描写,人们进行的祭祀活动却能够收买神,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们不再相信正义,也导致人们不再敬神。柏拉图认为,诗歌里描写神的形象是富于变化的,就像随时变形的魔术师。神应该是单一的,尽善尽美的,不会变化,不会说谎,永远处于既定的形式之中。神和英雄还是人所崇拜的对象,他们在儿童心里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形成儿童性格的主要影响,所以,柏拉图认为要对写故事的人们进行审查,写得好就选择,写不好就抛弃。柏拉图从这个角度分析《荷马史诗》,他指责《荷马史诗》里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就是说谎,把神和英雄的性格描写得不正确,“把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2],神应该是勇敢有节制的,在《荷马史诗》里,神却跟平常人一样,钩心斗角、耍弄阴谋、贪财爱色……但在柏拉图看来,神不会说谎,没有敌人,也不会丧失理性。《荷马史诗》对于儿童青年有着重要的教育作用,在这类的例子的影响下,是不能够教育青年儿童学会真诚、节制、勇敢的。而且史诗悲剧都往往不让好人有福报,坏人没有坏的报应,这暗示了福祸没有凭据,正义对于正义的人不一定有益处,这种思想也是不利于教育青年的,因为城邦里流传的诗存在的问题,所以目前城邦里大部分的诗都需要抛弃。在第三卷中,柏拉图对诗的批判进一步展开,在一开头他就指出,对于写作的人,应该加以监督。为了培养城邦卫士的勇敢,他认为必须要对诗的内容进行删减,《荷马史诗》里的一些内容描写死亡太可怖了,容易使人恐惧,这容易使城邦的护卫者意志消沉,对于未来的战士有害无益。诗总是借助于虚假表现自己,虚假对于神明来说毫无作用,对于凡人来说就像一味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平常人不允许触碰。他认为虚假的东西对于国家来说,可以用它来对付敌人,但平常来说,虚假足以颠覆一个城邦。柏拉图指出,诗歌最大的恶就是让青年人认为神明会产生邪恶,但神是善的本源,所以这种话虚假而荒唐。最根本上的问题是,他认为作为城邦的护卫者,不应该是一个摹仿者。即使放宽条件可以进行摹仿,也要摹仿高于人的事物,而不是摹仿不如自己的事物,在这里,柏拉图认为摹仿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是真实的东西。总之,柏拉图要求诗歌的内容能够符合城邦的利益,对年轻人有益。为了达到这一点,他认为需要对诗人和进行表演的艺人进行监督,如果他们不愿服从,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淫荡、邪恶、说谎的坏精神,就把他们逐出城邦。
二、摹仿——诗的主要创作方式
第三卷中柏拉图已经点出了诗歌和故事的体裁,并指出,诗人通过摹仿来进行叙述,但是城邦拒绝任何摹仿。在这里,柏拉图依然借助了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达了他的思想。前文已经点明诗在希腊中的重要地位,诗是希腊人生活的教科书,建立理想国的基础就是对诗和诗人进行合理安排。在当时,诗承载了希腊人的文化传统,《荷马史诗》一度成为民众信仰的来源,荷马因此也有了“希腊的教育者”之名。[3]在理想国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对于诗人的微词都出自诗人这个教育者的角色。诗人的第一个罪状是站在哲学的角度看诗的本质而提出的。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苏格拉底在开篇就提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中关于诗歌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做法就是拒绝诗歌。他没有直接讲对于诗歌的拒绝,而是说,要拒绝任何摹仿。因为我们已经辨明了心灵的三个不同组成部分(理性、意气和欲望),所以更加需要拒绝摹仿。他没有正面指出摹仿出自哪个部分,只是认为它不属于理性的部分。他用了荷马举例,他认为虽然荷马是所有人的老师,但是他依旧需要捍卫自己的观念,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这里,苏格拉底直接说,荷马不配当所有人的老师,因为通过诗人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接下来,他又提出了理念论,苏格拉底指出,有三种床,一种是自然的床,一种是木匠造的床,一种是画家画的床。这三种床的创造者分别是神、工匠、画家。他高度赞扬神创造的床,也就是理念,因为,理念才是真实的。工匠造的床是对于理念的摹仿,也就是说,具体事物的本质取决于形式,所有的技艺都是个别的东西,理念与形式就是一与多的关系,但是理念是没有产生没有消亡的,而形式由于材料的加入,就会产生消亡的结果。在《理想国》第十卷里,苏格拉底把诗人和画家看得比木匠和铁匠还要低,在他看来,创造是比摹仿更重要的事,木匠和铁匠能够创造器具,而诗人和画家之类的艺术只是摹仿工匠制作出来的现象世界的事物。工匠创造出来的现象事物是对理念的摹仿,而诗人画家只能是对现象世界的摹仿,是摹本的摹本。苏格拉底要攻击的就是画家画的床和诗人描述的床,诗只是对于其他技艺的摹仿,而非创造。苏格拉底控诉诗人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所有诗的本质都是摹仿,是用语句再现一个场景,再现人、世界,再现诗人想要再现的一切。
他直接在本篇中就点出了诗是对于影像的摹仿,“而模仿术又是距离真实很远的”[2],诗距离真理隔着三层,理念的东西最为真实,其次是现象世界的东西,最后才是诗人、画家描绘的东西。苏格拉底并不是认为诗人、画家就完全没有创造性,他的摹仿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摹仿,我们现在认为摹仿是效仿其他人的作品,没有创造性。但是苏格拉底口中的摹仿是具有创造性的东西。诗画作品的确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创造者不可能完全回避现象世界,它们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借助现象世界的东西来进行创作,本质上还是在摹仿现象世界。在借苏格拉底之口表明想法的柏拉图真实意图是,他认为理念才是真实的东西,现象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是理念的具体化,不具有真实性。诗和画就是摹仿现象世界中的某一方面。而人们被诗,被魔术师所迷惑时是不能区分知识、无知和摹仿的。苏格拉底接着考察悲剧诗人及其领袖荷马。他说,有人认为,诗人无所不知,知道人类的美德和罪恶有关的任何事,甚至还知道神灵的事情。诗人想要创作诗篇,那他一定知道关于这件事的知识,否则他就不能准确描述这件事。而诗人对于自己描述的事物是否有真知,这需要进行考察。柏拉图认为诗人是不拥有真知的。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就曾说过,为了查明诗人具有多少智慧,他对诗人进行查探,结果是在座的诸位对诗歌的解释都比诗人的解释要好。他接着进行思考,一个人既然可以造真实的东西,那他怎么还会迷恋虚假的东西呢?他一直坚持创造是比摹仿更为重要的,一个人是愿意献身于真的东西而不愿献身于摹仿的。他接着批评荷马,认为荷马虽然被希腊人当做生活的导师,但是没有一个城邦能够被治理好。荷马他既不是优秀的立法者,也不是指挥官,更未曾担任公职做出贡献,他只是一个摹仿者。作为摹仿者的诗人也没有任何技艺,不能在城邦中做出实际的贡献。如果荷马拥有真理,拥有智慧,那么自然会有青年向他学习,荷马也不会一直颠沛流离。但从荷马以来的所有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东西的影像的摹仿者,他未曾真正拥有美德。作为画家或诗人,对于他们描述的技艺——真正的技艺一无所知,诗作为对现象事物的摹仿,去掉韵律节奏之后,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摹仿不同于创造,摹仿者自身也无法判断自己描画的事物是否美,是否正确。摹仿者不能像制造者和使用者一样,他没有信念,没有知识。
三、情感——诗发挥作用的方式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与人性中非理性的低劣部分相关。诗距离真实很远,诗和画都服从感情,缺乏一定的理性。艺术品的首要特点就是要立马把人吸引住,按照柏拉图的定义,最优秀的人就是用理性控制一切的人。但是,人在被诗打动的那个瞬间,理性便失去了对自己整个生命和心理的管控能力,诗的力量足以动摇理性的统治。这对于城邦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柏拉图创作理想国就是为了建立他心目中的完美城邦。在理想国中,人性中有三大部分,最好的是理性,其次是意气,最坏是欲望。意气和欲望受理性节制,才能达到个人性格的正义。诗人和画家没有从理智出发,他们专门逢迎人类的弱点,让人挑动情欲,产生刺激与快感。智识低的人理性发展不健全,经常受原始冲动——感性奴役,听从感性就可以躲避理性带来的节制的痛苦。诗人的摹仿不是摹仿心灵最善的部分,因为这部分不但难以摹仿,而且也难以取悦观众,为了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只能摹仿恶的,情感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也是最容易摹仿的。柏拉图最推崇的理性对应的是统治者,国家的统治者如果靠感觉去认识事物,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经常会被不理智的感情影响,就不算一个好的统治者。诗人在进行舞台演出时,迎合了人们渴望得到满足的部分和渴望得到发泄的部分。因为悲伤而放任情感的流泻是可耻的事情,人处于这一种氛围下,容易成为一个悲伤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情欲越受刺激,就越需要刺激,久而久之就成为痼癖,就越不受理智节制。这个影响是危险的,因为理想国的保卫者需要勇敢来保卫国家。悲剧诗,会腐蚀不懂诗歌真实性质的听众的心灵。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人在剧场观看喜剧时也需要注意,虽然人羞于承认,但人本身就具有喜爱插科打诨的天性,这种天性平时被理性压制着,因为怕受到别人轻视,但是在剧场时,人就放纵自己沉迷于这种情绪之中,人也越来越习惯于这种情绪,这也被带到生活中来,于是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不知不觉成为一个爱插科打诨的人了。人的喜怒哀乐都是伴随着行为而表达,诗歌是行为的摹仿,自然也会表现出喜怒哀乐。但是喜怒哀乐应该受到理性的调节,而不是任由其发展。所以,诗歌也应该存在一个界限,越出界限的就不能进入城邦。
四、诗与哲学之争
柏拉图承认,诗与哲学的争论早已有之。柏拉图在前面用苏格拉底之口斥责了诗人的种种罪状,指出诗的种种不好。但是他不是为了放逐诗人,而是驯化诗人,城邦里诗人是必不可少的,人肯定会有欲望和感情。柏拉图还是给诗人留了一个余地,如果诗歌的拥护者能够证明,诗歌对于城邦和人们的生活有利,他还是会欢迎诗歌回来。接下来,柏拉图重点论述了诗与哲学之争。他认为这场斗争是重要的,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它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柏拉图为什么这么看重诗与哲学之争,这场斗争关乎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问题,那就是在人的心灵中是依靠着清明的理性还是依靠冲动、激情、幻象这些东西。诗与哲学之争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两端,这涉及两者如何把握世界的问题。从柏拉图的观点来看,诗人并未抓住真理,诗人也没有智慧,诗对世界的认识是不真实的。但是哲学是理性之光,它能够观照真理,哲学家是有智慧的,他们能够把握世界的本质。在前面已经说过,诗人借助想象,用美好的词汇将语言进行加工,失去了这些装饰,诗歌将平平无奇。诗所描绘的东西不是永恒的,是转瞬即逝的。作为诗的创造者是只看到事物的影像而看不到真实本身,他们全然不知实在而只知外表。诗人摹仿的对象——现象世界的事物是不构成知识的,知识存在于理想化的理念世界之中。诗人只是声色的爱好者,喜欢美的声调、美的色彩、美的形状以及一切由此而组成的艺术作品。诗人是无知的,诗人进行的摹仿术不能够从经验的使用中得到真知,摹仿者不能像制造者和使用者一样,他没有信念没有正确的意见。诗人无知的根本在于他没有接触到那个具有真正知识的理念,他接触到的都是倏忽即逝的现象。在柏拉图眼里,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理念才是永恒的。而与此相对的哲人是什么呢?哲人是拥有知识的,哲人能够触及真正的知识,是能够理解美本身的,哲人认识到的是事物本身的理念,在他的论断中,理念比影像更具有实在性,也更加接近真理。诗人对现象痴迷,而哲人更加关注现象背后的理念,追求本质。在柏拉图的认识论当中,哲人擅长理性思维,而诗人在作品中往往远离理性,宣扬激情和欲望,这样会破坏人原本完整的人格。而从艺术本质上看,诗人创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摹仿说,另一种是灵感说。“模仿术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2]摹仿术是远离真理,远离真实的,画家和诗人这类摹仿者所造之物和真实本体相隔两层。“模仿者离真理相隔最远。”[2]并且摹仿术没有正确的参考物,所以画家和诗人往往能够欺瞒世人。关于灵感说主要的讨论在《伊安篇》中,《伊安篇》中讨论了诗歌的创作只凭灵感而不是技艺。在《伊安篇》里,苏格拉底与职业颂诗人伊安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苏格拉底一一否认了诗属于任何技艺,虽然荷马的诗歌谈到战争,可是里面的知识并不能使人当将军打仗,诗歌既不靠专门一种知识,也就不能给予人们某一种专门的知识。在苏格拉底的连续追问之下,伊安得出来诗不属于任何一门技艺的结果。为了追问诗从何而来,最后,苏格拉底认为诗歌的创作来自灵感,他用荷马举例,荷马写出了享誉一生的《荷马史诗》,后来的作品再也难以超越《荷马史诗》,这是因为诗人凭借缪斯的力量作诗,神占据了诗人的身体,气息充满了诗人的世界,即对话中谈及的“被神凭附”,在神的凭附下,诗人创造出来优秀的作品。诗人在被神凭附时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诗人得到灵感就要失去理智,被动传递着神的语言,诗人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充当着神的代言人而已。而在《伊安篇》中的磁石环链的比喻也非常新奇,这个比喻反映了神的灵感或诗的传递过程。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是凭借诗神传递的灵感而作出了诗歌,诗人是无法凭借自身的技艺来创作诗歌的。诗人创作诗歌的时候并没有智慧女神降临,诗人创作是通过天性的,他们得到了灵感,然后借用这灵感来创作,其中没有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讲了很多美妙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也不懂。柏拉图认为诗人凭借灵感而干涉现实,这是危险的。在他看来,凭借灵感而作诗的诗人,他们是和理性无法兼容的。诗的创作一旦不受控制,国家就容易陷入不正义之中,城邦公民的心灵也会遭受腐蚀。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实际上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神的摹写,是人世间最接近神的东西。”[4]柏拉图以一己之力重新提高了哲人的地位,哲人在他的理想国里当王,受到人们尊重,他可以管理国家,对于大事具有决策权,哲人也是理性的代表。而诗人远远不能和哲人相比,诗人创作受到人们监督,当他们的诗歌不利于城邦时,还要面临被逐出城邦的危险,就像荷马年老以后被人们遗忘了,他无法像哲人一样建立自己的门派。甚至诗人连工匠和画家也不如,因为画家和工匠拥有自己的技艺。在柏拉图建立的理想城邦之中,哲人成为哲学王,而诗人只能四处流浪,柏拉图把这两者的对立提高到极点。本文以《理想国》作为出发点,看到的是哲学对诗学的批判,诗在这个时期与哲学对抗处于劣势之中,它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而战,在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他为诗与诗人做了辩护。
五、卷十中的神话故事
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花了很长的篇幅描写了一个神话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灵魂转世的神话故事,一名叫厄洛斯的勇士死后又重新复活,被允许观看另一个世界的情景并告诉人类。法官们对灵魂进行判罚,正义的升入天堂,不义的堕入地狱。升入天堂的灵魂干净无暇,而堕入地狱的灵魂形容污秽。厄洛斯告诉世人,一个人生前做过的坏事,死后会受十倍的报应。在对诗歌进行批判之后,柏拉图为什么要在第十卷讲述一个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一本书都是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述他自己的想法,在《理想国》第一卷,苏格拉底就曾提出,打算参加女神这次的祭奠,然后观看当地人是如何举办这个大型赛会的。然后在结尾的第十卷,柏拉图又抛出了一个篇幅不短的神话。有观点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呼应,柏拉图其实想构建一个新的神话体系。那我们来看看柏拉图写的神话故事有什么不同于城邦旧的神话故事。在这个神话中,厄洛斯在一开始看到走向天上之路的灵魂是幸福快乐的,而从地底下上来的人则经过了千年苦难的折磨。厄洛斯说生前做的每一件事在死后都会得到十倍的报酬或惩罚,崇敬神灵孝敬父母会得到福报,但是不敬神明忤逆父母的也会得到恶报。接下来厄尔看到了必然之“纺锤”和命运三女神,在这里有神使宣布:“不是神决定你的命运,而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涉。”[2]众灵魂进入新一轮的轮回,要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灵魂通过抓阄可以选择来生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灵魂将此生与来生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对换,妇女想成为男人,动物选择成为人,人选择成为动物,普通人选择成为地位显赫的人,地位显赫的人选择成为普通公民。好人选择成为恶人,恶人选择成为好人。当好人选择成为恶人时,他在此生成为好人是因为受到风俗教化、伦理习惯的结果,来生选择成为恶人是因为他本身自身含有的恶的因素,在脱离教化的环境之后,他的恶显示出来了,所以他选择成为坏人。来生的命运来自灵魂的选择,灵魂的选择取决于灵魂的政体,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成为好人还是由于理性的力量成为好人是很重要的。柏拉图在这个神话中想告诉我们,要靠智慧选择好的生活方式。
六、结语
在柏拉图看来,哲人高于诗人,由哲学王统治城邦是他的政治立场,所以他对于诗的否定是必然的。柏拉图在第十卷中从诗歌是摹仿、诗所带来的后果来否定诗歌,他站在哲学的立场去批判诗,从根本上是为了建立他心目中的理想城邦,所以他崇尚理性贬低感性,认为只有理性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方式。他批判诗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结束城邦中的混乱局面,拯救当时古希腊的颓势。
参考文献:
[1]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M].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4]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沃利青.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看诗人与哲人之争[M].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