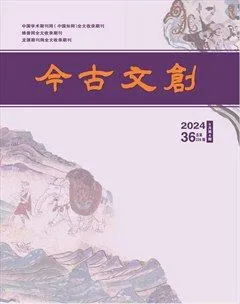清代“走西口” 移民背景下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摘要】“走西口”不仅是一部顽强拼搏的移民史,更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同时也是蒙汉两族人民建立友情,同创文明的发展史。“走西口”中的汉族移民,为了生存而留下来的种种足迹,已然成为促进蒙汉民族融合,口外地区社会变迁的钥匙。蒙汉人民共同培育的“坚持不懈,发奋图强,勇敢勤劳,开放包容”的“走西口”精神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已成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独具风采的地域文化。
【关键词】“走西口”;移民;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6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1735—1911)”(23BMZ016);吉首大学科学研究项目“清代‘走西口’移民背景下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dy23112)。
万里长城,起春秋,历秦汉,及辽金,至元明,西从嘉峪雄关而来,东到山海要隘,像一条矫健的巨龙蟠伏在中华大地上,分割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见证了金戈铁马、烽火狼烟的历史风云,承载着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记忆。烽烟远去,雄关犹在,关隘成为出入长城的要道。
从明朝中后期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的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大批晋、陕百姓离开故土,离开亲人,前往口外,开辟了通往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促进了蒙汉民族交融。山西人作为“走西口”的主力军,多从北部和中部出发。
一、“走西口”概况
“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等地的人们穿越长城内到口外谋生而开垦、经商的移民活动。关于“口”的说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中的“口”一般指位于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广义上的“口”指位于长城内外各个关口,例如陕西的府谷口、河北的独石口等,山西、陕西等地的人们通过长城的各个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很多人背井离乡,离开家人,踏上遥远而未知的路程,踏上一个陌生的地界去寻找那未知的生存希望。杀虎口作为其中之一的关口,当时还有匪患,有民谣传唱:“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心还抖。”到了口外以后,面临的还有戈壁沙漠、寒冷的天气等重重困难。
“走西口”大致有以下几条路线:
(一)神府线。主要以陕西榆林地区为起点,向北越过长城,途经大柳塔、纳林以及毛乌素沙地,最终进入鄂尔多斯地区。
(二)河保线。主要以山西省河曲县和保德县为出发点,在河曲县黄河边的西口古渡上船,横渡黄河以后到达内蒙古地区,过十里长滩,然后继续北上到达鄂尔多斯地区,可以在此进行定居,也可以继续北上,渡过黄河,最后到达河套、包头等地区。
(三)偏右线。主要以山西省偏关县和右玉县以及附近的县为出发点,先北上过杀虎口,到清水河或者归化(呼和浩特),可在此定居生活,或者继续出发到土默特地区和包头地区。
(四)雁门关线。主要以山西省忻州地区各县为起点,过雁门关出长城,这条线路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通关通道,这条路线可以通行商队,运输货物。
(五)大同线。主要以大同地区各县为起点,出大同北上,经过丰镇,到达察哈尔等地区,也可继续向西出发到达归化城。
(六)张家口线。主要以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各县为起点,从张家口大境门出关,经过草原,最终到达察哈尔、张北县等地区。
以上就是“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具体可能会有更多的路线,此处不一一阐述。
二、“走西口”原因探析
作为三次人口大迁移之一的“走西口”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背后却是一把辛酸泪,总之,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已“走西口”,这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人自古便有浓厚的乡土情结,是怎样的驱动力能让数百万先祖背井离乡,踏上那满是荆棘,生死未卜的道路,只为奔一个福祸难测的前程呢?古人云:“不通则痛,痛则不通,万物疏通,则民心可定。”
(一)自然环境恶劣,干旱多变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侧,华北大平原的西部,全省大约80%以上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平原面积不足20%,适合耕种的土地很少,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光绪《天镇县志》记载:“天寒地瘠,地土沙碛硗泊。”光绪《阳高县志》记载:“独居塞北,砂碛硗泊,低土难耕。”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虽辛苦劳作一年,但最终收成却很少,有时遇上天灾等不利因素,土地产量更低。康熙《灵丘县志》记载:“地土砂碛,坂田硗确。岁丰,亩不满二斗,稍歉则籽粒半失。”由于山西交通不便,外地粮食进入不方便,所以平常粮价就偏高,清代山西的百姓生活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一旦遇上灾荒年,就发展为极大的灾难,而山西素有“十年九旱”之称。雍正《朔平府志》记载:“夏旱,秋潦,早霜,次年大饥。”清末山西出现了“二百年未见”的“丁戊奇荒”。“光绪二年旱,三年大旱,二麦不登,遂大饥。” ①山西民人为了摆脱饥荒,只能另寻他路。
(二)人地矛盾突出,人口激增
清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安定,清朝发布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的措施,如康熙帝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后,口内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地矛盾日益激化。“雍正二年,晋、陕等省的人口已均达600万以上。” ②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没有足够的耕地去供应增加的人口,人均耕地不断减少,随着豪强地主持续进行土地兼并,农户们也面临着失去土地的风险,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食不果腹。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口外广袤的土地上。离开故土,走向口外谋生、经商的人也在不断增加。《调查河套报告书》记载:“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种土地。”
(三)清廷“借地养民”,招民垦种
“走西口”移民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在于清政府的政策趋向。清初,顺治皇帝曾允许少量山西、陕西百姓去口外垦荒,但必须春去秋还,不能在口外定居,也不能携带家眷,因此当时这批百姓被称为“雁行者”。“走西口”第一批移民浪潮开始于康熙朝,当时清廷放宽封禁,开放了部分蒙地,由此山、陕百姓开始大规模迁徙到口外。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伊克昭盟盟长贝勒松拉普奏请康熙皇帝,表示愿与汉人合伙种地,这一请求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同意,此即汉民开始大批进入蒙地开垦之路。“走西口”第二批移民浪潮开始于光绪朝,当时清廷为了巩固统治,推行新政,遂开放蒙地“移民实边”。于是在那个时期内蒙古地区中汉族人口急剧增长,开垦的土地也逐渐增加,贻谷在奏折中,曾这样描述这次大浪潮:“自开办垦务后,浚渠开地,谋生之路日广,该客民等或携亲属,或约乡朋,襁负而来。”
三、“走西口”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终清一代,大量的山西、陕西人度过长城关口,走向口外,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垦出大量的良田,推动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的晋商加强了草原与内地的沟通,促进了口外地区商业的快速兴盛和中大型城市的形成。随着“走西口”浪潮中大批内地人来到口外,促使草原游牧文化和内地农耕文化密切联系,蒙汉民族融合不断加深。
(一)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
当时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经济单一,以游牧经济为主,主要是畜牧业生产,对自然资源比较依赖,急需农业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而当时晋北和陕北地区由于天灾不断,人地矛盾突出等,大批的百姓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出关去“走西口”,他们带去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成熟的农耕技术,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走西口”的兴盛发展,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人逐渐增多,并由“雁行”慢慢发展为定居,并逐渐发展成村落,土默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区的农业开垦面积进一步扩大。经过蒙汉民族的长期共同实践,逐渐探索出适合当地环境的耕作技术,种植一些耐干旱、抗盐碱、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例如莜麦、小米等。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覆延绥镇总兵米国正奏:“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边民获粮,蒙古得租,彼此两便,事属可行。” ③在蒙汉百姓一起发展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的同时,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不断加深。
(二)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手工业的发展
最初,蒙古地区传统的手工业以牧民家庭为主,基本是自给自足。蒙古族传统的手工业种类比较单一,只有制毡、鞣皮、制乳等。随着“走西口”中大批内地百姓的进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手工生产技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的手工业开始逐步发展,并走向专门化生产。农业发展会促进相关手工业的发展,由于农作物的大量种植,需要改进农具,而制造锄头、镰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必须仰仗手工业,所以手工作坊也慢慢增多,制作工艺不断进步,以满足农户的多样化需求。
随着定居的内地百姓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些村落,有的村落命名和这些手工业者有关联,例如乾隆朝时沙尔沁有村名叫碱窑子村,因有人在这里制碱烧窑。把什窑子湾,因建立瓦窑,以卖瓦盆为生遂名。石沟村,因内地百姓在沟内制造磨刀石遂名。内地来的工匠逐渐从蒙古工匠那里学会了一些蒙古族的手工技术,例如制皮、擀毡、乳品加工等技术,同时他们把内地的铸铁、酿造、制砖瓦等技术传授给蒙古人,制作出牧民所需的皮衣、靴帽、木盆等生活用品。手工业的兴起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蒙汉民族交流,蒙汉民族交融不断加深。
(三)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商业的发展
“走西口”的大浪潮也推动了内地和口外物质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交流和城市的繁荣。清初,蒙古地区的商业不发达,都是以物换物进行贸易,贸易形式主要为“通贡”和“官市”。
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封禁令”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山西百姓来口外经商,被称为“旅蒙商”,他们最初是以行商的形式出现,先在内地或者归化等地备好牧民所需的生活用品,例如砖茶、绸缎、米、盐和铁器等,主要依靠肩挑、马拉、骆驼驮载货物到后草地后换取牧民的牛、羊等物品。内地商人通过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去赚取利润,后逐渐成立了一些商号,比较著名的有“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等大商号。“大盛魁”是由山西商人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三人创立,最初跟随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军队,作为随军的杂役,肩挑货担做随军贸易,逐渐学会一些蒙语,在右卫杀虎口创立“吉盛堂”,康熙末年,“吉盛堂”更名为“大盛魁”,总号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到归化城。“大盛魁”根据游牧民族的贸易形式,采取了以物易物,信用交易的方式,逐渐垄断漠北商业,运输路线遍布蒙古地区。同时随着晋商的发展,一些城市也逐渐繁荣兴盛起来,民间有民谚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些商号的建立以及贸易的往来,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商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推动了蒙汉民族的交往与交流,促进了蒙汉民族的交融。
(四)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文化的发展
“走西口”有近三百年连续不断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岁月中,一代又一代的内地汉族人民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来到蒙古地区,他们有的放牧,有的垦荒,有的经商,有的从事手工制造等以求谋生。在这些过程中,蒙汉人民聚居杂处,互相交往交流,这不仅有利于草原游牧文化和内地农耕文化的融合,而且推动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形成。
1.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蒙汉民族生活习俗渐趋一致
在“走西口”的几百年时间里,蒙汉人民长期共同生活、生产,从而促进了生活习俗的融合。乾隆七年,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等称:“数十年以来民人聚集归化城贸易,并携眷在各村与蒙古杂处种地者四五十万。”乾隆十九年,山西布政使多伦奏:“蒙古内地民人错杂居住,不下数十万户。”
在居住方面,大批山西人以“走西口”的方式,将农耕文明的晋文化带到蒙古地区。《归绥县志》记载:“邑民其先多晋产,亦多晋俗。”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许多蒙古人也开始用泥土进行砌筑、房顶架、灶火通炕。有一些蒙古居民放弃毡包,开始建造平房居住。在饮食方面,蒙古人传统的饮食仅有“红食”和“白食”,后随着晋文化的传入,他们开始吃谷子和小麦等食物,有的地方开始吃山西风味的醋和酸菜,而汉人吃大块牛羊肉,煮茶时加盐等则是受草原文化的影响。
2.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蒙汉民族语言文字趋同
蒙汉民族长期聚居在一起,除了生活方式外,语言也受到了晋语系统的影响,例如在包头方言中常见“圪”一字,如:圪蹴(蹲)、圪堆(堆)、圪塌(啰唆)、圪尖尖(尖),同时有些汉语词汇也引入了蒙语。“走西口”来的移民和蒙古族杂居,逐渐学会了蒙古语,而蒙古族同胞也逐渐通晓汉语,识汉字。《绥远通志稿》记载:“省境与晋地相接,住民亦多晋籍,所列方言间有与晋语从同者。要以省民承用已久,亦或言是而意非,字同而音异。”《土默特旗志》也载:“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蒙人遂多肄汉书。”
3.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文化艺术的繁荣
蒙汉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和交流,内地汉族人民给蒙古草原带来了具有汉族地区特点的文化艺术。随着笛子、四胡、三弦等乐器的传入,蒙古族音乐在以前“长调”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短调”歌曲,如《金杯》等。在“短调”的基础上,逐渐诞生了新的歌种“漫瀚调”,它是蒙汉两族音乐互相融合吸收,通过各自语言唱出来的,所以又称“蒙汉调”。同时“二人台”是在“走西口”这一历史长河中孕育而成的,它是蒙汉民族民间文化的天然融合,是民族团结之花结出的一颗令人喜闻乐见的硕果。“二人台”把民歌、歌舞、说唱、戏曲等诸多体裁融成一个整体,是蒙汉儿女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
四、结语
“走西口”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往和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推动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的繁荣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距离,增进了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团结,促进了蒙汉民族交融,“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一个历史见证。
注释:
①《(光绪)安邑县志》清光绪六年刻本,《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第1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529页。
②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页。
③《清圣祖实录》卷15,乾隆元年三月丁巳,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14页。
参考文献:
[1](清)沈潜.归化城厅志[O].内蒙古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三年修抄本.
[2]周少卿.河曲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3](清)圣祖仁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4]韩巍.清代“走西口”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社会发展[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
[5]刘春玲.论清代走西口对内蒙古西部社会发展的贡献[J].阴山学刊,2006,(03).
作者简介:
白文进,男,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