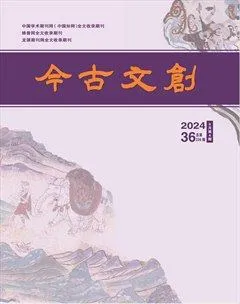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相关科研方法探究
【摘要】《中国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代表了袁行霈在文学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袁行霈以文学为本位,同时多侧面透视的研究方法,并对《中国文学史》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客观的探讨。
【关键词】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科研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4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14
一、研究综述
1987年,袁行霈应日本爱知大学中岛敏夫教授的邀请前往讲授中国文学概论,该课程的讲稿以《中国文学概论》为题目出版,这本专著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宏观把握和多侧面透视。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出版于1999年,是一部面向新世纪的文学史教材,关于它的研究从2000年起至今从未断绝。本文主要以袁行霈的专著《中国文学概论(增订本)》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为基础,探究其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几大类:第一类是访谈录,如马自力的《文学、文化、文明:横通与纵通——袁行霈教授访谈录》,这种文献是以记录问答的方式留下袁行霈本人对自己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阐述,能够比较直接准确地把握袁行霈对文学史写作的理解和他本人的着力方向;第二类是研究方法的总结,姜朝晖的《探源析流 守正出新——关于高教版〈中国文学史〉的体认》、董希平和庄永的《博采众长 独辟蹊径——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都属于这类;第三类是问题商榷,这类研究占多数,基本都围绕着某一细节问题进行商讨或纠错。如王万岭的《关于〈西厢记〉的“角门”问题——兼对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有关论述质疑》、苟德培的《〈柳毅传〉中柳毅人物再读——兼与袁行霈、罗宗强等先生商榷》等文;第四类是将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与其他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进行比较的研究,例如高淑婷的《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被很全面地概括出来,包括以文学为本位,辅以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的编写理念,“守正出新”的治学原则,“横通与纵通”的学术追求,“博采、精鉴、深味、妙悟”的为学气象等方面。这些研究结果都契合了访谈录中袁行霈对于科研方法的自我评价。此外,还有关于遗漏之处的指摘商榷。《中国文学概论》在袁行霈的文学史理念贯穿下也存在一些细节或是作品解读上的问题,却几乎没有指摘其问题的论文,相比之下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却有大量相关论文。这是因为四卷本成了高等教育的教材,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影响面要大得多,同时在高校教学的诸多学者对授课教材是不断研究体察的,所以更容易深入其中并发现问题。在不断地建议和商讨中,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相继印发了第二版、第三版,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更正。
二、研究方法
袁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增订本)》封皮上有两句话,很能代表袁行霈的研究思想:“既然是文学概论,就要讲文学,讲作品,讲其感动人的地方,讲其审美的价值。我所重视的乃是启发性,而启发性也正是一种学术的追求。”
第一句是说文学概论就是要讲文学,而讲文学的内涵是讲作品,讲作品的动人之处和审美价值。审美价值关乎审美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引起主体审美感受的某种属性,这里体现出袁行霈对于文学的看法是重视文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和价值,着意将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比如社会学进行划分。所以他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既宏观地考察中国文学这个整体,又详细论述各种文学体裁的流变和风格;既有概括性的论述,又引用了大量作品当作例证,回归到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本身。
第二句讲学术的追求是启发性,是指希望在自己的文中提出的新观点、新视角,能为看了这本书的人提供新的思路,进而将他们的研究发散式地引向各个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义赞扬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比如地域文化与文学发展不平衡或重心转移的问题,为什么唐代诗人多出于河南、山西,宋代作家多出于江西……” ①从这一点来看,袁行霈的学术追求是想要创造出更多的创新。此后出现了许多就文学史某一点的商榷论文,无论是批评还是指正,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交流与创新。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袁行霈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本位研究
在《中国文学概论(增订本)》的引言部分,袁行霈先对“文学”一词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做了详细的论述。这是为了明晰本书的论述对象是“中国文学”,中国的“文学”一词本就不是所谓的“纯文学”,而是有着多重内涵,如果再不厘清范围,就会将其他意义杂糅进来,使论述不再清晰。对此袁行霈认为,应该兼顾今人对文学的理解和古人的习惯,充分注意到“杂文学”的特点。同时,文学不是历史学,但是传统的文学史在分期上基本都是以朝代为断限,这种分期方法有其合理性,也有弊端,就是忽视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历程,用历史断代来限制文学的断代。事实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并非完全同步,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有超前性和滞后性。因此,袁行霈在结合社会制度变化和王朝兴衰的基础上,按照文学本身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体现出的阶段性来对文学进行分期,也就是“三古七段”。将上古期分为先秦、秦汉两段;中古期分为魏晋至唐中叶、唐中叶至南宋末、元代至明中叶三段;近古期分为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两段。“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包括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二,作品的思想内容;三,文学体裁;四,文学语言;五,艺术表现;六,文学流派;七,文学思潮;八,文学传媒;九,接收对象。‘三古七段’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发展变化的这九个方面,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 ②
地域性研究也是袁行霈研究文学史的一大特点。“这里所说的地域性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某些文学体裁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在它发展过程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地区的特点;二,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不同的风格特点。” ③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是相互关联而又各具特色的两种主要文化,因此,他将中国文学宏观上分为南北两类文风。文学家也各按邹鲁、荆楚、淮南、长安等地分成了地理性作家群。
中国古代一直有按题材内容分类的习惯,所以文学史不能避开对于题材内容的分类研究。《文选》按体裁分了39类,在赋类下又按题材列了15小类。《艺文类聚》分天、岁时、地、人、木等部,完全按题材内容分类。《文苑英华》仿《文选》进行体裁-题材内容的两级分类。但是这些分类太过琐细,袁行霈参考鲁迅的“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既着眼于题材,又兼顾文学产生的环境和作者,综合性地将中国文学分为四大类: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乡村文学。
(二)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主要是学科之间的交叉影响研究。袁行霈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偏重于史的描述和单个作家作品的评论,而缺少多侧面的透视和总体的论述。侧面透视是多学科交叉,将其他学科的命题或思路引入文学史的研究,就是“横通”,就是“将诗歌与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邻近学科沟通起来,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从事研究。” ④袁行霈将哲学、宗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孔门诗教、禅、老庄自然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隐性的角度讲,儒释道的宇宙观、人生观和道德规范影响着文学家的思想和创作理念;从显性的角度讲,三家思想直接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内容和趣味。
随着社会发展,传播的方式和媒介有所改变,这对文学的流传和创作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上古时代的歌谣、神话主要依靠口头的流传和演唱,因此便显示出内容的流动性,也很容易失传。纸的发明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流传广度,同时也使作品更容易保存,并影响着传抄和题写。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通俗文学的大量刊刻促进小说、戏曲的普及,加速雅俗文学之间的交流。这是传播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
《中国文学概论(增订本)》也结合了文艺学相关理念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鉴赏时,引入“滋味”“意境”等词进行解读,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命题。在论述中国文学体裁的演化特点时,谈及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其生命周期。当一批优秀作家发挥了这种体裁的各种表现力后,后人难以继续有所作为,便转向另一种正在发育着的体裁,去试验探索。这就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
总的来说,在“横通与纵通”思想的指导下,要进行以文学为本位,进行多侧面的交叉影响研究。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袁行霈的研究过程中是齐头并进、相互交融的。
三、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增订本)》总论的第一章论述了中国文学的特色,将中国文学的特色概括为“诗是主流”“尚善的态度”“乐观的精神”和“含蓄美”。在第三节“乐观的精神”中,袁行霈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下,中国人认为逆境到了极点就是顺境的开始,所以文学常以乐观精神看待人生,这点在戏剧、小说、诗歌中都有所体现。“中国的戏剧,往往带有一个喜剧的结尾,叫作大团圆。” ⑤而这种“大团圆”或者“喜剧的结尾”能否等同于乐观精神的体现,其实是值得商榷的。袁行霈举出了许多例证,比如《会真记》中张生抛弃崔莺莺的结局变为了《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终成眷属;《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蛇被法海永世镇在塔下不得翻身的结局,被后来的戏曲改写成白蛇的儿子中状元后救出母亲。袁行霈在这里所说的戏曲指的应该是方成培的剧本《雷峰塔》。
这种对于结尾的改写与其说是乐观精神的产物,不如说是传世作品对观众期望的妥协。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女主人公白娘子爱情的落空、她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男主人公许宣的背叛在《雷峰塔》中用状元救母这样一个所谓“大团圆”的结局进行遮掩,只是要以此平复观众愤激的情绪。或者说,这样一个结局还在半途中,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无论是《会真记》还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都是男女相恋——女子痴情/男子薄情——男抛弃女的故事结构,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数不胜数,而这种背叛——受难的主题会刺痛人们的感情,让观众感受到痛苦。《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作为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同时期同样结构的故事,女主人公最后死去,结局更加惨痛,却并没有在长期的流传中被改写成“大团圆”结局,为什么?因为女主人公杜十娘已经看清背叛者李甲的本质,与其决裂,让他落下病根永世不愈,破坏者孙富受到惊吓得病卧床,不久一命呜呼。而真正帮助过杜十娘的柳遇春被杜十娘的鬼魂救了命,又以匣中宝物回报了他的恩情。女主人公虽死,但她已经坚定地做出了选择,善恶最终各有所报,得到了观众的认同。结局虽然悲惨,却没有让人郁结在心无法释怀,所以无须改造成所谓的“大团圆”。而对于同为背叛者的许宣,女主人公对他仍有爱情,无法选择决裂,而是隐忍受屈,为了迁就女主人公爱情的合理性,同时为了回避真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的痛苦,观众们(对故事进行改编的作者也属于原故事的观众)便在故事流传中逐步改造男主人公的性格,让男主人公也深爱女主人公,实际上是舍弃了背叛者的形象,再创作了一个符合女主人公期望的也是大众理想的、翻新的男主人公配给她。近代以来,对于白蛇故事的演绎有许多,田汉的剧本《白蛇传》、影视剧《白蛇传》和粤剧电影《白蛇传·情》都省略了状元救母的情节,《新白娘子传奇》虽然还存在状元救母,但男女主人公已经是相知相爱的了。将背叛者许宣改造成痴情郎许仙,尽管其中还会有波折与误会,但故事的主要矛盾由恋爱关系内部受到背叛转为天理与社会等外界力量对有情人的阻挠。只要两个痴情的人是真心相爱的,再有什么困难也不要紧,是否被当了状元的儿子救出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故事警戒世人的功用消解,转向了大团圆结局。或许对于这个故事主题的改造,已经走向了相对稳定,符合观众普遍预期的结局。
黄天骥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张生为什么跳墙?》,
文中认为王实甫对张生“跳墙”故事的改动不是漏洞而是锦上添花,为故事增加了更多生动的情趣,也凸显了张生的性格。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中关于这段的论述完全沿用了黄天骥这篇文章中的说法,并且做了扩展解释,认为张生是被欣喜之情冲昏了头脑,所以才做出这一鲁莽之举。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疑问,主要来自对于“迎风半户开”中“户”字的不同解读,这个“户”究竟是围墙上的角门还是崔莺莺所住的西厢的房门。王万岭在《关于〈西厢记〉的“角门”问题——兼对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有关论述质疑》一文中,从崔莺莺的立场、户字的训诂、王实甫为了配合跳墙行为对《诗简》的改动等五个方面来论述在王实甫版本中,这个“半户开”指的是崔莺莺住的西厢的门,而不是角门。张生跳墙是必须跳进去才能与崔莺莺相会的无奈之举,而不是锦上添花或是深化性格。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作品解读的异议。《柳毅传》中柳毅与洞庭君性格分析的表面化;《窦娥冤》中聚焦于反映元代吏治黑暗,却没有扩展到更大的社会不公;《牡丹亭》片面性地划分正反两大阵营……
实际上,无论是袁行霈的专著《中国文学概论(增订版)》,还是他主编的四卷本文学史,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无论是他一个人创作还是和编写组一起创作,都无法做到将细节化的解读覆盖到全部作品,但是作品还需要解读,那么对于其中一些篇章,对它们的解读方向就要从前人的研究中获得。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如果选取的解读“参考书”是一种误读,那么学出来的解读自然也是误读,所以会被在这方面专精研究的学者发现并指出错误。这就像古代文献学研究中应该全面掌握书目和版本源流,合理选择底本和校本一样,如果太过依赖前人研究,就很容易导致以讹传讹。要想在研究中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对比多种前人研究,并结合作品本身分析出最接近真相的解读,但这也是很耗费时间与精力的,对于单方向单作品的研究还可以做到,如果扩展到某一段文学史或者整个文学史,那么体量就太大了,很难做到。所以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在尽可能汇集更多研究领域的大家外,可以采取有把握的部分深入解读,没有把握的部分介绍多种解读方向的手段,此外还有错漏之处,就由各地学者撰写论文加以商讨修正。
注释:
①闻一:《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研讨会综述》,《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②④马自力:《文学、文化、文明:横通与纵通——袁行霈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
③⑤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