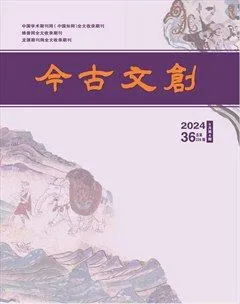论晚清上海小说中的声音书写
【摘要】晚清上海小说中有着大量的声音书写,尤其是那些新型器物的声音是作家们描述的重点。这些声音的存在让晚清时期的上海显得与众不同,上海不仅可见,也是可听的。声音唤醒了人们的耳朵,听觉感知成为理解晚清上海的重要途径。此时的上海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转型,人们在这样的一个声音环境中,呈现出犹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是一种听觉焦虑,是人们无法理解声音现代性的矛盾心态的体现。
【关键词】晚清上海;声音书写;听觉感知;听觉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4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13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社项目“现代文学中的都市声景书写”(2021SJA0735)。
陈平原在《“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一文中指出,“声音”是想象现代中国的四个关键词之一,那么对城市而言,声音与听觉同样能够帮助人们接近其精神内核。晚清上海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剧烈而深刻的。在上海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上海出现了一些此前未曾有过的声音。因而,我们不禁要问,有哪些声音引起了晚清上海人的听觉关注?这些声音又透露了怎样的信息?人们面对这些声音时又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本文将从晚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入手,从文本中的声音书写去寻找答案。
一、声音书写与听见城市
自鸣钟声是晚清小说中常见的声音之一。《新上海》第38回写道:“碰毕六圈,自鸣钟‘镗,镗,镗,镗,镗,镗’已敲了十二下。”[1]176与自鸣钟相比,公共建筑物上的大自鸣钟声更能给人听觉上的震撼。葛元煦曾在《沪游杂记》中对大自鸣钟有这样的介绍:“四面置针盘一,报时报刻,远近咸闻。”[2]65所谓“远近咸闻”指出了大自鸣钟在声音上的特点。在《海上繁花梦》的初集第2回中,作者便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苏州人谢幼安与杜少甫初到上海后,入住长发栈,次日早晨“及至醒时,隐隐听得大自鸣钟已敲九点。”[3]8长发栈位于英租界,大自鸣钟在法租界,二者距离较远,但大自鸣钟声音洪亮,极具空间穿透力,故而是“隐隐听得”。作者应是有类似的听觉体验,所以才能写得如此细节。
在自鸣钟声之外,火警钟声是晚清小说中另一常见声音。在《新上海》的第15回中,绸缎号店员王雨香向刚到上海的李梅伯介绍上海的火灾险时提到了火警钟,并且向李梅伯模拟了火警钟的声音。王雨香说:一旦发生火灾,“霎时,救火钟便‘喤’‘喤’‘喤’‘喤’‘喤’‘喤’‘喤’‘喤’‘喤’”[1]68。火警钟声对李梅伯而言是一种全新的声音,王雨香对火警钟声的模拟超出了李梅伯从前的听觉经验。因此,他说:“一味‘喤’‘喤’‘喤’什么?”火警钟声回响在上海上空,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声音向人们传递着城市变革的信息。小说中的李梅伯未曾听过火警钟声,当然便也不能触及这一声音背后所昭示的时代信息。
在晚清上海小说中,交通工具的声音也是作家们描写的重点。《新上海》第10回写到刁邦在电车站等电车,先是“听得‘叮当!叮当’一阵的警铃声音”,然后是“新式电车‘蚩蚩蚩!蚩蚩蚩!’一阵风似的如飞而来”,“‘叮’的一响,车就停了”,上了车后“听得‘叮叮’两响,那车便‘蚩蚩蚩’的开了”[1]43-44。这段文字描写了电车进站又驶离的过程。作者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声音上,非常传神地使用不同的拟声词来描绘电车在行驶、进站、停车或驶离等不同状态下的声音。相较于电车,西洋马车在晚清上海似乎更加受欢迎。西洋马车是晚清上海街头一道靓丽的景观,它的外观、速度和声音无不令晚清上海人耳目一新。《新上海》中写道:“四蹄跑开,拍拍拍”[1]1,《海上繁华梦》中写道:“那三匹马多跑得四蹄乱响”[3]139,《海天鸿雪记》写道:“马路上蹄声轮声,络绎不绝”[4]302。这些新式交通工具的车轮不仅轧在晚清上海的马路上,同时也轧在晚清上海人敏感的听觉神经上。
在晚清上海小说所描绘的声音中,留声机的声音是比较特殊的。留声机与大自鸣钟、火警钟、西洋马车等器物不同,它本身不会发出声音,但是却改变了声音的存在和传播方式。最重要的是,留声机能够保存人的声音。留声机传入中国后,国人对其“留声”功能最为感到惊讶与好奇。因而有人将留声机称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神器”[5]。但在《新石头记》中的宝玉眼中,留声机放出的是一种怪声音,这声音“不像人声,又不像畜声,怪讨厌的”[6]30。宝玉无法理解留声机和留声机的“留声”功能,是因为他刚从历史中穿越而来,对现代文明及其物质表征持有巨大隔膜。
皮鞋声是晚清上海小说中出现的一种与人有关的声音。一般说来,若是先听到皮鞋声,那么随后便会看到穿皮鞋的外国人。譬如,在《新上海》中,“坐不半刻,就听‘壳橐,壳橐’皮鞋声音渐渐的进来,却是个长而且胖的外国人”[1]260。又如《海上繁华梦》中,“正闹到个落花流水,猛听得耳朵边一阵皮鞋声响,来了一个外国三道头西捕”[3]240。在这两部小说中,皮鞋声指向人物的文化身份——洋人。正因如此,在晚清小说中,皮鞋与西服一样,成为塑造“假洋鬼子”的重要元素之一。在《文明小史》中,姚老夫子一行人在茶楼先是听到“咯咯咯一阵鞋响”,再看到一个人“穿了一身外国衣裳……脚上穿了一双红不红、黄不黄的皮鞋”[7]95。但这人并非是外国人,而是身着洋装的中国人,是一个典型的“假洋鬼子”。
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会拥有如此种类繁多又层次丰富的声音,它们相互交织,不停碰撞。这些声音在小说中被反复书写,它们不仅唤醒了人们的耳朵,也让上海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因而,上海不仅可以被看得见,也可以被听得到。同时,这些声音的存在,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城市的新途径。
二、听觉感知与理解城市
人该如何认识和理解他所生活的城市呢?城市是由无数个形象排列、叠加而形成的,视觉是人们认识和理解城市的首要途径。正如齐美尔所言:视觉能够帮助人们“‘占有’看得见的东西”[8]329。但这并非否定了身体其他器官的感知能力。其实,听觉也可以发挥同等功效。晚清上海出现的声音起初以其新奇的声音姿态唤醒了人们的听觉器官,重塑着人与城的关系。最终这些声音又回归到日常,在不断重复的逻辑中,人们在声音与现代都市之间建立了一种听觉关系。于是,人们可以通过耳朵辨别声音,以听觉感知城市。
譬如,因完善租界消防体系而建设的火警钟,它的声音本是为了报告火情,但同时又蕴含着重要的空间信息,我们掌握火警钟声的秘密便能解读出晚清上海城市空间变动的信息。租界的设立是晚清上海城市空间最直观的变动,这是在一个稳定、整一的空间格局中强行植入一个异质空间。当不同性质的空间被并置在一起,必定会引起强烈的差异体验。因而,租界内外的对比书写是晚清小说中的常见情节。在《海上繁华梦》中,租界内外的空间对比是以声音的对比呈现出来的。在二集27回中,作者以李子靖之口述说了一场起于租界之外的火灾。“前房后房一齐火发,只烧得红光烛天。邻舍人家见了,大家齐叫:‘救火!’多吓得魂飞魄散……此时惊动了地方保甲,立刻鸣锣报警,沸反盈天。”杜少甫听闻火灾报警是地保鸣锣而非敲火钟,遂表示惊讶。李子靖解释道:“那是租界里头。逢辰住的地方,因并不是租界了,才要地保鸣锣。”[3]416鸣锣声与火警钟声的差异实则是传统空间与现代空间的差异,人们只需在声音响起时,调动自己的听觉器官便可对空间进行辨别。
在《新上海》第49回中,作者再次写到火警钟声。“话说我与一帆在雨香店里闲谈,忽听警钟乱鸣,仔细一数,恰是七下。我道:‘了不得!七下乃是新马路记号,我须回去瞧一瞧。’”[1]224这原是极平常的一句话,但却隐含了一个重要信息,即通过火警钟声计数可以明确具体的火灾位置。为了更高效地处置火情,工部局先后将租界划分成不同的火政区。最初,租界内只有三个火政区,到1904年,租界火政区已有八个。从第一火政区到第八火政区,火警钟声计数依次是鸣钟一下到鸣钟八下。[9]这样,人们只需通过鸣钟计数便可推测火灾发生的具体位置。因而,小说中的“我”通过火警钟敲响7次便推测出火灾发生地点在新马路。
在《海上繁华梦》和《新上海》中,李子靖与“我”的人物设定都是拥有多年上海洋场生活经验的“老上海”,对火警钟声所承载的空间信息早已了然于胸。因而,李子靖能够向苏州人杜少甫解释租界内外火灾报警声的差异;而“我”则在听到火警钟声时保持冷静,同时依据火警钟声的次数辨别出火灾发生的具体位置。如此说来,火警钟声在报告火情的本职功能之外,还传递着重要的空间信息:火警钟声是租界内的火灾报警声,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空间的重要标志;火警钟声次数增多,火政区逐年增加,意味着这个现代化城市空间在不断扩张。晚清上海人可能无法触及火警钟声所承载的深层的空间秘密,但他们却在朴素的日常生活中掌握了其中的关键,火警钟声与空间在听觉上的关联在不断重复的日常逻辑中被建立起来。
如果说晚清上海人在火警钟声中听到了城市空间变动的时代信息,那么在自鸣钟声中,晚清上海人又精确地感知到了时间的流逝。自鸣钟是可以发声的计时工具,这意味着人们不用抬头去看,只依靠听觉便可感知时间的流逝。这种感知并非是模糊的,而是非常精确的,自鸣钟每敲一下,意味着时间流逝了一个小时。所以《海上花列传》第1回写到洪善卿叫赵朴斋留下吃便饭,是因为他听得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10]4,这意味着午餐时间到了。洪善卿对午餐时间的感知并非通过视觉,而是听觉。晚清上海小说家们在表达时间时已经摒弃了“日上三竿”“一炷香”“拂晓”“鸡鸣”等传统的时间性词语,转而采用更为标准化、精细化的现代时间表述方式。时间是抽象的存在,传统的时间性词语在表达时间时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自鸣钟却以其声音让人们感知到了时间的存在和流逝。
声音是无形的、破碎的、易逝的。因而,想要通过声音去理解城市,那么人则需要具备敏锐的听辨能力,这样才能够在一个烦嚣的声音环境中迅速、准确地理解声音所传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在现代都市中,声音“对听觉和其他感官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要求”[11]。了解了这一点,再去思考在《新上海》中,作者用不同的拟声词来反应电车的不同状态,便会觉得这一细节化的描写多了几分深意。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人们去乘坐电车,人的听觉器官就会反复接受电车声音的训练,从而变得更加灵敏、精细,能迅速、准确地对电车声做出反应。现代都市人的听觉辨别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声音环境中被训练出来。在晚清上海,火警钟声、自鸣钟声、电车声所蕴含的是一种普遍的城市生活知识。要理解城市,就必须理解声音,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听觉辨别能力,以一种现代化的听觉方式去感知城市的变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传统中国人不断地被纳入现代城市体系中去。这也是火警钟声、自鸣钟声、电车声作为一种现代性声音的意义所在。
晚清上海城中出现的新声音在给人们制造一种奇怪的听觉体验的同时,又重塑着传统中国人的听觉器官。彼时的上海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古与今、洋与中在此交汇,不同性质的文化在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声音在晚清上海城中持续回响。一个现代都市正带着迷人的魅力向人们款款走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声音场域中,传统的聆听方式,乡村式的经验感知在这个时代中已经不再适用。人们要理解他们所处的外部世界,便需要对自我感官系统进行调整与重塑。层出不穷的声音对人们的听觉器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细化的听觉感知方式成为理解城市的重要途径。
三、犹疑:现代都市的听觉焦虑
阅读晚清上海小说,总会让人有一种喧嚣繁闹之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所谓的“喧嚣繁闹”又何尝不是人们狂欢姿态的写照。在晚清小说中,四马路是繁华胜地,“狂欢”是它的底色。尤其是夜幕下的四马路,更加的肆意放纵。四马路的狂欢是声音的狂欢,听觉的狂欢。一旦进入四马路,人的听觉器官在瞬间被激活。池志澂在《沪游梦影》中写道:“过其间者,但觉檀板管笙与夫歌唱笑语、人车马车之声,嘈杂喧阗”[12]192。《海天鸿雪记》的开头也有类似的描述:“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薰天,笙歌匝地。”[4]191彼时的四马路冲破了古典美学的静谧灵动,以喧闹嘈杂表达着新的都市美学范式。在《文明小史》中,初到上海的贾家三兄弟和姚小通四人闲逛到四马路,“此时四马路上,正是笙歌匝地,锣鼓喧天”,而路边的野鸡楼上更是“人声嘈杂,热闹得很”[7]110-111。这些声音刺激着这四位初到沪上的外省青年,内心被压抑许久的激情也即将要顺势而发出。因而,呆呆看了一阵后,他们循声便上了野鸡楼。在《十尾龟》中,费春泉在四马路“听着歌管参差,曲声聒耳”,便“觉异常高兴”,待见到青楼女子的风流体态后,视觉又受到极大震撼。听觉与视觉的叠加刺激,让费春泉“不觉又疯魔起来了”[13]16。在古典时代,夜晚总能给人带来无限想象,但是对夜幕中的四马路而言,想象是多余的,因为那些不断晃动的视觉形象和嘈杂喧闹的歌声舞语给人带来了最直接的感官狂欢,人们往往耽溺于这种浅层的愉悦中无法自拔。
在所有的“喧嚣繁闹”中,跑马车的声音应有一席之地。跑马车是晚清上海街头最受欢迎的娱乐项目。马车疾驰而过,马蹄声、车轮声随着马车的速度由远及近地掠过人们的耳朵。在一场动态的狂欢活动中,人的听觉获得了极致的愉悦,“马蹄声啪踢啪踢,听进耳去十分清越。”[13]16在《十尾龟》第22回中,作者描绘了一场跑马车活动。费太太等人乘着马车从张园出发到大马路,浩浩荡荡,场面极为壮观。在这短短三四百字的篇幅中,作者反复书写了马车的声音。“一路蹄声得得,轮声飒飒”“鞭声嘹亮”“马蹄声,车轮声,竟如急风夹着猛雨打来一般,拍拍拍,飒飒飒,一往无前”[13]239。在作者的描述中,马车声的确足够吸引人,这是古典时代从未有过的一种声音。马车声以其强烈的节奏感和声音强度冲击着人的耳朵,让人获得了轻快奔放的听觉体验。外在的声音与人的听觉、情绪相互交织,在马车速度的带动下,塑造了一个狂欢化的场面。在世纪末的晚清上海,人们正是以这种感官狂欢向即将逝去的古典时代挥手告别。
当然,并非任何一个人都能在喧嚣嘈杂的声音环境中获得感官狂欢。在《新石头记》中,贾宝玉就对声音表现出了怀疑与不满。轮船汽筒“呜呜”的声音在宝玉看来是“怪响”[6]26;使别人听觉感到愉悦的马车声,却让宝玉感到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掌上灯,躺了一会,只听得街上仍是车马纷驰,闹得睡不着。”[6]29当薛蟠为他介绍留声机时,他又说道:“我听得他人声不像人声,又不像畜声,怪讨厌的。”[6]36薛蟠用留声机播放音乐,“宝玉听得不耐烦,便起身要去制止他……听他又唱了许久,更耐不住。”[6]70贾宝玉是从历史中“穿越”而来的,他无法在自己从前的经验中调动对应的知识去理解这些声音,因而便对这些声音表现出巨大的隔膜。当然,贾宝玉对声音的态度其实体现了《新石头记》作者吴趼人(笔名:我佛山人)在现代声音场域中的听觉焦虑。吴趼人是一个典型的晚清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声音只满足于浅层的感官愉悦,将会对现实社会无用。吴趼人还试图从物理学的角度去探讨有关声音的问题,譬如他在《新石头记》第22回就提到欧美科学家测量声浪一事。但吴趼人的西f97ff052fbc6b50ec75065bd01fa9426学知识毕竟有限,所以他无法想象声浪是如何被测量的。“倘谓无形不能测验,何以欧美声学家,尚能测出声浪来?”[6]172吴趼人借贾宝玉这一形象表达了晚清知识分子的听觉焦虑以及他们对现代性的朴素认知。
晚清上海不仅有现代中国的新声,亦有古典时代的余音。人们身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声音环境中时,既紧张又好奇,既欢愉也怀疑。这种举棋不定的犹疑态度,恰恰反映出他们的听觉焦虑。这一听觉焦虑说到底是现代性焦虑,是现代性焦虑在“声音-听觉”逻辑中的变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纳入世界文明的轨道,现代性及其物质表征如洪水般涌入,人们来不及细想,便猝不及防地与现代性撞了个满怀。因而,当人们置身于这纷繁喧闹的声音环境中时,多数人会服从最原始的感官冲动,止步于获得瞬时的听觉狂欢。他们企图以这瞬时的听觉狂欢去稀释因无法理解现代性而带来的焦虑。但同时也会有人秉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一如《新石头记》中的贾宝玉一般。声音是城市发出的,是城市释放出的信号。晚清上海正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变局的时代信息也经由声音传递给了人们。但此时的中国人缺乏足够解码这些声音的知识体系和理性精神,因而便无法触及声音背后的本质。
四、结语
晚清上海小说的声音与古典小说中的城市声音完全不同。古代社会,“城乡同质”,城市的声音与乡村的声音差异不会太大。但是晚清上海城中的声音却表现出了新的变化。这些声音引起了晚清文人的听觉关注,他们将这些声音写入自己的作品中。晚清上海小说中所描绘的声音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晚清上海正在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也经由声音表现了出来。外部世界的变化,重塑了人们的感官系统,听觉感知成为理解现代城市的重要途径。当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声音场域中,人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听觉焦虑。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此时的中国人还不具备理解声音背后的文化意蕴的条件。因而,所谓的听觉焦虑实则是一种现代性焦虑,是人们在被现代性包围的情况下却无法触及现代性真相的这一矛盾心态的反映。
参考文献:
[1]陆士谔.新上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葛元煦.沪游杂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孙家振.海上繁华梦[M].济南:齐鲁书社,1995.
[4]李伯元.海天鸿雪记[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5]高昌寒食生.留声机器题名记[N].申报,1890-5-3(1).
[6]我佛山人著,王杏根,卢正言校点.新石头记 白话西厢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
[7]李伯元.文明小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8](德)齐美尔著,林荣远编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金庚星.媒介的初现:上海火警中的旗灯、钟楼和电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12):62-80+127.
[10]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1]季凌霄.“听”得见的城市:晚清上海的钟声与感官文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1):98-113+128.
[12]池志澂.沪游梦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陆士谔.十尾龟[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童敏,女,安徽舒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