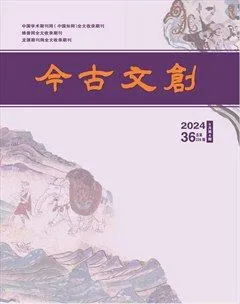浅论《毛诗正义》的颂诗美学
【摘要】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颂是至美之诗”的观点,本文便围绕孔颖达的这一论断,结合《毛诗正义》原文、相关辅助资料以及笔者本人的思考,挖掘“颂”的美学意蕴——美容、美情、美神,并探讨《毛诗正义》提出的“颂诗美学”对后世文学及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毛诗正义》;颂;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6-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01
“颂美”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关于《诗经》中颂诗的美学意义,前人已经从题材类型、章句结构、修辞手法、精神内蕴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探讨。本文只讨论《诗经》中的“颂”,并且以“周颂”为主,而不遍及《诗经》中所有与“歌颂”相关的作品。其次,本文将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入手,希望从孔颖达的视角出发,结合笔者本人的一些思考,以一个新的切入点来探讨“颂”的美学意蕴。
一、颂诗美学的提出
一般看来,“颂”是中国古代一种相对常见的文学样式,比如屈原有《橘颂》,班固有《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元结有《大唐中兴颂》等等,它们拥有不同的歌颂对象,也表达了不同的思想情感。但本文所要讨论的“颂”则与此相异,相传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诗大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大序》中所提到的“颂”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它是《诗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东汉郑玄所作的《诗谱序》曰:“何者?论功颂德,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孔颖达《毛诗正义》对其作出的解释是:
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雅之意。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刺过讥失之尔二事耳。党谓族亲,此二事各于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颂则美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1]554-555
“颂则美代至美之诗”中的第一个“美”字,按照上下文意,应出现了讹误,当为“先”“前”抑或与之意义相类的字。孔颖达认为“颂是至美之诗”,这个“至”字很有意思,战国庄周所作的《齐物论》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极矣,不可以加矣。”[2]32如此看来,“至”可以用“最”替代,那么孔颖达是将“颂”拔高到超过“风”与“雅”的地位,认为“颂”是《诗经》中最优秀,最突出的那部分吗?当然不是,《诗大序》曰:“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连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也接续而言:“四始之至,颂居其极。”[3]121而孔颖达《毛诗正义》在对《诗大序》中上述此句解释时既引用了郑玄的观点,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诗之至者,诗理至极尽于此也。[1]569
孔颖达认为诗理至极尽于风、大雅、小雅、颂四者,并没有刻意地去突出哪一部分,可见,它们四者在孔颖达心中,地位上是平等的,是同等重要的,也是缺一不可的。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在言语上严谨且慎重,中庸且平和,孔颖达既认为颂是至美之诗,强调颂的审美价值,又不能因此贬低风与雅的地位和作用,那么颂自然是《诗经》中最美的那部分,但不是唯一,而是之一。
综上所述,孔颖达说“颂是至美之诗”,我们就不能拘泥于“美”字本身,而应该打开思路,看到“美”字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厚的内涵,颂诗到底美在何处?根据孔颖达本人的评价,结合多方的资料以及本人的思考,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美容、美情、美神。
二、颂诗美学的内涵
《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正义》对其的解释是:
上解风雅之名,风雅之体,故此又解颂名颂体。上文因变风变雅作矣,即说风雅之体,故言谓之风,谓之雅,以结上文。此上未有颂作之言,文无所结,故言“颂者,美盛德之行容”明训“颂”为“容”,解颂名也……颂者,美诗之名,王者不陈鲁诗,鲁人不得作风,以其得用天子之体,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为颂,非周颂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颂名,故取备三颂耳,置之商颂前者,以鲁是周宗亲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1]569
《诗经》中的“颂”由“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构成,孔颖达认为“三颂”中最具代表性的,最符合《诗大序》对“颂”所下的定义的,应当是“周颂”。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鲁颂”和“商颂”本不该称为“颂”,这是为什么呢?《鲁颂谱》曰:
自后政衰,国事多废,十九世至僖公,当周惠王襄王时……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1]1311
《鲁颂》中《駉》《有駜》《泮水》《閟宫》等四篇诗歌都围绕鲁僖公生前所做的功绩展开描写,表达了对鲁僖公的赞颂与敬仰之情。孔颖达说:“鲁人不得作风,以其得用天子之体,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为颂,非周颂之流也。”后来又说:“此虽借名为颂,而实体国风,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孔颖达认为《鲁颂》在整体上更类于“风”,主要铺排鲁僖公作为一代君王个人的成就,并没有体现对神明祖先的敬意,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颂”,只是借了“颂”名罢了。那么从《鲁颂》四篇的具体内容来看,《閟宫》和《泮宫》风格类似雅,《駉》和《有駜》体裁类风[4]753,称之为“颂”确乎不大恰当。《商颂谱》曰:
自从政衰散亡,商之礼乐,七世至戴公……法莫大于是矣。[1]1338
《商颂》由《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等五篇诗歌构成,孔颖达认为《商颂》虽然是祭祀乐歌,祭祀先王于宗庙,记述了他们生前的功德,但是并没有把现世君王的功绩告于先王,以表对祖先庇佑的感激之情。因而,《商颂》也不能和《周颂》比拟,不能作为“颂”的代表。
如此看来,确乎只有《周颂》才是子夏和孔颖达真正讨论的“颂”,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颂” ?“颂”诗的美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孔颖达将“颂”训为“容”,“容”就是“形状容貌”,“美盛德之形容,则天子政教有形容也。”这里的“形状容貌”便是在天子统治下所呈现出来的政治面貌,一般来说,这是一种政通人和、民安财丰的政治风貌,而就是这样一种清明的政治面貌,正属于“颂诗美学”的讨论范畴,是最基本的。其次,“颂”还“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封建社会的人们深受“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观的影响,认为君主之所以能承业即位,而在君主的治理下之所以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除了君主本人的励精图治以及任贤使能之外,祖先与四方神灵的庇佑也是必要条件之一,所以他们常常通过宗庙祭祀和封禅活动来表达对祖先和神明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在对前人表示敬意的同时也对自我进行勉励,最后便是希望祖先和神明能够持续降福于人间,以表祈祷之意,上述种种特殊的情感也属于“颂诗美学”的范畴,是更深一层的。最后,无论是描绘先王的功业以表歌颂之情,还是陈述后王的成就以表承袭之意,抑或铺叙祭祀祖先神灵的盛大场面以祷告和自勉,种种面貌以及情感背后,隐藏的是中国古人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观念——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精神层面触及中国人的品格和灵魂,这是“颂诗美学”最深刻的一个层次。上述所言的三个方面可以简单概括为“美容”“美情”“美神”,下文将根据作品具体分析:
美容。“美容”大约与屈原所追求的“美政”理想相当,是一种君臣相谐、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面貌,君主的高尚品德是这样一种政治面貌出现的必要条件,因此也属于“美容”的范畴。《周颂》中有:
《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1]1271
《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行,子孙保之。[1]1262-1263
《时迈》: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1]1269-1270
《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1]1266
这四首颂诗分别写的是周始祖后稷、古公亶父同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的功绩。后稷播种百谷,养育万民,德配于天;亶父率族人迁于岐山之下,开荒拓土,具有建国之功;文王庚继为之,让险阻之岐山变为平易之道;武王替天行道,讨伐商纣,使天下太平;成王执政时则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勤勉于朝。寥寥数语,便将一代代明君的丰功伟业概括得如此简洁而翔实,也让人们看到了周朝初代君王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伟大品格以及在他们统治之下呈现的太平盛世。
美情。颂诗所表达的对祖先神明的歌颂、敬仰、感激之情自无须多言,因为这往往以陈述先王功绩的方式从侧面进行描写,读者在阅读时各自体会即可感知,而不至于详细表述。值得注意的是,《周颂》中有不少直陈自勉和祷告之情的篇章:
《维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1]1258-1259
《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1]1290
《雝》: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1]1285
《载见》: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绥以多福。俾缉熙于纯嘏。[1]1286
前两篇都有自勉之情,《维天之命》写周王后代在祭祀文王时,感念文王的美好德行和美政善道,立志要继承文王的德行并将之发扬光大,《敬之》则是成王想到天上的神明无时无刻不在察看世间,监视帝王的言行,因此而心生敬畏,同时生发自我警醒之情。后两篇则分别是武王祭祀文王和成王祭祀武王时,祷告求福的乐歌。他们在篇末都表达了自己的虔诚祈祷之心,期望先祖可以持续降福人间,使周族子孙健康长寿,使周朝统治永保太平。
美神。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表层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能体现出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最关键的是,它能展现出让整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颂诗便是如此,它最突出的理念和精神便是“以德配天”以及“敬德保民”,《尚书·蔡仲之命》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周王朝的统治者和前代统治者一样敬重神明,深信“得道者天助,失道者寡助”,认为总有类似于西方世界“上帝”的神灵在时刻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因而他们坚信若实行美政德治,则会得到神明的庇佑,相反,若是暴行虐施,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颂诗就将周朝统治者的这种信念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大兴祭祀活动,表达对先祖的敬仰之情以及对山川神明的敬畏之心,同时向他们陈述自己在位时的功绩,表明自己励精图治的决心,以祈求祖先神明的降福。从某种意义上讲,周王朝的统治者不仅仅看到了鬼神,也注意到了人民,虽然颂诗并没有直接提到黎民百姓,但是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君王的言行举止、性格品德对于人民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水平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若是周王因自觉受神明的制约,保持高尚的德行,鼓励发展农耕,那么这何尝不是“保民”的一种方式呢?何尝没有体现“保民”的观念呢?
三、颂诗美学的影响
文学上,就内容来看,后代颂文学的基本内容还是歌功颂德,“歌颂”和“赞美”仍然是颂文学的主题。但是事实上后代的“颂”已经和《毛诗正义》中的“颂”有比较大的差别,《诗经》中的“颂”是祭祀乐歌,仅仅歌颂君主的丰功伟绩,而后代的“颂”则不限于此,拥有了更宽泛的表现范畴,它们不单单为祭祀抑或封禅活动服务,它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歌颂任何东西,一件青睐的物品,一个敬佩的人,一段辉煌的历史,都可以是“颂”的对象。就情感来看,后代颂文学所要表达的情感主要还是歌颂和敬佩之情。但是后代颂文学所要表现的情感会比《诗经》中“颂”诗所要表现的情感更加丰富,有些文人愿意在“颂”中代入个人化的情感,借咏他物或者他人的经历来表达个人化的情感,比如屈原在《橘颂》中表坚贞不屈之意,牵秀在《彭祖颂》中表高蹈隐逸之情。无论如何,《毛诗正义》中“颂”内藏的美学意蕴就好像是颂文学这座大厦的基石,它鼓舞着后代的文人不断地从内容、形式、文词、情感、思想等方面开拓创新,为这座本来质朴简陋的大厦添砖加瓦,让它变得辉煌夺目。
政治上,《毛诗正义》中“颂”强调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观念在封建社会自有供它生生不息的土壤,它也因此拥有了自身稳固的根基和绵长的血脉,后世君王依靠这种思想和信念维护了自身的统治,一方面使得百姓相信自己承命于天,让自己对国家的统治变得合理化乃至神化,百姓因此而心有顾忌,不敢随意质疑皇帝的地位和统治。而另一方面,这种思想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又给予君王以心理暗示,每当国家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君王总会联想到是因为自己德行有亏,祖先神明才会降灾于民,作为对自身的警醒和惩罚,每当此时,君王便会下诏罪己,向上天和百姓忏悔自身的罪过,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锐意革新的北魏孝文帝等皇帝均曾下诏罪己,这本质上其实是缓和社会矛盾的欺骗性策略,但这种对神明的敬畏确乎在一定程度上让君王自觉责任重大,不敢肆意妄为,所作所为皆有所制约,中国的封建统治之所以能如此长久,不能说没有此种统治思想的助力。
参考文献: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王世舜.庄子译注[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3]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4]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7.
作者简介:
赖诗烨,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