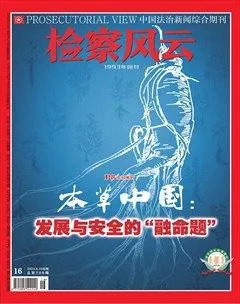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法治观察

中医药历经了千百年实践传承,博大精深,反映了我国人民独特的生命健康观和疾病防治观,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我国重要的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资源,关乎人民健康、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
当下,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呼唤更有力的法治保障。这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更需要知识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保护制度和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协同保护。本文将重点对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发展的现状、难点进行分析,并提出思考与展望。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分析
2021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提出“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指出“推动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202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内容涵盖对中医药专利、商业标志、商业秘密、著作权的保护,强调要严厉惩治中医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将中医药特色与改革相融合,将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上升到完备的法律规范层面。
在著作权制度保护层面,我国政府对中医药古方的挖掘、整理和编纂工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部曾于2007年开展过“1100种中医药珍籍秘典的整理抢救”的项目工作。对传统中医药知识进行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的作品若能够体现作者的独创性,则可依法获得著作权保护。
在商标权制度保护层面,商标权在中医药老字号及道地药材的保护上尤为重要。中医药老字号是拥有世代相承的中医药产品、中医技艺或独门中医药秘方并具有良好信誉的中医药商铺品牌,典型代表有北京“同仁堂”、广州“潘高寿”等。老字号具有商号和商标的双重功能。根据《商标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若在企业名称中出现他人注册的商标或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字号使用,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道地药材是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和条件下种植的传统中医药材,如“川贝母”“杭白菊”“宁夏枸杞”等,其疗效远优于其他地区所产的同类药材,具有很强的地域属性。依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或者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可使道地药材获得地理标志保护。
在专利权制度保护层面,结合中医药的特性,中医药发明专利的申请类型多为中医药复方及中医药提取物等产品发明,方法发明次之,用途发明较少。中医药复方是指改变用药种类和剂量形成的组合物,其功效相去甚远,这也是申请专利的关键所在。中医药提取物是指通过不同提取设备和方法对中医药中的活性成分进行提炼得到的有效单体,若提取物成分复杂,则保护程度有限,需要进一步描述其工艺参数来申请专利。中医药材炮制方法、中医药制剂方法、提取中医药材有效成分的方法等均可以依法申请方法专利的保护。此外,中医药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对中医药保健品、中医药化妆品和中医药制药器械等专利申请。通过申请专利的方式能够使中医药智力成果获得有效保护,并能够使相关中医药知识的利益开发最大化。
在商业秘密制度保护层面,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商业信息,使传统中医药的商业秘密保护更为全面。此外,我国还创制了国家秘密中医药秘方保护制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保密局联合颁布的《中医药行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明确规定了中医药领域的绝密级、机密级、秘密级具体范围,提高了对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医药方剂成分和制备生产工艺的保护力度。商业秘密保护所特有的保密性和稳定性,使其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中成为颇受欢迎的一种选择。
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其他保护制度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医药兼具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五大资源价值,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同时又是现代医药技术创新的源泉,中医药现代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医药文化保护和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三者之间存在交叉关系。中医药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保护,基于其创造的或者与其相关的现代智慧创造成果受到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其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知识表现形式之一还应受到专门立法保护。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难点探究
从理论角度看,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以激励和保护创新为宗旨,赋予身份明确的主体在一定期限内的垄断性权利,难以完全适应中医药的传统性、集体性、延续性等特征。而在实践中,中医药在有些情况下难以达到著作权的原创性要求和专利权的新颖性要求,商标和地理标志的保护对象和保护效力都极为有限,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商业秘密保护与传承、利用的目的之间存在一定协调困难,还需探索更有效的保护模式。
具体到中医药著作权保护中:第一,中医药大都源于生活、医疗实践,是代代相传的既有文化表现,判定原创性存在难度。第二,部分中医药早期皆由集体智慧发展而来,有的年代久远,著作权人查证困难。第三,著作权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而中医药许多秘方并不以著作形态表达,无法得到著作权保护。第四,中医药是活态的项目,往往伴随日常生活持续发展,较短的保护期限显然对中医药的保护不利。
具体到中医药专利保护中:比如,在现行专利制度的授权标准下,在古代经典医史古籍中有所公开的中医药可能难以满足新颖性;中药由于成分复杂难以界定其发生反应的化学式,使得其创造性难以判断;实用性要求药品能够制造并且使用,具有再现性,而中医药讲究辨证施治,个体差异大,难以满足实用性要求。又如,中医药专利保护制度在侵权认定方面存在局限。不同于大多数西药都有具体且相对单一的化学结构特征,中药大多是复方,致使中药的技术特征不够明晰,与西药专利相比,保护范围不够明确,从而使得侵权认定更加复杂;由于中药药物成分和化学反应的复杂性,其制备技术和相关配伍都很难被准确地分析,一旦发生侵权,很难界定侵权方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专利独立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的区别,侵权责任难以确定。此外,从中医药专利申请的实践来看,中药企业对中医药相关专利的运营以及专利布局缺乏重视,加之中医药配方保密等客观原因,中药专利申请积极性并不高。
中医药法律保护应坚持“守正创新”。
具体到中医药商标保护中:第一,中医药企业品牌意识淡薄,企业对利用注册商标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的积极性不高。第二,部分中药商标设计简单、随意,无法体现中药产品的特性,也无法体现中药商标的识别功能。第三,对道地中药材保护力度小。我国的道地中药材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对这些道地药材进行商标注册的却很少,出现了很多假冒道地药材的情况,从而使得行业的利益受到损失。第四,药品名和商标相互混淆。有些企业不注重对自身商标的宣传和使用,反而突出使用商品通用名称的现象,使得企业自身营建良好商标声誉难。
具体到中医药地理标志保护中:运用地理标志制度可以在保护道地药材方面起到规范中药材市场的作用,但实际中却在解决道地药材的名称权问题、保护道地药材的种质权和专有技术问题、保护道地药材所蕴含的多重市场价值、适应道地药材产区变迁的客观需要等方面存在难点。

具体到中医药商业秘密保护中:中药成分极为复杂,相比其他技术主题而言,能够进行反向工程可能性极低,因此,商业秘密保护对于中药而言不失为一种较为适用的方法。然而,当前与“中药保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仅仅在于明确了概念、范畴、基本要素等框架性内容,尚未形成实操性的指引。在实践中,中医药商业秘密保护多是家族性传承或师徒传承,对于能够对簿公堂的保密措施、商业价值等保护证据,鲜有相关合乎诉讼要求的素材支撑。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展望
在健全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层面,探索建立中医药专利的专门审查评价体系。在现行《专利法》下,从内部建立中药专利专属“专利性”审查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中药专利创造性领域专家评审机制,增加领域内专家组联合参评会诊机制;扩充中药专利专属审查体系,扩大ea578e285ac9aeacaa573f98ce736cc0中医药专业背景的专职审查人员;相关部门增加与国内知名中医药产业主体的交流质量和频次。
不断提升中医药商标的品牌影响力。商标质量是产品形象的关键,具体到中医药更是意义重大。设计中医药商标要从产品底蕴和企业历史出发,体现出中医药的文化精髓,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象征。当前应进一步重视区别管理与全面登记,充分发挥老字号的文化价值和品质效应,将一些老字号申请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明确老字号的使用范围,规范中医药老字号的品质。可以通过加大对中医药老字号和中华老字号的培育力度,把真正有品质的药企品牌做大做强,不断提高商标的知名度。
探索建立中医药处方注册登记制度,创设创作专用权。中医药传统处方作为中医药体系的重要内容,其特点不同于现代医学处方,对于那些确有疗效、药味组成或治疗方法相对稳定的临床处方,可以实行介于专有权和补偿权之间的“有限著作权”的特殊保护措施,相应调整降低中医药处方的著作权认定要求及著作权人权利。同时,建立中医药处方注册登记制度,并专门设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形成开放性中医药处方数据库与中医药标准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国际经验,创设以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为主要内容的创作专用权,通过国家所有权制度赋予国家知识产权权利主体资格。
以公、私法相结合方式对中医药进行商业秘密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可以将某些不符合申请专利的创造性要求的技术,在不公开其技术秘密的前提下进行保护。商业秘密中所要解决的主要困难是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的界限问题。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可以把私法层面上的权利规范化管理,把可以自由交易的信息予以行政化管理,保护中医药及知识的同时促进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中医药的流转和发展。中医药的商业秘密保护应进一步重视私权,逐渐构建以私权作用为主、公权力监督管制作用相结合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
在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层面,不断加强对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构建的理论研究,加快对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相关条例的起草研究与完善工作。遵循中医药传统知识自身规律,建立符合中医药传统知识特点的保护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利用中医药传统知识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围绕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传播等内容设计条款;处理好与现行法律的关系,在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层面,《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外商投资法》等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可不再重复规定。
同时,推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与专利审查机制的衔接。通过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对依法登记的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管理。建议参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印度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建档;印度政府建立了传统知识防御性保护制度,通过构建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进行保护。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确立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在线权益”,与专利审查相衔接,防止不当授权。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鸣谢第二届亚太生物医药知识产权创新峰会对本刊选题策划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