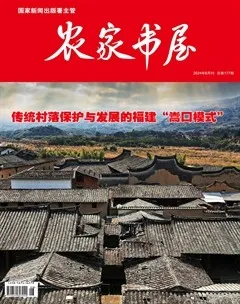《如风似璧》:芥子纳须弥

有一种说法是某一类的文章40岁或者50岁之前不要写,主要是指人的认知过程需要时间的沉淀,对一个素材的理解和把握很可能与最初想表达的意念完全不同。这也很好理解,有时候灵感翩然而至,但将其变成扎实的作品可能需要艰辛的水磨功夫。
我以前写过一些关于广州的都市小说,一直觉得自己很熟悉这座城市。不知从何时起,我很想写一部独具广州特色的小说,但是怎么写居然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浮在表面的元素很多,但是什么是广州人的精神内核却模糊不清。就像京派小说中的骆驼祥子,或者类似海派小说中的《上海的早晨》与《子夜》,那么反映广州人生活的载体是什么呢。
又如京派小说中强大的文化背景,海派小说中鲜明的城市情调,像广州这样一个千年商都,它的底色又是什么呢。
有一次我跟陈小奇聊天,我说你们音乐人那么努力,为什么永远超越不了《彩云追月》《步步高》《雨打芭蕉》这些前辈作品的高度呢。陈老师说那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全是讲自然景观或者丰收景象,当然还有那个年代的人文精神,的确是一座高峰。现在时代不同了,当然需要寻找匹配的主题,同时也要从相对单一走向丰富多彩。他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就是要在具象中彰显特色。
你看当年的广东音乐,它是有魂的,所以成为经典曲目流传至今。而我们今天的诸多广州元素已经琳琅满目,如满洲窗、广式园林、茶楼、生猛海鲜、粤剧、醒狮、赛龙舟、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等。但是人呢,关于具体的而不是概念的人的生活、故事和神采又在哪里。这才是最难的。
像广东音乐,哪怕是全部写景的曲目,都具备了人的情感,欢喜、相思、庆丰收、依恋、伤春悲秋,更有《双星恨》《杨翠喜》这样的曲目直接表达了对人物命运的惋惜与担忧。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名曲被广为流传。
人,人的情感,人性的复杂与幽微才是一部文艺作品的骨架。
芥子,当然是指其微小,而须弥山则是指古代印度传说中的大山。在我看来写作的精髓无外乎以小见大,以渺小的个体显现伟大的精神。
如果用佛家的话来说,它们是等量的。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我的芥子,这个过程是极其漫长的,也是对我写作生涯的严峻挑战。
后来我选择了1932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的广州,因为民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谓上流社会大多由军阀和买办构成,社会风气是异化加变态,表面攀龙附凤、极尽奢靡,实则毫无自立能力,基本是用金箔包裹腐朽。
任何小说都需要一个舞台,然后各色人等粉墨登场。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有书写当下中国无尽的寓意。那么,广州沦陷前后的社会是大起大落、动荡不安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时代,从繁华浮夸、纸醉金迷直接坠入黑暗、战乱、血腥、人性之恶与无奈的万丈深渊。
在这样绝望的背景下,我写了三位平凡的女性。
这些故事避开了以往这一类题材的套路:第一不是比惨。第二不是走投无路参加革命。第三不是“富人都是大坏蛋”,只有穷人才是又好又善良,对人的书写就是平等对待。第四她们都是凭借一己之力变成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因为指望不上任何人。
当然也是传奇,因为那样一个时代给女性留下的空间狭小而昏暗。她们只能在男人世界的缝隙里寻找出路,有得到,有得不到,还有的得到了大家觉得好、自己并不想要的结果,这正是女性一直面对的课题。这也暗合了当下对女性主义争论不休的严肃讨论。
说回广州的底色,长期以来,我一直被困在宏大叙事中找不到出路,后来放下身段找到了“美食”这个元素,因为你说广州人讲文化讲情调那是鬼都不信的,但是广州人讲吃那简直全民会意可以用眉毛交流。说到人物的精神内核,如果北京大妞是飒,上海小姐是嗲,那么广州女人就是韧,坚韧的韧。
同时我也放下了家国情怀和史诗情结,因为我不是一个能够驾驭大题材的作家,而广州又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市井城市,当年王为一老师执导的《七十二家房客》绝对是精准抓住了作为升斗小民天堂的广州的风貌,在这一类的题材中可谓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打通关节,想明白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进入创作状态。状态,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它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基调、叙述方式、语言和妥帖程度。
如封似闭,是吴氏太极拳的第九式,呈马步、双手收回后再推出。很能反映出广州人的低调、隐忍、有力道而不喜张扬的个性,以至于咏春、叶问出现在广东是不奇怪的。
最终确定书名《如风似璧》,是表达我对广州和广州女人的认知、理解与写照,她们一如风中的玉佩,既有风的凛冽又有玉的圆润。
感谢广州这座伟大的城市,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是千言万语,是百转柔肠,是我们心中的景仰与豪迈。
(来源: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