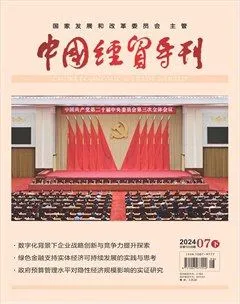社保标准对移民工人的适用效力及其实施路径
摘要:全球化推动了劳动力跨国迁移,这使得移民工人的社会保护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保标准对于移民工人而言,具有明确的适用性,而这种适用性主要通过国内立法、国际合作以及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来实现。其中,经济发展为移民工人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社会保护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撑和路径。
关键词:社保标准;移民工人;适用效力;实施路径
引言
社会保障不仅是一种避险措施,更是一种经济行为。作为避险措施,社会保障能够确保人们在面临疾病、残疾、生育、工伤、失业、年老或死亡等风险时,收入不会停止或大幅减少,从而防止普遍贫困和社会排斥。作为经济行为,社会保障是一项对人民具有显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投资,它赋予人们从不断变化的劳动市场中获益的能力。社会保障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和推动力量。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它能够有效缓解经济下滑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冲击,促进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然而,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享有社会保障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实际上,全球仅有45%的人口能够享受到至少一项社保待遇,而剩余的55%的人口则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社会保护[1]。在这些人口中,移民工人是一个重要的特殊群体。据估计,全球有超过8000万经济活动移民[2]。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在外国领土内工作的劳务人员将近93万人。此外,中国科技部部长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透露,2018年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万人[3]。因此,为移民工人提供充分的社会保护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保标准,其初衷主要是调整成员国的国内社保关系。那么,这些标准对移民工人是否同样具有适用效力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标准又是通过哪些途径在移民工人群体中得以实施的呢?下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社保标准对移民工人的适用性
社保标准除个别例外情形,如要求同为公约批准国、以互惠为条件等,原则上均适用于移民工人。理由如下:
(一)覆盖范围界定
几乎所有社保标准所界定的覆盖人员范围均包括了移民工人。如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号)规定,医疗、疾病、失业、老龄、工伤、家庭、生育、残疾、遗属九项津贴的受保护人应含规定类别的雇员,或规定类别的经济活动人口,或规定类别的居民,而不论其国籍如何。1982年《建立维护社会保障权利国际体系公约》(第157号)规定,各会员国应保证受益人获得老年遗属津贴、工伤职业病年金以及残疾补贴,而不论受益人是否是一会员国的国民,也不论其居住地点在何处。1967年《残疾、老年和遗属津贴建议书》(第131号)、1969年《医疗和疾病津贴建议书》(第134号)均规定,本建议书所称的“居民”是指在会员国领土上正常居住的人员,不论其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均在社保标准覆盖范围之内。
(二)待遇平等条款
几乎所有社保标准都含有非本国工人与本国工人待遇平等的条款。如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号)不仅对非本国居民与本国居民的社保平等待遇作了规定,而且把平等待遇覆盖于医疗、疾病、失业、老龄、工伤、家庭、生育、残疾、遗属九个传统社保分支。1964年《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第121号)规定,各会员国应在其领土上确保非本国居民在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方面与本国居民享有同等待遇。1925年《事故赔偿同等待遇公约》(第19号)和1962年《(社会保障)同等待遇公约》(第118号)更以“同等待遇”为公约之名,专门规定移民工人的社保同等待遇。
(三)专门移民标准
社保标准中还有一些专门针对移民工人的社保规定。如1949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第97号)规定,凡本公约业已生效的会员国承诺,对本国领土内的合法移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在社保方面实行不比本国公民更为不利的待遇。1975年《移民工人公约(补充规定)》(第143号)规定,在移民工人于某会员国无法获得正常地位的情况下,赋予该移民工人享有原来就业所赋予的社保平等待遇权和社保申诉权;公约业已生效的会员国应积极采取包括颁布法律在内的措施,有效保护移民工人的社会保障权。1975年《移民工人建议书》(第151号)规定,凡其地位不合法或未能合法化的移民工人,应当享有目前就业或过去就业赋予他们及其家属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平等待遇权。
(四)监督机构实践
国际劳工组织负责实施公约与建议书的监督机构通过实践证明了社保标准对移民工人具有明确的适用效力。作为监督机构的专家委员会,其监督公约实施的主要方式是发布“评论意见”。举例来说,针对埃及工人因海湾战争而被迫回国但未领取工资的情况,专家委员会在审查1949年《工资保护公约》(第95号)的实施情况后,于2001年年度报告中发表了“评论意见”,明确指出:第95号公约适用于所有工人,包括移民工人,不论其国籍或身份如何。鉴于公约现行条款在处理移民工人工资支付问题上的不足,专家委员会建议考虑对公约进行修订。
同样,在监督1964年《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第121号)及1969年《医疗和疾病津贴公约》(第130号)的实施情况时,专家委员会在“评论意见”中强调:这两个公约的批准国应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在国家政策框架内,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进行协商,制定并执行一项社会政策,确保移民工人不被排除在任何已通过的国家社保最低标准之外。
(五)人类共享人权
社会保障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当然也是移民工人应享有的权利。社会保障的普遍性人权属性已被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法庭的判例所充分证明。国际劳工组织1944年《费城宣言》明确指出:全人类,不论种族、信仰或性别,均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的条件下,以及在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基础上,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同样宣示:人人有权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见解或其他主张、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差异,均不得作为限制或剥夺这些权利的理由。联合国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各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此外,泛美人权法庭在2003年发布的一项裁决中指出:社会保障权应普遍适用于包括所有移民工人在内的所有居民,不论其国籍和移民地位如何。这一观点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保障权的普遍性和无差别性。
二、移民工人社保标准的实施路径
(一)国内立法
社保标准在一国境内的实施,依赖于各会员国制定相应的国内立法进行转化和落实。国内立法是确保移民工人社保标准得以实施的基本途径。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为移民工人制定的社保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2011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2011年人社部发布的《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及随后发布的《关于做好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201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5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这些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将移民工人纳入社保体系,但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在移民工人社保国内立法方面的发展仍显滞后。
首先,这些国内立法的层级在一定程度上较低,多数是以部委“办法”或“通知”的形式发布,缺乏足够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其次,这些立法在各地的落实规定存在较大差异,缺乏一定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再次,移民工人的参保率普遍较低,根据2013年的数据,在中国工作的60万外国人中,仅有33%的人参加了社会保险[4]。此外,对于移民工人中的特殊群体,如家庭服务和护理工人、建筑工人、非正规就业工人等,他们的社保问题尚未得到国内立法的充分关注和解决。最后,目前移民工人社保法律适用主要依据属地法原则,然而,这一原则主要基于本国工人的生活情况制定,未能充分考虑移民工人社会保障的特殊性,导致其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
(二)国际合作
社会保障的国家性质以及各国社保制度的差异性,给移民工人社保带来了重大挑战。因此,社保国际合作成为协调移民工人社会保护的重要工具。国际合作主要有两种方式:
(1)缔结双边协定。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已与德国、韩国、丹麦、芬兰、加拿大、瑞士、荷兰、西班牙、卢森堡、法国、日本、塞尔维亚12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定。尽管双边协定在协调移民工人社会保护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一是主要集中在双重缴费豁免上,缺乏关于转移接续和缴费累计的具体安排;二是仅涉及养老、失业保险的豁免,未涵盖医疗、生育和工伤保险的豁免。这表明双边协定仍有向更广泛领域、更高层次发展的潜力。
(2)建立区域框架。当前劳务移民呈现出新特点,以亚洲为例,劳动力多数在近邻或区域内国家间流动;劳动力迁移中女性比例上升;非正常移民或不合法移民数量增多;劳动力迁移多由私人中介组织。这些新特点表明,移民跨国流动的无序性是制约移民工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与采取个别移民输出国与个别移民接纳国的双边行动相比,建立一个经过三方协商的、具有指导性的、以权利为基础的区域性框架,以应对移民流动的无序性,具有显著优势。构建区域性社保框架的核心内容应包括实现劳务移民管理的区域联网,并通过制定保护移民工人的行为准则来确保其实施。
(三)经济发展
为增强社保标准的实效性,国际劳工组织宪章设立了监督机制。依据此机制,若会员国未能遵循调查委员会或国际法庭关于履行公约义务的建议或裁决,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可向国际劳工大会提出“合理且恰当的行动”建议。然而,宪章对于“合理且恰当的行动”的具体定义并未明确阐述。若考虑武力制裁,这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因此不可行;若采取经济制裁,这通常被视为霸权主义行为,也不应被采纳。
既然不能诉诸武力或经济制裁,那么“合理且恰当的行动”更可能是道德谴责或其他非强制性的外交手段。然而,仅凭道德谴责,其实际效果确实值得质疑,这也是劳工组织常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即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我们认为,提高社保标准实效性的关键在于:切实帮助那些难以实施社保标准的成员国发展经济,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任何社保制度都难以真正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在监督过程中,若忽视“特定国家的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无异于削弱了社保标准的实效性[5]。
试想,如果一个国家连本国国民的基本社保需求都难以满足,又如何能为外国人提供有效的社会保护呢?在这方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为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保平等享受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和实践范例。
三、结论
社会保障不仅是一种避险措施,也是一种基本人权,还是一种经济行为。全球化促进了劳动力的大量跨国迁移,而劳动力跨国迁移又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移民工人的社会保护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社保标准的覆盖范围界定、待遇平等条款、专门移民标准、监督机构实践、人类共享人权5个方面看,社保标准对移民工人具有适用上的效力。这种适用上的效力具体通过国内立法、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的途径来实现。但从社保运行实践看,经济发展是移民工人获得全面社会保护的根本路径。
参考文献:
[1]国际劳工组织.争取社会正义和公平全球化的社会保护底线:2012年国际劳工大会第101届会议报告四(1)[R].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11:6.
[2]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经济中为移民工人谋求公平待遇:2004年国际劳工大会第92届会议报告六[R].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4:5.
[3]新华社.逾95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EB/OL].(2019-04-14).https://www.gov.cn.
[4]房连泉.改善中欧移民工人的社会保护状况[R].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2019:13.
[5]春林.发达国家的“农民工”社会保障[J].中国社会保障,201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命运共同体理念下跨国工伤保险丝路万民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9XFX015)〕
(作者简介:李刚,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璐洋,喀什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