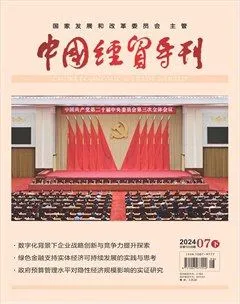财政预决算偏离度视角下政府预算管理水平对隐性经济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政府预算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保障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预决算偏离度视角研究中国政府预算管理水平、隐性经济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政府预算管理水平对隐性经济规模的影响效应。通过截取2007—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预算管理水平与隐性经济规模负相关;城镇化率(负相关)和政府管制水平(正相关)是影响隐性经济规模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政府预算管理;隐性经济规模;预决算偏离度
引言
政府预算在反映政府活动的同时,也体现社会公众对政府活动的监督,对国家治理有着巨大影响。政府预算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预算执行的有效性,对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防范财政风险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隐性经济作为一种非正式经济活动,其规模反映了经济体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不仅对就业、社会稳定和财政收入等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也对国家治理和预算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我国政府预算管理中仍存在诸如预算管理和控制方式不够科学、预算体系不够完善、预算透明度较低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经济良性运行。政府预算管理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影响隐性经济的规模和发展,而隐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会对政府预算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现有文献研究中主要集中于预决算偏离程度研究和隐性经济规模研究两个方面。研究有关财政预决算偏离度与隐性经济规模关系仍然较少[1]。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政府预算管理水平和隐性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机制。通过研究政府预算管理水平、隐性经济及其相互关系,提高政府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一、指标选择与基本假设
(一)指标选择
1.地方财政收支预决算偏离度
财政预决算偏离度,作为衡量预算编制与执行效能的关键指标,直接反映了政府预算管理的专业性和精准度。具体而言,较低的预决算偏离度意味着政府在预算管理上的高效与精准;反之,高偏离度则暗示预算管理可能存在的疏漏与不足。参照国际预算调整的普遍标准,理想的预决算偏离度应控制在5%以内,这一数值越小,预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便越高。在数据选取上,本文以《中国财政年鉴》中相关年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决算收支数据为基准,采用如下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我国财政预决算偏离度2007年至2021年总体较高,特别是财政赤字偏离度;地方本级财政基本呈现出“超收节支”的普遍特征,国家级财政呈现出“超收超支”的基本特点,收入偏离度较支出偏离度更高。只有西藏(12.37%)、内蒙古(9.05%)、宁夏(8.68%)、陕西、四川、重庆、安徽、山西、甘肃九省区收入偏离度高于5%;河南、江西、黑龙江、贵州、广西五省区收入偏离度高于国家财政收入偏离度(4.29%),其余各地财政收入预算管理水平较好。就财政支出预决算偏离度而言,仅有上海、安徽、河南、新疆、贵州五省区偏离度低于5%,其他26个省市支出偏离度均在5%—15%间。
2.隐性经济规模
现有研究文献中,主要应用收支差异法测算各地区隐性经济规模及全国隐性经济总体规模[2]。隐性经济规模=100%×居民隐性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其中:(1)居民隐性收入=居民消费支出+居民投资支出-居民统计收入;(2)居民投资支出=居民手持现金额+居民储蓄增加额+居民股票债券持有增加额+居民实物投资增加额;(3)居民消费支出=地区年末常住人口×人均消费支出;(4)居民手持现金额,参照李永海等(2016)的相关做法,以流通中现金(M0)的70%计算,各省数据以当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分解权重进行计算;(5)居民股票债券持有增加额,以历年证券市场境内发行金额的60%计算,省级数据采用各省生产总值进行权重分解得到;(6)居民实物投资增加额,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经济的投资额来表示;本文对2006—2017年个体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与地区生产总值权重分地区回归,并以此估算2007—2021年个体投资金额;(7)居民统计收入=地区年末常住人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数据库。
2007—2021年我国隐性经济规模有明显地区差异,仅有12个省市规模小于全国水平(7.69%);西部地区隐性经济规模普遍较大,其中青海(14.86%)、新疆(12.03%)、陕西(11.78%)、四川(11.20%)、宁夏(11.15%)五省区隐性经济规模高于10%;东部地区隐性经济规模普遍较小,其中辽宁(3.96%)、浙江(4.61%)、上海(4.84%)、山东(4.97%)四省隐性经济规模低于5%。
(二)基本假设
预决算偏离度作为反映政府预算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与隐性经济规模有重要关联。一般而言,较低偏离度意味着较高预算管理水平和较低隐性经济规模,而高偏离度则说明政府预算管理水平较低、隐性经济规模较大。作为国家财政管理的重要手段,高水平的预算管理通常意味着更稳定的财政政策、更规范的财政征管、更合理的财政规划以及强有力的法律监管框架,进一步影响市场主体在正规经济和隐性经济中的选择。现有研究证实,隐性经济规模与税收负担间的负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基本假设1。各地区预决算偏离度均为正值,即地方政府为完成当年税收计划超额征税。偏离度越高,意味着经济主体面临的计划外税收负担越重,从正规经济活动转入隐性经济的可能增大。
H1: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度越高,隐性经济规模越大。
地区级财政支出预决算偏离度均为负值,说明地方政府在支出方面积极性欠佳。造成“节支”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节省本级支出以寻求更多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保持收支平衡,导致地方财政难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公共需求及偏好,进一步导致部分正规经济转入隐性经济。基于此,本文提出基本假设2。
H2:财政支出预决算偏离度越高,隐性经济规模越大。
在探讨我国财政状况时,本文发现除个别地区特定年份外,多数地区财政支出普遍超过当年收入,形成财政赤字。这种赤字现象在“超收”与“节支”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往往导致决算时的财政赤字额远低于预算时的预期。基于这一观察,本文提出了基本假设3,以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经济逻辑与影响。
H3:财政赤字预决算偏离度越高,隐性经济规模越大。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选取
本文参照已有文献[3],选择面板数据模型:
SEit=α0+βFBDit+γControlit+μi+νi+εit
其中,SE表示隐性经济规模,FBD表示财政预决算偏离度,Control表示与隐性经济规模相关的一组控制变量,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黏度,表示常数项,和表示系数矩阵,和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变量,表示随机误差项。由于隐性经济成因众多,为获取更可靠的估计结果,本文选用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1)税收负担(TX),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正规经济税负过重往往是经济主体从事隐性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假定其与隐性经济规模正相关。
(2)政府管制水平(GOV),用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表示。政府管制水平越高,意味着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越完善,能够有效抑制隐性经济活动,因此,本文假定其与隐性经济规模负相关。
(3)人均生产总值(PCGDP),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平均指数表示。人均生产总值提出了人口规模的影响,能够有效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国内外相关研究均显示正规经济发展水平同隐性经济规模负相关,因此,本文预期其与隐性经济规模负相关。
(4)城镇化率(UR),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区域间发展越均衡,居民参与隐性经济活动的意愿越低,因此,本文预期其与隐性经济规模负相关。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7—202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全国的面板数据,隐性经济规模和预决算偏离度数据由前述方法得到,其他数据分别来自《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所有数据均为相对指标。
(三)实证结果
首先,本文针对各个模型实施了Hausman检验,其结果在95%的置信水平下,均支持为模型1至6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这些模型的估计效果均表现良好,且变量符号与预期相吻合。其中,模型1、3、5作为基准模型,而模型2、4、6则特别探讨了财政预算偏离度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模型1至6均有效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财政收入的预决算偏离度、财政支出的预决算偏离度以及财政赤字的预决算偏离度,与隐性经济规模均呈正比。特别是,财政收入的预决算偏离度通过了严格的1%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的“超收”行为显著推动了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张。然而,财政支出预决算偏离度虽表现出较大的系数,但在基准模型与实证模型间存在差异,表明政府的“节支”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对隐性经济规模有正向影响,但整体影响相对较小。至于财政赤字预决算偏离度,其系数较小,表明其对隐性经济规模虽有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4-7]。
此外,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虽呈正相关,但效果不显著;政府管制水平与隐性经济规模正相关,揭示了当前高管制水平可能促使经济活动转向隐性部门;人均生产总值与隐性经济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经济增长虽对隐性经济规模有轻微影响,但并非关键因素;而城镇化率的提高则显著抑制了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张。
三、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2007—2021年我国各地区及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预决算偏离度逐步缩小,但支出和赤字偏离度仍相对较大;结果显示各地区隐性经济规模平均在5%—10%之间,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同时,还发现税收负担、政府管制水平、人均生产总值与隐性经济正相关,而城镇化率与隐性经济显著负相关。为此,首先需要加强预算管理科学化,完善预算体系。政府应加强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和监管等环节的科学化管理,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确保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加强预算控制和监督,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公开度。其次,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财政信息公开。完善财政分权、宏观税负和转移支付等制度安排,使政府预算管理更加规范和有效。提高财政透明度,增强对政府活动的监督。再次,改革税收制度,提高税收征管能力。降低税收负担,减少税收计划与实际收支的偏离,提高税收的合理性和效益。加强对隐性经济的税收征管,减少税收流失,增加财政收入。最后,鼓励创新和创业。在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的同时,加强对隐性经济的监管,减少隐性经济规模。通过以上政策建议的有效实施,有助于提高我国政府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有效应对隐性经济的挑战,促进整体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关注预决算偏离度[J/OL].涉外税务,2008(1):5-6.
[2]陈志刚,吕冰洋.中国政府预算偏离:一个典型的财政现象[J/OL].财政研究,2019(1):24-42.
[3]吕冰洋,李岩.中国省市财政预算偏离的规律与成因[J/OL].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36(4):92-105.
[4]邵进.政府预算管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OL].商业观察,2023,9(32):109-113.
[5]张铭洪,侯笛,张福进.基于因子分析的地方财政支出偏离度监督[J/OL].当代财经,2013(7):23-32.
[6]冯辉,沈肇章.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晋升激励与税收任务[J/OL].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5,30(5):58-68.
[7]冯辉,沈肇章.政治激励、税收计划与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OL].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31(3):27-39.
〔基金项目:西北工业大学2023年本科双一流专业课程建设项目(06530—23GH0104017)〕
(作者简介: 段婕,西北工业大学西部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洪瑞舸,西北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