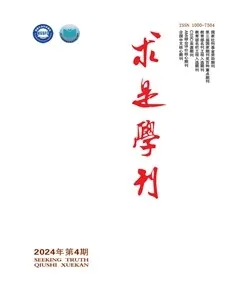中国传统“道-艺”观论要
摘 要:中国传统“道-艺”观对中国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道-艺”二元结构中去认识和处理艺术问题,充分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性。中国传统“道-艺”观既丰富又立体,其中,“道器”论是对本体(本原之道)与实在(艺术之象)之隐显关系的总体归纳;“道贯”论是对艺术创造中“一”与“多”关系的辩证提摄;“载道”论确立了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学“道主而艺从”的文艺认知格局;“同道”论主要涉及文化原型和艺术同构内秘之诠解;“乐道”论表征着中国古代艺术对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之合一的高度提倡。全面了解中国传统“道-艺”观,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艺术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和超越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艺术;“道-艺”观;民族性
作者简介:韩文革,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副编审(武汉 430063)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4.013
“道”“艺”关系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探讨中的一个核心论域。可以说,从“道-艺”二元结构中去认识和处理艺术问题,充分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性,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丰富复杂的“道-艺”观。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仍然停留在体用论层面的“道”本“器”(“艺”)用论以及工具论层面的“文以载道”论上,对中国传统“道-艺”观之丰富性的认识尚不够深入。中国传统“道-艺”观既丰富又立体,涉及文艺领域及文艺活动诸多方面,除了体用论层面和工具论层面的探讨之外,还有审美创造论层面的“道贯”论、文化原型论层面的“同道”论以及审美体验论层面的倡导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合一的“乐道”论。只有对中国古代“道-艺”观作不同理论层面的条分缕析的区分与总结,才能从惯常的认识中获得对古代中国艺术处理“道”“艺”关系的新知,也才能充分了解中国文艺理论在理解世界本原同文艺创造及其特征之关系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民族性、独特性。
一、“道器”论:本体(本原之道)与实在(艺术之象)之隐显关系的总体归纳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是作为世界之本体而存在的,是指自然、社会运行的规律、原理,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本质、本体、本原、本根性概念。如《易传·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①王夫之也说:“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①这些对“道”的理解都是从形而上意义上展开或进行的。“器”则指体现道的实体、运载道的工具。《易传·系辞上》曰:“形而下者谓之器。”又云:“形乃谓之器。”韩康伯注曰:“成形曰器。”②孔颖达对无“形”之“道”与有“形”之“器”的这种形上与形下之别有非常详细的阐述,其在《周易正义》中疏曰:“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③不难看出,老庄哲学中的有无论、《易经》中的道器论以及后世学者对道的理解都有其共同点,即强调有生于无,道统驭器,有形之器运载着无形之道,而无形之道又通过有形之器得以显现,亦即道于无中生有,器于有中寓无。道所具有的超形而不离形的特点在中国哲学中也被反复论说。如老子认为,“道”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且“不知其名”④,故而“道”具有超越普通形器的形而上特征;同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⑤,亦即“道”又具体落实到形而下的普通“物”“象”中。庄子也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信,可得而不可见。……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⑥《管子·内业》对道的描述也是:“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⑦不难看出,老庄及管子等人都充分注意到道与器、物、形、象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中国哲学中的“道器”论落实到艺术活动层面,其核心理念是将道与艺看作是隐与显的关系。那么“艺”以什么来显现“道”呢?中国传统艺术哲学有着惊人一致的回答,即文(象)以明道,文以载道。“文”本义指线条或色彩交错,引申为凡物之美丽而有文采谓之文。在古人看来,天文、地文、人文俱是道的显现。如汉代陆贾即云:“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⑧明代宋濂也说:“人文之显,始于何时?实肇于庖牺之世。庖牺仰观俯察,画奇偶以象阴阳,变而通之,生生不穷,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无遗,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⑨道以文(象)显的思想在《周易》《礼记》等中国古代元典中随处可见。刘师培曾总结说:
昔《大易》有言:“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考工》亦有言:“青与白谓之文,白与黑谓之章。”盖伏羲画卦,即判阴阳;隶首作数,始分奇偶。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奇一偶谓之文。故刚柔交错,文之垂于天者也;经纬天地,文之列于谥者也。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是则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由古迄今,文不一体,然循名责实,则经史诸子,体与文殊;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⑩
如果说《周易》《考工记》等元典中的显“道”之“文”还主要指的是事物的形式美,而尚未专门言及具体的艺术及其创造问题,那么,东晋葛洪即已明确指出文艺形式美的重要性:“筌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因为道是隐匿难见、难寻的,所以作为传道、达道、体道之重要载体的文、文章、文艺就不能视为“小道”或“余事”,因而他进一步断言:“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①相比于葛洪从现实生活经验的直觉中认识到文章作为“道”(与“德”)之“弟”而不能“呼为余事”,刘勰显然对此有着更高的理论综合,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明确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②即“道”是“文”之本,“文”乃“道”之显,显道之文由圣人出,故“文”因“圣”人而有明“道”之大用。刘勰首开的“文以明道”论,借助圣人这一中介把文艺与道的二元对立关系加以弥合起来,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真正建立起“道-艺”二元结构论,嗣后的中国文艺在讨论世界本体与文艺之间的隐显关系时,均不出此樊篱。汤用彤曾就“道”与“文”的关系作过如下精辟的概括:
万物万形皆有本源(本体),而本源不可言,文乃此本源之表现,而文且各有所偏。文人如何用语言表现其本源?陆机《文赋》谓当“伫中区以玄览”。盖文非易事,须把握生命、自然、造化而与之接,“笼天地(形外)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当能“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盖文并为虚无、寂寞(宇宙本体)之表现,而人善为文(善用此媒介),则方可成就笼天地之至文。至文不能限于“有”(万有),不可囿于音,即“有”而超出“有”,于“音”而超出“音”,方可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文之最上乘,乃“虚无之有”、“寂寞之声”,非能此则无以为至文。③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这种道隐艺显的观点无处不在。如唐代徐寅即认为“势”乃“诗之力”,“如物有势,即无往不克”,这是因为“道隐其间”。④清代布颜图在回答弟子何以“常论画山水必得隐显之势方见趣深”这一问题时,认为“所谓隐显者,非独为山水而言也,大凡天下之物莫不各有隐显,显者阳也,隐者阴也,显者外案也,隐者内象也”。在他看来,画潜蛟之腾空、风雨之施行、才士之意趣、美人之丰姿等,均不出“隐显叵测”四字至理和“笔墨浓淡虚实”之法。⑤不难看出,“隐之为体”是古人的基本看法,亦即道因其隐而不可言说,因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⑥。这种观念反映到对“道”“艺”二者关系的看法上,就是强调在艺术创作中要以“神遇”“顿悟”等方式把握那难以言说的创作之道。这在古代艺术理论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自庄子之以“庖丁解牛”喻道技关系后,代不乏人。如南宋严羽论“诗之极致”之其一,谓之“入神”,元代陶明濬曾对此解释说:“入神二字之义,心通其道,口不能言。己所专有,他人不得袭取。所谓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⑦对“入神”的解释说明诗艺达到最高境界绝非言语所能传达。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如清代刘大櫆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⑧章学诚也说:“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综上,在中国古代丰富的“道-艺”观中,道器论是至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是因为它从体用论层面对“道”的形而上本性与“艺”的形而下特征作了哲学上的阐明,并将之落实到道与艺的隐与显之关系的提摄上。围绕“道”之“隐”与“艺”之“显”,中国艺术理论还延展出“道”之“常”与“艺”之“变”、“道”之“无形”与“艺”之“有迹”等诸多相关命题。可以说,“道器”论从本体与实在之总体关系上探讨了艺术同世界本原及其内在规律之间的关系,因而尤其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往往首重“道器”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器”论为古人看待“道-艺”关系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视域,即古人在处理“道-艺”关系时,往往会将之放到形上-形下、无形-有形、不在场-在场、体-用、常-变等二元对立结构中去理解。换言之,“艺”作为万有之显现与“道”作为无形无名的万物所宗之隐匿,二者的关系在“道器”论中得到了全面的理论提摄。有学者对艺术创造中道器关系问题作过这样精辟的理论概括:“综是殊名,以生多故,赋之为物,陈之为彩,情因事以纠纷,事因物而结构,凡言旧事,必识故物。一时之制,百思攸托,一器一道,哲人谨焉。”①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以艺术实在之“象”(形、器、显、用、有等为之异名)去呈现(或描摹、形构、体证)作为世界本体或本原之“道”(隐、体、无等为之异名),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最重要也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理念之一,这一理念不仅具有艺术发生学的本源开示意义,还从本体论角度确立了古人思考“艺术为何”与“艺术何为”两大文艺核心问题的基本路径。
二、“道贯”论:艺术创造中“一”与“多”关系的辩证提摄
在《老子》《易经》《庄子》等中国元典中,“道”常与“行”“达”“通”“贯”等事物的运动特征及其规律相关联,因而道具有周行畅达、完整圆满之特征。换言之,世界万有之起源、本质、德性、原理乃至对其之言说,必以“道”一而贯之。正是由于“道”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且“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②等特征,所以在古人看来,它是万物的唯一原理或形现万有的整体性提摄,因而也必将贯穿事物及其发展的全过程。老子将这种“贯”称之为“一”。《道德经》第三十九章即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③《淮南子·原道训》亦云:“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④庄子将老子的“道贯”论拓展为“道通为一”:“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⑤意即细小草棍与粗大柱子,丑人与美女,或者宽大的、畸变的、诡诈的、怪异的等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从道的意义上讲都是相互贯通而且浑一的。这其中的“一”,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曰:“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⑥也就是说,“一”就是整体,它与“多”(部分或具体)共同辩证地构成了大千世界的基本图景。“道”之贯通可以显现为事物的同类相召。董仲舒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⑦这也可以显现为事物之间相反相成的转化。如王弼在剖析“睽”卦时承接并发展了庄子的“道通为一”论:“至睽将合,至殊将通,恢诡谲怪,道将为一。”⑧这便涉及事物(包括艺术中的美丑)互渗和相互转化的问题。古人在讨论艺术创造时亦将“道贯”论应用于其中。如就散文而言,刘大櫆认为“行文之道”在于“神为主,气辅之”,因为“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⑨这就是说,优秀散文的“行文之道”在于“神”与“气”始终贯穿于创作的各个环节直到作品的最终完成。就诗歌而言,陆时雍认为“诗道”归纳起来不外乎遵循“情真”和“韵长”两个基本准则:“诗之可以兴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韵也。夫献笑而悦,献涕而悲者,情也;闻金鼓而壮,闻丝竹而幽者,声之韵也。是故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也,二言足以尽诗道矣。”①亦即贯穿诗歌创作之始终的是“情真”和“韵长”这两个基本准则(即作诗之道)。就戏曲而言,王骥德主张“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实而用实也易,以虚而用实也难”,②因此戏曲创作之全过程始终要考虑或处理好艺术创作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虚构这一核心问题。
这种道贯论也渗透到绘画中,古人往往认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求道、悟道、证道。清代石涛的“一画”论便是其中的典型:
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行远登高,悉起肤寸。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听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腕不虚则画非是,画非是则腕不灵。动之以旋,润之以转,居之以旷。出如截,入如揭。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断截横斜。如水之就下,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着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贯之。”③
在这段著名的“一画”论中,“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俱各有道,然而画家只有用心灵去透悟“一画之洪规”,由纤微入广大,洞悉万事万物的方圆、曲直、大小以及事物隐显之至理、至态、至势,方能将“太朴”那似散而实为“整一”的宇宙图景呈现出来,而那能让“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使“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的,正是“道”之贯通使之然。质言之,石涛所谓的“一画”,既是绘画之始,亦是绘画之终,这“一画”既充分展示出“道成肉身”的过程,更将“道”的那种完满性包含在笔墨的一切可能性的变化与展开中。
值得注意的是,“道贯”论的思想还渗透到小说创作及其批评中。如清人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便以《易》理阐释《红楼梦》,认为一部《石头记》无非《易》道,并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一,《红楼梦》按照《易》的规律发展着故事情节。张新之评论说:“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细细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④其二,人物的命运也同《易》道相通。比如关于林黛玉的命运,张新之又评论说:“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致蹈杀机而不觉。”⑤其三,关于人物的关系,张新之认为是《易》道中的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直接影响着《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的处理:“或问是书姻缘,何必内木石而外金石?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恶。故《易》道贵阳而贱阴,圣人抑阴而扶阳。木行东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出于薛,薛犹云雪,锢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⑥其四,关于全书的结构,张新之则以“复卦”和“渐卦”的观念来阐述《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有贯穿的结构:“一部红楼演一‘渐’字。”
总之,“道贯”论是从创造论层面就“道”对艺术创造全过程的贯通出发去探讨艺术问题的。就艺术创造而言,无论是绘画的“经营位置”,诗文的“起承转合”“置陈布势”与“脉相灌输”,艺术创造中的取舍、聚散、主宾、整乱、开合、动静、呼应、简繁、空白、疏密、穿插、虚实诸多表现方式与手段,无不以道贯之。总之,大道有理法,小道有技能,艺术之妙,全在于“道”之贯通,这是中国古代艺术创造理论反复申说并加以强调的。
三、“载道”论:道主而艺从之文艺认知格局的确立
将艺术视为天道、伦理之载体并由此主张道主而艺从,是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特征。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安排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①,在天(命)的绝对统治力面前,人只有“知命”“安天命”“顺应天命”,因而作为人们活动与生存之依据的天命、天道也成为传统哲学反复宣扬的观念,如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②,孟子的“修身立命”③,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④,董仲舒为阐发君权神授而宣扬的“天人感应”⑤论,朱熹理学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⑥等。它反映到艺术领域中,便是将艺术看作天命或天道的载体,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载道”论。比如,在乐论中,《乐记·乐本篇》云:“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⑦这种声→音→乐→政→道的逻辑思考理路,实际上就是音乐理论中较早的“载道”论。在画论中,张彦远将绘画看作是名教乐事和“载道”极品:“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⑧清代画论家华琳甚至直接将这种“载道”论极端化到包括艺术创造的万事万物,他说:“天上浮云如白衣,须臾变化成苍狗,苍狗万变图,固宇宙间第一大奇观也。《易》云:‘穷则变,变则通。’程子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则又通于道矣。道既变动不居,则天下无一物一事不载乎道,何独至于画而不然?”⑨中国传统建筑同样是天道的体现或象征。比如明堂或朝堂,被看作王权或天道的象征。《礼记·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⑩《白虎通》卷四“辟雍”还对之解释说:“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都隐含着君权神授的法统永恒观念或等级秩序观念。在文学领域中,荀子的“明道、宗经、征圣”论直接启发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在他看来,“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因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一主张也开启了后世散文创作中关于文道关系的争论并形成影响深远的散文理论,如韩愈的“明道”论与“贯道”论、周敦颐的“载道”论和朱熹的“害道”论等。
这种道主而艺从的认知方式也直接形成了中国文艺崇“大道”而鄙“小言”的理论传统。比如,中国传统小说之所以后起且一直未能受到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它是“小言”而不能传“大道”。如《庄子·外物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齐物论》云:“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列御寇》云:“彼所小言,尽人毒也。”①这都是将小说视为闲言碎语或小言。《荀子·正名》中“小家珍说”的说法与庄子所言大意相同:“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②杨倞对这一句作注说:“知治乱者,论合道与不合道而已矣,不在于有欲无欲也。能知此者,则宋、墨之家自珍贵其说,愿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也。”③在古人看来,言不入道,故曰小言。这实际都是将那些喋喋不休、辞费而无当的言论看作是“小言”,即不载大道、不中义理、不合王制或礼义的浅薄言论。从先秦到两汉,人们对于不合大道的言论几乎都以“小”称之,如小言、小道、小知、小辩等,“小说家”即使被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录入,得到的评价也不过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因为在班固看来,这些都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即使在孔子看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因其“致远恐泥”,所以“君子弗为也”。④小说被看作是只能以春秋笔法进行褒贬善恶而并不能载道的这种观念延续到晚清。如西泠散人便痛批晚清以来的小说创作“非淫词艳说荡人心志,即剿袭雷同厌人听睹”,而“欲求其自抒心裁,有关风化者”⑤,则少得可怜。
四、“同道”论:文化原型和艺术同构内秘之诠解
在中国文化哲学中有一种特殊的理解“道-艺”关系问题的致思路径,即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均视为道之一体的不同显现,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中国古代的艺术同构论。
首先,“六艺”名异而道同。在古人看来,道同体而异名,如王夫之所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名者,言道者分析而名;言之各有所指,故一理而多为之名,其实一也。”⑥也就是说,道虽然在名称上有异同之分,但指的都是宇宙世界的本质或基本规律,因而,无论是老子的“反者道之动”⑦,还是儒家所提倡“中庸之道”⑧,甚或禅理所倡导的心性之道,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对道的共同体察。古人在阐释具体的兵、农、医、艺诸事(实践活动)时,也多秉持此“同道”论。如《易》之阐释天下之“道”,便“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⑨。这种“同道”论更深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原型的理解中。比如,《淮南子》就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根基提出了“六艺同道”论,其《泰族训》即云:“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⑩新儒家马一浮继承、发挥了这种“同道AIfaL56fYNES6AY2r5eIiQ==”论,并主张结合现代人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弘扬“六艺”之道。他认为:“《诗》教主仁,《书》教主智,合仁与智,岂不是至善么?《礼》是大序,《乐》是大和,合序与和,岂不是至美么?《易》穷神知化,显天道之常;《春秋》正名拨乱,示人道之正,合正与常,岂不是至真么?”这实际是将“六艺”视为中国文化原型的基本象征,又从“六艺”兼具真善美并构成完整之价值体系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六艺”对“道”的参与与显现。
其次,“同道”论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同构论的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诸如“诗画一体”“书中有画”“书画同道”等主张打破或融通艺术门类界限的理论表述贯穿了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过程,这些表述在理论内涵上的共同点就是将各艺术门类之间看成能相互融通的或可以异质同构的关系。如唐代张彦远早有“书画异名而同体”①的说法;苏轼提出了“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②的见解。类似的看法还有“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③等。清人冯应榴引用苏轼诗夸奖老杜作诗和韩干画马为“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④。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古代艺术理论家大多是从“同道”的角度进行解释。如明人宋濂云:“仓颉造书,史皇制画,书与画非异道也,其初一致也。”⑤清人华琳《南宗抉秘》亦云:“书成而学画,则变其体不易其法,盖画即是书之理,书即是画之法。如悬针、垂露、奔雷、坠石、鸿飞、兽骇、鸾舞、蛇惊、绝岸、颓峰、临危、据槁,种种奇异不测之法,书家无所不有,画家亦无所不有。然则画道得而可通于书,书道得而可适于画,殊途同归,书画无二。”⑥关于诗与画的关系,清人叶燮亦说,“诗与画,初无二道也”,原因就在于,画是“遇于目,感于心,传之于手而为象”,诗是“触于目,入于耳,会于心,宣之于口而为言”。由此,“乃知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⑦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认为,各种艺术门类虽然在传达媒介或者表现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在艺术创造的深层道理上都是相通的,即都是以“形”或“象”去传“情”、达“意”或悟“道”。这就是艺术传达过程中的“图文间性”⑧,艺术之所以能相通、相融,其根本就在于“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⑨,而“道”就蕴含在这种动态形式中,也蕴含在那些存在着普遍联系与和谐统一的媒介交互性中。
如果我们深入追寻“同道”论何以构成中国传统艺术同构论之理论基础将会发现,这与中国古代间性哲学对艺术结构创造理念的浸润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间性哲学强调以辩证视域处理天人、心物、阴阳、道器、形神、虚实、体用、动静、内外、有无、浓淡、隐显、繁简、方圆、巧拙、疏密、真幻、藏露、未发与已发等诸多关系,主张艺术创造要顺应艺术时空的变化,去捕捉艺术作品将成未成、将变未变之际的形式变化,去生成活化的艺术形式或者保持艺术形式的活化,也更推崇从“势”的角度去判断或考察事物的运动方式、轨迹和发展前景,并以此去处理艺术结构的创造问题,因而,山水布势或人物位置的隐显、映带、奇正、断续、疏密等结构关系成为画家与观者关注的中心;倡导“化空为时”(化人物活动空间为时间进程的结构模式)成为戏曲结构创造的基本理念;在书法创作中强调气脉连通,于提顿、离合、收放之间出境界、显性情;在文章结构布局上讲究变化波澜之妙、正侧穿插之奇、短长高下之度、轻重隐显之限、回互激射之势。凡此种种,均是间性理念在古代艺术结构创造中的显现,也是艺术同构、“同道”的结构内秘。
五、“乐道”论:对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之合一的高度提倡
古人常将艺术创造视为体贴和妙悟神秘之世界本原的重要方法或途径。比如,关于书法,古人有“书之微妙,道合自然”“书肇于自然”“书之气,必达乎道”①等说法;关于绘画,有“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②,“画之道,所谓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③,“笔墨之道,通乎造化”以及画之奥妙“乃在浓淡明晦之间能得其道”④等各种大致相似的理解等。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曾以山水诗为例,精辟阐述了山水诗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悟道、体道且最终合道的过程:。
作山水诗者,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扬其异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独,造其奥以泄其秘,披其根以证其理,深入显出以尽其神,肖阴相阳以全其天。必使山情水性,因绘声绘色而曲得其真,务期天巧地灵,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则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以其灵思,结为纯意,撰为名理,发为精词,自然异香缤纷,奇彩光艳,虽写景而情生于文,理溢成趣也。使读者因吾诗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情性,不惟胜画真形之图,直可移情卧游,若目睹焉。造诣至此,是为人与天合,技也进于道矣。此之谓诗有内心也。
从这段精彩的论述不难看出,古人往往将人生境界或精神境界的证得视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我们常常看到,艺术内在规律的探寻与把握固然也是古人所悉心追求的,但心性的证语、生命的安顿、胸次的陶洗才是其终极目的,即通过艺境的感悟与揭示去协和宇宙,参赞化育,深体天人合一之道才是他们真正的旨趣之所在,崇远(倾向于向“远”中求其韵味和意境)、尚空(推崇于“空”白处出大境界)和倡微(追求“物性的敞亮”)等才是中国文人审美追求的极致。
之所以将体道、悟道视为艺术的头等大事,这同古人对艺术之特殊功用的全面认识有密切关系。在画道中,由于“山水秉五行之精,合两仪之撰以成形。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结构之理,与山水所得于天,以独成其奇胜者,则绝无相同重复之处”⑦,因此,水墨能“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⑧。在书道中,“书之为征,期合乎道”,书法的妙用在于它“是以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类其形,得造化之理”。⑨在曲道中,那“度曲未终,云起雪飞”⑩的抑扬之道则又通乎人情事理,正如汤显祖所描述的那样:“万物当气厚材猛之时,奇迫怪窘,不获急与时会,则必溃而有所出,遁而有所之。常务以快其慉结。过当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势然也。是故冲孔动楗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纡纡。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极所致,可以事道,可以忘言。”总之,在古人看来,艺术是体道、传道、达道而最终趋于“乐道”的绝好载体。
“乐道”论主要从审美体验与人生境界合一的角度去探讨艺术的功能与效用。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强调,中国之学问在于人之相处、心之相通,其精髓当为一“乐”字,“乐”乃人生之本体或人生最高境界。①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道释各家均以得道、悟道、体道为乐事,并对之反复加以宣扬。儒家之乐道志在养成人格,去体验一种人格或人生境界之提升的快乐。如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孟子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②荀子的“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③,邵雍的“已把乐为心事业,更将安作道枢机”④等。道家之乐道在于以自然无为为法,在“虚静”与“心斋”中观照与体会宇宙的勃发生机,从而获得精神的“逍遥游”与大解放,如庄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⑤,又如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⑥。佛禅之乐道在于于顿悟中亲证佛性的自在与“般若智慧”的敞现,如南禅宗慧能法师所说:“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身性。……自性常清净。”⑦可以说,儒家的“人格之乐”、道家的“无为至乐”以及佛禅的“顿悟之乐”,皆在体道、悟道中得到完成。
正是这种“乐道”论使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始终将道与艺看作是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合二为一的关系,主张道艺相统一。《论语·述而》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⑧,将目标(道)、根据(德)、依靠(仁)和归宿(艺)联系起来进行阐发,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中有关“志道”与“游艺”之关系的基本理路——“道寓于艺”“道外无艺”。后世以之作为理论依据加以阐发的不计其数。其中又以明代方以智《东西均》之“道艺”篇论述最为精彩:“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又云:“心有天游,乘物以游心,志道而终游艺者,天载于地,火丽于薪,以物观物,即以道观道也。”更云:“易一艺也,禅一艺也。七曜、四时,天之艺也。成能皆艺,而所以能者道也。”⑨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方以智不仅从心—物—艺—道的内在逻辑联系上阐述了道艺相统一的关系,而且还从“能-道”关系的角度将宇宙万物的运行变化(如七曜、四时)、人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体察与洞悟(如易与禅)都视为广义的艺术化展开,大大拓展了艺术活动的范围。
质言之,“乐道”论蕴含着古人深刻的哲学追求,亦即对“通”的境界的追求。这种天人合一、从心所欲、逍遥圆通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中国美学所推崇的,它在中国美学中常常以达、敞、和、顺、澈、明、亨、化、宜、泰、融、透、游、合、交等语词表达或标示。这些既是审美活动的理论总结,更是古人对一种艺术化人生及其境界的倡导,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智慧在当代审美实践和理论建构中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人之析物、穷理、尽心、验行都以体道为旨归,而中国艺术对诗情、文理、词脉、书势、画韵、曲趣、园境等的追求或呈现也始终同对“道”的超越性的体悟密切相关。在形、文、法、技、言、笔、墨、势等形而下的以形象为主的艺术范畴群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诸如“大象无形”“立象尽意”“离形得似”“应目会心”“妙造自然”“化工”“入神”这类理论命题的提倡。所有这些,实际上都说明中国艺术哲学的开启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对“道-艺”观及其不同理论侧面的阐解上,也集中揭示出中国艺术精神的精要: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充盈着天地之大无出吾心,造物之妙尽入我意,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的宇宙意识;流动着自然—艺术—人必须在生命本体意义的高度上相通并得到统一的生命意识;高标着在审美体验中去实现对物理时空或心理时空的大超越,去寻求精神的“逍遥游”或大解放的超越意识。它与视轮廓、比例、模式、尺度、外观或结构为艺术创作与追求之核心的西方文艺创作理念有着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艺术理论的民族性或民族特色。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