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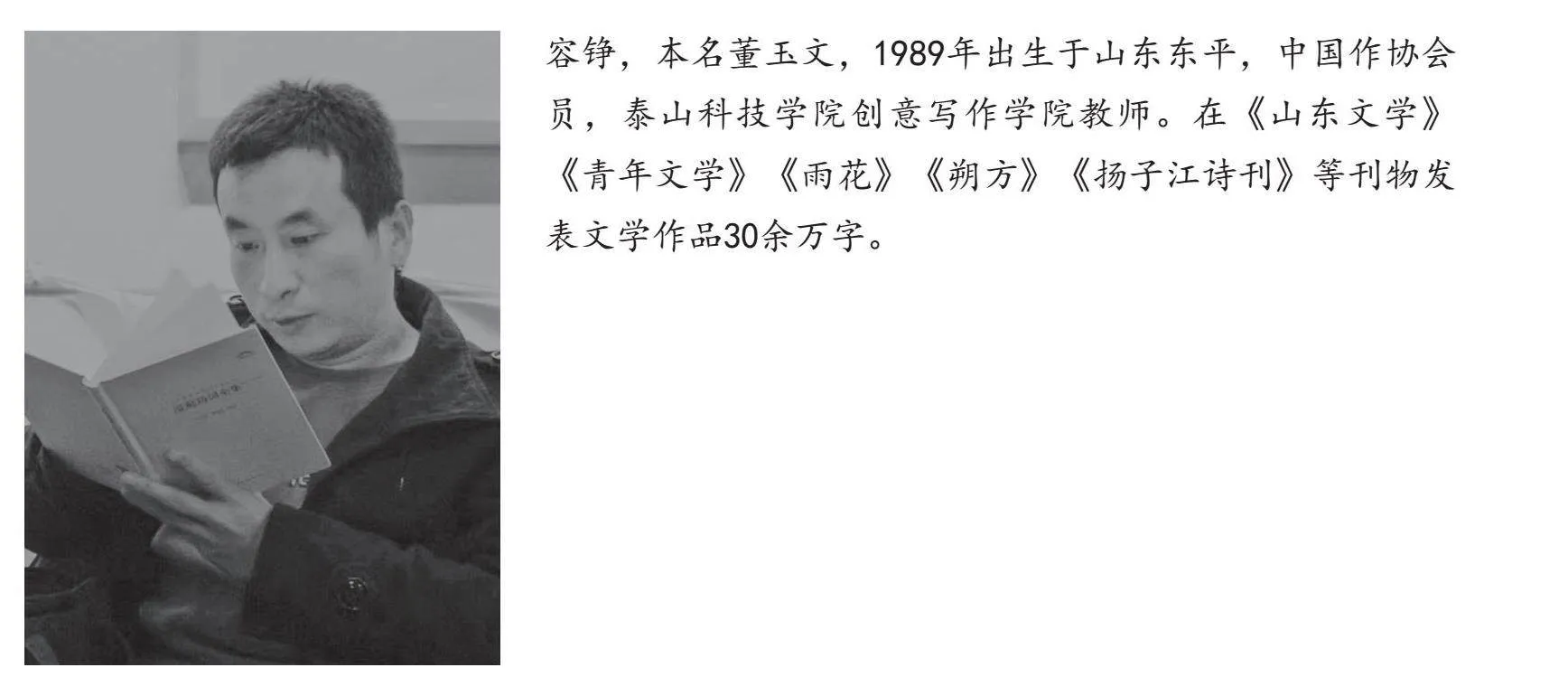
1
在我意识里,他们是一片模模糊糊的影子。
我受不了他们的气味。
每天晚饭过后,我沿着学院西路往南走,大约三百六十五步,右手边有一片小树林。一条黄土小道伸到树林深处,踩着落叶和枯草往里走,二百步左右有一方小水洼。我蹲下身,捞两把水,洗洗鼻子。洗掉他们的气味。每天我要靠这两把水支撑到明天。
如果天没有下雨,我躺靠在离水洼一丈远的树桩上,鼻子埋在朽木的凹槽,吸入尽量多的草木气息,腐木的气味更好,清香是无法与他们身上浓烈的味道相抗衡的,唯有腐烂的气味才可以。
整个秋天,我靠着几滴水和一根树桩支持过来。
到了初冬,水洼干涸,枯木缩紧,我必须寻找新的生命之源。
我还没来得及费心找寻,它就来到我身边。这是一条狗。我一觉醒来,鼻子里闻到它的气味。温糯糯的,有一些柔软,有一些刺鼻。在它将后腿搭上树桩的那一刻,我刚好来得及在它屁股上拍一巴掌。
它“嗷”的一声跌进枯草丛。
半晌,这只狗摇摇晃晃爬出来。为了安慰安慰它,我掏出午餐吃剩的半根香肠,丢给它。闻到香味儿,它靠近来嗅了嗅,立刻“呜呜”起来。看来对它来讲这是难得的美食。
吃完之后,它又过来靠着我。
这只狗还不太讨厌。
后来,我给它命名为“马蹄”。
整个冬天,“马蹄”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树林。冬至前后,下了一场大雪,起初还夹杂着雨,我打着伞,踩着泥泞的小道,站在林边和“马蹄”待了片刻。雪继续下着,踩上去能听到轻微的咯吱声。
整个冬天我瘦了十多斤,省下来的食物都给了“马蹄”,当然并不多,因此虽然“马蹄”从不挑食,却没有胖起来。
寒潮封冻了雨水和雪,早晨和傍晚走在冰渣渣的土地上,我在担心冰雪融化之后怎样来看“马蹄”。
坐在树桩上,我盯着冻住的泥土的纹路,几片灰色的落叶叶脉间交织着冰晶,“马蹄”时不时舔舔冰面,叹口气继续趴伏在我身侧。
低温持续了半个多月,我没有看到冰雪融化,但某一天的清晨,我惊讶地发现冰面之下的土地干燥了。冰面和积雪继续减少,踩上去“咔嚓”一下破碎,在颗粒状的黄土地上散开来。
在把“马蹄”带回宿舍之前,我想办法给它洗了个澡。
那天我掐好时间,马上要熄灯的时候窜进宿舍楼,用一只提包成功遮挡住宿管阿姨探照灯一样的目光。
第一次回来这么晚让他们略有惊讶,但只是一闪而过,他们继续专注于牌局。熄灯之后,他们继续打开六部手机的灯光,进行完最后一局。接下来,是一个小时的闲聊,尾声,一个个进入了梦乡。
听到某个人说了一句:“怎么听着有狗吱吱?”我如堕冰窖。
我蒙被捂住狗嘴。直到外面再无声息。
2
我们正在上课,一只叫“浅草”的猫溜进了教室。
那天原本是个雾霾天,下午的时候,刀片一样的阳光沿着窗帘一侧切在教室的地板上,给“浅草”铺开了一道舞台。它沿着光道不慌不忙地走着。
凤老师和铮老师正在合作给我们上课,猫进来的时候,凤老师正在讲“概率论起源”,猫踩着猫步弹跳在凤老师逻辑严谨的叙述上,仿佛在钢琴上弹奏出一首乐曲。到了铮老师那里可就不成了,他天马行空的叙述明显配合不上猫的脚步,于是他放弃准备好的内容,大谈特谈起“怎样虚构一只猫”来,貌似这只猫原本并不存在,而是被铮老师的语句召唤出来的,只是存在于我们的遐想之中。
在铮老师句子与句子的间歇,女生们“浅草浅草”地叫着,搞得男生们困惑不已。
待到铮老师提起“一只叫浅草的猫”,我们才恍然大悟。
“浅草”开始沿着教室的墙壁转着,忽然被暖气片挡住了去路,脑袋忽地后仰,右前蹄举起,做防卫状。片刻,它伸鼻嗅了嗅,后退两步,一纵身,众目睽睽之下跃上一米多高的暖气片。“浅草”在暖气片温暖的平面上俯卧下来,埋头在双爪之间。
凤老师微微一笑,铮老师松了一口气。但片刻之后,“浅草”猛然警醒,再次跃下地来。
铮老师一脸无奈地看着它。
凤老师大笑,齐整的牙齿映着右耳坠的一点白光。
“浅草”昂首阔步,继续在教室里奔腾。
绕过荡起的窗帘和窗棂组成的夹角形成的光锥,“浅草”终于找到了它的主人,跃上一位身穿淡黄毛衣、睫毛黑黑的女生怀里。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女生,并且在当天晚上宿舍的夜谈中知道她叫“吉彤”。吉彤脸一红,将“浅草”揽入怀,一边瞭着铮老师,看他有没有生气。
铮老师看着凤老师的眼睛。午后的阳光如此温暖,让整个课堂的氛围也温馨起来,大家的意识飘浮在半空中,从肉体中抽离出来,融成了一个闭环,允许那只猫逃离了规则的束缚。
课后,大家陆陆续续离开教室,四点没有课,因此都变得懒洋洋的。我在教室里一直待到六点,看着陆陆续续有不知名、不知道班级的同学穿过走廊去隔壁教室上课。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之后,同一批学生又三三两两返回来。
我托着一本书,同时,怀里像在抱着一只猫,我希望这只猫有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生平第一次,不再反感“诗意”。
这天晚上也没有课,在食堂里吃完一份蛋炒饭之后,我来到音乐楼。
音乐楼在学校西南角,楼前几株两三搂粗的梧桐树。音乐楼内部空旷,在乐池,一道旋转楼梯直通六楼,我坐在楼梯的最顶端,那里有一片阴影,黑夜降临的时候,很少有人到最高处来了,最多到三楼或者四楼,便拐向自习室。
每天晚上八点半前后,五楼的某间教室会有一支乐队排练,他们有两支保留曲目,一是窦唯的《靠近我》,一是许巍的《蓝莲花》。在发现草木气味可以医治我嗅觉的怪癖之前,我靠着这两支乐曲医治自己。
十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任何试图治愈自己的行动,都将导致更大的伤口。当你起意要医治自己的时候,你就已经踏上了一个错误的开端。
3
春天来临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马蹄”。
虽然它的气味已经深印在我脑海,但真实的它的丢失还是让我痛不欲生。我原本是想让它和“浅草”做朋友的,但它却把“浅草”吓得差点儿抽搐。
老二娄虎一脚踢飞了“马蹄”。我站在旁边目瞪口呆。
吉彤狠狠责怪了娄虎一番,让娄虎向我道歉。娄虎搂着我的肩膀,对吉彤说:“这是我们家小六,不会怪罪二哥的!”虽然并没有等来道歉,但吉彤的态度让我惊慌失措的心得到了安抚。
推开娄虎的大手,我去校外的小树林里等“马蹄”,我知道无论它逃多远,总会回到我们的约定之地的。它比我到得还早,“呜呜”叫着向我诉苦。我拍拍它的脑袋安慰它,一人一狗在野地里躺了很久。
几天之后,“马蹄”失踪了。
最初我还安慰自己,是“马蹄”不适合自己。日子久了,也不需要再老是向自己重复无力的理由了。
“马蹄”的气味还深印在我的脑海,我需要为它找一个实体。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明了“纸狗”,当我听说的时候,除了我们宿舍,几乎每个宿舍都有两三只纸狗了。在我们宿舍,老大第一个牵上了纸狗,并且占取了第二波潮流的制高点:他的纸狗是女朋友送的。
对于“原创性”,我一向并不在意,当我也打定主意做一只纸狗的时候,我甚至因为大家几乎都拥有了一只纸狗而高兴,当大家都有了,也就不会有人特别在意我。我必须努力做一个和大家类似的人。我必须下功夫模仿正常人的行为。
出了快递驿站左拐一百米左右有一排蓝墨色的垃圾桶,总是有人站在那里拆掉包装,因此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捡到了大大小小六七个纸箱。
在宿舍,我用略湿的抹布将它们仔仔细细揩拭一遍。之前,我已经将所有的连接处拆开,保证每块纸板的平整。等待晾干的间歇,我准备好了圆规、尺子、铅笔和固体胶,一边回忆着“马蹄”的音容笑貌、体形动作,一边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狗的模样。我得承认,比起“马蹄”,我在纸上画的狗确实是太简陋了,如果“马蹄”回来,它一定认不出这只狗是比照着我脑海里它的模样画出来的。
舍友们回来之前,我藏好了所有的道具。我是逃了课在做一只纸狗。在做成一件喜欢的事情中间,我不喜欢被别人看到,这也是我的怪癖之一。
下午,老五逃了课在床上躺着,我只好暂时放弃手里的工作,去了图书馆。
直到周三下午,我才得到整块的时间。而在这三天里,我差不多已经在脑子里将整只纸狗琢磨了七八遍,把每个关节几乎都琢磨到了。因此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我便在纸板上画好了每个结构的框架图。那个下午,纸狗的四条腿成功诞生了三条,而且其中的两条是蹲坐的、难度较大的后腿。
那天晚上我是抱着那三条狗腿睡的。
4
不能工作的日子里,除了用脑子琢磨纸狗之外,我发现自己对吉彤的关注度明显上升。
我发现她很爱学习,在第二自修室有一个固定位子。第二自修室在老图书馆三楼,比起新图书馆的第一自修室,第二自修室明显老旧许多,桌椅板凳遍布密集的划痕和木头茬口,水泥地面,粉刷墙壁的是老式的绿色涂料,斑斑点点剥落。尽管缺点如此显著,但也正因为此,第二自修室拥有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巨大优势:来的人少。第一自修室是不可能得到一个固定位子的。
本人终生与学习无缘。但我还是在离吉彤挺远的角落里也霸占了一个位子。偏偏脑袋越过一根尺余见方的立柱,可以看到她的背影。
自然,在自修室里我是坐不住的,陌生人的气味太浓烈,我不时用手掌捂住口罩,借助书中历代伟大人物的智慧与其对抗。每天上午和下午中间一段,我到地下室。一层和二层是报刊室,一些考研的同学经常来翻阅,所以我是不去的。地下室是老旧书籍,乏人问津,是我的天堂。
在地下室,我开辟了一个自己的书架,由于一年到头整理不到一次,所以我的私人书架从未被人动过。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新书的初版本,其中的一部分我在新图书馆做过对比,发现新校对的译本比旧版本好不了多少,有的甚至更差了。我私人书架的核心位置,放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用鲁迅先生的宠儿阿Q的话讲,人生在世,难免要模模糊糊坐几天牢,先提前增加点经验也好,虽然这些经验未必有用。
除了读书之外,我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胡思乱想。
每天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左右,吉彤离开自修室去食堂。下了自修室去食堂的楼房拐角,吉彤的闺蜜齐玉佳等在那里。我一度和齐玉佳走得很近,以至于她误以为我要追她,实情只不过是想从她那里多了解点吉彤。
吉彤就像一颗北极星,将我钉在离她三丈开外的地方。
我的脖颈弯曲,像一把汤勺。
音乐楼的排练一般九点半结束,余音绕梁,九点四十五,我起身往楼下走。音乐楼后面是吉彤她们的宿舍,我知道她们住四楼。音乐楼和女生宿舍之间有一条六棱花砖铺的小道,有一片竹林,我从路口摘一片竹叶,咀嚼着。竹叶会在嘴角留下淡绿色的印记,因此舍友给我起的外号,就叫“熊猫”。
说起来,整个大学期间,我和吉彤只有一次真正的交集。那天她拿着一本高数下册,在过道里拦住我:“熊猫!来给姐讲讲这道题!”
我愕然而立。
她笑得如此灿烂:“娄虎告诉我你叫熊猫!哈哈!”
不错,我的信息如此闭塞,我的感知如此迟钝。
5
三哥出门之前非要塞给我一支烟。
走了不到一分钟,他又回来塞给我一只打火机。
他说任何创造性的举动都离不开尼古丁的刺激。我不信他,但还是点着了烟塞在嘴角。烟雾刺激着我的眼睛和鼻子。烟雾一点儿也没钻进我的肺,全都白白浪费掉了。但就是这样,它们激发了我的灵感。
我给我的纸狗命名为“马蹄撇”,毫不讳言,它是“马蹄”的复制品。保留了对我来说“马蹄”的所有优点,避免了对我来说“马蹄”的所有缺点。而且,“马蹄撇”还承担着一项重大使命。
在烟雾的刺激下,“马蹄撇”身上原本僵硬的线条变得柔软了,尾巴波浪一般蓬松着。
将近60公分高的“马蹄撇”成型之后,明显不再适合塞进被窝里。而且接缝处用固体胶粘牢之后,我用橡皮泥勾了一遍缝,橡皮泥需要2-3天的干燥期。我听到老大的高声谈笑已经近在咫尺,急中生智,将“马蹄撇”拎到脚下,挨着衣橱的外壁放好。在他们进门之前,我还来得及在“马蹄撇”身上搭了一条毛巾。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用剩余的橡皮泥边角料在桌上捏着。
“老六!”老大一把抱住我的脑袋,“干吗哪?”
他没有等我回答,便往阳台走去,右手已经从口袋里掏出烟。
抽完一根烟,他回来,拉把椅子坐在我跟前,看我捏弄橡皮泥。
“老六,”半晌,他说。
隔一天的晚上,我回到宿舍,盘算着“马蹄撇”已经干拢了,可以抱进被窝了。但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被窝,这可是一个技巧。
我拿出一本书读着,心里盘算的都是“马蹄撇”的事情。
那四位,加上隔壁宿舍的老大和老五,六个人正在打牌。从眼角的余光,我意识到他们时不时地朝我微微笑着。我的意识从自己的世界里探出头来,听到了断断续续的议论纸狗的声音,我借着系鞋带往下面看了看,没有什么异常,毛巾还是我盖的,其下就是“马蹄撇”,没有问题。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心里越来越不安。忽然,老大一句带着讪笑的“可怜的孩子还没发现”让我猛然惊醒,俯身抽掉毛巾。毛巾拽出一只模样丑陋的纸狗来,哪儿还是“马蹄撇”?
我狠命在丑狗身上跺了两脚,七窍生烟。
大家都笑了。
老五笑得尤其夸张,前仰后合,咳嗽着,手里的牌撒了一地。
娄虎站起来,不好意思地朝我颔首微笑:“小六,我看你做得这么精致,像是要送人的,我就替你送出去了!”
“替你……”“替你送出去了……”“老二真会说话……”整个宿舍已经成了欢乐的海洋。
气愤之下,我口不择言:“谁要你他M的送?你以为你是谁?”
虽然好几个人拉着,娄虎还是一脚将我踹倒在地。
6
“马蹄撇”事件之后,我被两个宿舍的人冷落了一个多月。
我不在乎,这样更好,我不用再违心地每天应付着和他们聊天,乐得清静。不出三天,我用剩余的纸壳做了一只小号的“马蹄撇”,每天抱在被窝里嗅着。
宿舍只是我的睡觉之地,不到睡觉的时候我不再回宿舍。我在图书馆一直待到将近熄灯,拐到音乐楼后的小道一直逛到接近关闭宿舍。一大早我就出来,继续在音乐小道上徘徊,清晨从竹林里传出几声鸟鸣。
不错,娄虎说得对,我的“马蹄撇”是准备送人的。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娄虎,我一辈子也不会将“马蹄撇”交到吉彤手里。
吉彤有自己的宠物,她有她的“浅草”。当大家都在做纸狗的时候,她并没有加入纸狗大军里来。这段时间,“浅草”慢慢熟悉了各种各样的狗,学会了和狗玩耍。
我突然有点怀念真实的“马蹄”了。
“何为真实?真实何为?”当我看到娄虎搂着“浅草”和牵着“马蹄撇”的吉彤并排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我问自己。
吉彤轻抚着“马蹄撇”的脖颈,那里有我细心弯起的一道道折痕,如果把折痕打开,翻过来,可以看到我写给吉彤的一封信。但我预感到,这封信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心思细腻的人是有罪的。
我不再去第二自修室。我不再去音乐楼。我不再去音乐楼和女生宿舍之间的砖铺小道。我不再去校外的小树林。两年后的那个冬天,当我无意中再次路过那片小树林的时候,我发现羊肠小道已经硬化,所有的水洼全部消失了。
从某个时刻开始,我接受了周围的人,我的嗅觉不再敏锐。
我也学会寻找牌局,骂骂咧咧一直战到天光微明。每到周五,和三两个朋友到网吧里玩个通宵,那时宿舍里还没有个人电脑,正是网吧流行的年代。
偶尔,我会留意到吉彤和娄虎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有时我会想到,“马蹄撇”在这份感情里起到了多大作用。
“马蹄”“马蹄撇”和小号“马蹄撇”都已进入过去式。
7
十多年后,我几乎已经将自己的大学时代遗忘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吉彤的脸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也不会用了好几个夜晚追忆往事。
十多年来,我逐渐明白,一个连学校生活都适应不了的人,在职场上,只能是永远的白痴。我从未听懂领导和同事的话外之音,但敏感的性格又总是让我独自思索,想要弄明白里面的玄机。我既不能做一个玲珑剔透的人,又不能做一个心思单纯的人,在夹缝中苦受熬煎。
看同学们的经历,都是人往高处走,只有我,一直在底层颠簸浮动,仅仅没有淹死而已。
当对自己的一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体认,我在市区一个小区里安顿下来,用微薄的积蓄承接了一家快递驿站,每天收收快递发发快递,过上了一直向往的简单的生活。
日久天长,我和小区里的居民逐渐熟悉,老头老太太们尤其喜欢我。我从不吝惜时间,有问必答,教许多退休老干部学会了网购,他们的子女虽然对我怒目而视,却也毫无办法。在这个小区里,我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生活。我也从不想着积累客户,“巧者劳而智者忧”,个别网红迈着高傲的步伐来找我谈合作,都被我支到小区里另一家快递驿站去了。
三年多之后的一个冬天的黄昏,该拿的快递基本上都拿完了,我有了十几分钟的闲暇。我在考虑要不要换个地方,从某个时期开始,快递数量猛增,我有点过于疲劳,开始违背自己的生活信念。
我正盯着墙角出神,“23-12-365”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旁报出了快递号码,“哎!——”我下意识答应着,起身到架子上找到了包裹。
扫码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是一位身穿白色羽绒服的年轻女士,虽然戴着口罩,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的眼睛:“啊——吉彤?”
“吉彤?嗯?”她露出困惑的神色。
我相信我是不会认错的,拉下了自己的口罩:“是我啊,张文,熊猫!”
她笑了。
在我的要求下,她也拉下了自己的口罩,是吉彤,没错。
但她否认了,“我叫靳芸,刚来这里,您应该是认错人了。”她说。
她走后,我半天缓不过神来。不可能,这就是吉彤,怎么会是“靳芸”?什么靳芸?哪儿来的靳芸?明明是吉彤嘛!她不可能不记得我,她为什么不认我?娄虎呢?我思绪纷飞,难以抑制……
下意识地帮两个居民拿了快递之后,我拉下了卷帘门。
夜幕降临,我没有开灯,独自坐在黑暗中。
8
自那以后,她隔三差五地来拿快递,很快,当年的往事一幕幕在我心里复活,我原本以为再也不可能见到吉彤了。尽管她一再否认,每次见了她,我还是会叫她“吉彤”。后来,她也就不否认了,“随你怎么叫吧。你这人真怪。”她说。
她说对了,我就是个怪人,可见她记得我。
再往后,她每天都要来发3-5个快递,我注意了一下地址,全国各地都有。我注意到虽然仔细洗过,她的指甲缝里还是残余着少许绘画颜料。
我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靳芸”,出来了一串带“芸”或“芸芸”的名字,只有三个“靳芸”,但看地址,都离此处十万八千里。我合上手机,沉思片刻。又打开,输入“吉彤”,也不对。我又输入“吉童”和“吉瞳”,这次对了,“吉瞳”正在直播,就是自称“靳芸”的女士,在她面前摆放着几只面具,她一边讲解,一边用画笔蘸了颜料勾画着,其中的一只狐狸假面已经接近完工。
看到“吉彤”往这儿走来,我立马打开“吉瞳”账号的短视频。
“调色是重点朋友们,想要一只独一无二的面具……”
她的脸红了。
扫码的时候,她伸手划走了自己的页面。
“干吗!动手动脚?”我严肃地说。
“不允许你看!”她嗔道。
“知识产权,老天爷,你怎么可以不征求我的意见,就起名叫‘吉瞳’?”我朝她喊。
“难道你叫吉瞳?”她笑着问。
我噎住了。
朋友们,虽然先贤一再告诫,我还是要重复一句:“千万不要和女士争辩!”
但是,如果不和一位女士争辩上一次两次,又怎么能成为朋友?
那次争辩过后,“吉彤”再来,我们开始简单聊几句,如果恰好没有别人,我们就多聊几分钟。我每天看她的直播,和她讨论每个短视频的优劣,聊着聊着,她经常负气而走,这是我戳到了她的痛处。
不断改进的过程中,她的粉丝量越来越多,从百十人,到数百,突破一千的那天,她高兴极了,告诉我这一步很重要,就像迈过人生的一个坎。
坎不坎的我从来不在意,但我仍然为她高兴。
粉丝量过万的那天,她等我下班落门,说要请我吃饭。我受宠若惊,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拒绝还是答应。她并未征求我的意见,说在这里只有我一个朋友,一定要陪她分享喜悦。
喝完一杯白酒之后,她又给我倒了一杯。她喝啤酒。她说她算是离家出走,父母一直催婚,而她只想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如今有了网络这个机会,她可以自食其力,不受制于人。我赞同她的想法。
她要求我讲讲吉彤的故事。
怎么讲呢?根本就没有故事,只是一段毫无希望的暗恋。
结果在吉彤的故事里,吉彤所占的篇幅还不如“马蹄”和“马蹄撇”。而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吉彤”,兴趣逐渐转移到“纸狗”上。她觉得这是一个新商机,晚上没事的时候可以再做几只,她可以免费代卖,如果卖得火,可以五五分成。
这想法让我觉得意外,对于“五五分成”,我倒是不甚在意,但用做纸狗来打发打发无聊的时光,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答应她试试看。
9
透过三楼的玻璃往下看,广场上的人流开始稀疏。
我们下楼的时刻,人更少了,人和人之间出现了更多的空隙,我们穿梭在这些空隙里。左边胡同里一群人正在争吵,传来密集的酒杯摔碎在地的声音。我和“吉彤”跑过去看热闹,直到被一位高大苍白、挽着束发带的女性骂了娘,人群一哄而散,我们咯咯笑着跑出胡同。
“吉彤”家里的整洁超出我的预料,不只直播区域,其他地方也收拾得井井有条。客厅比直播画面显得小,靠北墙放着一张大案,案顶打着灯光。
“吉彤”打开灯,引导我欣赏案头的几张面具,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她已经从画狐狸、老虎、猎犬等动物的脸,逐渐转到人脸,在京剧脸谱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元素,虽然我对绘画是外行,但也可以看出“吉彤”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并非简单的爱好。
拉过一把椅子,“吉彤”坐下来,借着酒劲,在未完成的一张“茉莉花神”脸谱上勾画着。我抱着双臂挨在桌子上看着,不时打着饱嗝。“吉彤”画着画着,忽然抬头,照着我的鼻子画了一笔。我被吓了一跳。
笑声中,“吉彤”选了一张翘胡子绅士的鬼面罩在我脸上。
隔着面具,我只感觉到了她双唇的温热。
之后的几天我神情痴騃。一种从未拥有过的情感体验冲击着我的心灵,我没有办法认真思考,一再走神,连连道着歉替换拿错的包裹。
“吉彤”还是每天下午五点左右过来发货,对于我饱含深意的眼神从未正面回应,貌似我们从未一块喝过酒。
一周之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
我觉得自己想多了。
我冷静下来。
“吉瞳”在小区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每当她发完货往回走,时不时有人站在那里指指她的背影议论几句。有位阿姨拦住“吉彤”,问她直播和卖货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吉彤”笑了笑,说“不多不多,挺辛苦。”
待“吉彤”走了,阿姨又过来问我:“阿文,我看你和姑娘挺熟,你知不知道她直播和卖货每个月能挣多少钱?”
“不熟不熟,您关心这个干吗?也准备直播?”我问。
阿姨摆摆手,什么也没说,走了。
那天晚上,我从门口的垃圾桶里将废旧纸箱全部拣出来。夜深人静,关上卷帘门,将纸箱用抹布擦拭干净,找出铅笔、圆规、直尺和固体胶棒——哪承想十多年后,“马蹄”会再一次从我脑海里复活。
枕着胳膊趴在桌子上,仿佛我的周围下了一场雪。
在一只只做着纸狗的时候,我想起了当年写给吉彤的那封信,信的内容已经一句也记不起来了,年轻的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记忆力和某些事情在自己生命中的重要程度,只记得我怎样将那封信折好,折入“马蹄”脖颈的褶皱里。
我忽然第一次想到:吉彤曾不曾知道我对她的心意?
10
我和“吉彤”回到了纯粹的业务关系。我每天不时看看她的直播,她每天来发快递,如果没有别的人,我们简单聊几句家常。纸狗的事情她没有再提,我也没有再提,虽然我每天都在做着。
就这样又过了大半年,“吉瞳”的粉丝涨到3万露头之后,基本停滞,“吉彤”每天的发货量在十个包裹上下。有一次,她说就这样正好,不然日夜工作也画不了更多的面具。我猜直播间里打赏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面具的收入,有时候想要问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把面具买卖停掉,但看着她在直播间越来越熟练地索要打赏的话术,我忍住没有说。
那天上午我注意到“吉瞳”直播间没有开。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是停播一两个小时,但那天一直等到下午,镜头依然没有打开。傍晚的时候,“吉彤”也没有来发货,这还是半年多来第一次。
莫非“吉彤”病了?我胡乱思想着,考虑去看一看是否合适。
门口附近,几位等待拿快递的阿姨正在聊天。“……带走了,十点多钟吧……好几个警察,那阵势……”“……只看贼吃肉,莫看贼挨打,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干这事,真是……”“这世道,看不清好人坏人喽!”“……大摞大摞的面具,装了半车……”
我一整夜没有合眼。
我在床上躺了很久,梳理着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看能不能帮上“吉彤”什么忙。
我打开灯,找到角落里堆着的纸狗,一只一只仔仔细细拆开。
第二天上午,快递驿站照常营业,忙碌让我来不及考虑其他。
将近十一点钟时,门口停下一辆警车,两名警察同志来到我面前。
我真意外,放下手里的东西。
左手边短发、帅气的年轻警察问我:“张文同志对吧?”
“对。”
“这是逮捕令,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你涉嫌买卖违禁物品,麻烦跟我们去趟警局。”
签字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我根本没来得及想到分辩什么。
我放下卷帘门。
周围已经聚了一帮人,人们对我指指点点,仿佛我不是原来的我了。
弯腰上警车的时候,看着照射在车顶的阳光,我没来由地想起了毕业之前的那次集体登山。登到半山腰,下起了雨,而我们都没有带伞。我们随人流躲在厕所里避雨,挤挤挨挨。借着灯光,我们看到雨滴密密麻麻,像虫子一样从天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