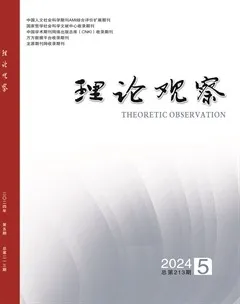纳粹时期德国知识分子迁移与土耳其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
摘 要:在土耳其建国之初的现代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德国流亡学者身影,他们缘何来此,作用如何,值得探究。从土耳其立国之初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与困境,土耳其如何与德国流亡学者接触并引进,以及德国流亡学者在土耳其的具体工作与进展来分析其背后的历史根源。经分析可知:以高等教育改革为代表的现代化改革是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为摆脱落后,实现民族崛起的主动选择。特别是德国流亡学者的到来解决了高等人才的缺乏问题,在土耳其政府大力支持下,这些德国流亡学者在土耳其有了用武之地,并助推土耳其快速建立高等学府,完成高等教育改革,加速其现代化改革的进程。
关键词:凯末尔;大学教育;德国流亡学者;犹太人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5 — 0120 — 09
一、绪论
1933年,根据3月23日《授权法》规定的立法权,希特勒以政治或种族为由,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 tentums),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的公职人员。因此,有相当一批具备创新力和活力的学者被迫流亡他国寻找新的工作岗位。然而多数“旁观者(国家)”为避免麻烦,搁置这些学者的就职申请,使得许多学者在最初的时候要么被迫从事与其专长相去甚远的工作,要么因种种原因只能在暂居地待业。而彼时,与众多国家拒绝流亡学者不同,土耳其选择接纳与包容这些“知识性难民”,给予这些优秀学者平等待遇: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给予充分信任,让他们教导土耳其的高等人才。这项政策从结果看影响巨大,对土耳其的国家建设发挥巨大作用。那么,为何当时的土耳其能够实行这项如今看来颇为超前的人才引进政策呢、该政策究竟有何收益、人数众多的流亡学者如何在近代化程度发展较低的环境中开展工作?这些学者离开后土耳其的高等教育发展又是怎样呢?
笔者因着这一线索,将视线投向土耳其,探寻其以开放、合理的人才引进政策为指导,如何一步一步地剔除封建教育的影响,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进而推动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走向新的高度。
二、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及其高等教育困境
对于土耳其国家历史而言,20世纪初这一时段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方面,土耳其在西方列强与东欧各新兴民族国家的共同撕咬下,成功地通过革命与战争摆脱了被瓜分的命运,建立起土耳其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在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领导下,土耳其开启政治现代化改革,走上世俗化道路。然而土耳其共和国所继承的是一个破败的国家、一套瓦解的行政机构和一部过时的法律体系。所有这些都与凯末尔及其支持者想要建立世俗国家的信条完全不相容。凯末尔曾讲道:“新的土耳其不能与伊斯兰教法(Mecelle)①绑在一起,这不符合我们今天的需要。用100年前、500年前或1000年前颁布的法律来管理,是粗心,是无知。”②当时的土耳其是一个疲惫而贫穷的国家,凯末尔非常清楚,这个国家必须经历一个快速的转变。年轻的共和党人充满理想和热情,实现其理想的动力几乎是无限的,但实现这些理想的手段却非常有限。社会希冀政府可以为其带来改变,为孱弱的土耳其共和国注入新的活力和发展前景,摆脱曾经“西亚病夫”的蔑称。
(一)土耳其的基础教育改革
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前,宗教教育是奥斯曼帝国神权政治的支柱,其目的是将伊斯兰教派的价值观传递给更多的青年,以求实现对“苏丹—哈里发”统治的认同。③而到1869年,土耳其政府才愿意承担起基础社会教育的责任,但是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仍然在宗教学校的控制之下,政府对土耳其青年一代的教育始终没有脱离宗教神学的范围。直到1913年,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影响下,土耳其政府颁布了《预备小学教育法案》(Provisory Primary Education Law),规定小学应教授以下内容:《古兰经》(对穆斯林);其所属宗教的知识(对非穆斯林);阅读和写作;奥斯曼语;地理,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地理;算术和几何;历史,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公民学、科学和卫生;美术、工艺和绘画;宗教和爱国诗歌;体育及在校运动;为男生提供军事训练;为女孩提高家务和缝纫学习。④然而因为一战的爆发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凋敝,这项政策的推行始终达不到预期效果,土耳其国民长期处于神学的愚昧思想之下,基础文化素质极低,无法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贡献具备良好文化素质的工人群体。
集中力量应对经济问题,实现共和国的工业化经济固然重要,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持续性发展应该始于良好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故此,随着土耳其“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的推进,作为社会变革核心的教育改革迅速展开。首先,政府重新统一教育,在1924年3月3日,教育部将教育权收归国有,并规定妇女和农村人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其次,土耳其对国内的教育机构进行重组:一方面,在1924年3月13日,政府下令废黜包括伊斯兰学校(当时奥斯曼帝国高等教育的唯一公共形式)在内的所有宗教学校;另一方面,1926年3月2日立法重组包括小学、中学和高中在内的基础教育体系。再次,为了有效推动教育的普及,土耳其还于1928年11月1日正式启用拉丁字母,放弃阿拉伯字母,在全国进行扫盲运动,让大部分人接受这种新字母教育。最后,政府还支持人文学科的研究协会建立,以助力教育改革的推进:1931年4月12日土耳其历史协会成立;1932年7月12日土耳其语言协会成立,1932年7月12日进行全面语言改革。
(二)高等教育困境
凯末尔政府的教育改革是全面立体的,其众多精准到位的改革措施也颇为有效,然而这些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体现一个国家科技文化水平的高等教育改革却迟迟未能推行。在当时倘若一个国家想要快速追赶西方强国,不仅需要建立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为发展提供保障,更需要在根本上提高这个国家全体公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建立一整套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而产生影响整个国家的教育理念、民族精神和科学技术,唯此通过稳定的制度和高素质的公民以及大量科学技术人员,弱国才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保证独立发展且繁荣。
显然,当时的土耳其并不具备这样的高等教育体系,继承于奥斯曼帝国的学校沉浸于宗教理论的研究和过时军事器械及战术的培养,完全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现代化”的大学。在19世纪早期之前,奥斯曼帝国从来没有计划过培养任何近代化的学术或研究人才,国家只愿意培养适合其发展的军事和官僚官员,因此在1933年之前,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建有的官方学校屈指可数:1735年在法国人亚历山大·博内瓦尔帮助下建有一所炮兵学院;1773年建立皇家海军工程学院(Muhendishane-i Bahr-i Humayun)以培训海图师和造船师;1795年成立了皇家军事工程学院(Muhendishane-i Berr-i Humayun)以培养技术人才;1827年建立帝国医学院;1834年建立帝国军事学院;①1854年建立名义上第一所大学“科学院(Darülfünun)”。②
土耳其鲜有适合现代化大学的教育人才,以往的学校里尽是宗教先知、神学讲师和封建式军官,哪怕少数几个具备科学素养的外国讲师,也因动荡的土耳其国情早已逃离。“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倾向于从那些外聘官员、专家和科学家中获益”,③并不在意培养本土教育人才。没有教室,可以新建更宏大的讲堂;没有学生,可以号召有识青年积极参与;没有科学器械,可以花大价钱突破封锁从西方购买;然而没有教师,这一切都是徒劳。
当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诞生时,继承于羸弱的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体系大约有400多所伊斯兰宗教学校,并且残存两所军官院校、一所土木工程学校和四所中等专门学校,④以及一所“准”大学,即科学院,后者设计建立的初衷是严格培训公务员。然而科学院几乎是一个中世纪的机构,在那里,业余教师年复一年地从他们破旧的笔记本上重复着同样的讲座,他们很少进行研究,也很少出版科学书籍。⑤这些便是共和国初期教育体制中的基本情况,绝大多数学校不仅无助于这个国家社会的现代化,甚至还可能成为这场现代化的阻力,因此它们很快被尽数关闭。如此僵化的旧体系明显不具备支持雄心勃勃的共和国缔造者实现高等教育理想的条件,“大学现代化”显然是必要的,而第一步就需要招聘教育人才。
(三)高等教育人才引进计划
为实现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计划,土耳其教育部长雷西特·加利普(Resit Galip, 1893~1934)于1932年邀请瑞士教育学教授阿尔伯特·马尔奇(Albert Malche, 1876~1956)前往土耳其考察,并要求马尔奇考察后提交一份关于土耳其教育改革的报告。马尔奇于1932年1月18日抵达土耳其后立即展开工作,于5月29日撰写了名为《伊斯坦布尔大学报告》(Rapport sur l’universite′d’Istanbul)的文件。⑥
正是以这份文件为基础,土耳其政府形成了以西欧大学为模式建立完全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的理念。该报告总结土耳其高等教育的问题在于:1.科学院教育质量较低,只对学生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教学,且实验性实践不足;2.科学生产力和独创性水平很低,任职教师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科学研究,且出版物极少,质量水平差;3.教员的语言能力很差(多数不会使用西欧语言),不足以跟上现代的进步;4.各部门之间不存在良好的协调性,工作效率低下。⑦马尔奇还表示,计划建立的新大学体系尚不能聘请到足够数量的本国学者来支持正常教学运转,建议派遣新一代学生出国培训并聘请外国学者来暂时弥补教职的空缺。为此马尔奇继续提议,为适应土耳其高等教育发展,建议土耳其政府邀请在德国因《重设公职人员法》而失业的学者到土耳其任职,以满足对教学人才的需要。
三、德国学者的流亡与土耳其的聘任
(一)德国的“文化流亡”
此时的德国正在解雇许多大学教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人,或者只是在名义上不能也不会接受纳粹主义的普通人。德国在1933~1945年颁布的多项政府法案禁止了近1200名科学工作者进入其教育及科研机构,至战后其中约650人成功移民。⑧
由于《重设公职人员法》的规定,⑨所有德国大学、研究所以及医学院中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其地位都受到质疑,因而很快导致了上千人的解聘。?輥?輮?訛疯狂的“解聘风波”不仅冲击了德国,而且伴随着纳粹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在1938年继而冲击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术界。因此,在纳粹德国统治的整个中欧,“以无与伦比的、无法抹杀的,伟大而非同凡响的文化成就为标志的德意志——犹太共生现象走到了终点。”①
这些德国学术人才被驱离后,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学术人才大交换。当1933年3月,纳粹德国政府还在酝酿《重设公职人员法》时,许多对政治较为敏感的学者就已经预感即将到来的可怕事情,因而能够较早地离开德国。其中就有匈牙利裔犹太学者、法兰克福大学著名病理学教授菲利普·施瓦茨(Philipp Schwartz,1894~1977),他带着家人一起逃到瑞士。由于在瑞士没有找到工作,施瓦茨便与流亡到此的其他科学家们一起,于1933年3月在苏黎世成立了“在外国的德国科学家紧急共同体”(Norgemeinschaf Deutscher Wissenschafiler im Ausland)。该组织的宗旨是“帮助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及非犹太学者在接收德国流亡学者的国家中找到工作。”② 当瑞士的马尔奇应邀对土耳其教育体系进行考察并给予聘请外国学者的建议后,作为施瓦茨的岳父西奈·舒洛克(Sinai Tschulok, 1875~1945)教授的密友,马尔奇意识到这是拯救生命与帮助土耳其的双重机会,于是联系了施瓦茨。③土耳其政府听取马尔奇的建议,向施瓦茨伸出橄榄枝。
(二)土耳其的聘任
虽然纳粹的行为对德国来说是耻辱,但对土耳其来说却是重要机会。正如前文所提,土耳其在推进教育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高级人才教育的严重匮乏。于是,在了解马尔奇教授的报告后,土耳其教育部长加利普返回安卡拉,正式向凯末尔提出建议:伊斯坦布尔大学师资严重短缺,而大量失业的德国教授是流离失所者,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前途堪危;土耳其能否找到一种机制,邀请其中一些人到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或者担任各部委的顾问?④凯末尔的反响非常积极;在经过快速需求评估后,土耳其政府开始正式与那些愿意来土耳其的德国教授和司法学者进行沟通。
在马尔奇教授建议下,秉持对德国科学和文化的好感,并认识到机遇的出现,土耳其于1933年7月5日邀请施瓦茨前往安卡拉商议招聘流亡学者的事宜。7月6日商谈会议开始,与会双方的任务是选出某一学科的最高学历者和对应目前土耳其最需要的专业的学者。经过9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在聘用移民教授的名单上达成了一致,共35名教授得到聘请。施瓦茨代表德国海外科学家协会,与土耳其政府拟定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就职合同。合同要求来土耳其任职的教授需要使用土耳其语授课,并翻译或出版相应的土耳其语教科书,且在工作的五年间担任各学科的主任直到培养出优秀的接班人后再进行修改。
教育部长加利普在协商会议中表示:“500年前,当我们来到伊斯坦布尔时,拜占庭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开始了文艺复兴。现在是欧洲把我们失去的东西还给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希望您能将创新带入我们的祖国,以便我们能够跟上现代秩序,并向新一代展示现代科学发展的道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表示我们的感谢和敬意。”⑤会后,土耳其公共教育部宣布:“作为国家请来的客人,前往土耳其的德国科学家不与大学签约,而与土耳其公共教育部签约。在与德国教授订立的国家合同中已经写明,这些流亡学者的薪金将远远超过土耳其本土教授的薪金”。⑥后来,当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外国讲师之一格哈德·凯斯勒(Gerhard Kessler, 1883~1963)在回忆录中称赞他获准进入土耳其时,他说,“我将感谢永远感谢这个具备高尚而绅士精神的土耳其给我这个机会”。⑦对于聘请人和被聘请人来说,有如此感慨足以证明这个“应聘”过程是愉快且满意的。土耳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教育教授,而众多流亡学者不再受流离失所的煎熬,仍可保持热情继续他们倾覆一生的学术研究。
聘请名单的确定使得土耳其可以相当充分地准备高等教育改革:“土耳其政府与一些教授签订合同,并同意支付给他们远超土耳其籍教授的工资。土耳其政府的目的是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术水平提高到西欧大学的水平。”⑧在1933~1945年间,总计有190多名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科学家和艺术家被土耳其所接纳,这也使它成为接受流亡科学家第三多的国家,仅仅排在美国、英国之后。①如此之多的德语流亡学者的到来,对教育体系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不仅带来高水平的科学知识,也带来自洪堡时代以来德国大学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直接促成土耳其旧有高校体制的改革和重组,从而使这个国家的大学教育现代化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四、德国流亡学者对土耳其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土耳其政府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彻底改革的政策是必然要实现的,而这些偶然来到土耳其的德国学者使得这项政策可以快速地推进。在短短15年间,土耳其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自各个领域的流亡学者在不同学院、不同机构中任职,他们在落后的教室里传授给这个新的国家各种先进的知识、技能和思想。待这些学者离去dA1tpweDFxIpE+6m/uXYFOp6FpYJmuT7XK383nznXtg=后,土耳其将继承自那些优秀学者的知识发扬光大,也将独立发展新的技术和知识。
(一)高等教育体系改革
根据马尔奇教授的建议,土耳其政府于1933年7月31日正式取缔旧有科学院,同时取消所有现任教师的合同;8月1日正式成立新“大学”(即伊斯坦布尔大学),并于1933年11月向学生开放授课。从这天起,土耳其拥有了符合现代化标准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这所以德国大学模式而建立的新大学,被所有现有的媒体通报,不仅在大城市,即使是在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心的小镇约兹加特,其周报进行头版标题都是“科学院成为历史,新大学已建立!”②
新的伊斯坦布尔大学由医学、法律、科学和人文学院组成,另外还有8个研究所:伊斯兰研究所、土耳其革命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土耳其地理研究所、形态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机电研究所。土耳其的知名学者被选任为校长以及各学院院长,如校长内塞特·奥马尔,医学院长为陶菲特·萨利姆帕夏,人文学院院长克普里扎德·福阿德等。③
在前期的筹备过程中,土耳其教育部也已经与一些德国流亡学者签订合约,在1933年11月10日之前,这所大学已聘用35位德国学者。在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的信中,对这35人有进一步描述:“据我所知,伊斯坦布尔大学有35名新聘用的外国教授,其中30人已经抵达,除一名奥地利人和一名瑞士人外,其余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要么被驱逐,要么因为最近的政治动乱而离开德国。”④而在此后数年间,数百名德国流亡学者纷纷来到土耳其,他们隶属不同学科,满足了土耳其政府“要使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术水平提升至西欧大学的水平”的要求,以至伊斯坦布尔大学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德国大学”。⑤
这些学者的专业范围极其广泛,科学、理学、文学、商学皆有涉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这两所大学中工作,其余的少部分学者分散在各研究所甚至政府部门中。无论身处何处,从事何种工作,他们都以其专业技能为土耳其教育现代化贡献自身力量,有些学者因突出的专业能力被另聘为政府官员,直接负责土耳其的某些现代化建设任务,而这些学者也因这种信任和重视更加愿意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的部分人虽然在1938年后因政治变革而选择离开,但是大部分学者依然在土耳其生活了10年之久,甚至有几位学者选择加入土耳其国籍并终老于此。对土耳其来说,得到数量众多的优秀教育人才,不光为其高等教育建设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而且还加速了土耳其近百年的现代化发展繁荣道路。
(二)德国学者的工作
来到土耳其的流亡学者以其专业的不同被分配到各类岗位中,其中大部分人任职于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还有少部分任职或兼职政府顾问和工作人员。他们与土耳其人共同努力,快速建立起高等教育体系,推行新的教育,培养了许多学术和研究人才。在土耳其,德国的流亡教授担任12个基础科学研究所中的8个主任,以及伊斯坦布尔医学院17个科室的6个主任,其教学方法,教育理念无不仿照当时代表世界一流学术水平的德国大学模式,一时间伊斯坦布尔大学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德国大学”。①
出于工作的需要,德国学者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障碍。在课堂中,学生和教授都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的语言,并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转换:从旧的土耳其语到新的土耳其语,从一种欧洲语言到土耳其语。②这些来自异乡的学者几乎都承担起了翻译家的工作,他们将不属于这个国家的语言更贴切地翻译成土耳其语,以便这些学生更有效地学习。德国学者对土耳其的教育贡献首先体现在这一点上,他们为土耳其建立了符合时代的科学语言,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知识得以顺利地在土耳其传播。德国学者对土耳其的教育贡献首先体现在这一点上,他们为土耳其建立了符合时代的科学语言,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知识得以顺利地在土耳其传播。
在教学过程中,虽然合同上没有规定,而且德国教授也不愿自己准备教材,但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工作的教授中大约有80%都至少出版了一本书,60%则出版两本或更多。医学系教授出版图书的数量最多,人均出版三本或四本。③除此之外,同样出于教学需要,一些德国学者还翻译了许多专业书籍,例如为土耳其化学学科奠定基础的阿恩特教授,70多年后,他的一位学生、伊斯坦布尔大学化学工程系退休教授伊斯迈特·古尔吉(?smet Gürgey, 1923~2009)指出在为土耳其科学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移民学者中,应该包括“奥德教授、弗里茨·阿恩特博士,也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他为土耳其带来了当代化学的基础和原理。”④因为在每本书的结尾,阿恩特都以现代土耳其语、奥斯曼土耳其语、德语和英语列出所有化学术语和概念。“阅读这些小词典,尤其是在将奥斯曼帝国的术语和概念与土耳其语同义词进行对比之处,就有可能看到化学语言的提纯程度,这些术语和概念沿其简化之路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这绝不会削弱他所取得的成就。在他的书中,没有一种渴望使用德语、英语或奥斯曼语的术语的感觉。除了阿恩特教授在化学领域对土耳其语言精炼以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人文学科、艺术和专业也有这类语言改革的代表。”⑤
同样是出于教学和工作的需要,土耳其的图书馆和学术杂志也快速发展起来。出于科研的需求,德国教授们列出他们需要的书籍和期刊,并经常为这些来自欧洲的出版物撰写报告和文章。而土耳其政府和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也不遗余力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短时间内,图书馆内汇集了大量德语、英语和法语书籍,恩斯特·赫希(Ernst Hirsch)教授带着助手担任图书管理员,对书籍进行登记、整理。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回馈社会,学术研究的进步也离不开同行的交流与评议,因此每年夏季会在不同地方召开开放式的“大学会议”和“大学批判”研讨会。一批学术杂志,如《法学杂志》和《科学学院学报》(1935)、《罗马学杂志》(1937)、《医学学院学报》(1938)、《经济学院学报》(1939)、《心理学和教育学杂志》(1940),也纷纷创刊。⑥
二战结束后,这些流亡的德国学者除个别留在土耳其外,大多选择离开,一些人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或回到他们的故乡。⑦ 留下来的学者依然对土耳其的科学教育与研究做出杰出贡献,如阿尔弗雷德·埃里克·弗兰克教授和科特·科斯威格教授,为感谢他们的付出,在他们在离世后,土耳其为其举行了国葬。⑧ 而德国流亡学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土耳其这10多年的教学经历也留下了突出的成果,即: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高等教育领域有221名讲师和2462名学生。15年后,这些数字增长到855名讲师(增长287%)和10213名学生(增长314%);1933年共有3437名学生被伊斯坦布尔大学录取,其中884人被医学院录取;1933年至1946年间,共授予博士学位41个。①
德国学者离开后,他们培养出的土耳其学生成为后来土耳其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主力。例如学习经济的雷菲·苏克鲁·苏维拉(Refii ?ükrü Suvla, 1908~1962)曾多次为央行和其他国有银行提供建议;穆利斯·埃特(Muhlis Ete, 1903~1975)成为商务部长;奥斯曼·奥基尔(Osman Okyar, 1917~至今)在中东理工大学任教,后来成为埃尔祖鲁姆大学校长等等。这些学生至今仍在土耳其高等教育领域和政府中为土耳其的现代化踵事增华。
德国学者留下的遗产不仅仅表现为他们直接培养的人才,还表现为他们帮助建立和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继续为土耳其培养人才。而伊斯坦布尔大学作为土耳其政府着力建设的高等院校,也是聘用德国流亡学者最多的大学;在此后十几年间,它在土耳其科学领域的影响性首屈一指,同时也领导着土耳其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运动。安卡拉大学于1946年正式合并多个学院而成,其中就包括1935年的历史和地理学院和1943年的理学院,二战期间有许多德国流亡学者在这里工作。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前身是1773年成立的公共工程学院,1924年改名为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以工科为重,许多工科领域的德国专家曾在这里工作,使其在相关学科有了巨大进步,并为土耳其培养出大量建筑、工业领域的人才。②
德国学者的到来直接帮助土耳其各大学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化的大学学科,众多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为土耳其带来了如经济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图书馆学等科学,③这些科学此前从未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出现过,但在德国学者的支持下,他们扎根在土耳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为土耳其国家现代化发展不断培养各学科人才。而土耳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德国学者离开后也十分突出。一方面,大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如伊斯坦布尔大学设立之初有4个学院8个研究所,现在扩展到17个学院、5个系、12所高等教育培训学院及数十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安卡拉大学根据社会需求不断设立新学科:政治学院(1950)、药学院(1960)、牙科学院(1963)、教育学学院(1965)、传播学院(1965)等,截至2015年9月,土耳其共有193所大学(不包括军事类院校),其中公立大学109所,私立大学76所,高等职业院校8所。④ 这些数量庞大、学科健全的高等院校机构不断为土耳其共和国输送人才,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五、德国学者在土耳其的生活和离开
在那个时代,这些流亡的德国学者的经历是坎坷的,他们被从故乡驱逐,流离失所,多数人在找到容身之所前穷困潦倒,他们的命运与那个动荡的时代一样波澜起伏,但他们的形象却又如星辰一般闪耀于人类文化的最高殿堂。
(一)德国学者在土耳其
学者们被从德意志驱逐,却因为当时盛行保守主义的世界而无处可去,但又因人性的高尚而绝处逢生。在1933年,当土耳其决定聘任35位德国学者时,希特勒命令时任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干预这些流亡学者入境土耳其,巴本在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命令我收回所有在土耳其的德国流亡者的护照,并剥夺他们的德国国籍。我拒绝了这个命令,并告诉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大多数移民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许可离开了德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土耳其的大学任职……我无法执行他的指示。”⑤由此这些颠沛流离的德国学者得以顺利到达土耳其继续从事他们为之自豪的工作。
而这些来到土耳其的德国学者在新生活的伊始并非如想象般顺利,异国他乡的生活所带来的陌生感和文化隔阂在一开始就困扰着学者们的心情。弗里茨·诺伊马尔克(Fritz Neumark)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我们想念那里的风景,尤其是‘我们的’语言。很难说哪一个对我来说更糟糕,可能是语言。卡尔·扎克梅尔(Carl Zuckmayer)在《格林兄弟》(The Brothers Grimm 1948)一文中提到了‘语言思乡’,并准确地指出,对于一个流亡在外的作家来说,这是‘最痛苦的思乡形式’——而我们几乎都是作家。”⑥对纳米技术突破有重大贡献的冯·希佩尔(Von Hippel)教授曾记载道:“我们这些新来的人,骨子里带着因流放而产生的失落感,当发现自己被一种陌生文化中的阴谋所包围时,任何成功或不幸都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①德国流亡学者怀揣着此类心理困境而在土耳其展开工作,但重回故土的希望却因战争的到来而一点点破碎。
可是他们面临的窘境并不只有这些不断的思乡情,在生活中他们必须面对来自被他们占据工作岗位而失业的土耳其各行业从事者的仇视。在土耳其本土教授的眼中,本该属于他们的待遇良好的工作岗位和高工资被分配给了外国人,而他们的工资却比德国学者少了许多,这种不公是不可接受的;同时,医学教授在整个土耳其医学界的支持下表达对德国学者的厌恶,而原因是德国学者提供的医疗服务远好于本土医生,这使得原有的土耳其医生诊所的生意大大减少。②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评价道:“土耳其人有一种强烈的反德情绪。”③然而在学术圈内及大学体系下的敌对态度并不能代表整个土耳其社会的想法。我们可以很高兴地看到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对这些流亡学者秉持着良好的欢迎姿态,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流亡学者是这个国家“尊贵的”客人。
时任德国报纸驻伊斯坦布尔代表维克多·穆勒(Victor Maurer)在其向德国的报告中表示:“应邀到该大学任教的许多德国教授(其中有犹太人)受到土耳其舆论的友好欢迎,从而促进了德国文化的宣传。”同时期的土耳其报纸头版上都在详细报道德国流亡教授的信息,无不表示了对这些学者的欢迎。而在政府建设工作中,安卡拉当局试图为德国教授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让他们继续工作。同时他们在实验室和医院的设备上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人们可以看到土耳其医院的设备与世界上任何一家医院不相上下;在安卡拉的高层人士中存在着对这些教授的大力拥护者和保护者,对他们提出的任何投诉都被国会充耳不闻。④这些支持和尊敬不仅体现在政府的工作上,更表现在国家庆祝活动中对流亡学者地位的肯定。1933年,土耳其举办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活动,当时到达土耳其的许多德国学者都受到邀请出席这一重大的庆祝活动。恩斯特·赫希教授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位德国教授,在他的祖国德国作为犹太人而受到鄙视,因为他的‘劣等’种族(身份)而被辞去了职位……但在‘遥远的土耳其’却被认为是该国前千名之一的精英!”⑤这种极高的尊重感动着流亡的学者,让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找回了在祖国失去的尊严,而我们在那个时代的土耳其见到的是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国家富强的期待。
(二)德国学者的离开
很可惜的是大部分德国流亡学者并没有在土耳其生活和工作太长的时间,他们在土耳其的历史烟尘中逐渐消去,转而回到人类历史的宏伟舞台中继续表演。这也正是在土耳其的流亡学者比流亡美国或其他各地的学者知名度更低的原因。
大部分流亡学者在两个时间段——1938和1948年——集中离开了土耳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择去往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或去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重建家园,少部分人选择回到德国。
而193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第一批来到土耳其工作的学者的五年工作合同已经到期,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因凯末尔去世而带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抬头而产生的敌视态度。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状况逐渐恶化,而政府并没有实行补偿性工资调整并缺乏相应的养老金计划,使得学者们在1938年签约时获得的工资因通货膨胀而不再有吸引力。⑥种种因素叠加起来使得许多学者决定在这一年离开土耳其去往他国寻求出路。
到1948年,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复兴建设。这一时期离开的学者多为续签了两次合同但要面临第三次续签的学者,战争的结束为这些学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土耳其的挽留并不能改变这些客人的决定,只能按照合同与他们解约。虽然他们离开了生活了十五年的土耳其,却留下了一个建设完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对土耳其来说,这些尊贵客人的离开并不会阻碍这个国家的持续发展,土耳其从此将创新发展道路,延续由流亡学者带来的知识,创造更符合时代的高等教育体系。
六、结语
“历史中充满了意外事件,有些是灾难性的,有些则是幸运的。有时一个国家的不幸却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幸运,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土耳其的大学改革时代。”①当纳粹德国因为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大规模清洗那些优秀的学者时,未曾预料到那些被歧视排挤的人会成为另一个落后国家日后发展的重要保障。当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为前途担忧四顾无望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命运会将大量的优秀学者送来这个羸弱的国家,帮助其建设梦寐以求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这个体系是一个国家在现代竞争中的基石。
建国之初的土耳其共和国面对落后封建教育的困境,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缔一系列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较为优秀的基础教育体系,保证了世俗化的稳步推进。而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思想文化教育水平,建设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和文化体系,土耳其的缔造者及时利用了德国民族主义激化后的反犹反社会主义浪潮,引进大批优秀学者充实其高等教育体系,在短时期内兴建众多模仿德国教育的高等院校,并培养了众多优秀的高等教育人才。
当1933年10月25日以施瓦茨为首的35位德国流亡学者到达伊斯坦布尔时,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列车终于添加了一罐优质的燃料,正式驶向新的时代。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约190位学者在教学、图书、翻译、科研等领域帮助土耳其快速建立起一个比肩西欧的大学体系,这些学者在战后多数离开了暂居的土耳其,但是其付出却永远被记载于土耳其的百年史册里。
土耳其的大学改革运动是其发展道路上必然的选择,新生的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和繁荣必然要经历学习、仿造到研制、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唯此才为国家的前途夯实基础,构建框架。德国流亡学者的到来却是偶然的,没有他们的贡献土耳其现代化的进程可能要推后更久的时间,流亡学者就像是为这辆即将飞驰的汽车进行改良修理的机械师,为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更换了性能更佳的发动机,加速了其发展。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