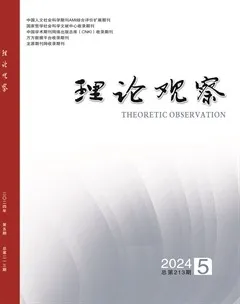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农户增收效应评估
摘 要: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是破解农村地区有效抵押物缺乏、信贷资金匮乏与收入增长迟缓困境的必要举措。本文以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广西91个县域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PSM-DID)法,研究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并利用分组回归法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改善作用,且该结果在更换匹配方法、安慰剂检验、剔除贫困县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但增收效应在不同的县域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健全配套机制体系和因地制宜改善地区基础条件等政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发挥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效果、促进农户收入提升以及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农地经营权;农地抵押贷款;政策效应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5 — 0097 — 10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参与和支持,持续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是缓解农村地区融资难题、摆脱农户收入增长滞后困境的重要途径。土地是农村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农户所拥有的最重大资产,如何用好农村土地资源,实现资源变资产再变资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钱的问题的关键。为此,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赋予农户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能,并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首次明确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可抵押性。2015年底,党中央选择了北京市大兴区、天津市蓟县等232个试点县级行政区域和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级行政区域,自2016年起开展了包括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试点工作。经过两年的试点,截至2018年9月,全国232个试点地区农地抵押贷款余额达520亿元,同比增长76.3%。2019年施行的新《农村土地承包法》更是给予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明确的法律依据,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金融创新的延伸。然而,随着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的逐步推进,各地在实际试点工作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进程缓慢、土地流转交易机制不健全、产权价值评估体系不完善等,严重制约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效果。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是否充分发挥了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困境,进而达到促进农户增收致富的目的,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在全国多个省份开展实施,但各地情况不一,可能导致政策试点实施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广西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范围广泛,农业资源禀赋条件较好,同时以田东县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典型案例为代表的广西农村金融改革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中,广西有8个县(市、区)被选为试点县,包括田东县、田阳区、玉州区、北流市、兴业县、武鸣区、东兴市和象州县。在近年试点期间内,广西8个试点县域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最高达到10.76亿元。由此,利用广西县域样本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农户增收效应进行评估,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异质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和代表性。
二、文献述评
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农户拥有的财富有限,为了自身生计和农业经营发展,需要通过有效的信贷渠道以获取资金,而农地抵押贷款正是各国缓解农村贷款难题的重要工具(Collins et al.,2009)[1]。Besley(199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中,抵押品稀缺是其显著特征之一[2]。一方面农户自身资产的匮乏,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产权制度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并非天然地缺少抵押品,而是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农户所拥有的资产无法实现资本化,进而成为“沉睡”的资产。土地确权能使土地实现流转并具备可抵押性,促使农户获得相对长期稳定的信贷支持。这种通过明晰资产产权使其具备有效抵押品的属性,进而使信贷市场运行绩效得以改善的现象(De Soto,2000)[3],被称为德·索托效应(De Soto Effect)。而农地抵押贷款正是一种可以将土地产权作为抵押物的金融产品,其可以通过发挥德·索托效应,缓解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困境。国外大部分学者支持农地抵押贷款能促进信贷可得性的看法。Kemper et al.(2015)以越南为例发现农地抵押贷款能够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对缓解个体农户的信贷约束起到一定效果[4]。Stupen(2014)认为将土地抵押化的信贷机制能促进农业部门的投资增加,进而提高农业效益[5]。然而,也有少部分学者持有相对保守的态度。Nikaido et al.(2015)利用印度样本研究发现持有土地产权与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可能的原因在于陈旧的土地管理制度导致以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交易成本较高[6]。
围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信贷可得性、抵押模式和风险成效等方面。高圣平(2014)认为以农地抵押为基础和核心的农地金融化制度改革既是必由之路,更是当务之急[7]。在我国推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过程中,各地因地制宜,进而在现实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模式。如以四川温江、陕西高陵、宁夏平罗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以宁夏同心、山东寿光等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刘钰等,2019;罗剑朝等,2014;王文锋,2015)[8][9][10]。宋坤和徐慧丹(2021)研究认为发展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应量,并发现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模式变迁是农地抵押贷款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11]。而根据抵押模式划分,可以进一步分为直接抵押模式和间接抵押模式。前者指的是单独用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后者指的是在农地经营权抵押基础上还附加反担保等其他担保抵押方式、引入财政风险基金或保险等其他风险分散机制,并且前者所具备的门槛与条件相对较高(黄惠春和徐霁月,2016)[12]。另外,还可以根据产权属性或融资主体划分为“分而不离”的承包型和“既分又离”的流转型(阚立娜等,2021)[13]。
随着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各地逐步推行,其中的阻碍与风险日益凸显,导致贷款发展进程缓慢。对于制约与阻碍因素,多数学者认为制度因素是主要因素(赵丽琴和王熠,2019)[14]。林一民等(2020)研究认为我国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可能导致农户经营权可抵押和农户不可失地的悖论、抵押物价值不高、供需主体积极性不高的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产权空转”的现象[15]。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陈菁泉和付宗平(2016)认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实践中发展困难是由于缺乏风险补偿机制[16],并存在经营风险、信用风险、银行操作风险等问题(秦大钊,2017)[17]。此外,荆会云(2021)结合辽宁省昌图县案例揭示了农地经营抵押贷款面临风控体系不健全、处置变现不畅、风险分担机制固化等风险问题[18]。随着各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持续推进与发展,不少的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多数学者认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可以提高农户的有效需求和金融机构信贷供给,对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作用显著(赵丙奇,2017;杨润慈等,2022)[19][20]。在促进收入提升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马嘉鸿等(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贷款能对农业收入有明显提高作用[21]。而梁虎等(2017)通过对宁夏和陕西地区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仅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农户起到促进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较贫困农户的收入增长问题[22]。李波和张春燕(2021)研究发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从促进地区金融信贷供给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显著促进农户收入提升[23]。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农业经济、普惠金融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等均有显著的促进效果(田杰等,2022;许恒周和曹旭欣,2023)[24][25]。
纵观现有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展开了广泛探讨与深入研究。我国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由于区域条件差异性,各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施进展不一,导致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信贷或收入的影响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性。针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农户增收效应,已有文献中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且少有同时探讨不同经济基础条件及土地资源情况的县域是否存在异质性的问题。因此,本文以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为例,研究分析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政策增收效应,既是对已有研究的实证补充,也可进一步丰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与农户收入的相关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2—2021年的广西县域面板数据,研究分析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改善效应。数据的初始样本为广西111个县域的数据,但由于个别县级行政区域发生变更以及研究数据的缺失,将秀峰区、平桂管理区等部分县域样本进行剔除,进而整理出广西91个县域的平衡面板数据。宏观经济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2022年的《广西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缺失数据则通过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各县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工作报告等进行补充。
(二)模型设定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可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为避免样本的自选择问题,参考孙焱林等(2019)及徐春秀和汪振辰(2020)的研究[26][27],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对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农户收入改善效应进行评估。即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为有试点农地抵押贷款政策的实验组匹配到相近的没有试点政策的对照组,再使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对检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净效应。其中,实验组为广西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的8个试点县,对照组为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匹配到的广西其他非试点县。为了进一步避免不可观测因素和时间效应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进行效应评估。模型设定如下:
incomeit=?茁0+?茁vtreatedi×postt+?撞?茁xcontrolit+ri+vt+?着it(1)
其中,incomeit为被解释变量,即农户收入水平,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县域和第t年,?茁0为常数项。treatedi为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个体虚拟变量,postt为区分试点实施前后的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treatedi×postt为衡量是否实施试点政策的核心解释变量,?茁v表示政策的收入改善的净效应系数,用来反映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净影响。controlit为一系列可能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资本支出水平等,?茁x为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vt为时间固定效应,ri表示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着it为随机干扰项。
(三)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实施目的在于盘活土地资产使其可抵押化,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富裕,故被解释变量将从农户收入这一维度进行选取。借鉴徐旭初等(2023)中的做法,用县域地区实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农户收入水平(income)[28]。为了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影响,利用广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平减计算。
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实施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treated×post)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某一地区是否实施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若实施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中treated为政策虚拟变量,若是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试点县,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post是实施试点与否的年份虚拟变量,政策实施时点以2016年为准,若该年份为2016年或在2016年之后,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为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通过参考周密等(2020)、罗明忠等(2023)多名学者关于农户收入方面的研究[29][30],本文主要从县域层面选取可能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财政支出规模、资本投入水平、城镇化程度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PSM样本匹配
本文利用Logit模型与核匹配法对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与非试点县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其中,结合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域的选取条件或特征并考虑数据资料的有限性,本研究参考胡原和曾维忠(2020)的做法[31],除了选用上文提及的6个控制变量即财政支出水平、资本投入水平、城镇化水平、粮食供给水平、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外,还选取了用县域常住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来衡量的人口密度作为匹配使用的协变量,以期获得与实验组更为相似且更具有可比性的对照组样本。为验证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是否有效,采用平衡性检验进行验证。平衡性检验要求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各个可观测匹配变量上无显著差异,并且经过匹配后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20%(王慧玲和孔荣,2019)[32]。通过平衡性检验,除了资本投入水平外其余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匹配后都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且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和变量的P值均满足平衡性检验要求,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有效。
为了进一步检验匹配结果的可信度,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分布图(图1)可以发现,匹配后的实验组与对照组核密度分布的重合范围明显增加,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存在较大的共同支撑域,表明匹配效果较好。其中,匹配前的初始样本量共有910个,匹配后处在共同支撑域内的样本共有653个,损耗样本257个。总体来看,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为接下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农户收入改善效应提供了较好的样本基础。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重要假设条件之一是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受到外生冲击前需具备共同趋势,即试点县与其余非试点县的农户收入水平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实施前应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为了验证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是否满足这一假设,本文将参考Beck et al.(2010)以及斯丽娟和田金铃(2023)的做法[33][34],运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的实证分析,即在回归中引入政策虚拟变量与各个年份虚拟变量形成的一系列交互项。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该图展示了系数以及其在95%置信区间内的显著性。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前即2013、2014及2015年系数的置信区间均包含0值,表示系数均不显著,反映出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农户收入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同时,2016年及以后年份的系数均显著,且总体呈缓慢增大的趋势,因此可以反映出农地经营权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增强。
(三)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前述模型设计和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数据,以农户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同时报告了未控制其他变量与控制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1)直接用核心解释变量即实施试点政策进行回归,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财政支出水平、资本投入水平、城镇化水平、粮食供给水平、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六个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和(2)中核心解释变量实施试点政策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在选定样本区域产生了明显的收入改善效果,对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发挥了显著促进作用。比较各列修正后的R2与组内R2可以发现,引入控制变量的模型(2)相比模型(1)具有更高的拟合程度。根据模型(2)的估计系数可以看出,实验组的农户收入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平均增长了8.34%,表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确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改变在倾向得分匹配过程中所使用的匹配方法、安慰剂检验、剔除贫困县样本等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匹配方法即将核匹配法分别改变为最近邻匹配法(1:4)、半径匹配法(范围为0.02)和卡尺最近邻匹配法(1:4且范围为0.02),由此分别获得282个、643个和278个样本,再针对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户收入提升的政策效应逐一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第二,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选取实验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在安慰剂检验中,随机抽取实验组后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将此过程重复500次,进而得出500个虚拟估计系数,再将其分布绘制成图,并与基准回归结果所得的真实估计系数进行比较,结果如图3所示。第三,根据2012年3月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广西共有隆安县、田东县等28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通过剔除这一部分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基于以上三种稳健性检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农户增收效应显著为正,由此印证了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五)异质性检验
区分农户收入水平的异质性检验。为考察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农户增收效应对不同农户收入水平的县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县域实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分组界线,将倾向得分匹配所得样本划分为高收入水平组和低收入水平组,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列2是高收入水平县域的结果,列3是低收入水平县域的结果。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于高收入县域的农户收入存在显著改善作用,而对低收入县域的农户收入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高收入水平农户相较于低收入水平农户往往拥有更强的偿债能力,而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安全性的考虑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这类新型贷款产品的发放较为谨慎,即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向高收入水平农户发放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导致低收入水平农户可获取的信贷资金相对较少,进而难以实现收入增长。
区分县级行政区域类型的异质性检验。为了研究不同行政区域类型的县域在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农户增收效应中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根据广西8个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域中所包含的县级行政区域类型即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分组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三组子样本再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其中列2展示的是县的结果,列3展示的是县级市的结果,列4展示的是市辖区的结果。结果显示不同行政区域类型的县域之间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所形成的农户增收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且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农户增收效应依次增强,由此可以反映出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在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时可以发挥出更好的增收效果。
区分农地规模的异质性检验。为研究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不同农地规模的县域的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县域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均值为准划分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7,其中列2展示的是拥有大规模农地县域的结果,列3展示的是拥有小规模农地县域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农地规模面积越大,土地评估价值可能就越高,致使农户所能获取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额度越大,从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农户收入提升效应更加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农地抵押贷款与农地经营权贷款试点政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西为例,将2016年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2—2021年广西91个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研究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改善的政策效应,并对不同经济水平与不同土地禀赋特征的县域之间的增收效应进行异质性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于农户收入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与非试点县相比,在试点县域内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了8.34%,且该结果通过了更换匹配方法、安慰剂检验、剔除贫困县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稳健。(2)广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农户增收效应对于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县级行政区域类型、不同农地规模的县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于农户收入水平偏高、行政区域为县级市或市辖区、农地规模较大的县域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农户收入提升作用,而政策增收效应对农户收入水平偏低的县域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切实扩大农地经营抵押贷款实施范围。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县域农户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佐证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于实现农户收入增长、推进乡村振兴以及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发展予以政策制度及法律层面的重视和支持,进一步扩大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试点范围。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有序探索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积极引导其在借鉴其他地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出台规范、具体、全面、有效的试点实施方案、贷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推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快速稳妥落地。另一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通过优化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贴息政策、税收优惠、风险管理等方式,提升金融机构、农户或农业经营主体等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第二,优化金融供给结构,着力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效供给。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现增收改善效应首先是要实现信贷便利化,而信贷便利水平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给息息相关,且直接依赖于金融供给体系。因此,应当适度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并鼓励城商行、国有行、政策行等非农金融机构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进一步拓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给主体。同时,还应优化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结构设计,积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进一步满足农户或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持续探索开发以农村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抵押贷款产品,积极创新抵押担保方式。
第三,健全配套机制体系,有力支撑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顺利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推进离不开贷款的顺利发放,应畅通贷款各项环节流程,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向农户发放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加快形成科学完善的农地产权价值评估体系,设立专门的农村土地产权价值评估机构,积极引入相关产权价值评估人才,形成统一合理的产权价值评估方式。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市场和交易流转体系建设,积极构建省(自治区)、市、县、乡镇四级联动、信息互通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大数据信息平台,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提高土地经营权流转处置效率。持续健全风险分担保障机制,着力提升风险保障基金规模,规范基金管理流程,协助建立第三方处置机构,并积极引入第三方担保机构、保险公司等,探索构建“政、银、保(担)”多方协作模式,以市场化的方式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可持续的风险保障。
第四,因地制宜改善地区基础条件,充分发挥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施效果。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收入提升效应对于不同县域之间存在异质性,为此应针对不同县域情况改善其相关基础条件,充分发挥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效果。注重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条件,从财政、金融、产业、就业等多个方面对其予以支持,多措并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户收入。一方面,持续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所依靠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等基础建设,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试点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村土地的保护,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破坏农用地行为的惩戒力度,持续推进农用地补充建设,同时加快推进土地流转,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Collins D, Morduch J, Rutherford S, et al. Po-
rtfolios of the poor: how the world's poor live on $2 a da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Besley T. How do market failures justify int-erventions in rural credit markets?[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994, 9(01): 27-47.
[3]De Soto H.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
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M]. Basic books, 2000.
[4]Kemper N, Ha L V, Klump R. Property righ-
ts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Evidence from a land reform in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1: 107-130.
[5]Stupen R. Development Of Land And Mortg-
age Crediting Of Agriculture Through Land Banks Mechanism[J]. Ukrainian Journal Ekonomist, 2014 (04): 31-34.
[6]Nikaido Y, Pais J, Sarma M. What hinders and
what enhances small enterprises' access to formal credit in India?[J]. 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 2015, 5(01): 43-52.
[7]高圣平.农地金融化的法律困境及出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4(08):147- 166+207-208.
[8]刘钰,宋坤.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履约机制研究:成都温江花乡农盟例证[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10):111-118.
[9]罗剑朝,杨婷怡.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验典型模式比较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4(06):10-17.
[10]王文锋.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运行机制探索——基于山东寿光市与宁夏同心县的考察[J].世界农业,2015(09):102-106.
[11]宋坤,徐慧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选择:转型与路径[J].财经科学,2021(06):92-104.
[12]黄惠春,徐霁月.中国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基于抵押品功能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12):95-102+112.
[13]阚立娜,苏芳,常建新.基于产权属性差异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评估价值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1(04):103-112.
[14]赵丽琴,王熠.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19(12):81-82.
[15]林一民,林巧文,关旭.我国农地经营权抵押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J].改革, 2020(01):123-132.
[16]陈菁泉,付宗平.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形成及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6(10):143-154.
[17]秦大钊.农村商业银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防范研究[D].安徽农业大学,2017.
[18]荆会云.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的风险揭示与控制[J].财会通讯, 2021(12):141-145.
[19]赵丙奇.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融资效果评价[J].社会科学战线,2017(07):55-64.
[20]杨润慈,石晓平,关长坤,蓝菁.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吗?——基于风险分担机制的调节效应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22,36 (05):51-60.
[21]马嘉鸿,兰庆高,于丽红.基于农户视角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绩效评价[J].农业经济,2016(06):106-108.
[22]梁虎,罗剑朝,张珩.农地抵押贷款借贷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计量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10):106-118.
[23]李波,张春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对湖北省50个县(市、区)的实证研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39(03):111-122.
[24]田杰,胡子豪,熊学萍.农地抵押贷款政策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17977个家庭农场30449个微观数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2(06):41-50.
[25]许恒周,曹旭欣.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试点县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中国土地科学,2023,37(05):57-66.
[26]孙焱林,李格,石大千.西部大开发与技术创新:溢出还是陷阱?——基于PSM-DID的再检验[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06):51-62.
[27]徐春秀,汪振辰.中部崛起政策对地区产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与机制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一项拟自然实验[J].产经评论,2020,11(02):68-79.
[28]徐旭初,徐之倡,吴彬.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吗?——基于801个县域的PSM—DID检验[J].学习与探索,2023(12):77-89+178.
[29]周密,赵晓琳,黄利.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南方经济,2020(05):18-33.
[30]罗明忠,魏滨辉.返乡创业、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01):83-96.
[31]胡原,曾维忠.碳汇造林项目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吗?——基于四川县域面板数据的PSM-DID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2):89-98.
[32]王慧玲,孔荣.正规借贷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了吗?——基于PSM方法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9(08):72-90.
[33]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05): 1637-1667.
[34]斯丽娟,田金铃.生态文明试点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基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J].财贸研究,2023,34(11):29-41.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