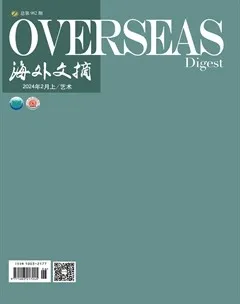洛神形象在古代文学史中的发展脉络
洛神,作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洛神自诞生起至今已逾千年,作为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学形象之一,以洛神为主题的创作,贯穿了自战国起至现当代的数千年历史,遍及了诗词歌赋、书法、舞蹈、戏曲、绘画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她在先秦时期已初具雏形,屈原的诗歌赋予了她姓氏和名字。在两汉作家的笔下,洛神形象逐渐丰满起来。到魏晋时代曹植的《洛神赋》中,洛神故事才有了完整的情节,一个美貌多情、高贵灵动的完美女神形象也得以塑造。唐宋时期的文学创作为洛神增添了凡人女性特有的魅力和生动。至明清时期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甄后》中,洛神的个性色彩再次被加强,展现出觉醒意识和反叛精神。经过了数代文人在其初始形象之上的不断加工与完善,洛神的形象特点及文化意蕴不断丰富,得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恒长的时间线上历久弥新,始终不曾褪色。本文依照洛神形象发展演变的时间脉络,以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及明清为节点,在梳理各时期文学作品的基础之上,结合部分具体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该形象的特点,并着重讨论该形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展现的文化内涵。
1 先秦时期屈原与朦胧的洛神形象
先秦时期,楚地受地理环境影响,与中原文化交流受阻。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吸收本土文化,形成稳定文化根基,这导致楚地文化相对滞后,原始宗教特征得以保留,崇尚巫祭之风盛行。楚文化,以楚族本土文化为基础,受中原夏商周文化与土著民族文化影响,涉及政治、宗教等方面。楚辞是楚文化的载体,反映楚国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屈原时代,楚地贵族推崇鬼神,《楚辞》中神女形象与此背景紧密相关。
洛神形象源于上古神话,早期无纸质记载。屈原的《天问》中首次书面记载洛神,在先秦神话中,洛神是河伯妻,后被夷羿抢占,作为配偶神存在,人物形象较为单薄。上古时期,母系社会形成生殖崇拜与女性神化的状貌,洛神形象的描写,更倾向于一种符号的表现方式,表达着古代人民对后代绵延、子嗣兴旺、征服自然的朴素追求。最早期的洛神便是一个与性爱、生产相关联的模糊符号。
在《离骚》中“求宓妃之所在”,洛神首次作为诗人所追求的神女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厥美”与“信美”是屈原对其外貌直接的赞赏,而屈原对其竭力的追求,也间接体现了其让人为之倾倒的美貌。但这里的“美”是模糊而朦胧的概括词,没有具体的描写,作为依托,后人在此描写之上,可以进行无尽畅想。在屈原笔下,洛神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即“信美而无礼”。诗人最终因其傲慢无礼、淫游无度弃之而去。诗人笔下,她是一个倚仗美貌而纵欲随意的女性。
无论是配偶神,还是“信美而无礼”的女神,屈原笔下的洛神形象,总体较为负面,这与屈原楚辞的整体思想倾向有关。诗人通过假借外物与浪漫故事衬托自我品格,宓妃形象迎合此目的,作为一种反衬。正是因为洛神初期形象的负面性,才使得其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着多样而丰满的人格。
2 两汉时期的洛神形象
受屈原影响,西汉文人初对“洛神”多持批判态度。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文人对“洛神”形象的思考,逐渐变得尘世化、个人化。“洛神”形象在演绎与发展中,也被赋予了多种深刻含义。
刘安的《淮南子·俶真训》中“宓妃”虽然是圣人的配偶之一,但身份从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神女转为了“妾”,与之前“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才能得见一面的境况已经相去甚远。此时,“洛神”作为衬托圣人的存在,已经逐渐脱去了神秘性,走向尘世。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将之与女乐画上等号,形象由神仙妃子变为宫中伶人。又如扬雄在《甘泉赋》中把宓妃视为祸水,在《羽猎赋》中写到“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肆意鞭打这样一位“神女”去给屈原送饭,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手法,但是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其中批判的意味。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成为大一统境况下的正统思想后,文人依然着重描写“洛神”外貌上的美丽,而未有内涵上的明显转变。虽然在技能上有所丰富,例如琴艺等,但是并未对此前黄老思想背景下“洛神”形象有根本性的影响。东汉时期,“洛神”形象发生了巨大转变,文人不仅肯定她的神女身份,其更是成为文人士大夫内心情感的寄托。
在东汉蔡邕的《述行赋》中,“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在这里,“洛神”是美貌与善良的化身,也表达作者呼唤统治者救黎民于水火,寄托了他浓浓的情思。但这里与之前提及洛神的动机不同,前代提及洛神,大多是与屈原有关,而在这里是因为作者赴洛阳,坐船渡洛水而思及洛神,这里的洛神,已经逐渐脱离了屈原而成了一个独立形象。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士人个性化抒情打破束缚,文学创作中的抒情方式和抒情内容,也随之有所转变。“在对政治和自己曾经倾心的经学失望之余,汉末文士开始尝试着在个性情感的自由舒放中寻找精神的愉悦。[1]”在这种解放与尝试之中,宓妃(即洛神)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3 魏晋时期的洛神形象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洛神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完美理想的寄托。相较于两汉对洛神德行方面的偏颇否定,魏晋文人抛却“形美质损”的特点,转而极尽笔墨描写、赞美洛神的外在形貌以及内在灵秀,并赋予其完备的神格,塑造出高贵灵动的神女形象。
细究洛神形象发生重大转变的来由,当首推曹植所作的《洛神赋》。《序》中言,“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即曹植笔下的洛神有两个灵感来源:一是有感于宋玉所作的神女故事《神女赋》《高唐赋》等;二是行至洛水时受有关“洛河之神”——宓妃的传闻启发,遂以第一人称叙写下《洛神赋》的故事,借此来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植摒弃了一切玷污洛神形象的负面言辞,从形与神两个方面极力赞美洛神的完美与高贵。“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由形貌衣着到行为举止,一笔一画地细腻雕琢,有极强的画面感,令人生出无尽的遐想。“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曹植抛却了前朝对于洛神“信美无礼”“形美质损”的描述,转而赞美其习礼明诗的美德,一位柔美灵秀的神女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与此同时,赋予洛神身份充分的复杂性和神秘感,引起后世文人对此的种种注说与揣测,之后的文人续写着《洛神赋》中的神女形象。
除了作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洛神也成了书画作品的素材。东晋画家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以《洛神赋》为根据,生动描绘了洛神与陈留王相遇、相恋、相离的爱恋故事。书法名家王献之以小楷抄写《洛神赋》,传至唐朝,被时人名为《洛神赋十三行》。
两晋以降,洛神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继续演变发展,日趋丰满。宫体诗歌中,洛神直接成为美人的代指,用以褒扬现实中的美人形貌,但其内在气质、行为性情等表现,却无法得见。如南朝萧衍所作《戏作诗》中“宓妃生洛浦”一句,以“洛浦”作为诗歌意象,指美人云集之地。
随着南北朝时游仙诗的兴起,洛神常以神仙的面貌见于诗文,用以表达作者对洛神的恋慕和对世外仙界的向往,有时也借追求洛神无果,宣泄现实中进退维谷、精神不得自由之恼。例如陆机《前缓声歌》:“宓妃兴洛浦,王韩起太华。”还有郭璞的《游仙诗》:“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此外,也有不少文人受《洛神赋》启发,将洛神作为典故寄托情感。魏收《美女篇》中“仍令赋神女,俄闻要宓妃”,寄托对洛神的企慕向往,洛神成为文人理想追求的化身。
于此,洛神形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摒弃了美而无德的相关特质,达成了形与神的高度统一,并在游仙诗、宫体诗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洛神形象的第一次大转变。
4 唐以后时期的洛神形象
唐代是洛神形象发展的重要时期。李善在《文选》注中将洛神的形象与甄氏的形象进行叠加,创造了一个符合当时审美观念的形象。他将洛神与现实中的美女形象联系在一起,使得洛神更具有了凡人女性的魅力和生动性,体现了当时社会审美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发展,展现了文人对于女性之美的追求和赞美。
自唐朝以后,曹植与甄妃的传说,基本代替了宓妃的本体神话,生成了一种文人艳遇模式。如晚唐人裴铏在传奇小说《萧旷》中的故事: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夜憩双美亭时,洛神被他的音乐打动而现形,主动提起她与曹植的感情际会。洛神欣赏萧旷琴韵清雅并声称会暗暗地帮助于他。
到了宋代,洛神形象也有了新变。苏轼的《赤壁赋》中,洛神不再只是象征性的女神,而是被描绘成一个聪明而机智的女性。在赋中,洛神通过挺拔的身姿、明亮的眼神和灵动的动作,展现出自己的智慧和机智。她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环境,赋予她生动的形象。这种聪明机智的形象,让人们对洛神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她不仅美丽,而且富有智慧和才情。
明清时期,洛神故事常见于小说、戏曲。明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市民阶层迅速扩大,作品内容出现市民化和趋向世俗化的特征。因程朱理学的影响,文人摆脱不了纲常伦理的约束,在进行创作时常将潜意识里的节欲与贞操观念渗透进作品。明代宓妃的神女身份隐去,世俗文学中她倾国倾城的美貌,以及与曹植之间无法言说的曲折恋情备受文人青睐,戏曲小说之中多以此为典,对原有故事底本加以想象创造。如明代汪道昆的杂剧《洛水悲》和清代黄燮清的《凌波影》都记叙了洛神与曹植再续前缘的故事。
清朝洛神形象转折点集中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甄后传中,化为宓妃的甄后,行为上无法被封建守礼者容忍,但宓妃并没有因为礼数的桎梏而约束自己的个性。相反,她是热情、大胆、独立、聪慧的,她全部的生命都属于自己,不因为世俗的眼光而做任何的改变。“旋见龙舆止干庭中,乃以玉脂合赠刘,作别登车,云推而去。”蒲松龄笔下的洛神不再是受人摆弄的弱女子,也不再是封建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和从属。洛神的个性色彩再次被加强,走向勇于表现自我、尊重自我的道路。
5 小结
中国的神仙并非以一种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形象出现,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守护者,用他们的职能,来为百姓带来各种好处。正如那句:“中国人不养闲神”,每个神仙都有着各自的职责和使命,他们的存在,与人们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密不可分。
洛神,作为司掌美丽和爱情的洛水水神,经过历代的文学作品的描写润饰,从缥缈的神女,变成了“人神之恋”中的主角,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与个性,以及更具体的身世经历与故事情节。其形象中神性与人性的此消彼长,也能体现世俗化的倾向,并结合时代的文体倾向、思想倾向,更加鲜活地出现在大众面前。■
引用
[1] 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521.
本文系2022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洛水惊鸿——‘洛神’形象溯源及其文化价值演变探究”(202211117125Y)
作者简介:赵李宝(2002—),女,江苏宿迁人,本科,就读于扬州大学;魏黎婷(2002—),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就读于扬州大学;王晓燕(2002—),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就读于扬州大学;顾玥(2003—),女,江苏扬州人,本科,就读于扬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