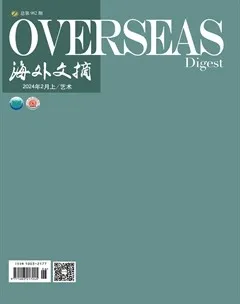浅谈西方现代视觉艺术作品中对不同具象符号的利用及其隐喻



长久以来,西方传统的学院派绘画以“完美地再现”为目标,创作出了一系列画技精湛的写实主义作品。到了20世纪,一批新艺术家动摇了这种古典主义绘画的统治地位,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新生画派成为潮流。这些艺术家通常以艺术揭示艺术,利用抽象、非理性的色块与线条拼贴,突出艺术的媒介特征,而不是盲目地追求逼真性或正确性。在这批艺术家中,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却极为具象,但依旧能够体现现代艺术作品的特征。本文将以杜尚的现成品艺术、马格利特具象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与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为例,主要结合皮尔斯符号学的第二个三分法(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阐释这些作品中对具象符号的利用以及其中可能的隐喻。
1 杜尚及其现成品艺术
1917年,杜尚从一家下水管道配件商那里买来一件男性陶瓷小便池,签上了年份以及R.Mutt(德语词汇“贫穷”的谐音)的字样,并将其命名为《泉》(Fountain),参见图1。他匿名向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寄送了这件惊世骇俗的艺术品,几经波折之后一经展出便引起了艺术界的震动,现成品艺术成为了热议的对象。如果说杜尚往小便池上签名这一举动已经使工业品受到了创作者的干预,“现成”的特点不那么纯粹,那么杜尚1915年的作品《断臂之前》(In Advance of the Broken Arm)就是一件纯粹的现成品——一把雪铲。
许多人无法理解现成的工业品是如何登上大雅之堂的,认为它们过于具象,并不表达任何意义,因此也不能将其称为符号。皮尔斯认为,没有什么是天生的符号,只有当人们将其理解为符号时,一件事物才得以成为符号[1]。在日常生活的符号系统中出现时,小便池是一个区别于陶瓷浴缸、陶瓷洗手池的卫浴用品,它的实用性远大于艺术性,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任何艺术阐释的必要。然而,当其作为现成品艺术被摆放在美术馆中,RNy1XFgip/TM43W7hSV+PAqvr5Nu2LwqEyntK19eOO4=就处在了艺术史的语境中,迫使人们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阐释。从皮尔斯符号学三分法的角度来看,现成品艺术似乎会被归入像似符的类别,但它又不是“像似”,因为它就是物品本身,冲破了相片或是画布的阻隔被摆在玻璃柜里展出。某种程度上来说,现成品艺术是一种指索符,观者看见小便池之后进行的思考并非是针对小便池本身的,而是会联想到超脱于展示物品之外但与其有时空接触的、将小便池放进美术馆的这一行为。并且,杜尚用“泉”这一在欧洲文化中象征源源不断的智慧的符号为其命名,这一行为已经将小便池变成了一个动力对象[2],势必会引出观者不同的思考。杜尚将纯粹实用的小便池等物品当作颜料,而他激活这块颜料意义的方式就是将其置于美术馆中,整个美术馆成为了画布,“现成工业品存在于美术馆里”的错位感与不适感导致观者在看见小便池的一瞬间就会萌发出“这是艺术吗”的想法,而这就达到了杜尚的目的。作为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尚对西方艺术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质疑与否定,并且想要通过创造“反艺术”对其进行破坏。诚然,他用现成品艺术破坏了旧艺术惯用的符号体系与文化价值,但他反艺术的举动却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观念艺术(尽管观念艺术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被提出,但《泉》普遍被认为是其早期实践)。观念艺术更多地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在对象里寻找一种普遍性的表达,因此,观念艺术弱化了外在的艺术形象,转而探求艺术内在的观念[3]。杜尚以最极端的方式让艺术品的创作元素隐去,不图解任何具体意义,把对作品的阐释主导权完全转交给观者,使其对意义的产生进行再探索,思考我们是如何建构意义的,并最终让观者进行意义再生产。在像《泉》一样的现成品艺术中,艺术符号与对象的表意距离非常远,甚至可以说是跳过对象表意,这种距离感成为了现成品艺术张力的来源,也需要观者调动更多的元语言进行阐释。这与皮尔斯对开放文本与符号接收者一端的重视不谋而合。在之后的美术史上,“小便池”自身也被塑造成了一个新符号。可以说,现成品艺术的符号性是从社会对其意义进行不断解读、不断再次演绎的过程中生成的,它的解释项与意义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衍生。
2 马格利特与其具象的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由达达主义演变而来。艺术家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将梦境与现实事物结合,创造出反逻辑、非理性的奇幻画面。马格利特作为超现实主义的代表画家之一,其独特的隐喻性图像使画面充满荒诞有趣又神秘深刻的视觉效果,对具象的图像符号的使用也成为他作品的一大亮点,他的作品曾被法国作家布勒东称为“最清晰的超现实主义”[4]。
在马格利特的绘画作品中,青苹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典符号。在《人类之子》(Le fils de l’homme)、《犹豫的华尔兹》(La Valse Hésitation)、《已婚的牧师》(La Prêtre Marié)、《听音室》(La Chambre d'écoute)等画中都出现了青苹果的图像。在著名的《人类之子》一画中,一颗悬浮在半空的青苹果遮挡住了穿西装戴圆顶礼帽男人的面孔,然而恰到好处地露出了男人的一半左眼,窥视着观者。作为一种像似符,青苹果在这幅画中被描绘得极为逼真,但是这种毫无逻辑的具象令观者有些无所适从,“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也许是所有人第一次看见这幅画作时的第一想法。有人问马格利特为什么要将苹果挡住人脸,他解释说:“我们眼前看到的事物,底下通常还隐藏着别的事物,人们对眼前清楚易见的事物兴趣不大,反而会想知道被掩盖住的是什么东西。[5]”当观者被夺走了仔细端详人脸的机会,他们才会下意识地开始在画中的其他地方游移,寻找这个男人身上的特点,试图找出其身份,从而消解一些人脸被遮挡带来的陌生感与距离感。
然而,对于为什么使用青苹果这个问题,马格利特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人类之子》像一个无解的谜题。如果结合超现实主义画家大都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历史背景,或许苹果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潜意识里超我对本我的管制,超我定下的道德准则阻止了本我去真正地犯下窥视之罪,然而即使窥视欲会带来罪感,人们的本我依旧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越过超我的规训——越过苹果去窥探掩盖之下的未知。此时,苹果既是一种道德准则的具象化体现,也是吸引着人们去打破这层准则的伊甸园的禁果的象征。
在马格利特的其他作品中,苹果有着不同的解读。《犹豫的华尔兹》中,两颗青苹果戴着一红一蓝的面具(见图2左),似乎想要请对方成为舞伴,两颗苹果的倾斜角度体现了一种对亲密情感的试探,头顶的枝叶也体现出它们的青涩。同时,处于阴影之下的设计也增加了氛围的朦胧和内心的躁动不安。而《已婚的牧师》中的苹果就显得更加成熟(见图2右),相同的白色面具暗示着婚姻,也与标题呼应,更加茂盛的枝叶却显出了虫蛀的痕迹,明亮平静的表象下似乎暗藏哀伤。在这两幅十分相似但感受完全不同的画作中,苹果作为画面的主人公,成双成对且都被拟人化地戴上了面具。马格利特用戴上面具的苹果喻人,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苹果在此处不仅是一个像似符,在西方文化的视角下,苹果这一符号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规约符。在圣经故事中,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而犯下原罪,自此苹果就有了欲望的隐喻。就像夏皮罗认为塞尚的苹果静物画体现了“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无意识象征”[6]。在这两幅画的对比下,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对亲密关系渴望向往而又暗中带有焦虑不安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在《爱侣》(Les Amants)一画之中得到进一步实证:一对情人正在亲吻,然而两人的面部都被白布蒙住,无法看到对方,无法真正触碰到对方,也无法用眼睛认识对方,就像带着面具的苹果一样,这种亲密与疏离之间的奇异的割裂感带来的张力使观者感到陌生与诡异,也对“情人”之间的情感产生了怀疑。有趣的是,读客文化在推出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的《鄙视》的中文版时,其封面使用的就是《爱侣》一画,作为一本讲述婚姻危机与现代人的爱无能的作品,选用此画作为封面无疑体现了大部分观者对亲密关系之中的焦虑这一解释项的认同。
马格利特善于将人的潜意识与内心的情感以具象的图像符号描绘出来,除了苹果之外,还有不断出现在其画作中的戴圆顶礼帽穿黑大衣的男人、铃铛、飞鸟、白云等。他以一切出其不意的手法,以真实来营造非真实的世界,经常会分离人们常有的视觉经验来重组事物间的传统关系,向观众的传统视觉和常规提出挑战。在更深层次上引起观众对于艺术真实与艺术客观的思索。可以说,他的绘画就是视觉化的思想。有些符号的意义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在观赏每一幅马格利特的画时所感受到的谜题带来的诗意与对不同符号进行个人思考与解读的过程[7],就是具象的超现实主义的意义所在。
3 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
1962年,洛杉矶举办的一场小型展览展出了安迪沃霍尔手绘的32张《坎贝尔汤罐头》(Campbell’s Soup Cans),这些绘画看起来几乎一样,除了每一个罐头上的名字略有不同(见图3)。而这被排成四行八列的汤罐头画成为了波普艺术的宣言。安迪沃霍尔仿佛将美国超市货架上常见的一角放进了美术馆,以直白的方式对大众消费品进行了复制。初见这一系列作品,人们的想法或许与看见杜尚的《泉》时一样:这是否能被称为艺术?放在室外,这些画更像是一则坎贝尔汤罐头的广告,但进入美术馆之后,人们就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这些重复的作品。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大同小异的汤罐头画表面上是形象像似,但其深层意义是用这些不断重复的汤罐头图像符号结构类比消费社会的机械重复与大规模生产,也就是一种图表像似。当无数个大小、方向、形状甚至色彩都相同的形象很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的时候,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它的视觉冲击,他们会发现这幅画中的单一形象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整体性。除了外表复制这一行为之外,安迪沃霍尔在绘制后几张汤罐头上的鸢尾花花纹时并未使用画笔,而是使用了刻有其纹样的图章来达到更快速高效地作画的目的,这也让人联想到现代社会中机械化的再生产。同时,在崇尚快节奏的时代,很少有人会在一幅画前停留去仔细思考其中含义,人们就像在逛超市一样各取所需、浅尝辄止。结合安迪沃霍尔同时期对可口可乐瓶图像的复制,在画中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思想、感情,只有等待被消费的商品。汤罐头和可乐这些超市货架上的日常消费品的共同特征是廉价、生产批量、标准化、人人都可享用[8]。他有意将美术馆变成摆放日用消费品的超市货架,也暗中指涉了美国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现状,人们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为了一种超脱商品本身的符号象征,欲望不断被制造,人们也在不断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陷入消费主义的循环。安迪沃霍尔通过坎贝尔汤罐头这一系列作品将这些符号再次凝结成画布上具象的图像符号,从而向观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真实和重要的?
安迪沃霍尔善于直接挪用大众热点符号,其后来的波普艺术作品发展到了对名人与明星形象的直接应用。例如著名的《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系列版画,他使用丝网版印技术大批量地复制了玛丽莲梦露的头像,并进行了不同颜色的变换。玛丽莲梦露在美国社会早已成为性感、时尚与魅力的符号象征,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人物。结合社会背景,人们可以从这种重复中解读出从文化产业到社会对明星病态的追捧,五颜六色的艳丽与光鲜背后是千篇一律的单调与麻木。但换一个角度理解,安迪沃霍尔也许只是利用了大众对玛丽莲梦露这一形象的迷恋来增加作品的曝光度,这些作品就可以解读为安迪沃霍尔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欣然接纳与宣传,不断印制出的新的梦露头像从照片被简化成直观的文化符号,明艳亮丽的色彩时尚而个性,无疑为其增添了观赏性与装饰性,加快了其传播速度,安迪沃霍尔则成为了助推流行文化发展的一部分。从波普艺术对艺术商业化、平民化欣然接受的态度来看,对《玛丽莲梦露》系列版画这样的解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4 结语
对于大多数视觉艺术作品来说,图像符号必不可少。对于具象的图像符号的使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变迁,在现代艺术中,像杜尚、马格利特与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大胆实践,在作品内融入了更多的符号学思考,以具象的符号体现人类抽象的思维与情感。对创作者而言,再现行为是对符号的个性化诠释,体现了作者本人对符号的感知,而当现代艺术作品被放进美术馆被大众审视时,观者即接收者一方也承担了探究新解释项的义务,只有作者与观者达到了有效的沟通,最终达成理解、共识与认同,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才能显现。■
引用
[1] 张彩霞.皮尔斯符号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
[2] 李娜,张乘风.“符号三分式”视域下关于杜尚艺术的研究[J].美术大观,2018(8):52-53.
[3] 张心雨.观念艺术发生与演进探寻[D].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21.
[4] 齐晓.论图像符号的不同呈现方式[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3.
[5] 史家静.探析马格利特绘画中的图像符号与隐喻[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20(2):153-155.
[6] 沈语冰著.艺术史名家文丛 图像与意义 英美现代艺术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
[7] 王延晖.皮尔斯符号学视域下视觉艺术的再现与传播[J].中外文化与文论,2021(1):426-435.
[8] 李馨蕾.具象与抽象[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8.
作者简介:方王彦儿(2001—),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就读于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