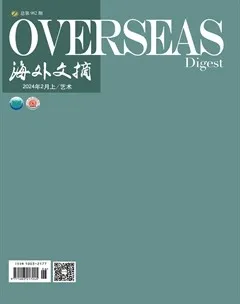与岁月和解
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危机越来越受到关注,“灰色海啸”“银发世代”等词不断涌现,反映了人们对衰老问题的关切。老龄化问题正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衰老主题亦成为重要的文学主题,是巨大的文学财富。
作为老年群体中的特殊弱势人群,老年女性的生存境遇不容忽视。以加拿大“文学之母”玛格丽特·劳伦斯(以下简称劳伦斯)为例,其代表作《石头天使》的主人公哈格·希伯利(以下简称哈格)正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年女性。劳伦斯通过多种叙事手法撰写哈格一生与父权制斗争以寻求自我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一位成年作家对老年生活的想象,提早洞察了西方社会的老龄化问题,蕴含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遗憾的是,现阶段对其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空间叙事、原型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等方面,但对主人公的老年特征仍涉足较少。故本文将聚焦哈格的老年生存困境,分析其弥留之际通过抗争与反思以寻求破局之路的自我建构过程,在彰显劳伦斯对现实社会的忧思及其深刻的人文情怀的同时,以期厘清老年群体共同的情感诉求,重塑老年生命的意义。
1 陌生化语言下的自我仇视
主人公哈格用陌生化的词句描述其老年生活境况,难掩对自身的厌恶之情。哈格的衰老最直观地体现在身体上。她非但不能为家庭分担家务,反而平添麻烦,已然进入“第四年龄”(the Fourth Age)阶段,即“因衰老而卧病在床需要依赖他人照料的老人”。
身体的背叛给哈格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挫败感与自仇情绪。然而,比起内心的无助,亲人的疑虑更令哈格备感煎熬,对于大儿子玛文和儿媳多丽丝友善的关怀,哈格反认为是嘲讽,愤怒地拒绝他们的帮助。她本能地不愿让他人看到自己丑态百出,更排斥多丽丝为她更衣时触碰她的私处,使自己尊严尽失。
面对衰老的无助,哈格在言语上将自我物化为动物或是廉价物品,如“多油的肉”“便秘的母牛”[1],无不充斥着自贬情绪。对于镜子映照的自我形象,哈格表达出更深的恐惧。她一连运用多个比喻,既表露了对自身的陌生感受,更兼具了对青春的追忆。借此,劳伦斯批判了西方社会年轻崇拜的扭曲观念,在这种单维度审美的风潮下,老年身躯被看作是对“美”的背叛。如波伏娃所言,女性衰老的过程正是经历自我他者化的阶段,作为男性眼中的欲望化身,身体的衰老引发了女性自我羞耻的负面情绪,由此消解了主体身份,失去了在社会的定位。
此外,哈格备受疾病的困扰,不得不依赖药物维持生命。就诊过程中,为回避年龄忌讳,医护人员客套地称她为“年轻的女士”或“乖女孩”,可见年轻崇拜观念在西方社会的根深蒂固,同时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便是年龄歧视,它不仅影响老年人的自我认知,还加剧社会对该弱势群体的歧视态度,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人们用夸张的方式故意缩小老人的年龄,意图讨好他们。对此,哈格展现出了极度的厌恶与不满。
年龄歧视的另一表现则为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冷漠与轻视。哈格因不熟悉诊疗流程而闹出许多笑话,医护人员象征性地安慰两句后便没了耐心。哈格原以为诙谐的口吻会促成医患间平等和谐的沟通,反倒尊严尽失,不得不将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困苦埋藏于心[2]。“老年人不是人”的扭曲观念加深了哈格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以致于似乎只有通过不断贬低自己才能宣泄内心的苦痛,这无疑形成了恶性循环。劳伦斯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老年女性的生存困境,涉及诸多身体衰老的细节,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女性写作的禁忌,尽显作家本人的胆识与人文关怀。
2 回忆叙事中的自我反思
年逾九旬的哈格相当要强,这一骄傲独立的品质虽非完全是天性使然,却足以解释其为何为实现自我价值而斗争一生。尽管她对诸如“上了年纪的人总是生活在往日的时光里”的言论嗤之以鼻,但身体机能的下降、自我厌恶的心理仍使哈格蛰居在楼上狭小的房间内,与照片为伴,沉溺于往昔,不断自我反思。在这里,劳伦斯采用了回忆与现实交织的写作手段,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颇具巧思。
哈格以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进行叙述,在其特有的双重聚焦下,两种叙述眼光交替作用,即小说既有老年哈格追忆往事的眼光,也不乏被追忆的年轻哈格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显然,前者更能体现哈格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其认知程度由稚嫩走向成熟。老年哈格作为事件的旁观者,鲜少在回忆中凸显主观情感,从而体现出回忆给人以自省的效果。
可以说,劳伦斯用回忆写就了哈格的成长历程。她的母亲因难产早逝,哈格从小便在父亲的规训中成长,缺少关爱,青春期表现叛逆,但她有幸接受教育,这影响了她的一生。毕业后的哈格回到家时,已经学会了许多具有“装扮性质”的知识,却非生活的真知灼见。对此,老年哈格承认了自己的年少无知,并清晰地意识到这些几乎不是她要过的生活,而年轻哈格持续与父亲对抗,变得更加独立,内心的女性意识也渐渐觉醒。
几年后,哈格在舞会上认识了布拉姆并与之交往。她无视父亲的负面评价,强硬表达了自己结婚的意图。这是哈格对父权制的规训的一次有力回击,挑战父权给她带来的喜悦甚至冲昏了她的头脑,使得父女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父亲至死都没原谅她。与父亲的压迫不同,丈夫布拉姆尊重哈格,给她以爱,但在老年哈格的回忆中,她与布拉姆的婚姻并不愉快。哈格曾以为婚后布拉姆会改变一些原有的“坏习惯”,可他非但没有改掉劣习反而变本加厉,加速了这段婚姻的终结。在回忆中,老年的哈格以一种更加理性客观的视角反思了这场婚姻,她的自作主张固然显示出女性的勇气与自立,却似乎仍在重蹈父亲的覆辙。
盲目的母爱使她忽视大儿子玛文,偏爱小儿子约翰,但约翰却屡屡辜负哈格的期待,在一次酗酒后不幸死于交通事故,自此哈格变得高傲冷漠。她在弥留之际接受祷告时,再度回忆起这段沉痛的过往,随着小说中内心独白的层层递进,哈格深藏于心的压抑情感终于得到释放。老年哈格终于在回忆中意识到自我的迷失,这也恰恰呼应了小说标题,哈格终于完成由“石头”向“天使”的蜕变。她幼年暗自发誓不能成为像母亲一样柔弱的人,于是竭力挣脱父权制的枷锁,但父亲的价值观却如影随形。哈格崇尚男性的坚强,对他人的关心呵护毫不领情,使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总是处于一种疏离、冷漠和异化的状态,而自己也不经意成为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在这一过程中成为那尊盲目的石头天使。
借助回忆,哈格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从前的故步自封造成了女性本能的缺失。叙事声音与叙事视角的错位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文本颇具张力。
3 逃离“家园”以求自我重塑
晚年的哈格选择与玛文夫妇住在城里,他们尽心赡养老人,却常因生活观念不合而发生争执。夫妇二人不得不决定将哈格送到养老院。哈格对此本能地排斥,她将养老院比作“兵营”甚至是“牢房”等一系列被社会公然抛弃的场所。面对玛文不加商量的告知,哈格感受到自己渐渐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显然与她想要有尊严地活着的初衷相违背,更与她一生顽强抗争的性格形成鲜明反差。
从回忆中看,哈格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家园付诸努力。作为保护心灵最稳固的、最安全的防线,家承载着哈格全部的人生记忆,熟悉的物品为她提供了心灵寄托。然而她的生存空间随着年龄增长而被不断压缩,到最后不得不受限于自己的房间内,从相片上寻求慰藉。玛文夫妇的举动显然触及到哈格的底线,她非但不能在家中得以善终,反而要“像运一包衣物一样”被送往养老院,而在那里的唯一解脱便是“走进棺材”,进入一个更加狭小的空间,象征着生命逐渐走向终结的悲凉。
老年人由于难以再为生产体系做贡献,故而饱受他者化的歧视,逐步沦为社会空间的边缘群体。文学老年学专家玛格丽特·古列特指出,“不管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类首先是被文化催老的。[3]”青春膜拜的文化进一步压榨老年人的生存空间,对于老年女性而言则意味着更大的危机。面对玛文夫妇提出的将她送往养老院的建议,哈格态度强硬,试图再度掌控自己的命运。对此,她决定挣脱家园的物理束缚感,通过空间的位移以重塑自我的生存空间。
一路上,哈格虽饱受身体的苦痛,却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善意,缓解了她的紧张。开阔的自然美景不同于狭小的家园空间,为哈格带来心灵上的疗愈,使她敞开心扉与人交谈。当听到陌生人同样与自己有着丧子之痛的经历时,哈格不由陷入回忆之中,在半梦半醒之间误将其当作死去的约翰,并深深忏悔。幸运的是,陌生人的善解人意给哈格以抚慰,让她对曾经所排斥的“软弱”“爱”有了全新的理解。哈格的心理空间不断向外拓宽、延展。
在病房这一狭小密闭的空间中,哈格却意识到自己一生的悲剧起因正是继承了父亲如“石头”一般坚硬冰冷的处世态度,使她与温暖和爱相隔绝开来。由此,哈格突破了心理空间的闭锁,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临终时动情地夸赞玛文:“你从没有对不起我,玛文。你对我一直很好。你是个好儿子,比约翰强。”哈格在空间的挪移中渐悟自己从前认知的狭隘,从一具石头雕塑转变为有血有肉的人,走出了狭隘的“小我”生命,重塑自我,最终与自己的一生达成了和解。
4 结语
作家劳伦斯在访谈中曾言:“在某种程度上,《石头天使》说的是生存问题。我想到的不是肉体的生存,而是精神的生存,能够给予爱、接受爱。[4]”劳伦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哈格的一生,着力描写其衰老困境,揭示了老人在人生暮年因病痛而失去自理能力所产生的羞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戒备、倔强等复杂心态,力求寻得一条破局之路,以诠释“老年的意义”,这也正是人文主义老年学探究的基本问题,即如何“跨越衰老的躯体进入自己的思考”[5]。具体来说,《石头天使》运用了双重时空结构的写作手法,哈格在相互交织的回忆与现实中得以用全新的目光审视过去,以更加自洽而内求的态度与衰老和解,最终实现了坦然地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
引用
[1] [加]玛格丽特·劳伦斯.石头天使[M].秦明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 张冠尧,主编.加拿大掠影[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112-121.
[3] Gullette, Margaret. Declining to Decline: Cultural Comba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Midlife[M]. Charlottesville,VA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7.
[4] Laurence, Margaret. The Long Journey Home[M].Montreal: McGiu-Queen's UP,1981.
[5] Cole, Thomas R. and Ruth E. Ray. “Introduction.” Handbook of the Humanities and Aging[M].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1992.
作者简介:崔宪慧(2000—),女,山东沂源人,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