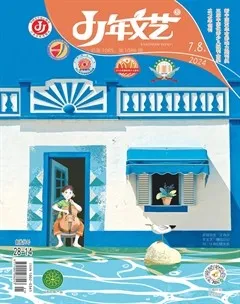桑树是吾乡


我喜欢写乡村生活的故事,一来是回忆儿时,二来是想写消失的事物。通过这篇文章,我想告诉小读者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相遇。
——惜午
1
东面张奶奶家来了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大。
我站在家门口,越过一丛低矮的湖桑林,瞅见了她头上好似牵牛花的发夹。她朝着我的方向望了又望,像在寻找什么。
我猛地蹲下了身。其实,我不能确定她是否发现了我在偷瞄她,毕竟我们两家中间不仅隔了湖桑林,还有一条一到雨天就涨满水的沟渠。
我咽了咽口水,心想,在这方大地,连路过的蚂蚁都没我会认路,我一藏起来,她肯定看不见。我低头看看自己灰扑扑的手背、小褂、凉鞋,慢慢起身,等视线刚越过桑树顶——嘿!我又看到了那发夹和面朝西的圆脸蛋。我赶紧猫着身子,溜到了后院的厨房里。
“粒儿回来了!东面张奶奶的外孙女来了,你找她玩玩?”妈妈走进后院,搁下一篓桑叶,对我说。
“不去。”我的脑海中又浮现那对发夹,说,“妈妈,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几对发夹?”
“买那做什么?没几天你就弄丢了。”妈妈拖着背篓进了蚕室。满屋子白胖胖的蚕,昂着脑袋,等待着桑叶。
中午快吃饭的时候,有一位打扮精致的阿姨端来了一搪瓷碗的桃形馒头,红红绿绿的。她正被妈妈往饭桌旁拉,空出的另一只手直摆手。
“哟!你家女儿也这么大啦?”她看到了我。
“快叫人,这是粒儿妈妈。”妈妈停了下来。
“粒儿妈妈好。”
“去我家找粒儿玩呀,她一直在家里。”一说完,她就趁妈妈不注意,把搪瓷碗往桌角一放,跑走了。
我不明白,我又不认识粒儿,为什么她们都让我找粒儿玩?为什么不是她来找我呢?
我不想去。
可是妈妈偏说我吃了张奶奶的寿桃,让我去问声好,顺便还碗。
下午,我不情不愿地从家门口往东走,路过湖桑林,就在快到低洼的小土桥时,我听到湖桑林里传来了奇怪的声响,一会儿像有什么东西快速穿梭在桑叶中,一会儿又静悄悄的。我停住了脚,好奇地侧耳细听,却什么也听不出来。
我弯腰低头,把头低到小腿那么低,从一排又一排湖桑间的土埂看过去。透光的湖桑桩间,黄色的裙子、乌黑的麻花辫,两只搭在桑葚上的手,正往外拽。
那是粒儿!
我喊道:“住嘴!不能吃。”
湖桑林里顿时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越来越远。
粒儿跑了。
等我走到张奶奶家时,她规规矩矩地坐着,黄色的裙子,高高的麻花辫,头发上别着漂亮的发夹,不似牵牛花那般明艳,而是温柔的蚕豆花色。她老老实实地坐着,仿佛刚刚被抓包的不是她。
我说:“你的发夹真好看。”
她听了,从头发上摘下来,说:“送给你。我还有很多。”
她的手指头是紫色的。
我接过来,说:“我知道哪里有更好吃的桑葚。”
听到我的话,她的眼睛忽地亮了。我才意识到,原来她一直朝西面看,琢磨的不是灰扑扑的我,也不是绿油油的桑叶,而是桑树下挂着的沉甸甸的桑葚。
2
我没有骗这个外乡人,喂蚕的桑树结的桑葚真不能吃。
从我记事起,这一片大多数的人家都养了蚕。给蚕吃的桑叶采自湖桑,湖桑枝粗叶大,长不高,一排排栽在田地里,每年都会修剪,来年发的桑叶又大又绿,结的桑葚又鼓又胖。从小我就知道,喂蚕的桑树结的桑葚不能吃,因为早就有吐着红信子的贪吃蛇抢先尝过,它们很自私,吃完还会吐有毒的口水,让别人不能吃。它们也很懒,在地上吃饱后,就懒得盘上野桑树吃桑葚了。
我也没有骗粒儿,野桑树结的桑葚真的很好吃。
粒儿站在我家旁边的沟畔,一棵不太粗的野桑树立在身边。她望了望细小的桑葚,再看看我,眼里满是不相信。
我卷起裤腿,一脚踩在旁边的草垛上,另一只脚钩住树干,慢慢往上攀爬。我将手压在枝条上,喊:“粒儿,快摘!”
粒儿踮起脚尖,把够得到的桑葚都摘了。一会儿工夫,小半棵桑树的桑葚就被薅光了。
粒儿一颗接着一颗吃。
我问:“好吃吗?”
“还不错。”
“比起地里的桑葚果呢?”
“地里的大又甜。沟畔的桑葚果味更浓,甜中带酸,我更喜欢。”粒儿露出白紫色混合的牙齿,在风中银铃般地笑。
我咧开嘴笑了。我虽然没尝过地里的,可每年都会摘野桑葚。我就说好吃的吧,没欺骗这个外乡人。
“桑葚真好看,像外婆的耳坠。”粒儿一边翻看桑葚,一边往嘴里塞。
“是啊,像紫色的蝴蝶。”我说的是发夹。我仔细地把发夹别在头发上,吹着桑葚味的风,耳边满是桑叶的沙沙声。
一来二去,我和粒儿就熟了。
她只有周末才回来,平日里还得在城里上学。一到周末,我总找她玩,谁让她家的电视机搜到的电视频道比我家多呢!
可是,总看电视也没什么好玩的。
我从蚕室精心挑了一只肥胖的蚕宝宝,放在手上,手心麻麻的,痒痒的。我快步走,路过湖桑林时,扯了两片大桑叶,托着蚕宝宝,在小土桥上蹦蹦跳跳。忽然,“咻”的一声,一条长长的、亮亮的,比蚕宝宝大上百倍的玩意儿,从我跨的步子中间游过去了,消失在青青绿草中。
我愣了一下,然后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了粒儿家。
我跟粒儿举了举手上的蚕宝宝,说:“看,我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粒儿尖叫一声,她的脸比蚕宝宝还要白,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不知道她不喜欢蚕。我心里想着,要是她偷吃湖桑林的桑葚时,遇到更大的“长虫”,还不得吓哭。
我把蚕放到她家厨房的盆里,然后跑到房间里,和她一起看电视。等鸡蛋黄般的阳光斜斜地洒在窗沿东边,我左思右想,还是叮嘱道:“粒儿,你以后要是想吃桑葚,就去我家沟畔。”
然后,我带上趴在叶梗上的蚕回家了。
3
老实讲,我觉得粒儿有点娇气。一连几个周末,我都没去找她玩。我期待的暑假就在梅雨中来临了。
粒儿每天都在。别问我怎么知道,春蚕的蚕事结束后,湖桑林就被砍到桩了,新发的芽还没长高,长壮,长密,我不用偷瞄,就能见着她那惹眼的发夹,天天不重样。
她天天都在家看电视肯定很无聊,所以没几天就来找我了。
我有很多乐子,像搭砖头积木、吹芦竹笛、河边摸鱼等等,就是保不齐会遇到长毛虫啊,大蜘蛛啊。她一来,我搔头抓耳也想不出好玩的,只能打开电视机。
翻来翻去都是咿咿呀呀的戏曲,我快睡着了。
“听外婆说村里不定时会有马戏团来,我还没看过呢。”粒儿刚说完,我就清醒了。
我最爱看马戏了!
我撑开雨伞,带着粒儿来到爷爷家。爷爷早年在村里当会计,人脉可广了。我仔细一问,马戏团正在巡演呢,趁着不下雨的空当,隔几天换一个村,现在应该到了邻镇的千汇村附近。
我央求爷爷,有准信了一定要带我们去。
一周后,爷爷骑着三轮车停在门口。我喊来粒儿,她穿了齐脚的黄裙,头发被扎成左右两个球,夹着一对油菜花色的发夹,端正地坐在车斗边。我躺在里面望着蓝天,三轮车颠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把我的蓝天颠得摇摇晃晃,把粒儿的黄裙和日光颠得分不清了,我的眼皮不知道啥时候闭上了。
粒儿将我摇醒时,我已经睡了一个美美的觉。
“那就是马戏团吗?”粒儿激动地喊。
我坐起身,抬头看去,是一个超大的彩色帐篷,顶上五颜六色的丝带在风中招手。我点头:“是啊,是啊,就是马戏团扎的帐篷。”
爷爷掏出两个一元硬币放在我和粒儿手里,让我们去买些吃的。
我挤在放着绕绕糖的自行车前,舔了舔嘴角,又从人群中钻出去了。我和粒儿逛了一圈,最终粒儿停在卖青皮甘蔗的叔叔前,甘蔗有我和粒儿加起来那么高,一块钱一根。她挑了一根很粗的。我握紧了手心的硬币,说:“粒儿,我可以和你一起吃吗?”
“当然可以。”
于是,我们拎着削好的甘蔗,欢喜地掀开了帘门。里面有一个大圆台,周围摆了不少长凳。我们和爷爷坐在一张靠前的长凳上。
一会儿人就满了,还站了不少人呢。连凳子都被往前紧了紧,直到再也塞不下人,马戏团就开演了。
台子上火光飞舞,一个光头大汉喝进汽油,喷出老长的火焰。粒儿的嘴巴圆得可以横着塞进甘蔗了。我鼓掌喊道:“好!”粒儿也跟着我鼓掌。周围站着的人也拍手叫好。
又一个健壮大汉上来了,他扎上马步,拉长手臂的皮,用粗长的针刺破后,居然不紧不慢地挂上线,再放上一块红砖头!他腮帮子鼓鼓的,好似在运气,砖头就跟棉花一样轻飘飘的。
粒儿比我还抢先鼓掌,甚至她已经站起身叫好了。周围都是噼里啪啦的鼓掌声。我咬住甘蔗,举起双手鼓掌。
节目一个接一个,直到一个穿着艳丽、束着高马尾的阿姨出来,她拿着铜锣和小槌,敲出“咚咚锵”。
我连忙拉起粒儿,围到大台子旁。大家都围过去了,争着给赏钱。
“哐当——哐当——”
粒儿看看我,再看看空空的双手,她把目光停在了臂弯挂着的甘蔗袋子上。她正要拿,我按住她的手,说:“这个不能换钱的。”
于是,粒儿拿下了头上的发夹。刚好铜锣伸到了我们面前,爷爷已经率先投进去了一块钱。
“哐当——”
她的发夹刚要落在铜锣时,我一把抓回了她的手,另一只手扔进了一块钱。
“哐当——”
我说:“有五毛是我的,还有五毛是她的。”
阿姨对我们都说了谢谢。
粒儿的眼睛亮亮的,脸上浮起了水蜜桃般的粉色。她扭过头,小声对我说:“还好你留了一块钱。”然后捏起发夹,一个夹在自己的左侧发球边,另一个夹在我的脑袋上。
我嘴角咧得比束发阿姨的脸还要大,挠头说:“按照江湖规矩,也可以不给的。就是看个热闹,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挠头时,我碰到了发夹,哇!那可比桑蚕丝都柔软。
粒儿惊呼道:“哇,还能这样!”
我嘿嘿一笑,挽起她的胳膊,开心地继续看。
那天,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粒儿还约我,下次我们一起去大剧院看表演。
我没去过大剧院。我感觉我俩又能玩到一块儿了。
4
暑假过得很快。秋季开学后,粒儿回城里上学了。
九月下旬,中秋佳节,刚好是秋蚕要上山的时候。蚕上山,就是指蚕要吐丝造一个小窝,把自己包进去。
每到这时,家家户户跟蜜蜂一样,哪家蚕要上山,“蜂巢”就在哪家。大家跟归巢似的,“嗡嗡嗡”地一拥而上。
蚕室里已经站了十来个人,连粒儿妈妈都来了。妈妈说不用她动手,她说是粒儿外婆让来的,说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齐心协力。她还说春蚕上山的时候刚回乡下,跟大家没那么熟,不好意思来,因此被张奶奶抱怨了好久。
她套了农忙时的大外罩,把瓷盆端在手上,捡起一直抬头寻觅的蚕。我也蹲下,兜起一围裙的蚕,然后倒在一个个方格组成的纸模具中,妈妈说那叫方格簇,我管它叫方格子。
粒儿束手无措地站在门外。她一会儿走近,一会儿又跑远。她就像想安家的蚕,不受控制地乱走。
“你回去照顾外婆。”粒儿妈妈说。
“你家丫头真漂亮。”孙奇妈妈喊道。
“外婆叫我也来帮忙。”粒儿扯着裙角说。她头上夹着柿子红的发夹,跟一身粉裙子十分相配,怎么看都不像来干活的样子。
“张奶奶往年都会来帮忙。都这个时候了,她还操心这么多。”妈妈拉住走来奔去的我,说,“你别玩了,带粒儿去房里看电视。”
得!没多出份力,还少了份力。
我领着粒儿到了房里,开了电视,甩下一句:“你自己翻翻看啊!”我就跑回了后院。蚕上山多有意思呀!它们昂着头,在等我帮它们找到家,在方格子里做出窝,结出一个个又大又白的茧子。
妈妈看到我就催:“去和粒儿玩呀!”
我嘴上应付着:“马上,马上。”
直到粒儿又站到了后院中。妈妈似乎有点生气,拎住我后脖颈的衣领:“不要捣乱了,都去看电视。”
我朝着粒儿瞪了一眼,气鼓鼓地回:“谁爱去谁去。”
“我……我也想来帮忙,蚕……”粒儿扯着裙边,忸忸怩怩的,“蚕也挺可爱的,我可以帮你们端盆子。”
说完她就梗着脖子,冲进蚕室的走廊里,像一阵粉色的旋风。吴丽妈妈喊:“小心点儿,踩到蚕啦!”
粒儿一脸抱歉地望着脚,踮起脚尖端起她妈妈刚捡的盆子,放到吴丽妈妈旁边,吴丽妈妈会把透着光的蚕安排到每个小家里。粒儿再拿回另一只空盆送到她妈妈身旁。
粒儿一身粉红,却跟白蚕儿一样可爱,憨憨的。我跑过去,拿了个盆捡,捡到一小半,就和粒儿一起端走。
用不上半天,蚕都顺利上山了。
妈妈来不及宴请大家,就一起吃了个便饭,人们又浩浩荡荡地去了另一家。
我和粒儿都被留下了。
粒儿回家前,跟我说:“蚕上山挺好玩的,没那么可怕。”
我说:“他们应该到了西边吴丽妈妈家,她家院子里有一棵超壮的柿子树,要不我们一起去帮忙?顺便尝尝。”
粒儿瞪圆了眼睛,说:“不了,不了,我得回去照顾外婆了。”
“你是被留下来看家的。”她又提醒我,“就当这就是柿子,我们下次再一起去。”她把柿子红发夹摘下来,放到我的手心,然后就跑了。
我的手心暖洋洋的。
粒儿应该还是怕蚕的,因为蚕下山的时候,粒儿和粒儿妈妈都来了,她两眼放光,欣喜地说:“还是蚕茧亲切些。”这次,她主动跟在我后面。
我问:“难道蚕就不亲切吗?”
“蚕很可爱,就是不耐看。看多了,会头皮发麻。”粒儿挽起我的胳膊,悄悄说,“其实我上次是从睫毛缝里看路的。”
难怪踩到了不少蚕,把妈妈心疼得晚上做梦都在喊。
我说:“你可以回家啊,或者去看电视。”
“我不想跟你闹别扭,也不想外婆不开心。”粒儿软软地说。
我放下手臂,主动挽起她的胳膊,拉着她跟我一起摘蚕茧。
刚一摘完,妈妈立马就喊住门口收蚕茧的三轮货车,一股脑儿都卖掉了,这算是秋收的一种了。
在包饺子宴请来帮忙的叔叔阿姨时,我拉着粒儿到我房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蚕茧,摇一摇还有响动。
“送给你。”我一共就偷偷留了两个。
粒儿眼睛亮了,把手在裙边反复擦了擦,才伸出手,像接宝贝似的收下了。
5
国庆过去了,十一月很快就来了。
粒儿回来得越来越勤。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她也经常来找我玩。我们一起坐在小板凳上,伏在折叠桌上写作业,一边咬着笔头计算数学题,一边互相诉苦语文课文多么难背。
在一个彩霞铺满天的傍晚,粒儿一路小跑着来了。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票,说歌舞团马上要来镇上的大剧院表演了!她爸爸在城里工作,单位发了票,刚好两张,够我们俩一起去看。
我听了,激动地举着票绕着粒儿转圈。
看表演那天,妈妈特地把我的头发扎成马尾,别上蚕豆花色发夹,配上牵牛花般的毛衣,穿上炒熟的蚕豆壳似的小皮鞋。
我和粒儿约好了在大剧院门口集合。
我在门口等了很久,直到能看得见的小石子都被踢到墙角了,粒儿还没有来。
穿着整齐的人们一波一波地进去了。
“你进去再等也一样。”妈妈也在陪我等,她要赶回去割羊草。
我往左右两边街道望了望,寻不到粒儿的影子。于是,我攥紧手心,鼓着脸,独自验票进门了。
大剧院里有超大的表演台,比马戏团的帐篷里面规整,红色的椅子整整齐齐,坐了一大半人。我挑了两个连着的座位,端正地坐着,右手搭在右边的椅子背上。
座位渐渐满了,直到头顶一个声音响起:“小姑娘,我可以坐这里吗?全场就这一个空座位了。”
我噘起嘴,收回了手。
一直到开场,粒儿都没来。
歌舞团的服装比马戏团的更加精致,演员们的妆容也不夸张。我看得想欢呼,可是又没人陪我一起欢呼;我看得想拉旁边的粒儿分享,可是粒儿不在旁边。
我高兴地晃动小腿,椅子发出“吱呀”的声音,旁边的阿姨盯着我。我不敢动了。
我看得没那么开心。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马戏团的自由。
直到散场,粒儿都没出现。
我垂着脑袋走出门口,妈妈已经在等我了。
我说:“粒儿没来。”
妈妈说:“粒儿外婆紧急住院了,就在镇上。粒儿也去了。”
什么?!粒儿不是故意爽约,我的嘴角不知不觉地弯了。然后想到张奶奶,我又皱起眉毛,粒儿这会儿得多担心啊!
其实我对张奶奶的印象并不深,她平时都不见人影,也就在往年蚕上山的那阵子,她才会突然出现。
6
在路上,我听妈妈讲起张奶奶的事。
她女婿,就是粒儿爸爸,不喜欢乡下,逢年过节也不来。于是,粒儿妈妈就让张奶奶把田里的桑树扒了,都种上麦子,把张奶奶接到城里,让她做做饭,接送粒儿上学放学。春蚕和秋蚕上山,刚好在春种秋收的农忙时,每年张奶奶都会回来给乡里乡亲帮忙。毕竟是一个人住,没人照顾,有一年她夜里起身受了寒,咳嗽了好久,自那以后就落下了病根。今年,张奶奶状态大不如从前,非吵着要回家。粒儿妈妈心一横,把工作辞了,回到乡下照顾张奶奶。
我歪着头想,难怪粒儿之前几乎都没来过。
一连好几天,我都没见到粒儿。直到东面传来唢呐声,我的视线越过湖桑枝,才看到粒儿家门口聚满了人。
我跑了过去。
粒儿的眼睛红红的,比我外婆家养的兔子还红。我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粒儿先开口了:“那天真是对不起!”
“没事儿,演出我很喜欢。你外婆的事更重要。”我想了想,还是补上一句,“就是少了你,有点孤单。”
“你喜欢就好。我骗了你,一开始我就没法陪你去。爸爸总共就两张票,原本两张都要送给镇上的赵医生,因为外婆的事儿经常麻烦人家。是我央求爸爸,至少留下一张。我就是怕你不愿意去,才没和你说这些。对不起。”
粒儿的声音哑哑的,带着歉意的风钻入耳朵里,痒痒的,让我的心也痒痒的。我想起了那天要坐右手边座位的阿姨。原来不是她抢走了我留给粒儿的座位,而是那个座位原本就属于她。原来粒儿啊,为了让我去看演出,费了这么大劲儿。
就算我那天不去,也没什么。
去了我才更加知道,大剧院没什么好向往的。我宁愿坐在草垛上,沿着叶脉慢慢撕开一片片桑叶,看秋风裹着秋收的万物翻滚着歌舞,我和粒儿哼着走调的歌儿加入风中。
但我不想拒绝粒儿的好意。
“一起看才热闹。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我轻轻地说。
“可是,外婆没了。妈妈说,我们乡下的家没了,我再也不会回来了。”粒儿低下了头,抽抽搭搭地说。
秋风吹过,拂过开始发芽的麦苗,滚过开始光秃的湖桑林,掠过整齐划一的白萝卜,扫过开始干涸的沟渠,直至沟畔细弱的野桑树。
我站起来,指了指野桑树的方向:“粒儿,瞧,那是我们的野桑树。这棵桑树,在我们两家中间的沟畔上,它是属于你和我的。我会把它养得好好的,你每年都能回家吃桑葚。只要你想回来,它一定在那里等你。”
桑树是吾乡,也是你的家乡。
粒儿瞅着我,再望向野桑树的方向,重重地点头。
7
粒儿走了。
粒儿的家落了锁。她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来年,野桑树结了果,我吃了一半,留了一半,直到那一半掉在地上也没摘过一颗。
一年过去了,我找钥匙拉开抽屉,翻找着,摸到了一个蚕茧。茧子的表面发黄发毛,它很轻,顶端破了个洞。我眯起眼,从洞里看过去,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跑去问妈妈:“为什么会这样?”
“它变成蛾飞走了。”
我呆呆地翻看手上轻飘飘的茧子,仿佛粒儿也轻飘飘地从我的生活中离去一样。直到此时,我才相信粒儿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
渐渐地,地里的农作物品种越来越多,打的农药越来越杂。养蚕的人家跟很多人家都有了矛盾。常常一阵风吹来,裹着残留的农药,卷到了桑叶上,被蚕吃到了肚子里。好多人家的蚕快上山了,却耷拉了脑袋,一动不动。
越来越多的人家扛着锄头、钉耙站在刚打农药的人家门口,吵吵闹闹。来看热闹的人们一时分不清该劝架还是加入。
于是,村书记骑着自行车,举着喇叭喊:“把湖桑都扒了,种上甜叶菊。”
第一年,村书记就做了示范,赚的钱不比养蚕少。
“养蚕还要起早贪黑,甜叶菊种上了只要锄草。”村书记喊得更起劲儿了。
于是,家家户户都把湖桑扒了,晒干了,扔灶膛里烧了。
就在妈妈拎着锹去沟畔时,我跟了过去,拦在野桑树面前:“这棵不行。”
“看着就来气。”
“这是我和粒儿的约定。”
我望着妈妈带着锹回家的背影,怕别人也动野桑树的心思,在沟畔拾了不少芦竹,折断成差不多长短,一根接一根地扎在野桑树周围,形成围栏,又绕上两圈渔网线固定。
第二年,火辣辣的夏天,家家户户都赶着在雨前割完甜叶菊。一帮人今天来这家,明天去那家,割得热火朝天。欢声笑语又回到了这块大地,伴随着整晚剁甜叶菊秆的“咚咚”声。
野桑树被我浇过肥,长得越来越壮。
落了锁的东面人家和别着漂亮发夹的小姑娘,仿佛被人们忘在了记忆的旮旯里。每当我拉开床头柜,看到那一抽屉的发夹,金黄的、粉紫的、天蓝的、火红的,粒儿的名字就像下雨时小河里缺氧的鱼,迫不及待跳出记忆的水面,那些过往便跟阵雨似的朝着脸汹涌而来。
后来,我住校了,再也不能每天回家。
十一月,我刚背着书包回家,妈妈就喊住了我:“张奶奶满坟,粒儿回来过。她来找你没找到,就去了你们约定的那里了。”
听到这话,我把书包扔在前院,一路狂奔。十一月的野桑树都在掉叶子了,哪里还有桑葚。我跑到了野桑树那里,心“怦怦”地跳,快要蹦出来了。树脖子那里有根红丝带打的蝴蝶结,挂了一只透明袋子,在风中飞舞,里面有一对桑葚似的发夹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我回来啦!娇娇,谢谢你把我的家乡照顾得这么好。
“我的家乡”被划掉了,下面重新写着:
我们的家乡。
发稿/朱云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