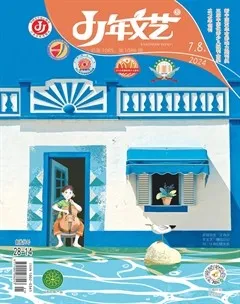荔枝灯

今夏的福州,脸变得有点让人猝不及防。前不久省级防汛部门还在通过网络、手机短信通告防汛信息,转眼间,小暑过,大暑来,“三伏”也都赶在七八月凑热闹。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此时的鼓屏路,在我办公室窗外的香樟树上,蝉声一浪排过一浪。如果说夏天是幅多彩画卷,蝉就是拉开这幅斑斓卷轴序幕的使者。回想小时候,每到暑假就迫不及待地放下书包,拎起衣包,往乡下跑,在万安农场的荔枝林中,乘着阴凉,吃荔枝,听蝉音,是最美的享受,也是我喜欢的消夏方式。漳州荔枝极盛,以漳浦荔枝为最,在明清时期就被列为朝廷贡品。到山中吃荔枝消夏的惬意,是逃暑南山的米芾也无法想象的。
表姐家是农场里的荔枝种植大户。每次上山,进入漫山遍野的荔枝林,辛勤劳作采荔枝的人们就像是搬家的蚂蚁,大人叮嘱孩子不能走远,以防迷路。表姐脸上的表情是收成的晴雨表,她的两只大手各抓起一大把荔枝,大笑的嘴巴向上扬起,开到耳朵,眼珠里闪烁着朴实而真诚的光。她把荔枝的品种一串念出来:兰竹、乌叶、早霞、金钟……最后一句话总是“放开肚皮吃”。
荔枝林中,最怕一种叫辣屁虫的虫子,扁平状,绿色,潜伏在枝叶中,善于伪装,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它的毒素喷到。有一次,我的手臂被喷了,皮肤刺疼,表姐立即掰了几颗荔枝,将荔枝肉在伤口上用力擦,说:“荔枝肉可解辣屁虫毒素,这是秘方。”我眼看着一颗颗荔枝肉被糟蹋,手臂疼,心更疼。
荔枝以鲜为美,现采现吃,原味中夹杂着木质香。孩子们扎进荔枝林,就是吃。半天下来,孩子们的脸蛋、脖子、四肢已经被蚊虫叮咬起许多包。俗话说:“荔枝水,越吃越馋嘴。”大人拿清凉油给孩子们涂抹,孩子们只顾着吃,挑到果实大核小的,更是满心欢喜,忙着向大人炫耀,荔枝汁顺着嘴角流到脖子上、衣服上。吃撑了,就挑选饱满圆实的,仔细剥开壳,左手捏住荔枝,右手小心翼翼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剥,渐渐露出一层完整的白皮,再小心用指甲在尖头上画圆圈,把尖头上的白皮剥掉,然后将剩余的白皮往下掰,直到蒂头,露出整个果肉,就做成一个“荔枝灯”。孩子们相互比较,一边向大人们炫耀,一边在舌尖上舔着,“荔枝灯”跟孩子们的眼睛一样清澈澄亮。林荫下,蝉声噪,我的内心一片清凉。
消夏之旅有乐有苦。我家住在城关,到农场路途并不远,但在那个年头,家里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两辆自行车。爸爸和妈妈各骑一辆,载着我和妹妹,经过火烧铺,绕过狭窄的县道,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遇见陡坡,只能徒步推车爬坡。两位大人牵着车把,两个小孩在后面推,艳阳下我们晒得满脸通红,汗流浃背,偶有手扶拖拉机“轰轰”经过,卷起漫天尘土。早在童年,我就和手扶拖拉机有过亲密接触,有时候爸妈没空,便托拖拉机师傅送我到CpO4Tvam+IFGcWg16f7GpZHdkQfTvrsEtjwBok/CO38=农场,这在当时是最高规格的待遇了。手扶拖拉机真是宝,能耕田,能拉货,有“铁牛”的美称,电影《喜盈门》的结尾,仁芳开着拖拉机驰骋在前,龙刚追赶在后,灿烂而青春的笑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了防止行车颠簸,小屁股坐得疼,要先在车斗铺上厚厚一层草,我上车坐在后面,再把三面木板扣紧了,爸妈交代我,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木板。有时候路不平,车辆震得厉害,我就本能地抓得更紧了。天气虽热,但有风,看着徒步或骑自行车的人被拖拉机扬起的尘土和“突突突”冒出的黑烟迷漫,慢慢被我们甩在身后,我内心还有几分窃喜。
紧赶慢赶,终于到了农场,这里是妈妈的娘家。迎接我们的全是诚恳的笑容,大家捧出一箩筐荔枝,边吃边聊,大概都是说我长大了,越来越帅气,书读得好之类的话,这是每个夏季见面的开场白。剩下的时光我便与表哥、表姐们玩在一起,上山捡柴,下溪捞鱼,田间捕鼠,草垛堆里躲猫猫,夯土层中烤红薯,饿了就吃,饱了就睡,醒了就玩,日日如此,无忧无虑。低矮的夯土房,曾外祖母暖心的笑、清澄的双眸,是我心中的“荔枝灯”,装得下整个夏季的美好。
暑假即将结束,临走,亲戚们还送来一大袋荔枝,乡亲们就是这么热情。从农场到县城,吃荔枝的战场转移了,阵地的选择可重要了。我家在东街31号,传统的明清建筑,按今日的行情,算得上沿街的旺宅。因为沿街,所以门口高悬一面竹织的屏风,以示内外有别。整板青石制成的门槛,小时候的我喜欢躺在上面,清凉,舒服。我喜欢用头顶着一边,脚丫子极力伸展,希望能触摸到门槛的另一边,这成为我丈量身高的一个方法,直到那青石门槛已经容不下我了,可我还是喜欢坐在青石门槛上吃荔枝。
荔枝保鲜不易。偶然读到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乐天兄真是吃荔枝的行家,对荔枝的物态、物理、物情观察细致入微,好像就在我面前讲授一堂生动的农业课。冰箱保鲜的荔枝以一日为佳,低温催发了荔枝中的糖分,我的32颗健美牙齿挡不住冰荔枝带来的酥麻感,嚼碎后的荔枝经过食道,进入胃部,整个肺腑迅速清凉,顿时有两腋生风、飘然欲仙的感觉。
参加工作以后,虽然每到夏天还吃荔枝,却多了几分不到荔枝林中的惰性,少了一份与蚊蝇面对面斗争的勇气。听听乡下来的亲戚说说荔枝的收成,时盈时亏,我的嘴里是甜的,心里是酸的,荔枝林在我的回忆里已经走过了三十来个春秋。
闽人对荔枝有特殊的情感。《西湖志》载:“吾闽荔枝,胜于岭南、巴蜀,西禅所产尤美。”每次到福州西禅寺,我都要拜谒宋荔,树干已经被岁月镂空,看似一张枯萎的皮,向上生长的意志顽强不屈,无法想象这浓密的新叶如何在枯木中生长,难道这就是枯木逢春?
昨天,妻子和小天到福州,带来老家乌石荔枝,肉丰、核小、味甜,妻子说:“是母亲专门挑选的。乡村振兴,老家引进了新品种,柴娘喜、桂叶、仙进奉、井岗红糯、大丁香、双肩玉荷包,以前少见的妃子笑现在也多了。”
眼前的荔枝灯,如同儿时所见,仿佛我的心灯,一直亮着,从未改变。
发稿/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