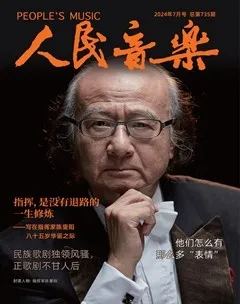从政府主导到人民自觉
甘肃和青海的花儿在民众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花儿的传承依托花儿会所形塑的集信仰、民俗、商贸于一体的文化空间,成为一种由民众自发组织、自主参与的社会实践。“从明清到民国以来,或因回民起义的失败;或因军旅的转移;或因农业经济破产迫于贫困的生活,大量的回族农民和士卒,由甘、青、宁等地,或集体,或单独,经过长途艰苦的跋涉,陆续进入新疆,散居于沿天山一带的广大区域。”①人口迁徙使甘、青、宁花儿逐渐被带入新疆,但民众自发组织的传统花儿会随之脱落。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政策的推动下,由政府主导的新的传承空间和花儿共同体得以重建。当下,新疆花儿主要流传在当地的回族聚居区。在“非遗”保护研究中,以往在以保护“作品”为导向的理念中,追求“作品”的真实性和本真性,由此,学者一般对传统的重建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视其为“传统的发明”。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强调“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②,当我们关注“人”和“过程”,而不是作品时,新疆花儿共同体的重建将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解框架。
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鄯善县东巴扎回族乡和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花儿歌手的个案调查为论域,以遗产化进程中的新疆花儿为观察向度展开讨论。
一、新疆花儿“非遗”共同体的重建
中国“非遗”保护体系是由政府、民众和学界共同参与和驱动的,其特色在于政府主导,由此带动民众的主体实践和学界的智力支持。新疆花儿便是在此体系框架下实现“非遗”共同体的重建的,具体路径包括以下三种:
(一)政府主导
在中国“非遗”保护体系中,政府是多元行动方合作机制的主要驱动力,四级名录体系则是其主导的具体方略。当某种活态实践得到国家认可被列入名录体系,代表着该项目由此进入遗产化进程。在新疆花儿“非遗”共同体的重建中,政府的龙头带动作用首先表现在传承空间的重建上,这里以焉耆回族自治县的“花儿大舞台”,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市的花儿培训班为例具体来谈。
2008年, 借助新疆花儿被以扩展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以下简称“非遗”项目) 名录的东风, 焉耆回族自治县政府开始重视花儿,在文化馆原馆长韩斗的组织下,在人民广场举办“花儿大舞台”, 为老百姓重塑花儿演唱提供了必要的文化空间。由于传承人每晚到广场上唱花儿、跳花儿舞蹈,使各族民众受其吸引并参与其中,其间不乏有主动报名习得花儿者,其影响力辐射至博湖县、和硕县与和静县。2017年后,“花儿大舞台”中断,但其培养的一批花儿歌手现已成为该县“非遗”传承人。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与文化馆每年开办四期新疆花儿培训班,学员少则四五十人,多则上百人,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秀芳担任培训师,对象为米东区各社区的音乐教师、文艺骨干和花儿爱好者,其中也有慕名而来的学员。王秀芳还将花儿带入乌鲁木齐市幼儿园、小学、中学和艺术学校为孩子们教唱和讲解花儿。此外,因行政区划的变化,原本是新疆花儿重要传承地的昌吉州米泉市与乌鲁木齐市的东山区合并,成为现在的米东区,原米泉市的传承人随之并入乌鲁木齐市。由此,作为新移民的马成(从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迁入)和寇红(从焉耆回族自治县迁入)成为昌吉州花儿传承的重要力量。自2010年以来,作为扩展名录,昌吉州花儿被列入自治区级“非遗” 项目名录后, 该州党委宣传部、文联、文化馆就组织培训班为各县镇文化专干、业余团体或教师,以及花儿爱好者培训花儿演唱,马成和寇红担任培训师。经过培训班的学习,青年歌手马晓琴、马金兰、加尔肯别克·纳斯依奥拉、马晓棠和马英萍逐渐成长起来。政府主导的培训班使花儿在昌吉州和二六工镇落地生根,马成和寇红也分别成了自治区级和州级“非遗”传承人。
(二)群体和社区中的个人实践
在《非遗公约》框架下,“非遗”保护的实践主体包括社区、群体和个人,其间群体和社区不仅由个人组成,个人还在生活实践中维系着群体和社区的文化边界。
作为新疆花儿的传承社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以开都河为界,河以北的民众讲焉耆方言,唱甘肃和宁夏花儿;河以南的回族民众因从青海军屯或民屯迁居至此,讲青海方言,唱河湟花儿。以传承人马生龙所在的永宁镇黑疙瘩村为例, 该村共有百姓千户,大多从青海大通、湟源、湟中等地迁入,其中回族占80%,汉族占10%,维族占10%,家家户户都有人用青海方言唱花儿。马生龙为永宁镇培养了二三十位花儿传承人。作为焉耆社区的个体实践者,歌手马桂芳因“花儿大舞台”上演唱的《尕鸳鸯》而想起父亲用青海方言演唱的同名花儿,于是自愿加入到花儿传承队伍中; 寇红听着父亲演唱的花儿长大,父亲唱过的《直令》如今是她演唱最多的曲令;75 岁的蒋福林是永宁镇青海人的后代, 讲西宁话,唱河湟花儿;支边青年的后代苗族花儿歌手杨莉玲在与当地花儿歌手接触后,开始喜欢、学唱并传承花儿; 回族歌手冶秀英从唱蒙古族民歌改唱花儿,一唱便是几十年。正是这些个人的坚守与热爱,才构建起当下焉耆花儿“非遗”传承的群体和社区。
作为“非遗”社区的吐鲁番市鄯善县东巴扎回族乡, 老一辈花儿传承人和实践者丁老太为了不让花儿传承中断,为花儿人才队伍建设呕心沥血。她和接班人马绍福创建了一支由乡干部、村干部、个体户老板、农民、教师和退休职工组成的三四十人的传承团队。作为个体户的马绍福,在生意之余为团队成员教花儿。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花儿传承团队的影响下, 东巴扎回族乡的老百姓亦经历了从不懂花儿到喜欢花儿的过程, 成为作为实践者的受众。
(三)特色课程的学校实践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重视青年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提倡赋权青年,使青年成为传承的生力军。在考察中,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和高校也逐渐开始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来传播“非遗”,提高其可见度。作为昌吉州唯一一所地方高校,受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研培计划的启发,昌吉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自2019年开始在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两个本科专业开设花儿特色课程, 使其成为本科教育的必修课。经过32课时的学习,学院要求每个学生会唱两至四首花儿, 并从中选拔成绩优异者继续开展教学。2023年,学院将马成请进校园教授花儿,开创该院“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的先例。
由此,在政府主导的传承空间中,在各类教育培育的个人、群体和社区中,在高校、传承人和青年多方行动的协力合作中,新疆花儿“非遗”共同体得以重建。以政府主导为开始,逐渐激发了民众对新疆花儿的自觉意识和传承热情, 使花儿反哺民间,扎根在人民的生活中,使文化表现形式重新嵌入焉耆回族自治县、昌吉回族自治州和鄯善县等社区民众的婚礼仪式中,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民众自觉的主体共建,为花儿“非遗”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实践路径。民众在生活实践中重新定义了花儿之于社区和群体的功能和意义,强化了社区群体的认同感和持续感,这是新疆花儿共同体重建的意义所在。
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歌手实践
在历史实践中,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根基,故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与阐释很多来自历史学界。倘若我们将历时性的眼光延伸至当下,那么蕴含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非遗”,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则不容忽视,它或可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的路径之一。作为移民文化进入新疆的花儿,从与甘、青、宁的民俗文化空间和生活语境中脱嵌,又在新疆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生境中,在与各族人民交流、交往和交融的生活中完成了再嵌过程,从演唱技艺转化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进路,进而使甘、青、宁等地的区域认同转换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新疆花儿歌王”韩生元曾以花儿曲令填词歌颂共产党和民族团结,其花儿叙事贯穿于社会和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接续韩生元的演唱主题,当下花儿在重塑社区和群体的传统音乐功能和意义时,亦强化了特定社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持续感。韩生元通晓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方言土语,从而将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融入花儿的演唱实践。如果说韩生元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新疆花儿的本土化重塑过程,那么当下花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则是由不同民族的同胞共同构建的,其构建方式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作为中介的汉语方言。与甘、青、宁等地花儿地方方言的排他性相比, 新疆花儿虽然保留了迁出地语言的基本表达方式, 但又有包容性和通俗易懂的特征,能被各族人民广泛接受。汉语方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成为多民族音乐文化互嵌交融的重要黏合剂。哈萨克族小伙加尔肯别克·纳斯依奥拉和哈力木哈孜·托哈塔尔将花儿唱词翻译成哈萨克语,与青海汉语方言交替演唱。从他们合唱的《尕妹妹是牡丹花中王》来看,译作哈萨克语的花儿虽然保留了青海方言中的特色音腔, 但已在唱词与音乐的融合中实现了汉语方言到哈萨克语的转换。
第二,政策宣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旅厅、乌鲁木齐市和米东区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王秀芳将党的政策编成花儿唱词,带领宣讲队,每年数次在乌鲁木齐市各县、镇、乡、村,以及市政机关等地区进行宣讲,让老百姓了解党的政策;鄯善县东巴扎回族乡以马绍福为首的花儿志愿者服务队有80%是共产党员,他们将富民安居、计划生育补贴等党的各项政策编入花儿唱词进行宣传, 歌颂民族团结。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将防疫政策编成快板进行宣讲,使“非遗”项目在紧急情况下的人民生活实践中发挥了作用; 哈力木哈孜·托哈塔尔用花儿曲调《四季歌》填写新词歌颂党的二十大,再用哈萨克语在本族民众中传唱。
第三,多民族的主体实践。加尔肯别克·纳斯依奥拉和哈力木哈孜·托哈塔尔用哈萨克语演唱、冬不拉伴奏的二声部花儿重唱, 不仅受到哈萨克受众的欢迎,还被带入该族民众的婚礼。同时,他们通过青海和西北五省花儿比赛将其带给青海民众。对于这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哈萨克和青海民众都经历了从诧异、好笑,再到逐渐适应、接受和认可的过程。两位哈萨克小伙也使花儿在民众生活实践中完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与交融。
在乌鲁木齐米东区,回族、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的许多民众都有参与花儿演唱实践的经历;在焉耆回族自治县,花儿在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多个民族间传唱。其中,作为在焉耆支边青年的后代,苗族身份的杨莉玲亦因喜欢花儿而唱花儿;马桂芳因曾在和硕县曲惠乡维吾尔族村落生活而掌握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的演奏技艺,并用它为花儿演唱伴奏;由维吾尔族四位青年组成的红雪莲组合将传统花儿改编,融入维吾尔族音乐元素的同时,分声部演唱,他们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深受广大民众喜欢,而且在西北五省花儿大赛中频频获奖。
在表现形式上,新疆花儿融入维吾尔族音乐的节奏风格和舞蹈动作,吸纳哈萨克族音乐的诙谐幽默,采借新疆曲子、陕北民歌和秦腔的音乐元素,拓展了花儿的艺术特点,借助这一艺术形式极强的包容性,各族歌手在花儿“非遗”实践中共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三、对新疆花儿“非遗”属性的认知
新疆花儿的案例为我们理解什么是“非遗”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国家层面,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的花儿,虽然被划入“传统音乐”的分类中,但除宁夏回族山花儿之外,甘肃和青海的花儿均将“花儿会”并置于项目名称之上,如花儿(莲花山花儿会)、花儿(松鸣岩花儿会)、花儿(老爷山花儿会)、花儿(瞿昙寺花儿会)等。可见,国家层面对花儿的评审认定是强调作为文化空间的花儿会的。在国际层面,2009年花儿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但申报书却未将2008年作为扩展项目进入国家级第二批“非遗”项目名录的新疆花儿包纳其中,无论是申报文本,还是社区的知情同意书均未述及新疆花儿。因此,国家和国际层面是如何认定新疆花儿的,尚不得而知。接下来,我们从《非遗公约》对“非遗”的定义③来看新疆花儿当下传承和价值认定层面的复杂性。
第一,《非遗公约》的价值认定主体是社区、群体和个人。新疆花儿通过移民迁徙从甘、青、宁等地的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主体性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导向中从复数走向单数,而是在政府主导、民众积极参与的遗产化进程中重建了以“非遗”项目为纽带的社区和群体,在新疆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再嵌于各族人民的社会关系和文化间关系中, 且这种重建是从政府主导逐渐走向人民自觉的。社区和群体被重构后,由其认定和确认的作为“非遗”项目的花儿,也在内涵和外延上得以扩展,他们将词曲作家创作的歌颂共产党政策和恩情的花儿歌曲亦认定为作为“非遗”的花儿,而这与我们以往对“非遗”的认知有所不同。与词曲作者的创作相比,“非遗” 更强调民众的口头创编过程和创作主体的集体性。《非遗公约》强调尊重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选择与价值认定, 那么当公权领域的“非遗”转换为私权领域的个人作品时,我们对“非遗”理解的边界将在哪里?
第二,《非遗公约》“非遗”的保护对象是“社区、群体和个人”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且以包容性原则统领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五大领域。领域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比如青海、甘肃的花儿会就涵盖上述五大领域前三项,而目前调研中看到的新疆花儿更多的是去语境化和舞台化的表演艺术展演, 返回到民众婚礼的社会实践亦基本上是重建的,迁出地青海、甘肃花儿中宗教信仰的观念表述和民众自发组织的花儿会文化空间已不是新疆花儿的文化语境。虽然新疆花儿也参与到节庆活动中,但这类节庆活动更多是由政府举办的,而非民间自发。仅就调研现状显示,新疆花儿的归属更多在表演艺术领域。
第三,《非遗公约》中项目的活态性取决于“世代相传”并被“不断地再创造”的动态过程。焉耆回族自治县马生龙的花儿传承构成了前后四代的传承谱系。同时,新疆花儿的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地理、文化和民族环境以及与迁徙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完成再创造过程。青海、甘肃花儿的活态性更多表现在口头即兴创编上,遗憾的是,此次在新疆的调研并未见到即兴创编的花儿唱家。仅就调研来看,新疆花儿的再创造更多体现在表演形式上,比如哈萨克小伙的二声部花儿重唱;马桂芳用都塔尔弹唱的花儿串烧;红雪莲组合演绎的多声部花儿;蒋福林在花儿演唱中加入维吾尔族舞蹈;杨莉玲在《河州大令》中融入“尕妹妹”的唱腔,形成慢- 快- 慢的速度变化风格等。表现形式上的再创造是否符合“非遗”定义中的“再创造”内涵值得深思。
第四,如前所述,新疆花儿在政府主导和民众参与下重建了花儿之于社区和群体的功能与意义。这个“社区和群体”不再,由单一民族、单一文化所构成,而是以花儿为纽带构建多民族人民和谐共处的社会关系和文化间对话的共同体,构建了一种促进包容和融合、凝聚和团结各族人民的内在驱动力。因此,社区本身是流动的,且不受物理和地理空间的限制,有时又是跨越族群边界的,与“非遗”项目互构共生。
第五, 基于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遗”保护的最终导向是对不同文化平等地位的尊重。新疆各族人民能够在交流、交往和交融中共同传承花儿,这表明花儿已不只是一种表演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还是各族民众、不同文化间交流、理解与对话的中介。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介,不同民族民众愿意且能够将自身的文化与花儿相融合,应该首先建立在对文化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基础上。花儿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缓和或消解同一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矛盾冲突的积极作用。
结语
新疆花儿的遗产化过程为中国以政府主导的“非遗”事业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在学界,很多学者对于传统的重建持批评态度,视其为“传统的发明”。事实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表述并非贬义,而是强调传统的建构和不断赋予新功能的过程。对于新疆花儿而言,假如当时政府不积极搭建平台,不及时抢救和保护花儿,难以想象是否今天还能看到拥有自身风格、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的新疆花儿。自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之日起, 新疆花儿已进入被遗产化和项目化的建构过程,而这也是所有“非遗”项目不可避免的被建构过程。虽然新疆花儿歌手与我们以往普遍认可的“非遗”传承人有所不同,如部分传承人或有学习美声唱法、接受过视唱练耳专业训练的经历,或从专业院校毕业具有学院派演唱风格,但仅就新疆花儿的重建而言,笔者仍持积极态度,因为新疆花儿虽然发起于政府主导,但在遗产化进程中逐渐转化为人民的自觉意识,而这恰恰是新疆花儿提供给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非遗”事业的基点。
姚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