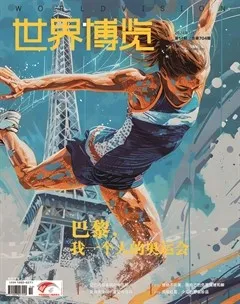万里烟尘入大都

公元1325年,元大都,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伫立在雄伟的城门前,凝望着这座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
11年前,他从威尼斯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向东而来。他与大都的缘分,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在那本著名的游记里,这位威尼斯商人断言,如果罗马教廷能够早日派遣传教士前往遥远的东方,元朝皇帝恐怕已经皈依天主。无独有偶,出生于大都的旅行家列班·扫马千里迢迢拜访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也带来好消息:元朝境内活跃着一批基督徒,就连忽必烈本人也对宗教有浓厚的兴趣。在东西两大旅行家鼓吹之下,罗马教廷下定决心重新探寻东方,派出意大利教士孟高维诺前去一探究竟。但在教皇使节怀揣致忽必烈的书信抵达大都之际,那位名满世界的大汗兼皇帝已撒手人寰,继任者是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
满怀憧憬
山水相隔,音书难至,孟高维诺断断续续寄回3封书信,自言受到礼遇,元成宗不仅封赏官职,还希望会见更多罗马使者。在德高望重的意大利前辈召唤之下,自幼苦修的鄂多立克踏上追寻东方之旅,从威尼斯到波斯,再由霍尔木兹海峡转入大海,乘船抵达印度,途经锡兰与爪哇,自广州登陆。进入元朝疆域后,他跟随商旅路线,先后造访泉州、杭州、南京、扬州等繁华都邑,惊叹东方的富足与奢华之余,更对元大都的盛景平添几分憧憬。
忽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端坐在皇宫里的那位威严的大汗,会是欧洲人寻觅200年的约翰长老吗?据他所知,十字军东征时代,一封署名约翰长老的来信震惊欧洲。约翰长老宣称自己来自东方,是天下之主、君王中的君王,统治的国度里香甜蜂蜜和牛奶四处流淌,奇珍异宝遍地皆是。更重要的是,他信奉天主,愿与欧洲人共同夹击伊斯兰帝国。这位天降盟友让罗马教廷欣喜若狂,不断派出使节寻找,可惜一无所获。每当听闻东方的贤君或名将,欧洲人就不由自主地将他附会为约翰长老,耶律大石(1087-1143,在辽被金所灭之后建立西辽)、屈出律(?—1218,西辽末代皇帝)、王罕(?—1203,克烈部首领。克烈是辽金时代蒙古高原上的一大部族)概莫能外。蒙古铁骑袭来,欧洲人仍抱有一丝希望,幻想约翰长老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期待能够化敌为友。约翰长老自然无法永生,但他早已化身为一个东方梦。鄂多立克是个务实之人,不太相信约翰长老传说,但他追逐东方梦而来,必定要亲眼观察真实存在的大汗之城——元大都,或依马可·波罗更钟爱的称呼——汗八里。

鄂多立克脑海里飘过烂熟于心的《马可·波罗行纪》,威尼斯商人笔下足以容纳6000人宴饮的壮丽宫殿,雕刻龙、兽、鸟的金银宫墙,常青树与琉璃矿石遍地的绿山,注满美酒的金瓮。半信半疑的欧洲人,时常讥讽马可·波罗不过是小说家之言,毕竟威尼斯商人终年奔走异国,惯用浮夸辞藻吹嘘奇闻。但鄂多立克一路走来,目睹中国南方都市的繁盛,早已相信马可·波罗所言非虚。当他终于走进大都,竟发现真实景象比游记更胜一筹。
抵达大都
眼前的城市,仅外围城门就有12座,周长40英里(约64.37千米)。大汗居住的宫殿另有宫墙,4up7EsIsrVdIvnHHmGvBfg==周长4英里(约6.44千米)。宫墙之内,就是举世闻名的大汗宫殿,堪称全世界之最美者。而宫殿旁边的小山,正是马可·波罗描绘的“绿山”。后来,鄂多立克才知道,那座绿山继承自前朝女真人,寓意着蓬莱仙境,上面的小宫殿,更是以月亮女神嫦娥居住的广寒宫命名。绿山之外,大汗寝宫高高在上,由24根金柱支撑,连墙面都铺满质地上乘的红色皮革。最引人瞩目的,是宫殿中央用宝石打造的大瓮,据说价值4座城池。大瓮边沿以黄金装饰,雕刻着凶猛搏击的金龙。美酒佳酿从管道流进瓮里,只需拿起旁边的黄金酒杯,就能开怀畅饮。可惜鄂多立克自己长年苦修,褐衣赤足,以面包和白水为食,无缘此等美味。
还没来得及拜谒宫殿,鄂多立克就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元成宗早已辞世。不止如此,十几年里,大都先后送走3位大汗,如今登上宝座的是忽必烈的曾孙泰定帝。就在2年前,元朝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政变,一伙对政治改革心生不满的蒙古贵族,在避暑结束重返大都途中,刺杀了年轻气盛的元英宗(元成宗的侄孙)。镇守漠北的泰定帝趁乱登上皇位,在大都继承宝座,诛杀叛党,稳定住局势。鄂多立克原本为亲善基督教的元成宗东行。面对纷繁的变局,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依然不改初心,希望能够当面拜见大汗,唤醒大汗的宗教热情。
若无重要人物引荐,面见大汗,谈何容易?鄂多立克唯一能够依赖之人,正是已在大都站稳脚跟的孟高维诺。这位意大利同胞,既是罗马教皇任命的东方大主教,又是侍奉大汗左右的宠臣,不仅能够出入皇宫,还享有专座的待遇。借着这层关系,鄂多立克终于见识了大汗的威严和排场。朝堂之上,大汗端坐中央,左手边是皇后,其下是一众妃嫔,蒙古贵妇头戴形似人腿的顾姑冠,上面装饰着华丽的鹤羽和珍珠。右手边则是将会继承汗位的儿子,其下是皇亲国戚。陪侍的还有4位书记官,小心翼翼地记录大汗的一言一行。浑话连篇的伶人,不时说着逗乐的俏皮话,为宫廷威严的气氛添加一些笑声。除去这些亲信之外,一群蒙古贵族子弟守卫宫门,任何形迹可疑的人都会被捉住盘问。
面见泰定帝
鄂多立克在大都一住就是3年,入宫机会寥寥,更别提单独跟大汗说上几句话了。面圣的希望,只得寄托在大汗出宫或回宫的时机,好在泰定帝每逢出行,都要孟高维诺给予祝福,如此一来,鄂多立克总能收到同胞传来的第一手消息。虽然统治汉地多年,蒙古大汗仍旧留恋草原,要在故土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度过盛夏光景。到了隆冬,北风凛冽,大汗一行再返回大都避寒。鄂多立克得到大汗回程的消息,立马动身前去恭迎圣驾。在他眼中,大汗仪仗恰是十字架形状,前后各有一支骑兵开路与殿后,两翼各有一支骑兵护驾。大汗与子孙、嫔妃位于十字中央,坐在一辆大车上,那里是沉香木与黄金打造的移动宫殿,用兽皮覆盖,点缀着宝石。大车由4头温驯的大象和4匹披戴华丽的骏马拉拽,卫兵在四周辛勤巡逻,肩上站着12只猎鹰。不消说闲人免近,就连聒噪的鸟群飞过,卫兵都会放出猎鹰把它们驱散,以免打搅大汗的清静。此情此景,与马可·波罗的记述别无二致。
即便如此,当看到御驾临近,鄂多立克依然决心冒险一试。为了避免被卫兵驱散,他把十字架绑在一根长木杆顶端,高高举过头顶,希望被远远瞧见。但大汗坐在移动宫殿里,一时无法注意到远处的细长木杆。情急之下,鄂多立克大声唱起用于庆祝新年和赎罪的歌曲《伏祈圣神降临》。圣神并未降临,歌声倒是成功地惊扰了圣驾。好在大汗为人和善,没有怪罪这位莽撞的基督徒,反而令人召他上前说话,问询所唱是何方音乐。鄂多立克毕恭毕敬地举着十字架走来,原本躺卧车中的大汗赶忙起身,将价值连城的皇冠摘下,谦逊地亲吻十字架,又从他的手中接过香炉,虔敬地焚香叩拜。鄂多立克在大都学到一个规矩:不能空手拜见大汗。因而,在十字架和香炉之外,他随身带了几个苹果。礼轻情意重,大汗接过两个苹果,吃了一个,留下一个,算是接受欧洲来客的祝福,片刻之后就做出送客的手势,以免他被随行的车马误伤。

成为传说
尽管只有匆匆一面,夙愿得偿的鄂多立克已然心满意足。不过在大都生活的日子里,这位基督徒也清醒地观察到,大汗对待各色教徒,都不失体面。在大汗周围,不止有孟高维诺,也有信仰坚定的穆斯林。大汗曾下令限制僧侣和道士敛财,却也同样宽容佛教和道教。他包容汉地佛教,同时也敬重藏传萨迦派佛法。大汗谦恭的姿态,只是出于天下共主的身份。他尊重基督教,却并不信奉,纵使亲吻了十字架,也只是对基督教“有些兴趣”罢了。想通这个道理,鄂多立克的3年大都生活就不算虚度。
此时,鄂多立克又肩负起新的使命。驻扎大都30年的孟高维诺垂垂老矣,自感时日无多,希望鄂多立克代自己拜见罗马教皇,请教廷再派一批教士前来,守住多年奋斗的成果。这位旅行家只得匆匆告别元大都,重新上路。2年之后,鄂多立克终于回到罗马,教皇听闻他带回元大都的消息,不禁喜上眉梢,立刻差遣50人随他再次东行。然而,漫漫路途、万里烟尘已经严重侵蚀了他的体魄,尚未来得及动身,鄂多立克就病倒了,只能争分夺秒,奋力挣扎着向教友口述自己的东方之行。1331年,回到欧洲一年之际,旅行家病入膏肓,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这位传奇人物最后一程。当他闭上双眼之际,虔诚而狂热的信徒蜂拥而上,撕碎他身上的布条、剪掉他的发须,带走一切神圣的痕迹。他的尸骨被收进神龛,供千万人崇拜。他的神圣,源自游历东方。
不久之后,远在西欧,一本游记名声大噪,一位曼德维尔先生以毫不逊色于马可·波罗的笔触,讲述自己在中国、印度等地漫游的奇妙旅程,着重描摹美丽、高贵、富庶、商贾云集的大都和拥有无限权力财富的大汗,令那些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如痴如醉。百年之后,许多探险家仍对他笔下的大都心向往之,他的热心读者之中就有热那亚水手哥伦布。但又过了百年,有心人发现,那位被誉为“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和“英国散文之父”的曼德维尔先生,似乎并不存在,至少不曾抵达中国。游记里关于东方的生动文字,全盘摘抄自鄂多立克口述,只是加以润色和修饰罢了。在剽窃与洗稿里,鄂多立克的远行阴差阳错地在文学世界得以永生。
(责编:李玉箫)

鄂多立克(?—1331),意大利人,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尼科洛·达·康提并列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在元代来华的旅行家中,鄂多立克对欧洲的影响力仅次于马可·波罗。他口述的《游记》(中译本名为《鄂多立克东游录》)以包括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形式在欧洲广为流传。

元成宗(1265—1307),名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年号大德。《元史》称他﹃善于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