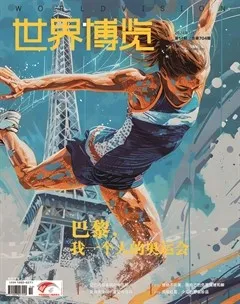凤凰红茵,少见的野茶珍品

每次到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的凤凰镇,都是由黄瑞光老师陪同我上乌岽山访茶。黄老年过七旬,是凤凰单丛茶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更是广东乌龙茶界的泰斗。生于斯长于斯,又加上半个世纪的单丛茶工作经历,使得他对乌岽山了如指掌。随着老先生翻山越岭,走村过寨,使我受益匪浅。
种类繁多,既是单丛茶的特点,也是单丛茶的难点。黄老细心,每次上山都尽力教我这个“外地人”辨识各种茶树。大名鼎鼎的大庵宋种,开价最高的通天香,甚至少为人知的香番薯、鸡笼刊、棕蓑挟,我都在黄老的陪同下多次实地考察。
但遗憾的是,几圈走下来我却从来没有见过红茵茶树。以至于我对红茵的了解,更多来源于资料。红茵属于野生型茶树,因嫩梢新叶的前端呈现斑斓的浅红色而得名。凤凰镇先民,偶然发现红茵叶,拿回去烹制后饮用,滋味鲜爽怡人。随后便有意遴选,从而拉开了凤凰镇种茶的序幕。如今大名鼎鼎的国家级优良茶树品种凤凰水仙(华茶17号),即是由此培育而成。
若论资排辈,红茵在凤凰镇乌岽山茶树中应属元老。换句话讲,想喝懂今天的单丛,就不能不了解红茵。但如今红茵已如江湖宿老般淡出茶界,我多次上乌岽山也无缘得见真容。红茵为何如此神秘? 第一是生长环境太险,第二是采摘难度过大。
红茵之“苦”
红茵,多生长在乌岽的深山老林当中。按照黄瑞光老师的经验,海拔600米以下根本看不到它。由此看来,红茵倒是百分之百属于高山茶了。今天饮茶人,只知高山茶之美,却不知上高山采茶之险。茶圣陆羽,就曾多次上高山访佳茗。其好友皇甫冉曾有“采茶非采菉,远远上层崖”的诗句,描述的即是陆羽高山采茶的艰辛。

凤凰镇山势陡峭,道路崎岖难行。即使从镇子里出发去乌岽村,一来一回也要有大半天耗在路上。上世纪90年代,吴伟新镇长带头修了200余公里的山路,才使上山下山便捷了许多。即使如此,许多茶树生长的地方仍是崎岖。至今,很多山上茶园采下的茶青,也要靠钢缆才可以运下山坡。红茵生长的地方,基本上人迹罕至。我几次上乌岽山,都不曾与它邂逅,原因就在于此了。
有人可能会说,那直接把山上的红茵挖下来,种到山下不就行了?还真不行!作为野生茶树品种,红茵保存了很多茶树的原始特性。《茶经》中就曾写道茶树种植“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也就是说,种茶树应像种瓜那样以种子发育繁殖。明代《天中记》中进一步阐释说:“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
后来的茶树,在人为驯化下既可有性繁殖也能无性繁殖,移栽也未尝不可。但红茵,保留了“老脾气”。有一年,有茶农费尽心力将10株红茵请下高山,移种到茶田之中。结果来年开春,无一存活。
野茶,如同隐士。习惯了山野村夫的生活,一时半会儿估计难以融于现代社会。找到野茶,绝非易事。但即使找到了,采摘野茶更是难上加难。红茵并非集中生长于一处,而是散居于山野之间。东一棵,西一株,根本没法大规模采摘。有时候一天下来,一半的体力用在采茶,另一半的体力都耗在转场上了。
由于无人打扰,红茵大可任性生长,有时候植株达到四五米之高。当然,几人高的茶树在乌岽山不算新鲜。来凤凰镇走一圈,随处可见扛着梯子去茶园的采茶工。架梯子采茶虽然麻烦,却也算是行之有效。
可是这一套办法,在红茵这却也行不通。原来红茵作为野茶,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她生长越茁壮。以至于红茵生长的地方别说架梯子,就是连个板凳都放不稳。茶农无奈,只能上树采茶。有时候无计可施,只能直接连枝带叶的将茶树砍断,再慢慢采上面的嫩叶。采制红茵,费力不讨好。
虽未见茶树,但是我却喝过红茵。如今“野茶”二字,几乎可以与“优质”“美味”等词画等号。作为货真价实的野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采来的红茵,味道如何呢?若让我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便是:苦!
康熙年间,苏州的洞庭东山出了一款名茶。由于香气太冲,吴中俗称其为“吓煞人香”,即如今的碧螺春。按照这个思路,红茵茶就该被叫作“吓煞人苦”了。爱茶人,多半不怕“吃苦”。但红茵之苦,在口腔里横冲直撞,让人猝不及防。一杯茶下肚,突然想起一段旧事。南宋末年,天下大乱。元人南下,攻破临安。潮州当地传说,宋帝赵昺逃难,途经乌岽山。正在口干舌燥之时,当地村民特献来“红茵茶汤”。落难中的皇帝喝后,竟是连声称赞。想那末帝赵昺也真是走投无路了。若不然,怎么会对这样的苦茶大加褒奖呢?
脑子里正在胡思乱想,口腔中的感觉却有了变化。红茵茶入口,只觉其味苦硬。但静候片刻,竟可回甘。入口的苦有多刺激,回口的甘便有多持久。茶圣陆羽,曾以“啜苦咽甘”四个字作为好茶判断标准。茶中有苦,持久不散,就是缺点。茶中带苦,若可回甘,便是特点。因此从专业审评角度来评判,红茵茶的“苦”应描述为“浓强”才更为妥帖。
毕竟对于苦味的衡量,还要看个人口味。有人觉得如饮汤药,可能就有人觉得似啜甘露。据黄瑞光老师回忆,当年茶叶公司也会收购一些红茵。虽然出自凤凰镇,但红茵与单丛的特征相差甚远。因此,大都被归为“假茶”降价销售。潮州人大都喝不惯,但近海的汕头茶客却痴迷此茶。原来海边居民常吃咸鱼一类的腌制食品,致使饮茶口味偏重。红茵的野性,刚好可以征服他们的味觉。
“野味”红茵
其实红茵不仅茶树品种古老,制作方法相较单丛也更为简单、原始。鲜叶摘下来,不经5次碰青的细腻处理,而是直接锅炒杀青再经烘干。严格意义上讲,新制出的红茵更像烘青绿茶。单丛特有的丰富香气,红茵并不具备。可是按我的经验,凡新茶不香者,久存往往倒给人惊艳之感。这次在单丛制茶高手黄继雄家中,邂逅了一款存放近30年的红茵。托他的福,让我又一次验证了这个观点。
久存的红茵干茶,黝黑中透着一层乌亮。近鼻深嗅,只有一股淡淡的陈味。若不和我透题,还真以为是存放经年的六堡茶呢。煅水泼茗,其汤如血。看似浓酽,入口却已无苦涩,反只觉醇和。虽不香,但满口却是饱满丰富的滋味。这时莫急着咽下,且在嘴里“咀嚼”一阵,体会茶汤的“骨肉之感”,别有一番滋味。

正赶上那两天在山上,多少吹了些山风,总是觉得要感冒似的。结果3杯老红茵下肚,浓沉滃然,微疴尽脱。不知不觉间,额头竟然已是汗涔涔的了。据说当地老人咳嗽不止,也多是用老红茵茶兑上野蜂蜜饮用。化痰平喘,另有一番奇效。我未曾亲身体验,仅做一家之言收录,以备方家参考。
如今市场上野茶概念被炒得火热,但大都名不副实。一些茶树荒放几年,便也敢以“野茶”自居。在消费者的潜意识里,“野生”与“毫无污染”“绝对安全”“质量优异”的概念紧密关联。一些不本分的商家,就是利用大众对饮食安全的焦虑,暗示消费者“野茶”即是“好茶”。您还别说,吃这一套的爱茶人还真多。非野茶不喝,甚至成了一些人茶桌上炫耀的品位。
对野茶的狂热追求,是大众潜意识里对工业时代的厌倦与反思。同时,也有多年来热衷“野味”的饮食陋习在作祟。这篇关于野生茶树品种——红茵的文章,只是想尽可能拨开笼罩在野茶之上的一层神秘面纱,让大家真切了解野茶的采摘、制作以及品饮过程。想象可以很丰满,现实可能很骨感。真正的野茶产能低下,能做成大众茶饮吗?不能。真正的野茶口感霸气,会博得大众欢心吗?够呛。面对充斥市场的“野茶”,爱茶人可一定要多加警惕才是。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