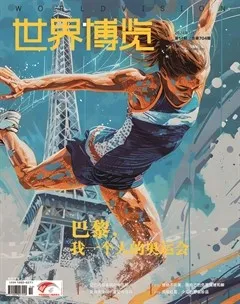若无古琴,宋朝该有多寂寞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是岳飞词作《小重山》中的句子。所谓“瑶琴”,指的便是至今具有3000年历史的古琴,又称玉琴、绿绮、七弦琴,曾经深受文人的喜爱。两宋时期,文人治国的基本国策推动了古琴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官琴”与“野斫”齐头并进的局面,留下了不少传世名琴。20世纪50年代初,在河南方城县征集、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石泉”七弦琴便是其中之一。
石上听泉
北宋斫琴名家石汝砺在他的论著《碧落子斫琴法》中写道:“凡面厚底薄,木浊泛清,大弦顽钝,小弦焦咽;面底俱厚,木泛俱实,韵短声焦;面薄底厚,木虚泛清,利于小弦,不利大弦;面底皆薄,木泛俱虚,其声疾出,音韵飘扬。是故为琴之法,必须底面相当,虚实相称,弦木声和”。正如其言,“石泉”七弦琴琴面由桐木所制,木质偏软;底面则为椊木,木质较硬,薄厚正当的同时又有软硬之分,声音便可以经过多重反射而更显浑厚圆润。虽然形状扁平,但它的琴面在中心处有一个向上凸起的圆弧,覆盖在琴底的平面之上。
在琴颈的底面用篆书刻着它的名字——“石泉”,龙池两侧刻有琴铭,都是隶书:“匪木之为象,石之响;匪丝之为声,泉之清;匪泉之为激,石之力。石耶!泉耶!琴耶!”琴铭不但代表了古琴的风格特点和精神内核,更是将书法、诗文与古琴艺术融为一体的典型代表。宋代偏爱行草,而用隶书写就琴铭,意味着斫琴者有尚古之风,而其琴音也必有悠远的古意。然而不同于汉隶、唐隶水波似的圆融丰润,“石泉”七弦琴上的隶书更像浪花,弱化了蚕头处的圆润感,而在燕尾的处理上比较轻盈,显出清雅逸趣的味道来。
琴铭的内容,短短30字,便为人们勾勒出一幅石上听泉图:当此琴奏响之时,人们将忘却这乐音来源于一张木质丝弦的古琴,仿佛置身于山间石上,聆听着清泉于高处倾泻而下,在与石相触碰的一刻迸发出的玉碎般的激越声音。
“石耶!泉耶!琴耶!”在琴铭结尾,斫琴者如感叹、如咏唱,仿佛已经模糊了石、泉、琴三者各自的边界,融合成为统一的精神。我想,以易斫之木奏以金石之声,以细软之丝奏以泉水之清,以泉水激石之力奏以慷慨激昂之音,这不正是古代士大夫精神的缩影吗?
宣和殿中藏名琴
宋徽宗作为一位“艺术家皇帝”,对古琴也是推崇备至的。宋徽宗在宣和殿内设立了“万琴堂”,专门收集各类名琴。南宋词人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说:“琴则‘春雷’为第一,向为宣和殿万琴堂称最。”可见这宣和殿中的万琴堂所藏之琴,确实俱为上品。
万琴堂中的琴,有官方所制的官琴,也有民间所制的野斫。流传至今的北宋名琴大多为民间制作的野斫,官琴数量不多。说到现存著名的北宋官琴,又进过宣和殿万琴堂的,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金钟”琴一定榜上有名。
“金钟”琴是一张仲尼式的古琴。仲尼式,又被称为孔子式或夫子式,顾名思义,仲尼式古琴相传是孔子所创制的。宋代文人治国,推崇儒学、敬重孔子,再加上孔子对琴的教化作用推崇备至,孔子自己也曾学琴唱诗、自编琴曲,因此,仲尼式古琴在宋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出自官方琴局工匠之手的“金钟”琴,可以算得上是“赶时髦”的产物。古琴如同美人,结构上亦对应美人的身体,有头、颈、肩、腰、尾、足。“金钟”琴琴首为方形,琴颈和琴肩处各有一个向内收的弧形;到了琴腰则又内收成一方条,整体造型简洁流畅,颇有儒学的含蓄内敛之风。想来,若“金钟”琴真的化生为美人,也必定是位削肩细腰、落落大方的窈窕淑女。
琴名“金钟”,以小篆体刻于龙池上方。钟在古代是一种打击乐,多为礼器,一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在朝聘、祭祀、宴请等重要场合使用。最早的钟是铜制,被人们称为“黄钟”。宋代关于音乐的著作《大晟乐书》中记载:“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只有当黄钟演奏完毕,其他乐器才能够继续演奏,可见黄钟地位之高。而金钟则是指黄金制成的钟,相较于铜制黄钟要更高一层,更凸显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
从另一方面讲,黄钟演奏的声音和其他诸多乐器相比,声调最为宏大,音色最为庄严,“黄钟”也由此成为传统音乐的五音十二律中的第一律,代表着庄严、正大、高妙与和谐。这正与“立以中,明以正,失于过与不及”的琴德有所呼应。魏晋嵇康的《琴赋》中写道“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当黄钟渐渐消失于历史,只有古琴的琴音还能保持雅正之德。琴名“金钟”,除了彰显皇家贵气之外,更有修身养性、宣导情志之意。龙池左右所刻隶书琴铭“闲邪纳正,导德宣情”,也正是“金钟”之名的最好佐证。
之所以判断它是万琴堂中的一员,则是因为龙池下方所刻的草书“宣和殿”。而下面九叠文“御书之宝”的大印,说明“宣和殿”三字可能是宋徽宗亲笔书写。
时隔千年。“金钟”琴的琴面已经布满牛毛断的纹路,护轸、琴轸与琴弦不知去向;蚌徽仅存四枚;通体漆黑的琴面也因磨损多处失漆;琴背铭刻原有的贴金也散落将尽。
古琴上的“断纹”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白在听了蜀僧浚为他弹奏的琴曲后,挥笔写下了这首诗,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极为生动的山中听琴图。这位浪漫诗人一定想不到,到了宋代,诗中“万壑松”的意象“火”了,成为当时备受欢迎的琴名之一。
单从如今传世的古琴来看,为数不多的宋代古琴,其中就有三张以“万壑松”的意象来命名——一张于1983年入藏于故宫博物院,斫于北宋年间,琴名“万壑松”;另一张名“万壑松风”,斫于南宋时期,现藏于湖南博物院;还有一张是私人珍藏,琴名“万壑松声”,是南宋时期的官琴。
和许多名琴一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万壑松”琴也是以桐木作为琴面,梓木作为琴底的,但却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古琴的琴面大多只有一种断纹,像北宋“石泉”琴的蛇腹断、北宋“金钟”琴的牛毛断,都是单一形态。而这张“万壑松”琴,除了有蛇腹断、冰纹断、牛毛断几种常见的断纹之外,还有罕见的梅花断断纹。在古琴界,以梅花断最为名贵。这种断纹非千年不能有,其纹路圆而攒簇,正如片片梅花花瓣。因为形成不易,通体皆是梅花断的古琴几乎没有,因此只要琴身的某一部位有,便可认定为梅花断琴。“万壑松”琴的梅花断纹在琴头上。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梅花状的形状和纹路清晰能辨,确是一张历史悠久的好琴。
实际上,琴身漆面出现断纹,本来应当是一种缺陷。然而,琴面的断纹意味着此琴年代久远,便受到了好古的琴家和收藏家的青睐。“好古”这一风气,最早来自先师孔子——他曾直接对学生谈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意思是自己并非生来就很有学识,而是因为崇尚古人之风,不断学习的结果。宋代文人治国,加之根植于儒家思想的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好古”更成了文人士大夫“赶时髦”的追求。这一风气也同样带入了古琴界,文人们钟爱弹琴,更钟爱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琴。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爱琴,他谈到自己的藏琴时说:“琴面皆有横纹如蛇腹,世之识琴者以此为古琴,盖其漆过百年始有断纹,用以为验尔。”可见,古琴的断纹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成为鉴定古琴年代的依据之一了。
(责编:马南迪)
“金钟”琴


“金钟”琴,通长115.7厘米,隐间107.9厘米,额宽16.4厘米,肩宽19.6厘米,尾宽13.6厘米,厚4.8厘米。
“石泉‘七弦琴

“石泉”七弦琴通长121.00厘米,宽19.20厘米,厚4厘米。此图为“石泉”七弦琴琴底(局部)。
“万壑松”琴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万壑松”琴,通长128.6厘米,隐间117.1厘米,额宽19厘米,肩宽20.4厘米,尾宽14.9厘米,厚5.9厘米。琴名以楷体刻在龙池上方,龙池左右则以行草刻了琴铭:“九德兼全胜磬钟,古香古色更雍容。世间尽有同名器,认尔当年万壑松。”